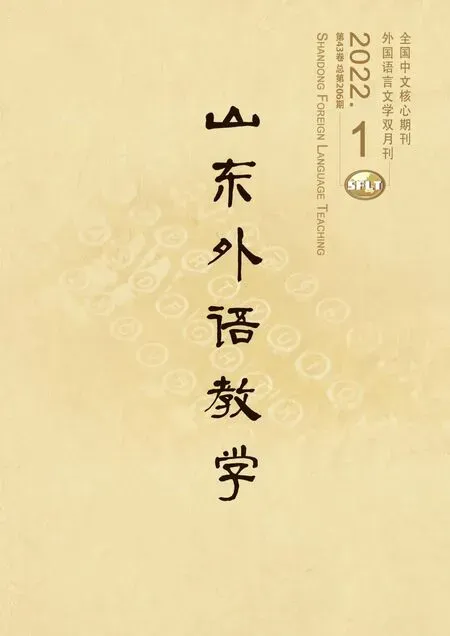泛美政治經濟視域下美國奇卡諾移民小說中的成長敘事
李保杰
(山東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1.引言
1630年約翰·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 1588-1649)率領船隊到達北美洲殖民地之際發布了《基督教慈悲之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表達了“天定命論”(manifest destiny)的理念,明確提出了建立“山巔之城”(City upon the Hill)的理想。幾百年來,這個理想一直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2019年美國移民的總數量為4493.3萬,其中移民輸出最多的地區是拉丁美洲,共輸出移民2258.8萬,墨西哥移民占比24.3%,是其中的主力。根據皮尤中心(PEW)的調查數據,美國拉美裔群體的人口總數不斷增長,在2019年達到了6060萬,其中61.5%的為墨西哥裔(Noe-Bustamante, et al., 2021)。
美國墨西哥裔文學對這些問題早有關注。2014年莫拉利斯(Alejandro Morales, 1944-)在小說《天使之河》(RiverofAngels)的前言中將移民的遷移視為人類生物本能的表現:“軍隊、隔離墻、高科技手段,都無法阻止人們的遷移——這并不難理解,因為遷移是人類的本性,是無法阻擋的,所有人為的手段都難以阻擋”(2014: ix)。以書寫非法移民主題而著稱的格蘭德持有類似觀點,但是她強調了經濟要素在移民問題(特別是非法移民問題)中的核心作用,“只要還有1小時掙5美元和一天掙5美元的差別,人們就會源源不斷地來到這里”(Grande, 2006),“富足自由”的美國與飽受貧困暴力困擾的拉丁美洲之間的強烈反差正是移民問題的關鍵所在。如果在泛美視域下綜合考察奇卡諾文學(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墨西哥裔文學)①中的移民問題,格蘭德所說的經濟要素以及莫拉利斯強調的人性要素,是否與美國國民精神核心的天定命論存在關聯?奇卡諾文學中的移民書寫局具有何種意義?這種文學范式對美國文學具有何種價值?
2.移民驅動:泛美版圖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經濟與政治力量的對比
奇卡諾小說中的移民主題范式源于墨西哥人移民美國的歷史。19世紀末開始,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進而發展為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其天定命論及其相關的財富神話深深吸引著拉丁美洲各國的人民,其中墨西哥與美國的淵源更甚。美國西南部諸州曾經是墨西哥領土,被歸化的墨西哥人保留著與母國的文化血脈,逃避動蕩、到美國謀生成為眾多墨西哥人的選擇,在墨西哥革命時期(1910—1919)、20世紀80年代墨西哥經濟危機期間尤其如此。
移民對美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是20世紀中期以來美國文學書寫的一個重點,更是奇卡諾文學的代表性范式。維拉里爾(Jose Antonio Villarreal, 1924-)的《美國化的墨西哥人》(Pocho, 1959)、瓦斯科斯(Richard Vasquez, 1928-1990)的《奇卡諾人》(Chicano, 1970)、伊斯拉斯(Arturo Islas, 1938-1991)的《雨神:沙漠故事》(TheRainGod:ADesertTale, 1984)、莫拉利斯(Alejandro Morales, 1943-)的《制磚人》(TheBrickPeople, 1998)都是奇卡諾文學中現實主義移民主題的作品,它們以墨西哥革命時期的墨西哥和美國為背景,其人物既有遭受了理想挫折的墨西哥革命者,也有飽受戰亂生活困苦的普通墨西哥人。這類以移民人物和移民經歷為主題的小說可稱作移民小說。奇卡諾移民小說多以墨西哥移民從南方往北方遷移、并最終在美國落地生根的經歷為脈絡,以人們的線性移動和地理空間的變化為線索,講述移民及后代的身份變化和文化適應,書寫代際間的血脈延續和文化傳承。
這些移民小說凸顯政治動蕩和經濟困頓在移民過程中的核心作用。在被稱為“第一部奇卡諾小說”的《美國化的墨西哥人》中,胡安·盧比奧代表了墨西哥革命時期遭受挫折的革命者。在1923年革命領袖維亞被暗殺之后,盧比奧改良社會的夢想破滅,加之生活困頓,他被迫攜家眷遷移到加利福尼亞。《制磚人》講述19世紀末至20世紀50年代加州西蒙斯3號磚廠的歷史,廠址的變遷、磚廠的運作模式、墨西哥工人的招募等環節,都透視出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政治經濟力量對比:加利福尼亞被割讓給美國后,尤拉莉亞夫人的莊園被侵占,兒子被害,她神秘的死亡和詛咒成為西蒙斯家族未能逃脫的魔咒;磚廠采用西班牙莊園模式運作,使用來自墨西哥的廉價勞動力,然而這些為加利福尼亞創造財富的人卻遭到小鎮居民的抵制和歧視。究其原因,美國和墨西哥的政治經濟力量懸殊正是移民的驅動力。
20世紀80年代以后奇卡諾移民文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移民社區和移民人物在族裔社區內的經歷成為一個代表范式。希斯內羅絲(Sandra Cisneros, 1954-)的《芒果街上的小屋》(TheHouseonMangoStreet, 1983)和《喊女溪》(WomanHolleringCreekandOtherStories, 1991)、維拉蒙特斯(Helena Maria Viramontes, 1954-)的《飛蛾和其他故事》(TheMothandOtherStories, 1985)和《在耶穌腳下》(UndertheFeetofJesus, 1995)、德梅特里亞·瑪提內斯(Demetria Martínez, 1960-)的《母語》(MotherTongue, 1990)等均聚焦于移民社區,移民經歷與美國夢之間的協商是重點,女性成長主題得到充分觀照。《芒果街上的小屋》以“房子”這一物質意象作為主線書寫移民社區內移民的美國夢,講述美國財富神話下的女性成長。維拉蒙特斯塑造的移民人物形象有《在耶穌腳下》中的弗洛雷斯,《加里布小吃店》(“The Cariboo Café”)中的姐弟二人和無名母親。這些人物為了謀得更好的生活而移民美國,他們的移民經歷中投射出父權制下的經濟架構。例如,短篇小說“喊女溪”的主人公是墨西哥女孩克萊奧菲拉絲,在生活的重壓下她向往著電視劇里中產階級女性的優雅生活,當一位求婚者許諾帶她去美國時,她仿佛看到了擺脫貧窮的希望。在美國沒有經濟獨立的克萊奧菲拉絲不得不忍受丈夫的暴力和背叛,最終她決定逃回墨西哥。誠然,主人公的移民經歷之痛令她覺醒,美國夢的破滅讓她意識到以尊嚴為代價的衣食無憂令人窒息;然而,值得商榷的是,這種人物塑造是不是有理想主義之嫌?因為女主人公回到墨西哥后的首要問題還是生計,而這正是她曾努力逃離的生活。
21世紀的移民小說不像先前那樣書寫家族歷史或者代際傳承,而是集中于移民過程,重點書寫人物穿越邊界的經歷,映射地理空間的政治表征。代表作品有維克多·里奧斯(Victor Rios)的《街頭生活:貧困、幫派和博士》(StreetLife:Poverty,Gangs,andAPh.D., 2001),瑞娜·格蘭德的《越過萬水千山》(AcrossaHundredMountains, 2006)和《我們之間的距離》(TheDistanceBetweenUs, 2012),安娜·卡斯蒂略(Ana Castillo, 1953-)的《守護者》(TheGuardians, 2007),威爾·郝博思(Will Hobbs, 1947-)②的《穿越鐵絲網》(CrossingtheWire, 2006)等。這些作品多采用主要人物內聚焦的敘事模式,從局內人的角度解釋移民背井離鄉的社會歷史;或者運用生命書寫范式,基于文學的真實講述移民經歷。作品人物都是非法移民,有的曾經是街頭幫派成員,最終通過教育成長為知識分子;有的曾經是拉丁美洲的留守兒童,移民之后依舊掙扎在社會的底層。
小說情節多涉及墨西哥國內的經濟衰退、經濟結構畸形和犯罪猖獗,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墨西哥社會的再現。《我們之間的距離》中父親為了掙錢蓋房而遠走美國,“他進退兩難,要么兩手空空地回墨西哥,那以后可就抬不起頭來了;要么待在那里,拼命掙錢,寄錢給媽媽。他選擇了后者,希望他們兩個能夠賺夠錢蓋房子,那可是他們的夢想啊。到那個時候,他就能夠昂首挺胸地回到家鄉,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Grande, 2013: 7)。在《穿越鐵絲網》中父親在美國打工時死于意外,年僅11歲的維克多就開始擔當起養家糊口的重任,他每天辛勤勞作但依舊連年虧損,因為玉米收購價被美國大財團故意壓低,普通農民根本無力競爭,維克多無奈之下才考慮偷渡美國以幫助母親維持生計。尤利亞(Luis Alberto Urrea, 1955-)的《去往美麗的北方》(IntotheBeautifulNorth, 2009)聚焦于危險的穿越國界,反映墨西哥的貧窮混亂與美國的富足繁榮之間的巨大反差。這些小說都涉及“危險的穿越”這一主題,如警察對移民的無情毆打和肆意侮辱,公共汽車司機和匪徒暗中勾結偷竊移民的財物,黑幫在野外進行伏擊、搶劫,均指向了經濟因素這個驅動力。維拉蒙特斯的中篇小說“加里布小吃店”以兩條故事線索揭示了經濟驅動背后政治與經濟的勾連:在內戰中失去幼子而精神錯亂的母親,將女孩的弟弟錯認作兒子,被警察當作誘拐兒童的嫌疑人而擊斃,移民的生命在法治國家的國家機器面前不堪一擊,迷路的非法移民姐弟因此被警察解救下來。然而,這個結局與故事開頭姐弟二人時刻躲避警察的情節存在矛盾,問題也接踵而來:被國家機器解救的非法移民將會面臨什么樣的命運?小說凸顯移民經歷中的情感取向和移民訴求,對移民主題中身份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3.成長范式:邊界、夢想與合法性協商
2019年美國非法移民總數為1030萬,占移民總數的23%,占美國總人口的3%(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2021)。移民問題特別是非法移民問題的背后,有著復雜的甚至是不可言說的社會因素。文學中的移民主題即充分運用文學想象,呈現那些在現實中被強權壓制的話題,如跨越邊界背后的故事。
文學文本中顯性移民主題的背后,投射出深層次的政治權力關系。《母語》就是其中的一例。小說取材于20世紀80年代的薩爾瓦多內戰,基于作者馬提內斯幫助薩爾瓦多難民而遭到起訴的經歷。19歲的墨西哥裔女孩瑪麗亞在接待薩爾瓦多的政治流亡者羅梅羅時愛上了這個神秘的男子,小說通過他們的苦澀愛情故事呈現被戰爭和暴力所撕裂的個人生活,映射拉丁美洲的沖突和暴力。瑪麗亞追求愛情,但是羅梅羅卻認為沒有自由保障的愛情是虛幻的,因為在薩爾瓦多的國家命運未卜之時,他不能為了愛情而停留下來,所以最終回到薩爾瓦多繼續反獨裁斗爭。小說強調了文學虛構背后的“真實”:“人物是虛構的,但背景是真實的。在12年內戰期間超過75,000薩爾瓦多人喪命,大多數人死于政府軍之手。內戰正式結束于1991年,美國提供了6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一直是內戰的支持者。美國國務院文獻顯示,美國政府高層非常清楚薩爾瓦多軍事政權針對平民的暴力,包括1980年奧斯卡·羅梅羅主教被暗殺一事,但當權者對此視而不見”(Martinez, 1994:扉頁)。小說通過批評美國插手薩爾瓦多內戰,質疑美國國家機器將避難者和移民非法化的做法。
從美國國家機器的角度看,這種立場也許有偏頗之處。然而,美國在歷史上對移民合法性的界定并沒有一貫的標準,隔離墻和檢查站與邊界本身也不等同。1924年之前美墨邊境上未設立檢查站,拉美移民可以自由跨越邊界或返回家鄉,跨界人數則取決于美國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即使在邊界跨越的合法性以國家意志的形式規定下來之后,移民身份合法性的判定依舊基于美國利益,甚至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美國合法地接受了相當數量的非法移民,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60年至1962年的彼得·潘計劃(Operation Peter Pan)。經過中央情報局和天主教會的策劃,美國政府專門給予經費支持該計劃,各類團體和個人參與其中:“貝克發給沃爾什學生名單,沃爾什將名單轉給古巴流亡者諾瑪·倫伯格,她從戴德縣科勒爾·蓋布爾斯高中的艾格尼絲·艾爾沃德那里拿到相應數量的I-20簽證表。沃爾什把這些簽證表發給哈瓦那的貝克,貝克再發給學生的家長”(Triay, 1999:18)。通過機構性的系列運作,該計劃將14000多名古巴兒童和青少年運送到美國,以期用美式民主對他們進行教化,最終顛覆古巴共產主義政權。《母語》展現的正是暴力衍生的意識形態背景以及權力關系,因此質疑美國對移民合法性的界定。因為美國政府的區別對待,真正面臨生命威脅的薩爾瓦多流亡者難以得到政治庇護而被判定為非法移民,瑪麗亞參與的救助同樣也是非法的,避難所運動(Sanctuary Movement)被迫將羅梅羅等人送往加拿大。小說通過呈現這些權力關系,質疑國家機器對移民合法性的界定。的確,相比于美國政府同一時期對于古巴移民的做法,這種質疑是值得探討的。
除了表達移民身份被國家機器所操控以外,移民小說還呈現了另外一種不確定性,那就是合法移民的身份非法化。合法移民會遭遇歧視、迫害等生命政治鉗制,受到各種有形與無形邊界的限制,如社區界限、階層分化、薪酬差異,令他們和其他群體特別是主流文化群體區分開來,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可謂“身份的非法化”。《制磚人》中磚廠需要大批的廉價高效勞動力,墨西哥工人是資方最理想的選擇。在尚無國界警察和墨西哥移民法的時代,墨西哥工人都屬于合法移民,他們的努力為蒙特貝洛注入了經濟活力。然而,市民卻對他們充滿敵意,甚至給市政廳寫抗議信,反對“討厭的墨西哥人”到商店購買生活必需品。因此,墨西哥人被孤立在西蒙斯小鎮這個移民社區,“墨西哥人與蒙特貝洛居民之間保持著安全的距離,因為建設之初就沒打算讓其成為任何城市的一部分”(Morales, 1988:64-65)。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二者的矛盾更是被全面激發:美國民眾將移民視為經濟衰退的替罪羊,視他們為“非法進入美國的外國人,沒有權力享受美國公民的公共設施”(Morales, 1988:194)。因此西蒙斯社區失火時,消防員只負責阻止大火向白人居住區蔓延,任由奧克塔維奧家的房子毀于一旦。墨西哥移民的家園尚且不保,遑論夢想的實現;他們不僅被磚廠圍墻圈起,還被無形的圍墻所困,成為“合法的非法移民”。
無論移民是合法進入還是非法跨越,跨越邊界與身份的合法性之間無法關聯。大多數小說中的移民并沒有衣錦還鄉,因為他們大多缺乏專業技能,只能依靠體力勞動勉強維持生計,難以得到美國國家話語體系的接納。同時,合法移民在美國境內的遷移貌似自由,實際上局限于種族和階級的維度,他們背負著流動的邊界,其身份的合法性因而令人質疑。所以,移民在獲得工作機會、改善經濟條件的同時,同樣也受制于政治關系,經濟表征與“邊界”的政治延伸實現互文,令邊界與身份的合法性界定趨于復雜,無論是非法移民還是二代移民,都難以逃脫其束縛。
4.文學的力量:書寫族裔營地與“美國噩夢”協商下的成長
移民小說話語的意義在于揭示合法性協商中遭遇挫折的夢想,而人物的成長正彰顯于對夢想的再認識,話語建構的意義就在于個體經歷文本化中的價值表達。奇卡諾移民小說典型地展現了移民經歷和美國夢之間的協商。這類小說的主人公在試圖跨越國界等邊界中經歷迷茫和迷途,最終依靠文學的教化力量而獲得成長。
這些小說多帶有生命書寫的特征,體裁有自傳、回憶錄和自傳體小說,多從第一人稱敘事講述人物的成長,追溯他們從家庭走向社會的迷茫、迷途和返航,代表性作品有路易斯·羅德里格斯(Luis Rodriguez,1954-)的《永遠奔跑:在洛杉磯幫派中的日子》(AlwaysRunning:LaVidaLoca,GangDaysinL.A., 1993)、《心連心,手拉手:在暴力時代創造家園》(HeartsandHands:CreatingCommunityinViolentTimes, 2001)和《它呼喚你回來:跨域愛、毒癮、革命和治愈的艱苦旅程》(ItCallsYouBack:AnOdysseyThroughLove,Addiction,Revolutions,andHealing, 2011),圣地亞哥·巴卡(Jimmy Santiago Baca, 1952-)的《黑暗中摸索:貧民窟詩人的回顧》(WorkingintheDark:ReflectionsofaPoetoftheBarrio, 1992)和《立錐之地》(APlacetoStand, 2001)、里奧斯的《街頭生活:貧困、幫派和博士》等。這些小說的側重各不相同,羅德里格斯講述幫派犯罪和國家機器對少數族裔生命的鉗制;里奧斯的回憶錄重在講述移民少年的成長與蛻變,但其中非法移民的危險越界和艱難生存令人印象深刻;巴卡強調了貧窮和階級,以及其由此催生的叢林法則對青少年自我認知的局限。生命書寫的敘事策略增加了敘述的可信度,但是記憶和回憶具有選擇性和不準確性,個人敘述帶有主觀性,因此這種“真實性”也只是文學上的真實,本文將其劃歸到移民小說的范疇。
在這類關于墨西哥裔少年迷途的敘述中,移民少年成長中的貧窮困頓和階級閾限是導致他們無所適從的直接原因。作品大都涉及少數族裔青少年在學校和社會中承受的種族歧視和校園暴力,他們因而以暴制暴,采取了簡單化的方式來進行自我保護。他們在幫派中尋找認同,將暴力誤認為男性氣概,通過群毆、搶劫、火并、吸毒販毒、強奸等暴力行為定義自我的價值。里奧斯在回憶錄《街頭生活:貧困、黑幫和博士》中講述自己從非法移民到幫派成員再到伯克利社會學博士的經歷,坦言貧窮、歧視等社會問題成為非法移民少年成長中的巨大障礙,所以在標題中即突出了“貧困”這一個要素。他認為,移民社區中貧窮混亂的環境對青少年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我們的住處被稱為‘貧民窟公寓’,學校里所有的‘壞孩子’都住在這里,這里非常糟糕。這個地方以暴力和毒品而臭名昭著,這和露絲女士居住的高檔中產階級社區有著天壤之別”(Rios, 2001:79)。移民少年難以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在職業生涯中處于劣勢,經濟驅動下的階級閾限令他們難以突破現實的種種障礙。
《永遠奔跑》中,羅德里格斯回憶了自己加入街頭幫派的過程,講述了幫派之間的爭斗和自相殘殺,探討幫派犯罪之社會根源。羅德里格斯兩歲時隨家人移民到了洛杉磯,在東洛杉磯的少數族裔社區長大。他們一家是合法移民,為了謀得更好的生活而來到美國,但是遷移使他們的階級所屬發生了根本變化:在墨西哥擔任中學校長的父親如今只能從事體力勞動,常常忙于生計而無暇顧及孩子們的教育。羅德里格斯在家庭中被忽略,在學校里因為文化差異而受到歧視,所以他11歲時就加入街頭幫派,到17、18歲時他已經成為洛杉磯勢力較大幫派的頭領人物之一,中間經歷無數次幫派間爭奪地盤和勢力范圍的暴力行動,他的教育也因為數次被捕而中斷。書名中的“奔跑”象征著移民少年努力擺脫各種枷鎖的努力:“我們不斷被捕獵,獵人群體很快就匯集了一大幫人:警察、幫派分子、癮君子、卡威大街上勒索我們的那幫家伙,他們很快就沆瀣一氣。有時候老師也加入進來,仿佛我們生來就帶著無可饒恕的缺陷。所以我們始終生活在恐懼中,不得不一直奔跑”(Rodriguez, 1993:28)。羅德里格斯認為,警察對墨西哥人社區的毒品泛濫和幫派斗爭采取了放縱的態度,只要不危及白人社區就任由他們自生自滅;族裔少年面對來自家庭、學校、社會的各種壓制和歧視時,幫派的誘惑力無疑是巨大的。他指出了移民少年和族裔少年幫派犯罪背后的心理機制,“像帕德羅這樣的年輕人,他們加入幫派不是為了實施犯罪,也不是要去殺人、坐牢。對他們而言,幫派接受他們,給予他們所需的心理認同,因為他們需要這種認同來掌控自己的生活;他們在幫派中獲得的力量,是其他組織,包括學校和家庭,都無法給予的”(Rodriguez, 2003:25),幫派成員間的所謂兄弟情義使他們彼此認同,幫助他們躲避來自學校和社會的挫折和失落。當然,他也承認,在沒有正確引導的情況下,幫派活動很容易導致災難性的后果;他本人就見證了身邊朋友一個個死于非命,進而萌發對這些社會痼疾的追問。
在羅德里格斯、里奧斯和巴卡等作家看來,能夠讓移民少年從迷途返航的重要一環就是教育,其中文學的教化不可忽略。巴卡21歲時因為販毒、持械斗毆而被逮捕,在獄中服刑的6年半時間里開始自學文化知識,并且對詩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曾經依靠寫詩跟獄友換取煙卷,通過寫作讓自己頭腦清醒,不至于隨波逐流而徹底沉淪。由此看出,在精神貧瘠的監獄中,相比于麻痹神經的香煙,文學更具有陶冶情操、撫慰心靈的作用。同樣,羅德里格斯在20世紀60年代奇卡諾運動時期參加社區和學校的族裔文化項目,如墻報、戲劇表演和阿茲特克舞蹈等,其他幫派成員也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在游行、請愿等政治運動中,幫派之間開始停火,幫派矛盾得到了暫時的緩解。基于這些切身感受,羅德里格斯堅信社區的關愛和文化教育能夠挽救迷途的青年。他致力于將其用于犯罪青少年的救助,充分運用文學書寫的教化力量,發起公益活動,推進各類改造項目。第二部回憶錄重點講述他和同仁們為建立和諧社區所做出的努力,通過典型案例分析幫派相關的少年犯罪問題,在族裔政治視域下追溯街頭幫派的歷史根源。第三部作品聚焦下層族裔青少年的“生存怪圈”:幫派、涉毒、暴力犯罪、被監禁,如此循環,很多人在這個惡性循環的某個環節早早喪命。這部作品的重點在于“回歸”:標題來自羅德里格斯邁出監獄大門時警長助理對他的嘲諷“你還會回來的”(Rodriguez, 2011:1),隱含了監獄和幫派對這些無所適從青年的誘惑;而他的文學創作、文學讀書會,就是在艱難對抗自己“回到過去的老路上”的沖動,對抗國家機器暴力的挑釁。
在這些文學作品中,幫派、監獄、貧民窟代表了族裔青少年的閾限空間。移民被局限在這些生命政治治理下的族裔營地之間,他們的美國夢理想淪為了被暴力所標記的美國噩夢。幸運的是,其中的一些人發現了文學教化的力量,用文字建構起了文化認同和自我認知;這種鳳凰涅槃式的成長能夠越過監獄的高墻、超越種族和階級的界限,直擊被不同邊界所隔離的靈魂。
5.結語
縱觀美國奇卡諾文學移民成長小說書寫中的各個階段,可以看出經濟因素發揮的核心作用,即美洲地緣政治視域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經濟懸殊。移民在遷移中或者移民后代在成長中,均受到有形邊界和無形邊界的限制,階級、種族的政治表征與邊界隱喻達成互文,凸顯出移民主題與政治經濟的多重關聯。文學正是通過書寫不同類型的身份非法化過程,呈現被經濟和族裔政治所裹挾的成長。這些移民小說同時講述主人公如何謀求族裔文化認同、接納自我,從而突破這些閾限,獲得精神和心靈的成長。從美國文學整體來看,奇卡諾移民小說盡管涉及挫敗的夢想,但也講述了移民夢想建構和自我蛻變,迎合了美國主流文學的經典范式,在族裔性和美國性之間取得了平衡。
注釋:
① 關于“奇卡諾文學”概念,參閱李保杰:《美國西語裔文學史》,山東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5頁。
② 郝博思并無墨西哥裔背景,但小說涉及奇卡諾主題,學界對此類作品的界定有爭議,本研究采用較為寬泛的概念,視其為奇卡諾文學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