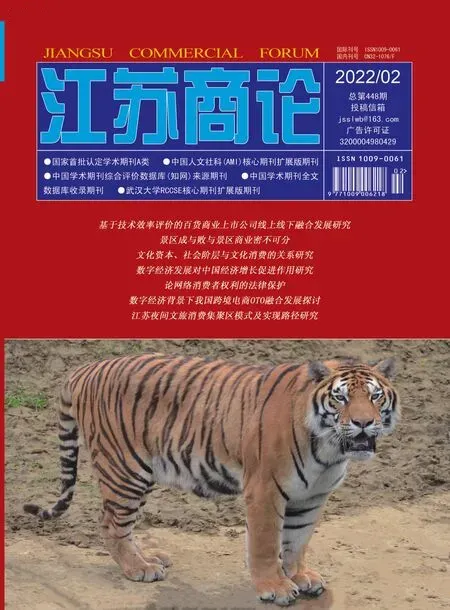數字媒體時代的美術館運營探索
丁 燁,施怡晨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 會展與旅游學院,上海 201620)
一、引言
美術館作為藝術博物館承載著收藏保護、學術研究、陳列展示、公共教育等多項功能,是滿足公眾精神需求的重要藝術場所。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大了對公共藝術機構的投入,我國的美術館事業發展迅猛,尤其是許多經濟發達地區,美術館數量快速增長,越來越多的人走進美術館接受藝術文化的熏陶。以上海為例,截至2020年10月,上海市美術館數量89座,十年間美術館數量翻了4倍之多1數據來源: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2020年度上海市美術館運營情況報告》。。2020年清明、端午等國定假日,上海各大美術館共計舉辦展覽265項、公教活動超過100項,接待觀眾28.8萬人次。后疫情時代,美術館參觀更趨火爆。參觀美術館,已成為市民休閑游憩的一種重要方式,成為公眾文化生活中重要組成部分。2020年上海市各美術館共計舉辦了600場展覽,吸引眾多觀眾。傳統藏品陳列方式已較難滿足當下觀眾的需求:一方面觀眾對展陳方式的數字化、互動要求更高;另一方面,一些IP沉浸式藝術展發展迅速,例如teamLab、“棉花糖與白日夢”等網紅展覽迅速崛起,廣受歡迎。
數字媒體時代的到來,對美術館運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向公眾普及藝術教育的同時,更好地提升觀展人的體驗,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社交平臺的運用,為美術館的運營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渠道——用數字媒體連接藝術與大眾。數字媒體不僅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而且在美術館場館運營中的使用,極大地豐富和增強了觀眾的體驗。本文探索如何在美術館運營過程中,通過數字媒體增強觀眾的參與感,提升美術館的重游率。
二、美術館與社會公眾
隨著人們藝術審美觀的不斷提高以及對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美術館的功能不再局限傳統的展示陳列,美術館的運營方更加關注公眾教育。政府相關部門也逐漸意識到,通過美術館這樣的藝術場域,是提升社會大眾藝術審美,普及美育教育,提高整個社會綜合素養文明程度的最佳場所之一。一個美術館的知名度和活躍度,不僅取決于新游客的到來,重游率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標之一。當下我國美術館除了基本的常設展覽外,臨時展覽占據很大一部分。美術館的重游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臨時展覽來帶動。展覽活動是知識生產重要的組成部分,作為知識生產的受眾,社會公眾對于展覽的接受度決定了美術館展覽的成功與否。而數字媒體,在美術館的運營過程中,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數字媒體在美術館中的運用
數字媒體的高速發展,在文娛、交互、傳播、服務等多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據《2020全球數字報告(Digital 2020)》顯示,目前全球有超過45億人使用互聯網,而社交媒體用戶已突破38億大關,中國的社交媒體用戶更是超過10.4億。數字技術、社交平臺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對于美術館這類需要借助文字、圖像、音像等媒介來向受眾傳播藝術理念的藝術場所,數字媒體的運用極大地豐富了美術館的宣傳和推廣方式,為藝術的呈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拉近了美術館、策展方與觀眾之間的距離。
數字媒體時代,美術館向觀眾傳播藝術文化的途徑越來越多元化。首先是展覽的呈現方式,數字媒體技術的使用讓藝術變得可觸摸,從視覺藝術向感官藝術轉變。柴秋霞(2012)提出,虛擬現實技術為數字媒體沉浸式交互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越來越多的美術館通過技術的使用,讓藝術變得看得到、聽得見、摸得著,讓觀眾可以身臨其境,獲得沉浸式體驗。其次,藏品的數字化,打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制,帶來了觀展方式的改變——線上觀展成為新的潮流,更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好處是,觀眾可以隨時隨地的利用碎片化時間觀展。參觀藝術展覽不僅是一種充滿儀式感的活動,也逐漸成為一種日常的生活方式。
借助移動媒體等平臺,通過圖片、影像、音頻的傳播讓藝術能夠被廣泛地傳播與分享。所謂公眾移動媒體平臺,當下使用最多的就是微博和微信公眾號等社交平臺,在這些社交平臺上,大部分美術館都建立了自己的公眾號。另外一種傳播方式就是觀眾也可以成為美術館宣傳推廣的一分子,在線上社交平臺的每一次觀展分享,都是一次信息的傳遞。觀眾與館方的互動、觀眾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都能達到很好的宣傳效果,通過這樣的方式大大提高了觀眾的參與感和體驗。
(二)用參與連接美術館與觀眾
目前大多數美術館展覽所傳達的藝術理念與普通觀眾的接受程度之間還存在一定差距,這是由于社會公眾的教育背景不同,對藝術的接受程度存在差異。傳統的藝術策展方更趨向于“學院派”,很多美術展覽曲高和寡,與觀眾之間的藝術審美存在一定差距,對普通觀眾吸引力不足。在第五屆亞洲美術館館長論壇上,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王璜生提出,策展的學術性問題是美術館事業發展的一大阻力。深圳美術館館長宋玉明認為,美術館、博物館的策展人多是館內的專業研究人員,研究性學者策展的重點往往與普通大眾期望看到的內容不盡相同。
相對于傳統美術館藝術展的敘事呈現方式,數字媒體對于信息的傳播相對更直觀,互動性更強:大量的圖片、視頻、聲音、動畫將藝術全方位地呈現。觀眾不僅可以觀看,還能通過聽覺、觸摸等來進行沉浸式的體驗,更能下載進行長期觀摩。要連接藝術和大眾,就要讓大眾參與,這也是目前沉浸式展覽快速發展,廣受觀眾歡迎的原因所在。線下活動與各式場景中的數字媒體技術運用已經較為普及,但對線上平臺的運用還遠遠不足。
確立美術館的定位與發展模式,需要美術館與社會公眾共同努力,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要想更好地吸引觀眾,就要站在社會公眾的角度,以社會公眾為核心。無論是美術館呈現的內容還是表現形式都要考慮受眾的接受程度,增加良性互動,為觀眾增添參與感。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進行:
1.線下活動與場景的多樣化。2020年上海市各大美術館共舉辦2700余次活動,吸引了來自線上線下的觀眾109萬2數據來源:We Are Social&Hootsuite,《Digital 2020》,https://wearesocial.cn/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common/digital2020/digital-2020-global.pdf[DB/OL].,為美術館帶來了巨大的活力。2020年疫情期間,為了響應疫情防控需求,公共場所紛紛閉館,但各大美術館借助線上平臺,閉館不閉展,將藝術搬到云上。結合抗擊疫情主題,中華藝術宮舉行了《“召喚”——上海市抗擊新冠病毒美術、攝影主題展》,接待了5萬余人,線上訪問量超10萬人次,在疫情期間為美術館吸引了大量客流。
與此同時,數字媒體技術在藝術場景的打造上功不可沒。近些年,沉浸式展覽成為參展熱潮,沉浸式展覽正是數字媒體技術與藝術展覽的很好結合。借助數字媒體技術打造的互動體驗藝術裝置將藝術家、藝術作品與觀眾緊密連接,讓觀眾身臨其境地融入藝術場景之中,既是觀眾,也是場景的一部分。以上海teamLab無界美術館為例,大量燈光、音樂等藝術裝置被運用其中,打造了大型光群體互動裝置。不同于其他美術館,無界美術館如同一座黑色的迷宮,沒有地圖,沒有導引,參觀者在黑暗中摸索,尋找不同場景的入口,不掀開簾子,沒有人知道下一個場景會帶來怎樣的震撼效果,給觀眾留下了不少懸念和樂趣。每個場景都美輪美奐,在光影之中,觀眾也成了藝術場景的一部分。在無界美術館的官網上,每個場景的照片都堪稱一幅幅藝術作品,而這些藝術作品的中心,無一例外,都是光影中的參觀者。
2.線上平臺資源的整合利用。美術館作為藝術場館,宣傳推廣必然少不了圖片視頻的運用。數字媒體擁有信息量巨大、傳播范圍廣、不受時間空間限制、可保存等特點,數字媒體所帶來的大范圍傳播,彌補了傳統博物館在傳播互動方面的限制,成為美術館傳播宣傳的主要途徑。上海市的89家美術館中,擁有微信公眾號的美術館共計68家,擁有官網的美術館共計46家,且全年各大美術館共發布11400余條宣傳推廣信息,線上平臺成為美術館宣傳推廣的有利窗口。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線下展覽受到極大影響,線上平臺的整合利用成為展覽的出路。相較2019年,2020年上海共舉辦線上展覽351次,同比增長122%。
但縱觀現實,美術館雖然創建了微信公眾號,但功能主要集中在宣傳推廣和參觀預約。如何進一步利用線上資源,建立數字美術館,進一步增強公眾的參與與互動是下一步值得思考的方向。就“數字美術館”而言,目前更多的是線上展覽方式,即運用虛擬技術展示美術館藏品。如中央美術學院的數字美術館,整合了100多場不同類型的展覽,數量大,形式豐富,運用360全景、語音導覽等功能,帶給觀眾別樣的體驗。線上平臺是對傳統美術館功能的補充和延伸。在互聯網時代,有了大數據的支持,無論是在宣傳推廣還是挖掘受眾興趣點上,線上平臺都有極大的優勢,但目前線上參與程度還很低。整合線上平臺資源,結合社交網絡在參與上的優勢,將線下活動和場景搬到線上,形成館方和觀眾的良性互動,有利于美術館的長遠發展。線上展覽彌補了時間空間的限制,但數字技術所支撐的線上平臺有更多值得挖掘的作用。同時,利用互聯網技術將藝術與公眾連接更能體現出美術館的傳播及公共教育功能。
三、線上平臺促成觀眾參與模式的變化
美術館是傳播藝術的平臺,公眾參與的深度和廣度是體現美術館的價值所在。公眾對藝術的審美和追求在不斷提高,美術館已不能滿足作為單項傳播知識的機構,更要借助平臺優勢,將館方、策展方、藝術家、社會公眾集結關聯,共同生產知識,創造價值。
傳統的參與多體現在線下參觀、講座活動的舉辦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時間地域等諸多因素,且觀眾多處在被動接受的情境下消費館方提供的內容。館方或是策展方決定活動的內容,較大程度影響參與體驗。相較線下參與,線上平臺的優勢在于觀眾可以從自己喜歡的角度尋找切入點,自主地參觀學習,獨立地去創造價值。同時,隨著自媒體、社交平臺的廣泛運用,觀眾的參與模式也在發生變化,美術館從傳統的藝術機構轉變為藝術創作與社交的平臺。
(一)社交平臺的分享
拍照、打卡、上傳社交平臺分享似乎成了當下年輕人生活的一種方式。越來越多的藝術愛好者在參觀完美術館后會選擇通過在社交平臺上上傳大量的圖片視頻來分享感受,體現自己此行的價值。對于美術館來說,社交媒體、短視頻等平臺的崛起成為營銷傳播的主要戰場,為迎合觀眾的需求,越來越多的美術館開始追求視覺效果與潮流互動,很多美術館借此成為網紅打卡地。如teamLab無界美術館之類的沉浸式美術館憑借其酷炫的視覺效果獲得了年輕人的青睞。在感受沉浸式互動體驗的同時,拍照打卡,每一張照片都是一幅作品,觀眾也成為創作者,在自己的社交平臺上獲取大量流量,也為美術館吸引來了大量前來參觀的粉絲群體。
(二)在虛擬品牌社區內互動社交
移動App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也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社交方式。人們積極地在各種平臺上交友,分享快樂。美術館觀眾通過社交平臺,分享參觀體驗,渴望得到認同,獲得有共同興趣愛好的伙伴的回應。今日新媒體實驗室創始人兼總監高鵬(2016)曾提出:“嘗試建立虛擬社群來提高參觀者線上交流的體驗。”今日美術館未來館被稱為中國藝術的先鋒,為了探索新的美術館及藝術交流展示方式以及美術館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系,今日美術館上線了“Future云端館”移動App,聯合藝術家、策展方等打造了高端的新媒體藝術展示及互動平臺。觀眾和藝術愛好者可以在平臺中彼此互動,分享理念、技術和經驗,并且可以與策展人直接進行互動交流。“Future云端館”將館方、策展方、藝術家及觀眾聚集在一個平等自由的空間內,為不同的受眾表達想法提供平臺。
將美術館濃縮進App,讓原先比較遙遠的藝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動態的、多元的、能引起共鳴的虛擬社交平臺會為觀眾帶來不同于線下實體的參與感和體驗感,這也提高了觀眾與藝術場館之間的黏性,使得彼此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
(三)為藝術場館創造價值
美術館在為觀眾提供參與機會的同時,通過積極引導觀眾也可以成為內容的生產者,為美術館創造價值。相較于實體參與,線上平臺可以更廣泛地連接藝術愛好者,為他們的創作提供展示的機會。仍以今日美術館的“Future云端館”App為例,在為不同受眾提供交流機會的同時,通過與新媒體藝術家建立合作,簽約大量新媒體作品的互聯網授權,在平臺上展示作品,分享理念,傳播知識。借助線上平臺吸引聚集藝術愛好者,鼓勵藝術愛好者們在平臺上交流創作,從而培育年輕藝術家,將年輕藝術家開創性的思考與理念吸納汲取,又反過來對美術館的發展起到了推動和引領作用,互利互贏。
顯然,藝術消費和藝術創造所帶來的體驗是截然不同的。為美術館創造價值能讓觀眾有更實實在在的參與感,在自身的價值得到了體現的同時,也為美術館帶來更加多元化和個性化的改變。
四、結語
數字媒體時代,美術館被賦予了新的特征——不僅是藝術展示的場館,更是交流分享藝術理念的社交平臺。數字媒體改變了美術館內容的呈現方式和傳播途徑,再借由社交媒體之利,改變了觀眾的參與模式,從獨立分享到互動交流到價值共創,美術館的長遠發展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來達成。
數字媒體的發展雖然提升了觀眾的參與度,但社交平臺對于流量過高的依賴,可能造成藝術過度商業化。此外,一些觀眾僅僅是為了感受數字媒體技術打造的場景與效果去參觀美術館,將美術館作為打卡地。參觀目的是為了在社交平臺上炫耀,吸引流量與關注,忽略了美術館真正的教育作用。
數字媒體的發展對于美術館來說是一體兩面。首先,美術館與策展方要多方面考慮數字媒體在美術館展覽與活動中的效果,平衡流量與藝術傳播教育之間的關系。其次,作為館方和策展方,要合理地使用數字媒體技術,探索適合美術館的觀眾參與模式,讓觀眾參與美術館價值創造的同時,獲得藝術的熏陶與洗禮,真正提升藝術審美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