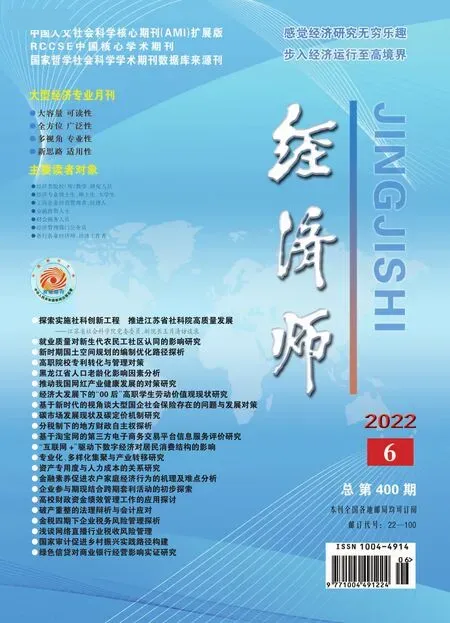破產重整的法理辯析與會計應對
●喬 欣
企業踏入破產重整之門,就不再是正常生產經營的規則流程了,而是轉入了司法主導的非常規生存空間,猶如一個重癥病人通過“住院”來恢復健康一樣,所遵從法律也從《公司法》轉換為《企業破產法》。同時,財政部現行規定并沒有針對破產重整的會計處理專門規范,重整業務明顯區別于破產清算、破產和解。因此,本文將對破產重整的財務處理在法理分析基礎上提出財務處理思路。
一、破產重整活動的現實背景
破產一詞,曾經是人們總是回避的不祥之物。不過,財務總是需要面對一些冷酷的挑戰。透過現象看本質,債權債務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而債權債務解決的最后底線也就是破產。破產與市場競爭肯定是水乳交融的情形,破產重整就像一枝帶刺的玫瑰,看似華麗又滿身荊棘,已發育成一種頻繁發生的客觀選擇。近年來,中國經濟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政策調整、新冠疫情持續三年的全面襲擊,以及美國發動的科技與貿易戰,都導致以前鮮見的企業破產案層出不窮,且有持續增多的趨勢。剛剛過去的2021 年,一股撲面而來的破產重整熱潮特別強烈:囊括航空、旅游、地產、零售等眾多產業的海航集團,國內曾經最大的校辦企業、輝煌一時的方正集團、紫光集團,當今中國汽車品牌強手——華晨集團,還有華夏幸福、匯源食品、雨潤集團等許多曾經耳熟能詳的企業也紛紛進入破產重整程序……。其中,作為中國經濟先進力量的代表,上市公司也有83 家上市公司被法院受理破產重整。
有經濟活動,就有會計核算,那么匹配破產重整這種特殊經濟活動和商業交易的會計核算該如何進行呢?除破產清算、破產和解已有相應會計制度規范外,獨具特性的破產重整肯定也需要精準的會計核算給予導航。在破產重整環境下,由于處于司法主導的法律程序中,“三會一層”的常規治理結構就其形式而言依然存在,不過源起于債權的清償權則明顯限制了原來的股權,公司控制權已明顯由股東方強制地轉移給了債權方,債權方憑借法定債權人會議等機構行使其權利;而公司管理權則由法院指定的重整管理人承接。這種法人治理實質性變異之后,相應的會計核算主體是不是也發生了變異,這對破產重整過程中的會計核算主體、會計核算事項又將產生什么影響,此類問題都需要討論分析。
二、破產重整框架下的公司法理辯析
相對于破產清算來說,破產重整(Reorganization)即重新整合股債關系、整理資本資源,再出發去面向市場,它能更大力度、更廣層面地保護債權、股東及其他相關權益方的合法權益,債權方通過重整獲取的債權清償率通常會大于通過破產清算獲取的債權清償率。因為,重整常常是相關各方普遍接受的選擇,能夠在法院主導下整合資源來拯救企業,保護企業繼續營業,實現債務調整和企業盤活,從而使債務人企業“涅槃重生”。①當然,現實中,走重整之路也有清償難、受理難和過程難等節點風險壓力。不過,兩害相權取其輕。人們總是在重整風險與重整優勢面前理性地選擇了破產重整,從而義無反顧地走向了破產重整的法律框架,其公司自治勢必逐漸從股東自治演變為司法主導下的債權人自治。
我們知道,公司生產經營活動是《公司法》框架下帶有邊界約束的公司自治。公司股東方和債權方對于自由的訴求表現在法律制度中就體現為股東自治和債權人自治。進入破產重整程序后,圍繞化解債務糾紛之困,股東自治權利限縮,債權人自治凸顯,并轉入法院主導下的關系調整。從經濟學角度看,股東方和債權方之間圍繞“欠賬還錢”的博弈更加直白,“你我矛盾”十分激烈,圍繞企業財產的爭奪戰變得更加白熱化。這個共同體的初級目標是通過重整讓企業活下來,終極目標則是各自利益最大化。經過法定程序的博弈,出現帕累托最優,并能找到雙方愿意接受的“次優選擇”。自從重整開始,就拉開了從股東自治演變為司法主導下自治的序幕。從法理分析,破產語境下,提起公司自治就始終不能忘記《企業破產法》,強調的是社會本位特征,講求對股東方、債務人企業、債權方、職工和其他社會公共利益的“一碗水端平”,這種公平保護使命——“公司自治”的本質逐漸從股東自治演變為司法主導下的債權人自治。我們知道:不走清算而進入破產重整的前提,一是債務人不能償還到期債務,二是債權人擁有債權的即期要求權,三是司法主導,專門設置了破產管理人,此時的公自治需要重新配置三者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破產重整程序中公司自治的制度選擇也是從實際情況出發,最大限度地圍繞相關利益者的均衡,可選的管理模式也值得分析。
司法主導正當性的法理基礎是顯而易見的,司法主導重整的確定性兼具合理性和可行性。《企業破產法》第八章“重整”體現司法主導性的條款比比皆是。這些法律條文明確具體,對各利益主體具有法律預期性,故具有合理性。外來的專業應該在實踐中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故具有可行性。由法院進行主導,積極發揮司法能動性,有利于保障破產重整程序的公平有序進行,有利于推動破產重整的成功,故具有合理性。司法主導的實現方式就是關鍵事項法院批準+ 重整推進委托管理人現場組織。這也是管理人管理模式的效力所在。管理人掌握公司的經營控制權,使原公司基礎下的委托代理關系發生了“主體角色”的變化使股東喪失了控制公司的渠道,管理人取代了原董事會的主要職權,管理人在重整程序中還有一些特有職權,如審查確認債權、合同履行選擇權、撤銷權、提議召開債權人會議、重整計劃制定權等等,當然,管理人可聘任原經理等組成辦事班子,是在管理人領導下的新個人職務行為。
從一般認知原理看,一個務實有效的破產重整管理人模式選擇,也應該注重在上述債權人管理模式、債務人管理模式和管理人管理模式三者之間,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理性選擇來源于外部專業人員組成的管理人管理模式成為多數案例的選擇,當然也有在管理人監督下自行管理模式。這都是《企業破產法》第十三條、第七十三條等的內在規定。遵從破產法之立法宗旨,并形成破產法重整法條之下的相關利益者之間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法理氛圍,在設計各相關重整事務決策時,以法辦事,注重尋求最大公約數,從而實現法院主導下各方整合機制下的治理優化。但不論破產重整執行事務的管理人是何者,其重整過程的會計事項務必獨立核算,形成專門的會計主體——特殊目的主體進行單獨、專門的核算。
三、破產重整活動的會計主體假設
主體,在漢語語境之中擁有相當豐富的內涵與外延,通常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在不同的學科范疇有著差異的理解,主體一詞在哲學視角,強調的是對客體有認識和實踐能力的人,在法學領域,主體則指享受權利和負擔義務的公民或法人,在會計學的天地里,主體肯定是圍繞著記賬算賬的出發點與歸宿點而定義“為誰而算”。因此,會計主體假設就是一種會計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沒有這個假設就無從進行具體的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等職能活動。會計主體強調會計工作在空間(強調經濟關系)所設定的前提條件,是人們對某些尚不明確、無法求證或者變化莫測的會計環境因素所做出的合理推斷。葛家澍教授認為:“會計處理的數據和提供的以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不是漫無邊際的,而是嚴格限制在每一個在經營上或經濟上具有獨立性或相對獨立的單位之內。……這一單位就應當視為會計主體”。②會計主體與法律主體是兩個概念,需要有所認知。前面已經論證,在破產重整框架下,債務人權利受到明確限制、債權人權利的、司法主導的背景下,管理人代表法院依法履職,組建“強大”的專業團隊、管理人與法院之溝通技能、破產案件債權審核及債權表編制、債權人會議召開、破產債權的定性與分配、財產調查及處置應注意的關鍵點、破產重整計劃制定、破產和解的適用甄別,提升破產管理人執業技能,完全可以也應該重生一個專屬破產重整使命的會計主體。因為其使命已經完全不同于企業正常經營時期了,為破產重整為宗旨成為其核心功能。
(一)會計主體假設的一般分析
進入破產重整之后,從理論上講,重整價值通常應該大于清算價值。顯然,一套運轉且產出產品的機器、廠房總比分拆成一塊塊廢僑資銅爛鐵和磚瓦廢料更加能賣出高價錢。當然,重整價值判斷的主體,可以包括債權方、債務方、原股東方、職工、新投資方甚至于地方政府,各個主體自有其自身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期待。基于多個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重整價值判斷的微觀目標是實現其判斷主體利益的最大化而政府追求社會價值最大化③,破產管理人也會追求其自身報酬最大化,而,因此需要在這個利益共同體的前提下,遵循權益均衡和全面判斷的原則,還要追求發展性原則、整體性原則和效益性原則,專門構建一個特殊目的主體(Special Purpose Entities,簡稱SPE),并通過這個特殊目的主體,對重整活動進行連續、系統、全面、綜合的會計核算。
當然,基于破產重整活動搭建的特殊目的主體,所謂的空間范圍和邊界是邏輯范圍和邏輯邊界的概念,而不是通常所指的物理意義上的空間范圍與邊界定義。這其實就是假定所有資產的產權或控制權歸屬都是清晰的,是脫離了債務人企業而進入破產管理人直接控制的主體范圍。一個會計主體的資產核算范圍與另一個會計主體的資產核算范圍不應存在重疊或交叉。在國際會計領域,特殊目的主體(SPE)或特殊目的載體(Special Purpose Vehicle,簡稱SPV),就是為了特殊目的而建立的法律實體,它在資產證券化中、信托等領域應用十分廣泛,建立SPE 是為了完成有限的、特殊的或臨時的目標,主要是隔離稅收、破產、經濟等風險)。一旦SPE 成立,其必須作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實體運作。值得注意的是,SPE 必須在管理和所有權方面與發起人分離。作為獨立實體,SPE 對自己的相關決策負責,是在事先確定好的指導方案下運作,不需要進行任何經營決策,更多的是“平臺作用”或者稱為“通道作用”。
(二)破產重整的會計主體分析
會計主體假設的界定,不僅限定了會計要素確認、計量、報告的空間范圍,而且為會計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空間載體,《企業破產法》框架下破產重整會計主體假設的準確界定,必將對重整核算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在企業破產重整期間,公司已經被法院主導了,并且不再以經營活動為主,“重整活動為主+必要的維持”成為主基調。破產管理人作為一個法院指定的現場代表,負責破產重整企業相關利益關系人的協調,因此,破產管理人應該是破產重整條件下的會計主體。從破產管理人進駐與接管債務人企業開始,企業會計主體就區別于前期正常經營的會計主體了,重整階段的資產、債權及債務的接管,有關會計處理和會計報告,會計檔案的移交工作;破產企業的資產保管、債權債務清理以及資產處置等工作,都是一個獨立的會計主體。這是顯而易見的。與此相類似,破產重整會計在法院宣布進入重整程序開始,管理人進駐和接管之后,破產重整企業的會計行為主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破產管理人扮演著既維護債務人利益又確保債權人權益的角色。這種地位中立的特征,決定了破產管理人只是在企業破產重整特定期間產生的一個履行重整職責的特殊工作機構。總之,破產重整會計主體就是一個特殊目的主體,針對破產重整活動而非供、產、銷等企業經營活動,具體通過債務清償所發生的資產清理變現、債務償付等,重整的特殊目的主體不再具有循環周轉的特征,卻呈現出一次性、階段性特點。
四、破產重整活動的會計業務核算
(一)破產管理人的重整業務
破產重整的會計核算,也始終圍繞重整業務的推進而進行的。重整從法院受理并裁定進入重整理程序算起,一般為6個月,經法院批準可延長3 個月,共9 個月。但其中的重整關鍵節點繁多,包括但不限于:破產公告并通知債權人、債權申報與審核、接管債務人財產并組織審計評估、召開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招募投資人并設計投資方案以及提交重整計劃草案、法院批準重整計劃、重整計劃的執行,等等。其中,破產管理人推進的財產調查及處置、有效開好債權人會議、破產債權沖突與清償順位以及可能發生的企業破產涉刑民交叉問題實務應對都是比較復雜的事項。
客觀看待重整過程的控制,主要取決于法院、管理人和債務人三個角色。顯然,法院是重整的后盾,所有重大事項如是否受理重整申請、是否確認債權、是否確認債權人會議決議、是否確認重整計劃等等,都必須由法院最終裁決。而債務人是否能夠有效配合,是重整成功的基礎。提供準確的財務信息,便于審核債權、制定重整計劃打好基礎。債務人及債務人股東在重整過程中必須放棄部分權利,如放棄部分股權,以換取重整計劃的通過。不過,管理人卻始終是重整工作的核心。
基于重整管理人的獨立主體,為完成其特殊的階段性使命,就需要建立一個獨立主體的重整會計賬務體系,需要從被重整企業剝離出來用于清償的特定資產與負債,并交付給專司重整業務的重整會計主體。重整會計主體是在債務人與管理人共同為履行重整使命而搭建的特殊目的主體。由此形成債務人企業與重整會計主體兩個并存的會計主體。因為,企業在重整期間,作為重整賬務執行機構(重整會計主體)需要接管債務人企業移交的各類剝離資產,并進行包括但不限于債權申報、剝離資產變現、債務清償等重整活動;同時,債務人企業還要繼續進行一些生產經營活動,另一方面,重整計劃的實施,包括重新確認債務、處置財產、按比例減少資本等。這種側重于維持的持續性經營活動與側重于清理的限期性重整活動并存態勢,決定了企業重整期間會計核算的特殊性。因此,顯然需要劃分兩個會計主體,一個是專門進行債務、債權以及其他剝離資產處理的重整會計主體;一個是債務人企業主體,分別核算其各自的收支動態與重整結果。需要說明的是,正常經營活動所匹配的資產負債活動、收益支出活動不在本報告研究對象之內,本報告主要針對重整范疇的資產接收與處置、負債接受與兌現,以及重整活動的損益,并關注重整會計主體與債務人的賬務對接。
(二)重整業務節點的會計核算
圍繞著破產重整程序的漸進推進,當重整管理人接受法院指定進場開始,承接了一部分債務人的職責,從而組成一個特殊目的主體(重整會計主體)單獨存在。梳理重整過程中的全部業務,重整會計主體圍繞“接管建賬——資產處置——債務清償——損益結算——歸還關賬”的模式進行其核算使命。現分析其中的一些重點業務核算節點。
節點之一是接管重整范疇的資產。主要是一個重整實質性展開的基礎和開端。現實中,多數資產(房產、設備等)都可能被設置擔保權而保證了債權人優先愛償權,擬作為擔保資產單獨核算。其他資產則用以償付普通債務的資產。對于納入重整資產范圍內資產項目,在債務人、管理人協同進行各種確認手續后,重整會計主體應該及時、準確地辦理接收手續,形成與債務人企業資產移交之間的無縫對接,并辦好接收手續進行重整資產的核算。
節點之二是接管重整范疇的債務,這是面向債權人組織清償和分配的前提。擔保債務是以一定財產為債權人的債權提供擔保而形成的債務。對于債權人來講,債權人已經取得了對擔保物的處置權,其債權的履行有了物資保障。因此,擔保債務不應屬于普通債務,是優先償付的債務。普通債務是債權人依法申報確認,并應由重整資產中獲得公平清償的債務。需要注意的是,普通債務的履行受債務人財產價值的限制,如果重整資產大于普通債務,則普通債務能夠得到全額償付;如果重整資產清償優先清償債務后小于普通債務,則普通債務只能得到部分償付。
節點之三是全面組織重整業務事務。包括但不限于:一是接收重整投資人投資的核算。通常,對全權人的清償資金來源主要依靠重整活動中尋找的重整投資人所投入的資金。債務人企業進入重整程序后,重整管理人設立專用銀行賬戶用于償債資金的統一管理,償債資金的來源主要償債資金在銀行賬戶中孳生的利息。二是處置變現資產、重整費用與收益的核算。在納入重整投資人合并范圍前,應全面檢查存量資產狀況,目前存在哪些資產需要進行核銷。此外,還要對各項重整收益與費用分別進行核算,如共益債務支出、破產費用、穩定發展基金等業務的核算。
節點之四是重整資產的分配。普通債權的實際規模與清償率,包括環節主要有:本次清償財產的金額,根據重整投資人重整資金、拍賣資產變等計算;破產費用及共益債務等,特定優先愛償、破產費用、共益債;再計算第一順位(清償職工債權)、第二順位(需償普通債權,擬分為大額債權、小額債權、預計債等計算確定。
節點之五是重整損益的核算。重整損益是破產重整企業自破產重整日起至重整結束日至的重整期間內的重整成果。重整損益包括重整收益、重整損失和重整費用。對這些重整,通常計量模式是:
重整收益=債務豁免收益+ 重整費用與相關重整新增支出(主要指重整前未入賬的職工債權支出與新增及預計負債)。
相關項目的內容:第一,重整期間企業財產變賣收人高于其賬面成本之間的差額;第二,重整期間由重整管理人追回的因破產重整企業發生破產法特指的無效行為或欺詐行為而轉移的資產價值;第三,其他依法無須償付的債務。如果發生重整損失,即在按公允價值計價和重新確認債務中發生的資產價值減少和負債金額增加,則包括以下內容:第一,重整期間企業財產變現收入低于其賬面成本之間的差額;第二,重整期間企業依法重新確認債務而產生的債務增加額。其中重整管理費用主要是指破產財產管理、變賣和分配所需要的費用,包括重整管理人員辦公費、聘請的會計師、審計師和工程技術人員的聘用費、公證費等;重整案件訴訟費用是指重整管理人在重整案件審理過程中支付的費用。
最后一個節點是重整賬務結清結束。在完成各項重整事項,并報法院核準之后,破產重整這一特殊目的主體也將結束其使命,即將重整完成日資產負責表各項回歸給債務人企業。結轉完成后,將極大地優化債務人公司的負債結構,偶合其能夠卸下債務包袱,輕裝前行。
當然,破產重整是一項涉及多個方面的經濟活動,其間的每一步,都應該在法院主導下進行的,作為特殊目的主體,破產重整應該定期編制重整過程中的會計報表,并在重整完全結束時編制一份終結性的重整會計報表,并同時就專項信息實施必要的信息披露。
注釋:
①丁燕,破產重整程序中的公司自治[J].理論月刊,2011(04)
②萬壽義,趙聚輝,高等學校教育成本核算理論體系的構建研究[J].蘭州學刊,2009(02)
③欒甫貴,侯晶,上市公司破產重整價值判斷體系的探討[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