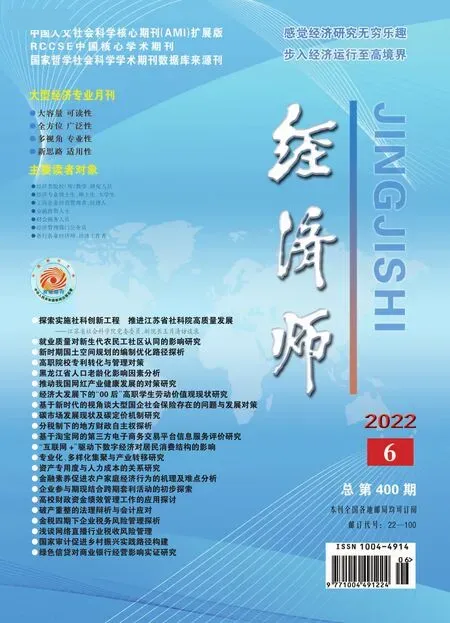“雙碳”目標下碳會計實踐與關鍵問題研究進展
●白 鴿 趙永斌
一、引言
我國力爭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下稱“雙碳”目標),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中國引領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舉措。圍繞“雙碳”目標開展的碳達峰、碳中和行動,必將在未來引發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實現“雙碳”目標的首要工作,就是對碳排放權這一公共物品設置排放總量上限,賦予碳排放權以稀缺屬性,從而使碳排放權成為一種有價值的商品。作為碳排放產生的主體之一,企業需要付費取得碳排放權,這就使碳排放權作為一種有價的要素,進入生產經營活動之中,企業會計核算體系也由此產生,催生了碳會計的概念。特別是碳市場啟動后,碳會計中又增添了碳配額、氣候變化風險、碳減排與碳核證等方面的內容(Bebbington et al,2008)。
“雙碳”目標下,碳達峰、碳中和行動加速開展,企業作為控制碳排放的核心主體,企業碳會計勢必會加速變革。如何制定合適的會計準則,選擇合適的會計處理方式,使得減排行為對企業經營效益影響最小,是企業關注的現實問題。目前,實踐層面雖然有《碳排放權交易有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等相關文件的出臺,但學術界對于企業碳會計關鍵問題的處理,仍存在較多爭論和探討,學者們基于不同的會計目標,對企業碳會計處理關鍵問題提出了諸多方案,但目前尚未取得一致觀點。
在“雙碳”目標提出的背景下,企業碳會計關鍵問題的處理,不僅要重視降低“碳活動”對企業生產經營效益的影響,還要兼顧“雙碳”目標下的社會減排效率。因此,回顧碳會計實踐進程,總結企業碳會計關鍵問題處理研究進展,展望“雙碳”目標下企業碳會計關鍵問題的研究方向與框架,就顯得十分必要且迫切。鑒于此,本文在“雙碳”目標背景下,圍繞碳會計準則制定與執行、碳會計的確認與計量、列報與披露等關鍵環節,對企業碳會計關鍵問題處理進行研究回顧與展望,以期為本領域學術研究提供參考,為企業碳會計關鍵問題處理實務提供借鑒。
二、碳會計準則制定的實踐進程回顧
碳會計并不能直接減少企業對節能降碳的支出費用,但合理的會計準則制定可以減少與減排支出相關的交易成本;企業對不同會計準則的選擇,也會影響其減排投資的體現(張先治和石芯瑜2021)。總體而言,企業碳會計的發展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息息相關。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大致經歷了從普遍認知到一致行動的過程,企業碳會計的發展也經歷了從一般性碳會計信息披露向碳會計規范化核算的過程。與之對應地,企業碳會計準則的制定與執行,也是從信息披露準則開始,逐步制定碳會計核算準則。
在碳會計信息披露準則方面,國際上一般將可持續發展報告、社會責任報告等作為碳會計信息披露的載體。全球性組織或協會、不同國別間,都提供了可供參考的企業碳會計信息披露框架和建議。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在2000 年至2013 年期間制定了4 個版本的可持續報告指南,提供了貨幣定量指標、非貨幣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等系列披露指標體系,為企業開展碳會計信息披露提供了范本。國際綜合報告委員會(IIRC)也在2013 年制定了《國際綜合報告框架》,給出了一種財務信息、環境信息與社會信息集中披露的模式。近年來,可持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陸續制定了77 個特定行業的可持續會計準則。碳排放信息披露項目(CDP)也要求上市企業披露其碳排放信息及相關管理措施。總體來看,目前多個國際組織對企業碳會計信息披露都給出了框架或指南,呈現出具體化、可操作性逐步提高的趨勢,但也存在非財務信息計量難度大、編制成本高等問題,而且受制于企業綜合成本和不同國家對碳會計信息披露的強制程度不同,碳會計信息披露在全球范圍內的透明度和規范程度差別較大,上市公司基于投資者和信息公開的需求,在碳排放和碳會計信息披露方面相對健全,但一般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披露相對滯后或不足。
總的來看,目前各國企業層面的碳信息披露呈現出碳排放信息和環境風險披露較多,主觀定性信息披露較多,貨幣等定量信息披露較少,“會計”成分不足,碳信息披露與碳會計核算體系發展要求差距較大,對會計和財務決策的支撐性較弱。
在碳會計核算準則方面,碳會計核算準則制定是伴隨或支撐碳排放權的有價化進程而推進的,特別是隨著碳市場這一市場減排工具的產生,使碳排放權成為一種有價值、可交易、可計量、并實實在在影響企業經營成本和效益時,實踐層面對于碳會計核算準則提出了需求。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IFRIC)在2003 年給出了支撐“cap and trade”模式的碳交易會計核算草案,并在2004 年底發布了正式版的《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3 號——碳排放權》(IFRIC 3),該方案將碳排放配額界定為一種無形資產,并根據國際會計準則中通用的無形資產計量方式進行計量,但由于該方案不能在碳交易會計處理中實現邏輯閉環,受到學術界和實踐層面的爭議較大,不久后即被撤回,這也引發了學術界對碳會計的進一步討論。
2011 年后,我國陸續建立了7 個試點碳市場,2017 年,正式啟動了全國統一碳市場的建設進程,并于2021 年7月正式開展線上交易。2016 年,國內公布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有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征求意見稿)》,并于2019 年底發布了正式規定《碳排放權交易有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下稱《暫行規定》)。與《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3號——碳排放權》不同,我國對市場購入和無償從政府取得的碳配額分別做了會計處理相關規定,從政府無償取得的碳配額不做會計處理,只在市場購入或超配額排放部分確認成本費用。之所以從政府無償取得的碳配額不做處理,是因為無償分配這一過程并未實現經濟資源從政府到企業的讓渡,而且碳配額分配也不是政府對企業的一種補助。盡管國家層面給出了上述碳會計處理準則,學者們和實踐層面對碳會計的討論和探索仍在繼續,特別是“雙碳”目標的提出和全國統一碳市場正式開展線上交易,并完成一個履約周期,碳會計的處理問題也逐漸引起重視。這些討論,我們將在下文中予以回顧和分析。
三、碳會計關鍵問題研究梳理
碳會計最初來自于環境會計,是環境會計的一個重要分支,其研究范疇涉及到碳資產、碳負債、碳權益、碳收益、碳成本、碳利潤等(韓艷,2020)。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碳減排方面行動較早,特別是歐盟早在2005 年就啟動了歐盟碳市場(EU-ETS),與之相對應地,碳會計的實踐和研究在國外也起步較早。國內開始關注碳會計是在2008年左右(郝玲和涂毅,2008;Saurav Dutta和楊繼良等,2008),特別是2009 年我國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提出“到2020 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45%(簡稱‘40-45 目標’)”以來,國內碳減排行動加速,碳會計相關研究迅速增多。2008年以來,國內以“碳會計”為主題發表的文獻達到943 篇,發表數量最高的兩個年份分別是2016 年和2018 年,分別是《巴黎協定》簽訂后的一年,和我國宣布啟動全國統一碳市場的后一年。可見,應對氣候變化重大事件和政策的推進,是推動碳會計研究的關鍵政策因素。
從研究視角來看,除單純從會計專業視角探討企業碳會計處理問題,低碳經濟視角也是企業碳會計研究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碳排放權交易是碳會計研究的關鍵場景。從研究內容來看,企業碳會計研究的內容主要涉及到信息披露和會計處理。其中,涉及企業碳信息披露的研究較多,部分研究涉及到企業碳會計的確認與計量、信息披露等處理過程,但對于企業碳會計的會計準則制定與執行研究相對較少。基于上述梳理,本文接下來重點回顧企業碳會計的確認與計量、列報與披露等關鍵處理環節的研究進展。
四、碳會計關鍵問題研究進展
1.碳會計的確認與計量。隨著碳市場的建立、“雙碳”目標下能源轉型的加速推進,學者們對碳會計確認與計量的討論逐步增多,但由于對減排行為的屬性和排放權的歸屬界定等因素認識不同,導致出現了多種碳會計確認與計量思路。另外,與傳統會計相比,碳會計的計量主體從經濟活動拓展到環境與減排活動,計量屬性也由貨幣計量向貨幣與非貨幣結合的方式轉變,而且由于碳減排活動的長期性和碳資產、碳負債概念的出現,碳會計在會計分期和持續經營判定標準上,也與傳統會計存在一些區別(張先治和石芯瑜2021),這使得會計確認與計量成了阻礙碳會計發展的一大難點(曹國俊,2021)。
在碳會計確認與計量理念上,鑒于清潔能源在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中的份額都迅速上升,學者們開始關注到這一現象并呼吁,對清潔能源勘探、論證、開發與生產等環節設計到的會計處理,做出體系化設計和規范,在能源消費環節,也可以以單獨開發清潔能源使用會計處理,來引導或激勵企業消費清潔能源(張先治,2021;唐洋等,2021;曹國俊,2021)。在碳會計確認與計量的細節上,部分學者認為宜將綠色減排技術研發費用予以“有條件”的資本化,這樣不僅可降低費用,而且能夠提升企業價值和投資者信心(Tsoligkas 和Tsalavoutas,2011);張倩倩等,2017)。在采取歷史成本法還是公允價值法計量方面,歷史成本法觀點早在20 世紀90 年代初就已產生,但該方法無法反映碳配額的市場價值,公允價值法目前在實踐或理論層面的接受度較高,但也存在加劇碳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暫行規定》指出在企業購入碳配額當日按照購入成本計量,部分學者主張采用公允價值法計量(葉豐瀅等,2021),但劉梅娟等(2021)認為,長遠來看,公允價值法計量碳資產確實是大勢所趨,但目前在碳市場機制不成熟的情況下,歷史成本法計量是較為穩妥的做法。還有國內外學者提出了期權估價法的思路,該思路雖然可以鎖定碳市場價格波動風險,但該思路操作性相對較為復雜。
上述理念和細節處理,在一般性減排活動中,確認與計量較為簡單,但在碳市場這一特殊情形中存在較大爭議(涂建明等,2019),圍繞碳市場開展的碳會計確認與計量的研究,也成為碳會計研究中的焦點之一。這是由于碳配額的來源有政府免費分配與市場購入兩種形式(未來全國碳市場還會有拍賣的形式),碳配額的用途又有履行配額清繳義務和出售獲利兩種形式,配額分配、交易、履約又有多個活動環節,這就使得碳配額這種有價商品在確認過程中存在無形資產、存貨、交易性金融資產等多種資產確認觀點(王愛國,2012;張薇等,2014;崔也光和周暢,2017),在計量過程中存在歷史成本法、公允價值法等多種主張,在科目選擇上,也有負債、費用或者不計量等多種處理方案。
在碳配額的會計屬性確認和計量上,IFRIC3 中將政府免費分配的配額確認為一種政府補助(Cook,2009),而我國《暫行規定》將市場購入的碳配額確認為資產,而無償取得的配額不做賬務處理。對此,學術界爭議較大,早期的學者傾向于將碳排放權確認為一項資產(鄧海峰和羅麗,2007;Mete et al.,2010;苑澤明和李元禎,2013),理由是碳排放權代表著與碳排放相關的支配、處置和收益的權力。但之后學者們認識到碳配額的取得具有不同的經濟實質,碳配額的交易和清繳情況復雜,對碳配額的屬性認知也呈現多樣化趨勢。
在企業取得碳配額環節,趙永斌等(2019)認為碳配額具有同質性,即不論何種來源的碳配額,均代表一份額的碳排放權力,均可用于交易和履約。張先治和石芯瑜(2021)認為在同質性下,若對市場購入和政府免費分配采取不同的確認方式,有失會計信息的一致性,結合資產確認的條件和政府分配配額的性質,認為政府免費分配的配額也應確認為一項資產。涂建明等(2019)、鄭穎等(2021)諸多學者也持類似觀點。有學者提出針對碳排放權單獨設置資產科目進行計量核算,是一種權利性質的資產(張薇等,2014;呂忠梅和竇海陽,2017),但與之相對應的,也產生了一項義務性負債。涂建明等(2019)按照這一思路,考慮到配額免費分配不應虛增企業資產,提出獲得免費配額時,借記資產(借:碳排放權—法定碳排放權)的同時,貸記預計負債(貸:應繳碳排放權—法定配額義務),并按實際排放量在報告期內予以攤銷,結余的配額收益與政府補助做相同處理,期間由公允價值變動造成的配額資產損益,按當期損益計量。葉豐瀅等(2021)學者的觀點與此類似。鄭穎(2021)對企業取得碳配額的目的和經濟實質做了細分,認為如果企業獲得政府免費配額之后當即售出,則日后的超額排放還需全數購買碳配額,所以當即售出獲取的收益本質上是預計負債;如果企業購買配額的目的不是用于履約,而是為了低買高賣,則應確認為交易性金融資產。還有學者基于發展的視角提出目前來看,碳排放權確認為一項無形資產符合實際,但在碳市場不斷完善和參與主體逐步擴大的未來,將其確認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更為合適(韓艷,2020)。在企業出售碳配額環節,《暫行規定》將企業出售碳配額的損益計入營業外收入中,但鄭穎(2021)認為免費獲得配額需要確認預計負債,那么出售政府免費配額應當計入遞延收益,而出售市場購入配額的投機行為,其損益應當計入投資收益,而不是《暫行規定》中的營業外收入。
在企業清繳配額完成履約階段,《暫行規定》規定,免費取得的碳配額不做處理,購入的碳配額用于履約的,按配額的賬面余額,借記營業外支出,貸記碳排放權資產。如果還有配額盈余,企業自愿注銷,與履約處理一致。鄭穎(2021)主張在期末將企業手中的配額確認其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并在最后注銷配額,完成清繳履約時,將其損益計入營業外支出。葉豐瀅等(2021)認為《暫行辦法》中超額排放成本不確認為成本而確認為營業外支出,也會降低對企業的減排約束。為了使配額清繳環節能夠對企業形成成本約束,涂建明等(2019)提出履約清繳階段要盯住“cap and trade”這一碳市場設計機制,將市場購入的碳配額確認為非法定碳排放權,其購入成本攤入企業的制造費用或管理費用之中,以實現減排成本的內部化;反之,若存在配額結余,則沖減制造費用和管理費用。
總的來看,學者們對碳會計的確認與計量開展了大量且具有探索性的研究,研究的核心在于碳排放權的會計屬性界定問題,目前比較一致的觀點是,界定碳排放權的會計屬性需要依據“碳活動”的經濟實質,但不同學者對于該經濟實質的認識不同。關于碳排放權的會計確認,學界的觀點總體上經歷了單純確認為資產、確認資產的同時確認一項預計負債的認識,關于究竟確認為何種性質的資產,也呈現出根據不同經濟目的和性質、不同交易環節,逐步細化會計科目的趨勢。在碳市場納入范圍擴大、交易主體增多,甚至構建全球碳市場的趨勢下,碳會計的確認與計量將會呈現確認規則逐步細化、計量規范逐步統一的趨勢。在“雙碳”目標背景下,如何體現碳減排和碳中和成效與收益,也將是碳會計確認與計量的研究方向。
2.碳會計的列報與信息披露。國外較早呼吁披露碳會計信息(Callon,2009),表外與表內相結合同時披露碳財務信息及其附注,是一種比較推崇的披露方式(Petersen et al,2014)。除此之外,國外學者還較早地提出了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通過社會責任報告、CDP 氣候變化報告等途徑披露碳信息,直至在企業年報中反映碳會計信息(Shawn,2015)。我國學者也較早主張開展碳信息披露,張彩平(2010)提出應在核算、管理、審計三方面建立我國碳信息披露框架,崔也光等(2017)建議企業通過官網或者公眾號等途徑開展碳信息披露。沈洪濤和馬杰(2012)認為應該通過輿論和政府監管來倒逼企業披露碳會計信息。早期的碳會計信息披露以定性信息居多,定量較少(陳華等,2013),在披露的行業范圍上,以能源重化工等重污染企業為主。
為規范碳會計信息披露,提升質量,學者們對碳會計信息披露標準與框架也進行了諸多探討。張先治和石芯瑜(2021)主張將減排成果納入財務報告,具體來說,就是在資產負債表中展示減排固定資產設施價值和無形資產價值,或者在財務報表附注中有所體現,并在利潤表中單獨體現減排費用以及綠色信貸、綠色補貼等收入,這是一種非獨立報表的思路。還有部分學者提出了獨立報表報告碳會計信息的思路,例如王薇(2021)圍繞低碳政策、低碳戰略、風險與機遇、溫室氣體排放情況、減排措施、碳排放權交易、財務數據影響等建立碳會計信息披露框架,并主張單獨編制碳會計報表。
總的來看,碳會計信息披露的關鍵問題在于統一碳會計信息披露標準與規范,但這種統一不是所有行業、企業范圍內的統一,而是分行業、分類型內部的披露格式和要求的統一。披露的方式不僅要有碳會計信息報告,而且要將減排活動與生產經營活動相融合,編制非獨立報表,甚至是獨立碳信息報表,來披露碳會計信息。另外,權威的第三方鑒證機構對碳會計信息的鑒證,也是提高碳會計信息質量的必要配套保障。未來研究應關注基于大數據的環境信息質量評價、非正式制度對環境信息披露的作用以及環境信息披露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等領域(張晨等,2022)。
五、總結與展望
1.研究總結。本文在“雙碳”目標背景下,回顧了碳會計實踐歷程,特別是碳會計規范制定與執行的歷程,梳理了碳會計研究的總體概況與重點領域,重點回顧了碳會計確認與計量、碳會計信息的列報與披露等關鍵問題的研究進展,并在“雙碳”目標背景下,初步展望了未來碳會計發展的方向與要求。本文的主要觀點與結論如下。
碳會計在環境會計的框架下,研究與實踐起步均較早。隨著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推進和碳排放權的有價化,碳會計正式進入實踐實施階段,但各國出臺的碳會計標準不一致,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參與度低,使得目前尚無一項全球公認的碳會計準則。
在碳會計處理的關鍵環節中,碳會計的確認與計量是核心,但與信息披露相比,該類研究相對較少。碳會計確認與計量問題的焦點在于,碳排放權的會計屬性認定問題,目前學術界基本認同在將其確認為一項資產的同時確認一項以碳減排義務為標的預計負債這種思路。但確認為何種資產、不同環節、不同目的下的碳交易行為下的會計處理,目前學界仍在探索和爭論。本文認為碳排放權具有來源多樣、用途多樣、交易目的多樣等特點,有必要針對各類情形,確認其經濟實質,依照經濟實質進行會計確認與計量。
在碳會計信息披露方面,目前全球也無統一的碳會計信息披露規范,但總體來看有編制碳會計信息報告、編制非獨立會計報表和編制獨立會計報表多種可選披露方式。在實踐中,定性的碳會計信息披露是主要方式,未來研究的重點應該是碳會計信息披露標準與規范問題,該規范不僅需要具有信息可比的統一性要求,還應具有可反映行業特征的分行業特色指標。與碳會計信息質量相關的碳會計信息第三方鑒證機制與標準、碳會計信息分析與評價也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
2.研究展望。本文認為,與傳統會計相比,碳會計體現出兩大區別。這兩大區別是導致碳會計研究一直處于爭論與探討過程的核心原因,也是導致碳會計實踐進程不盡如人意的關鍵因素。未來碳會計研究與實踐,宜重點把握碳會計的這兩大特性,開展相關研究。第一,碳排放是全球問題,碳排放權在全球范圍內都具有同質性,以碳減排為核心的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也呈現出全球治理、全球合作的工作要求,這就要求碳會計準則制定要具有全球適用性。這就要求全球碳會計準則的制定,要建立在廣泛的實踐與國情分析基礎上,調研將成為日后國際碳會計準則研究的基礎環節。另外,國際碳會計的研究與制定,不僅要有統一性,而且還應具有多樣性,以滿足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碳會計確認與計量需求。換言之,碳會計準則制定和研究要考慮到各類應用情景與經濟實質,突破原則性、指導性、建議性條款。在此要求下,碳會計的發展中國家適用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碳會計能力建設體系建設問題也是未來研究的重點方向。第二,傳統會計的核算對象是企業的生產、經營、投資等企業活動,不考慮企業活動導致的外部性。而碳會計是將企業活動產生的外部性,也納入到企業的成本收益核算體系之中。目前階段,碳排放權采用的是以免費分配為主,但從長遠來看,碳排放權的分配將會以拍賣為主,將成為企業不可或缺的一項生產要素,這種趨勢下,如何將外部性成本內部化,重構傳統會計核算體系與規范會計科目,也是未來研究的重點方向之一。若依據科斯定理,將碳排放權免費分配給企業、企業拍賣取得碳排放權、免費與拍賣相結合,是三種不同的初始產權界定方案,不同產權界定方案下的碳會計體系構建,也應是未來關注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