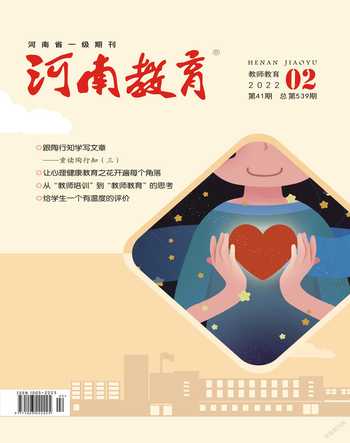“教師培訓”到“教師教育”的思考
常亞歌
新一輪教育改革中,市、縣教育局的“師資培訓科”更名為“教師教育科”的行動正在悄然進行。從“教師培訓”到“教師教育”,雖然只有兩個字的不同,但其基本理念、工作定位、實踐要求及目標愿景等有著本質的差異。這個稱謂變化,反映了我國教師專業(yè)發(fā)展正在經(jīng)歷重要的歷史轉折,即由以往對教師的單一技能的培訓轉向系統(tǒng)設計、整體推進的教師教育體系建設。那么,教師教育科如何應對這一轉變呢?
首先,“教師教育”不能脫離當下的信息環(huán)境,要建立與時俱進的教師發(fā)展觀。21世紀的前20年,是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高速發(fā)展期,信息技術所帶來的社會變革之大,遠超過去幾百年的總和。2020年,中國一年新出版的圖書在40萬種以上,中國成為5G塔站與商用的第一方陣,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以免費、開放的方式為數(shù)以億計的大中小學生提供海量學習資源……這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傳統(tǒng)教師培訓的理念與做法。我們應該反思:過去引以為豪的集中式、講授式的培訓是否適應教師的發(fā)展現(xiàn)狀?是否有更為快捷、有效的方式來適應新環(huán)境下的教師專業(yè)發(fā)展?我們應該更為理性、包容地看待教師的階段性成長與終身發(fā)展的關系,應該從教師自主發(fā)展的角度去引導教師自覺成長,而不是強制性、計劃性地發(fā)展他們。
其次,“教師教育”不應單一管控,要建立符合新時代教師發(fā)展要求的成長觀。在“教師培訓”時期,我們有一個共識,即“校長是教師發(fā)展的第一責任人”,校長掌管著教師外出、財務、崗位、職責分工的決定權,教師的發(fā)展是校長職責之內的重要工作。但這種被領導、被指派下的教師發(fā)展思維,很容易養(yǎng)成教師發(fā)展的自我惰性。把發(fā)展的主動權交給管理者,而各級管理者也始終把住教師培訓的“權柄”不放,嚴格控制教師需要的學分、學時,久而久之教師便失去主動發(fā)展的意愿,成了“躺著走路”的人。
由“教師培訓”到“教師教育”的轉變就是需要我們下決心、下力氣扭轉這種單一、管制的教師培養(yǎng)觀念,讓“校長負責制”變成“自主負責制”,把過去集中的學分、學時、資源壟斷分出合理的比例,放權給學校、教師、教師自組織團隊等,大力構建利于教師自主發(fā)展的教師教育制度體系。比如,我們鼓勵教師建立教師工作坊、名師工作室,在建立教師學科團隊組織的同時,賦予他們必要的學時自主權,讓教師的組織發(fā)展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又如,我們鼓勵教師通過中國慕課網(wǎng)站等平臺獲取個人所需的學科及人文知識,把教師的人文閱讀列入學時積分等。在完善集中統(tǒng)一培訓的同時,我們與學校、教師、培訓管理者達成教師教育的理念共識,只有這樣,一個區(qū)域的教師發(fā)展才會多樣化、可持續(xù)化。
最后,“教師教育”注重全流程配合,對標教師專業(yè)標準,樹立專業(yè)系統(tǒng)的教師專業(yè)觀。學科專業(yè)化仍是目前中國教師發(fā)展的最大瓶頸。近來,有多則新聞引發(fā)輿論關注,如深圳某中學新招的教師中,北大、清華等名校畢業(yè)生占近2/3。鄂爾多斯高薪聘請清華、北大畢業(yè)生等。就學歷與能力而言,這些“新教師”是優(yōu)秀的,但他們是否具備完備的教育學知識,還需要在實踐中觀察。對于教育而言,具備所教學科的專業(yè)知識,教育學、心理學的實踐能力,以及相應學科的教師資格證,是一名教師從教的基本條件。但是,在教師崗位中,所教非所學的情況突出。比如,一名學習金融專業(yè)的學生,本專業(yè)就業(yè)無望,于是考取了初中語文的教師資格證,并考入教師編制。此類所學專業(yè)與教學崗位學科不統(tǒng)一的現(xiàn)象極其普遍,這些教師有的需要數(shù)年時間的磨合,才能達到教學崗位的能力要求。但數(shù)年間很多孩子因為這種制度缺陷影響他們學科的持續(xù)性學習,甚至影響其終身的學科興趣與職業(yè)選擇。這種隱藏的教育傷害是當下教師教育的硬傷。可見,教師教育作為教師隊伍建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各級管理者應該從教師隊伍建設的頂層設計高度,在教師的入口、培養(yǎng)、使用、管理四大環(huán)節(jié)中考慮教師培養(yǎng)與隊伍建設。
從“教師培訓”到“教師教育”是我國教師工作發(fā)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從教育大國發(fā)展到教育強國的必然要求。但要從30多年的培訓觀念中突破出來,站在教師終身發(fā)展、服務教育發(fā)展、承擔立德樹人教育目標的角度,重新審視教師教育工作,則需要一種取舍果敢、勇于擔當?shù)穆殬I(yè)勇氣與使命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