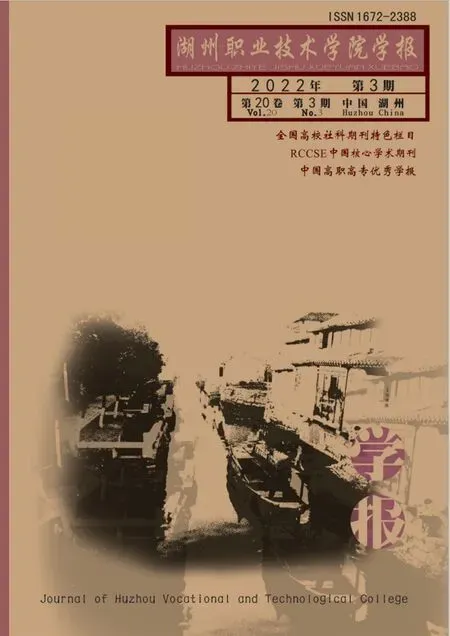薇拉·凱瑟《一個(gè)迷途的女人》空間敘事分析
徐 明 麗
(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 外語與商務(wù)學(xué)院, 江蘇 連云港 222006))
《一個(gè)迷途的女人》是薇拉·凱瑟(Willa Cather)于1923年發(fā)表的一部小說。她此前的作品《我的安東妮亞》奠定了她在美國文壇的地位,而《我們中的一員》在助她榮膺普利策文學(xué)獎(jiǎng)的同時(shí),也給她招來了多種批評(píng)聲音。《一個(gè)迷途的女人》發(fā)表后,批評(píng)家們頗感欣慰,認(rèn)為凱瑟終于將寫作中心又轉(zhuǎn)回到自己擅長的題材上來了,并認(rèn)為這是一部“沒有瑕疵的杰作”[1]。凱瑟對(duì)于拓荒題材早已駕輕就熟。但是,與以往的拓荒頌歌不同,《一個(gè)迷途的女人》被認(rèn)為是美國拓荒時(shí)代的最后一首挽歌。
《一個(gè)迷途的女人》通過美國西部小鎮(zhèn)青年尼爾的視角,講述了西部拓荒者福瑞斯特上尉破產(chǎn)沒落后,他的年輕美麗的太太瑪麗恩·福瑞斯特背離了拓荒人的為人處世原則,認(rèn)同了坐享西部開發(fā)成果的新興資產(chǎn)階級(jí)(如艾維·彼得斯之流)的價(jià)值觀,走上了物質(zhì)主義和拜金主義迷途的故事。小說篇幅相對(duì)簡短,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第一部有九個(gè)章節(jié),故事時(shí)間延續(xù)了九年,敘述主人公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以上尉在丹佛破產(chǎn)回到甜水鎮(zhèn)告一段落;第二部也有九個(gè)章節(jié),同樣由代表性事件組成,以瑪麗恩每況愈下的生活為主線,完成了小說敘事和對(duì)故事人物的刻畫。
薇拉·凱瑟曾說,世界在1922年的時(shí)候一分為二了。她本人多次聲明,無意對(duì)福瑞斯特太太進(jìn)行道德上的譴責(zé)。福瑞斯特太太的原型是紅云鎮(zhèn)創(chuàng)始人,內(nèi)布拉斯加州前州長塞拉斯·加伯的妻子。她的優(yōu)雅和活潑給少女凱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凱瑟對(duì)加伯一家懷有溫暖美好的回憶,她力圖恰如其分地將真實(shí)的“福瑞斯特太太”刻畫并展示出來。這種刻畫本身就是對(duì)一個(gè)時(shí)代的描摹。她創(chuàng)作《一個(gè)迷途的女人》時(shí),像福瑞斯特上尉這樣的拓荒者們已垂垂老矣,主宰社會(huì)的是艾維·彼得斯之流的新興資產(chǎn)階級(jí)。整個(gè)社會(huì)將金錢作為衡量成功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物質(zhì)主義、金錢主義甚囂塵上,虛榮攀比之風(fēng)大行其道,拓荒精神日漸衰微,拓荒者的光輝幾近消失。《一個(gè)迷途的女人》代表著凱瑟的創(chuàng)作主題由“精神力量勝過物質(zhì)力量與自然力量”轉(zhuǎn)為“物質(zhì)力量、金錢力量可以戰(zhàn)勝任何崇高理想和偉大精神”。正如哈羅德·布魯姆所說,這部小說“標(biāo)志著以天真、優(yōu)雅、充滿希望為核心的美國夢(mèng)的失敗”[2]2。
本文擬從空間理論的視角,解析小說中的地理空間、社會(huì)空間和意象空間。通過分析小說中的人物角色身份來探析其人格特征,通過解析人物擺脫困境的努力與嘗試,來探究時(shí)代更迭中人物的選擇,通過小說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意象,來闡釋意象空間對(duì)敘事的有效拓展。
一、地理空間:構(gòu)建角色身份
貫穿凱瑟小說的地理空間——西部大草原的小鎮(zhèn)和鄉(xiāng)村,大多是作為人物“感覺—體驗(yàn)”的地理背景出現(xiàn)在主人公的回憶中。凱瑟本人有著豐富的空間經(jīng)驗(yàn):兒童時(shí)期移居紅云鎮(zhèn),青年時(shí)期在林肯市上大學(xué),畢業(yè)后到匹茲堡工作,最后移居紐約,其中,童年時(shí)期在紅云鎮(zhèn)的經(jīng)歷對(duì)她影響至深。《一個(gè)迷途的女人》以甜水鎮(zhèn)作為背景空間,因?yàn)檫@里既是凱瑟熟悉的西部小鎮(zhèn),又能最直觀地反映拓荒時(shí)代的歷史變遷。凱瑟未對(duì)甜水鎮(zhèn)做整體性的描述,只用了一句頗為傳神的描寫一帶而過:“三四十年前,勃林頓鐵路沿線有不少灰暗的小鎮(zhèn),這些鎮(zhèn)現(xiàn)在是越發(fā)灰暗了。”[3]265
這一句用的是傳統(tǒng)的全知敘述,力圖客觀地概括甜水鎮(zhèn)的全貌。甜水鎮(zhèn)作為一個(gè)空間,規(guī)模不大,但鞋店、裁縫鋪、雜貨鋪等應(yīng)有盡有,旅館、租車行、法律事務(wù)所等也一應(yīng)俱全。小鎮(zhèn)的基調(diào)是“灰暗”,它的發(fā)展得益于鐵路的新興。后來,隨著鐵路行業(yè)的不景氣,再加上農(nóng)業(yè)的連年歉收,人們紛紛離開。因此,失去活力的小鎮(zhèn)顯得更加“灰暗”。這也寓意著整個(gè)拓荒時(shí)代由盛轉(zhuǎn)衰。但是,在福瑞斯特上尉眼里,小鎮(zhèn)所在的草原地區(qū)卻是風(fēng)光無限:“天天都是好天氣,可以打獵,有許多羚羊和野牛,天空一望無際,陽光普照,草原也無邊無垠,青草隨風(fēng)蕩漾,長長的大湖,水流清澈,開遍了黃色的花朵,野牛換季遷移的時(shí)候到這里來喝水、洗澡,在水里翻滾。”[3]284
福瑞斯特上尉是拓荒者中的佼佼者。他身材高大,做事果敢,從部隊(duì)退役后,做過長途貨車司機(jī)、鐵路承包商以及銀行家,從看到甜水鎮(zhèn)的第一眼起,便對(duì)它念念不忘。正如段義孚在《戀地情結(jié)》中所說:“外來者本質(zhì)上是從審美的角度去評(píng)價(jià)環(huán)境的,是一種置身于世外的視角。世外人看重的是外在,其評(píng)價(jià)依據(jù)是一般意義上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4]94在上尉看來,鄉(xiāng)野不是不毛之地,而是處處彰顯著美與活力。“他恰恰喜歡小河這樣曲曲彎彎地流過草地,兩岸還有薄荷、節(jié)連節(jié)的草和閃閃發(fā)亮的柳樹。”[3]267他拒絕抽干沼澤地里的水改種莊稼,嚴(yán)禁在林子里打鳥打獵。對(duì)于大草原,對(duì)于甜水鎮(zhèn),對(duì)于被稱為“福瑞斯特之家”的土地及其周邊地區(qū),他發(fā)自內(nèi)心地?zé)釔邸K麑?duì)工作伙伴真誠相待,寧愿自己破產(chǎn)也要維護(hù)銀行儲(chǔ)戶的利益。他是老一輩拓荒者的杰出代表,是凱瑟謳歌和贊美的對(duì)象。
作為拓荒者的仰慕者和追隨者,小鎮(zhèn)青年尼爾一直尋求拓荒時(shí)代的火熱與美好。他本應(yīng)該看到豐饒的大草原和宜居的甜水鎮(zhèn),然而,現(xiàn)實(shí)是:在他眼中,冬日寒冷蕭瑟的圖景是甜水鎮(zhèn)的常態(tài)。
“馬兒不用指示方向,沿行人不多的寒冷的大街駛?cè)ィ邕^冰凍的小河,跑上兩邊栽著楊樹的小道,奔向山上的別墅。晚霞映照在白雪皚皚的草原上。楊樹又高又直,在冬日蕭條的景色下顯得冷清而又肅穆……”[3]277
“雪下了三天三夜,三十英寸厚,刺骨的寒風(fēng)又把雪卷積成大雪堆……路上的積雪齊他的腰,有時(shí)候沒到他的腋窩。路邊的籬笆都被雪蓋住了。”[3]292
“陰沉的天色黑了下來……大風(fēng)夾著雪花吹過山與鎮(zhèn)之間寬闊的草地,房子周圍高大的楊樹發(fā)出嘎嘎吱吱的聲音。”[3]321
小說此時(shí)從尼爾的視角進(jìn)行描述。作為故事中的人物,他不像第三人稱敘述者那樣客觀,而是傾向于從自身感受出發(fā),對(duì)自己所觀察的對(duì)象寄予同情或表現(xiàn)出其他情感[5]217。這個(gè)西部小鎮(zhèn)對(duì)于尼爾來說,粗糲單調(diào),缺乏溫度。在晚間,尼爾出門拜訪福瑞斯特上尉一家,感受到的是冰凍的道路,死寂的街道。尼爾對(duì)“福瑞斯特之家”無比依戀。這種依戀并非出于要“守護(hù)”優(yōu)雅、迷人的瑪麗恩,而是出于對(duì)上尉等老一輩拓荒者的敬佩。他試圖親近僅存余輝的拓荒時(shí)代。他認(rèn)為,瑪麗恩應(yīng)該無條件地對(duì)上尉忠心耿耿。因此,當(dāng)他發(fā)現(xiàn)瑪麗恩違背了這一設(shè)定時(shí),他對(duì)瑪麗恩的“著迷”立刻轉(zhuǎn)化成了鄙視和厭惡。因?yàn)楸说盟箤?duì)上尉缺乏起碼的尊敬,他愈加厭惡彼得斯。他趕走闖入上尉家聒噪的小鎮(zhèn)婦女,維護(hù)了上尉的尊嚴(yán)。他休學(xué)一年貼身照顧上尉,讓上尉得以在平和安靜中離開人世。福瑞斯特上尉與尼爾亦父亦子,亦師亦友。上尉高潔的人品吸引了尼爾。尼爾對(duì)上尉的臨終護(hù)理是惋惜整個(gè)拓荒時(shí)代的隱喻。上尉的去世,預(yù)示著整個(gè)拓荒時(shí)代的終結(jié)——“這里的人們,這鄉(xiāng)間本身……將來是沒有什么值得他回來看望的。”[3]330沒有拓荒光環(huán)籠罩的甜水鎮(zhèn),更加“灰暗”了。
二、社會(huì)空間:擺脫人生困境
甜水鎮(zhèn)是一個(gè)代表美國歷史又反映典型美國文化的社會(huì)空間,固執(zhí)地蘊(yùn)藏著傳統(tǒng)的價(jià)值觀。它的社會(huì)維度是它的等級(jí)觀念:“在這些大草原的州里有兩種顯著的社會(huì)階層:一種是分得土地遷居來的和干手工活的,他們到這里來為的是謀生;另一種是銀行家和辦大農(nóng)場(chǎng)的紳士,他們從大西洋岸邊來,為的是投資,或者用他們常用的話說,為的是‘開發(fā)我們偉大的西部’。”[3]266
簡言之,甜水鎮(zhèn)居民分為兩類人:一是有產(chǎn)階級(jí),一是普通勞動(dòng)者。這兩類人群之間有著鮮明的界限,無論是小鎮(zhèn)居民,還是外來訪客,對(duì)此都熟諳于心并遵照?qǐng)?zhí)行。如拜訪“福瑞斯特之家”的人,都是銀行家、鐵路負(fù)責(zé)人、醫(yī)生、法官等,其他小鎮(zhèn)居民雖然對(duì)福家好奇萬分,但從不涉足,就連十來歲的孩子們,也知道福瑞斯特太太屬于社會(huì)上“幸運(yùn)的特權(quán)階級(jí)”。恪守階層劃分已成為甜水鎮(zhèn)人的一種不自覺的行為,他們以此處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孩子們慫恿尼爾向福瑞斯特太太懇求,要她允許他們進(jìn)入沼澤地野餐,只因?yàn)槟釥柕木司耸欠ü佟D釥枏臉渖纤は聛砗蟊凰腿敫H鹚固靥呐P室,其他孩子也只是謙卑地待在廚房外面等候。在小鎮(zhèn)空間里,福瑞斯特之家是獨(dú)特的私人領(lǐng)地,代表著難以跨越的階層鴻溝。
這種局面在上尉第二次中風(fēng)的時(shí)候被打破。此時(shí),上尉經(jīng)濟(jì)拮據(jù),甚至開始入不敷出。在甜水這樣的小鎮(zhèn),人們按部就班地生活,總體上人們的生活是單調(diào)平淡的。凱瑟曾在《小鎮(zhèn)生活》里談到,西部小鎮(zhèn)人民生活的貧乏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不是上帝、鐵路或天氣與他們作對(duì)[6]85。為了在單調(diào)的生活里尋找一些樂趣,人們熱衷于說別人家的閑話,樂此不疲地將各種消息散播出去。上尉第二次中風(fēng)以后,鎮(zhèn)上的主婦們以照看上尉為名,公然出入福家,翻遍屋子的每一個(gè)角落,驀然發(fā)現(xiàn)福家既不神秘也不高貴,到處都是過時(shí)的家具和老朽的陳設(shè),并公然詬病瑪麗恩酗酒無用,不守婦德。至于上尉能否盡快恢復(fù)健康,以及瑪麗恩如何重整旗鼓,她們并不關(guān)心。在熱情助人的表面現(xiàn)象之下,小鎮(zhèn)居民實(shí)則自私又冷漠。“為什么那些使得生活一帆風(fēng)順、多少能彌補(bǔ)其中的更大失望的起碼禮節(jié),在小鎮(zhèn)里就那么難做到,比石頭里擠出血還難?”[6]87這樣的社會(huì)空間令人憤懣、窒息,無論是少女時(shí)代的凱瑟還是少年尼爾,最終都選擇了逃離。
小鎮(zhèn)婦女讓瑪麗恩原本私密的私人空間暴露在公眾眼光之下。以前的老朋友們認(rèn)為她“誤入歧途”“背信棄義”。瑪麗恩從人人仰視的迷人貴婦變成被人鄙視的風(fēng)流寡婦。人們對(duì)于瑪麗恩的情人艾林格卻寬容很多。瑪麗恩與艾林格保持通信聯(lián)系,時(shí)而秘密幽會(huì),但艾林格最后娶了“可以做他女兒”的康斯坦斯,徹底拋棄了瑪麗恩。瑪麗恩被斥責(zé)為蕩婦,但人們卻只記得艾林格是個(gè)孝子,認(rèn)為他是“大好人”,即使他年輕時(shí)放浪不羈,“在光天化日之下帶妓女騎馬”。可見,無論是相對(duì)閉塞狹小的甜水鎮(zhèn)還是丹佛等大城市,人們對(duì)男性寬容、女性苛刻已經(jīng)成為社會(huì)風(fēng)氣。上尉破產(chǎn)后,出身富裕之家、一直以來備受愛護(hù)的瑪麗恩不再享有衣食無憂的生活。但是,她并沒有指責(zé)上尉,在接受現(xiàn)實(shí)的同時(shí),不忘告誡尼爾:“尼爾,你得抓緊,做一番事業(yè)……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開始就得看準(zhǔn)這一點(diǎn),要好好對(duì)付這個(gè)問題,不要像我們?cè)S多人一樣,弄到最后出洋相。”[3]308
瑪麗恩意識(shí)到金錢的重要性,要生存下去就要順應(yīng)社會(huì)變革,這樣才能擺脫人生困境。她將這一人生感悟傳授給尼爾,希望尼爾能有一個(gè)更好的未來。瑪麗恩清楚地知道,正視現(xiàn)實(shí)才能走出困境。面對(duì)流言蜚語,瑪麗恩不屑一顧,我行我素。她把草地租給彼得斯。尼爾曾問瑪麗恩是否懷念沼澤地,瑪麗恩回答道:“不太懷念。我永遠(yuǎn)沒有工夫到那里去了,再說,我們也需要這筆租金。”[3]308為了增加收入,她把上尉的業(yè)務(wù)都轉(zhuǎn)移給彼得斯,她因此遭到“老朋友們”的批評(píng)。上尉去世后,她和彼得斯繼續(xù)來往,并把錢財(cái)交給他打理。即便這樣,瑪麗恩的狀況仍很糟糕。直到她將房產(chǎn)賣給彼得斯,離開甜水鎮(zhèn),再婚嫁給一個(gè)富有的英國人,才走出人生困境,并且一直到死都受到很好的照料。憑借著不屈不撓的精神,瑪麗恩重回有產(chǎn)階級(jí),重新成為“幸運(yùn)的特權(quán)階級(jí)”。
在尼爾看來,艾維·彼得斯是“下人”,是齷齪下流的代名詞,不配和瑪麗恩平起平坐,更不用說與上尉相提并論。實(shí)際上,彼得斯處于甜水鎮(zhèn)的“謀生”階層,但他的理想和行為都是爬向甜水鎮(zhèn)等級(jí)結(jié)構(gòu)的上層。他甫一出場(chǎng)便聲明,自己的“地位”和瑪麗恩“一樣高”。這一言論讓恪守階層劃分的在場(chǎng)聽眾覺得“荒唐可笑”。彼得斯想從處于“謀生”階層的普通勞動(dòng)者躍升為有產(chǎn)階層、“投資”階層的理想,是他各種行為的動(dòng)力。而他抬高自己社會(huì)地位的方法,是踐踏曾經(jīng)的有產(chǎn)階級(jí)如上尉等人的驕傲和尊嚴(yán)。如,他租下草地后馬上將上尉喜歡的沼澤地改為農(nóng)田,廢除打獵禁令,從波梅洛埃法官手里搶業(yè)務(wù)等等。艾維·彼得斯代表了一類人:他們沒有拓荒情懷,只熱衷于斂財(cái),無視自然生態(tài)、社會(huì)規(guī)則甚至法律法規(guī),坐享老一輩拓荒者的財(cái)富積累,最終,實(shí)現(xiàn)了階級(jí)跨越,一躍成為主宰操控社會(huì)的新興資產(chǎn)階級(jí)。
三、意象空間:拓展敘事意蘊(yùn)
凱瑟在《一個(gè)迷途的女人》中描寫了豐富多彩的意象,如樹林中的啄木鳥,玫瑰花園中的日晷和上尉家的客廳,這些意象反復(fù)出現(xiàn),隱喻人物的性格和命運(yùn),推動(dòng)故事情節(jié)向前發(fā)展。同時(shí),這些意象有專屬于自己的空間,勾畫出與描繪一樣的視覺效果,并突破意象本身單一、孤立的形象,營造出與周圍空間或和諧統(tǒng)一、或沖突對(duì)抗的意象空間。
故事開篇,尼爾和鎮(zhèn)上的幾個(gè)孩子正在小樹林里玩耍和野餐。小樹林在上尉家房子的后面,是坐火車進(jìn)入甜水鎮(zhèn)的人第一眼能看到的風(fēng)景。樹林里野花盛開,蜂飛蝶舞,啄木鳥、野鴨子隨處可見。孩子們吃著福瑞斯特太太送來的甜餅,非常快樂,直到被孩子們稱為“毒”艾維的艾維·彼得斯出現(xiàn)。艾維·彼得斯用鐵彈弓打下一只啄木鳥,并殘忍地用小刀把啄木鳥的眼睛挖了出來。然后,任由小鳥在林子里左右亂撞,在陽光下打轉(zhuǎn),慌亂而又絕望。這讓原本清涼靜謐的樹林變成了危險(xiǎn)與邪惡的所在。在這里,失去方向感的小鳥象征著瑪麗恩。瑪麗恩漂亮、迷人,善于交際,極富魅力。她在福瑞斯特上尉破產(chǎn)后不知所措,“誤入歧途”。恰如被剜去雙眼的啄木鳥最終躲進(jìn)了自己的洞里一樣,瑪麗恩沒有被動(dòng)地任憑命運(yùn)擺布,沒有放棄對(duì)生命的尊重與渴望。她還舉辦了一次宴會(huì),希望為鎮(zhèn)上的年輕人提供一個(gè)“文明的去處”,并教會(huì)他們做文明人。雖然宴會(huì)慘淡收?qǐng)觯硖幠婢车默旣惗鲄s展示了她不屈不撓,在現(xiàn)狀中掙扎,對(duì)時(shí)代反抗,不會(huì)輕易被生活打敗的一面。從“迷人”到“迷途”再重回“迷人”,瑪麗恩完成了自我蛻變。日晷是小說中的一個(gè)重要意象,它出現(xiàn)在被福瑞斯特上尉稱為“玫瑰花園”的地方。玫瑰花園屬于上尉的私人空間,他有時(shí)可以連續(xù)幾小時(shí)坐在那里看日晷 。對(duì)于上尉來說,日晷記錄的不是時(shí)間的流逝,而是時(shí)代的漸漸消亡。福瑞斯特上尉是探險(xiǎn)家,也是征服者,有著屬于拓荒者的驕傲與自豪——每個(gè)拓荒者的血液里都流淌著自豪感。“在美國大平原邊緣地帶的農(nóng)場(chǎng)上,農(nóng)民必須堅(jiān)持不懈地與干旱和沙塵暴抗?fàn)帯D切o法堅(jiān)持下來的人紛紛離開了,而留下來的人們則在心中產(chǎn)生了一份源于堅(jiān)守的自豪感。”[4]144這種自豪感是彼得斯之流無法體會(huì)到的。但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恰恰又是彼得斯這類唯利是圖、精明小氣的年輕一代摧毀撕碎了上尉這樣的老一輩拓荒者們的驕傲和尊嚴(yán)。福瑞斯特上尉參與了拓荒者的全盛時(shí)期,同樣也不幸見證了拓荒時(shí)代的黯然落幕。上尉代表了拓荒者們牢固不變的價(jià)值觀。然而,在時(shí)代變革和經(jīng)濟(jì)變革面前,他變得無奈又無助。可以說,終日坐在花園里看日晷的福瑞斯特上尉,已經(jīng)先于拓荒時(shí)代老去了[7]51-62。福瑞斯特上尉去世后,瑪麗恩提出將日晷呈放在上尉墓前作為墓碑,日晷因此被賦予了紀(jì)念性的意義——紀(jì)念所有曾經(jīng)火熱戰(zhàn)斗過的拓荒者們,以及漸行漸遠(yuǎn)的拓荒時(shí)代。
綜上,薇拉·凱瑟從來沒有因?yàn)檫h(yuǎn)離故土而在情感上背棄家鄉(xiāng),從而使其作品失去根基和給養(yǎng)。相反,她的拓荒主題從來沒有離開過西部,離開過讓她魂?duì)繅?mèng)縈的大草原。她的作品是想象世界和經(jīng)驗(yàn)世界的完美融合。在拓荒時(shí)代行將結(jié)束、拓荒精神日漸衰微之時(shí),凱瑟正視這一歷史趨勢(shì),沖破狹隘的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的束縛,拒絕悲觀地吟唱時(shí)代挽歌。她力圖在復(fù)雜的現(xiàn)代社會(huì)中弘揚(yáng)拓荒精神,勉勵(lì)人們將對(duì)拓荒時(shí)代的緬懷轉(zhuǎn)化為適應(yīng)社會(huì)變革的動(dòng)力,在時(shí)代更迭中走向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