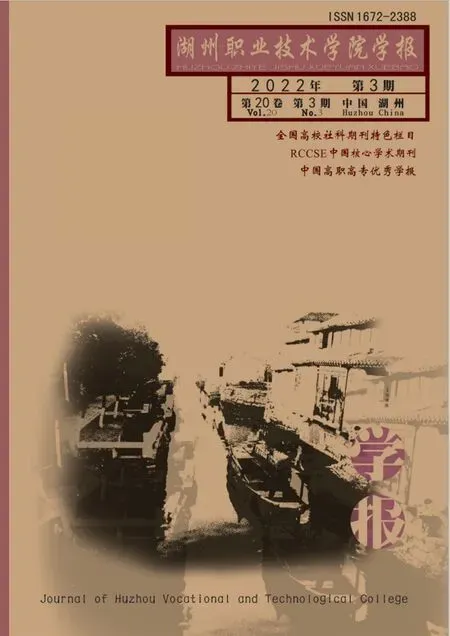論波德萊爾的藝術批評原則
黃 邁 , 禹志云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年)是法國19世紀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同時也被美國文學批評家韋勒克(René Wellek)評價為19世紀最偉大的評論家之一。他將詩人的才華與藝術家的敏銳洞察力運用于藝術批評之中,把握住時代的脈搏,在浪漫主義美學的基礎上提出了審美現代性的維度,為現代藝術批評奠定了美學基礎。
在《現代生活的畫家》中,波德萊爾給“現代性”下了一個著名的定義:“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1]19這一定義充滿了辯證的哲理,用對立統一的觀點,肯定了美和藝術既包含暫時的、相對的、變化的因素,又有永恒的、普遍的、不變的因素。正如波德萊爾自己所言:“美永遠是、必然是一種雙重的構成……構成美的一種成分是永恒的,不變的,其多少極難加以確定;另一種成分是相對的、暫時的,可以說它是時代、風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種,或是兼容并蓄……沒有它,第一種成分將是不能消化和不能品評的,將不能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1]4-5這段話也是在告訴我們:永恒的、絕對的美必須由暫時的、相對的、時代性的美來表現,當下的過渡性與偶然性中包含著永恒和不變。正是基于此,波德萊爾認為,每個時代都有屬于自己時代的美,這種時代性的美能體現出永恒的美。所以,藝術要“捕捉審美現代性,極力發掘現代社會特有的現實的美、瞬間的美、獨特的美”[2]52,要通過現代性的美來發掘永恒的美。這便是波德萊爾對于審美現代性的理解(1)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波德萊爾雖然主張表現現代社會的美,但并沒有全盤肯定社會的現代化,相反,他還對現代化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持反思與批判的態度。。圍繞這一理解,他提出了自己的藝術批評理論,形成了自己的藝術批評原則,并將其運用于自己的藝術批評實踐之中。
一、波德萊爾藝術批評的黨派性原則
在批評立場與批評標準方面,波德萊爾秉持著黨派性原則。在19世紀的法國評論界,浪漫派在擺脫了古典主義推崇的客觀法則(2)例如三一律、人物形象塑造類型化、理性克制情欲等藝術創作法則。之后,不再相信藝術批評有一個永恒的客觀標準。他們轉向了另一個極端,為追求“公正”采用折中主義的評論,使藝術批評變為沒有任何共同標準的爭論,陷入了主觀主義的泥沼。
波德萊爾和浪漫派一樣,不相信藝術批評存在著一個永恒不變的客觀標準,但他也絕不認為藝術批評是沒有任何標準的主觀爭論。他覺得藝術批評的立場和標準是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的,一個時代可以有一個時代的臨時的藝術批評標準。這一觀點正是來自他對于審美現代性的理解,既然藝術的一半是永恒和不變,一半是變化和短暫,藝術是永恒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是絕對與相對的統一,那么藝術批評就自然可以有臨時的、相對的標準。沈語冰教授在《20世紀藝術批評》的導論中探討波德萊爾的批評理論時就指出:波德萊爾認為,“批評已經不再有一種永遠的合理性基礎,卻可以有一種臨時的合理性基礎。”[3]28
也就是說,波德萊爾認為,藝術批評沒有永恒的批評標準,但不能沒有批評立場和標準。他在《批評有什么用?》一文中指出:“公正的批評,是有其存在理由的批評,應該是有所偏袒的,富于激情的,帶有政治性的。也就是說,這種批評是根據一種排他性的觀點做出的,而這種觀點又能打開最廣闊的視野。”[4]103這段話,集中體現了波德萊爾藝術批評的黨派性原則。這一原則,具體體現在排他性和政治性兩個方面。
(一)排他性——藝術批評要有所側重
波德萊爾藝術批評的黨派性原則,首先體現為鮮明的排他性。從波德萊爾的藝術批評實踐中可以看出,波德萊爾對于自己喜愛的藝術家從來都是不遺余力地褒揚,而對于不符合自己的審美理想與藝術批評標準的藝術家,即使這些藝術家在當時獲得了極高的聲譽,他還是持堅定的批判態度。
波德萊爾對眾多的藝術家都有過藝術評論。在同時代所有的畫家里面,德拉克洛瓦(Ferdinand Victor Eugène Delacroix)的藝術風格最符合他的藝術批評標準。因為,在波德萊爾看來,美與藝術是具有時代性的,所以,藝術創作也要符合時代的藝術標準。在波德萊爾所處的時代,“浪漫主義是美的最新進、最現時的表現”[4]106。因而,波德萊爾以浪漫主義作為時代的藝術批評標準。與新古典主義強調理性相對立,浪漫主義強調感性,主張藝術要富于創造力,要張揚個性,要充滿想象力。德拉克洛瓦的藝術作品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波德萊爾在對其進行藝術評論時開篇就說道:“浪漫主義和色彩把我直接引向歐仁·德拉克洛瓦。”[4]115德拉克洛瓦的畫作也確實如波德萊爾所分析那般,充滿了瑰麗的想象力、豐富的創造力以及深沉而又憂郁的激情,《但丁之舟》《自由引導人民》便是最好的印證。
正因如此,波德萊爾非常推崇德拉克洛瓦,根據自己黨派性的藝術批評原則,熱情地肯定了德拉克洛瓦的藝術創作,并駁斥了其他批評者對德拉克洛瓦的攻擊。他指出,德拉克洛瓦在細節上的缺點,對于他在浪漫主義藝術上的偉大成就來說是瑕不掩瑜的。波德萊爾還在《燈塔》一詩中,將德拉克洛瓦與拉斐爾、米開朗琪羅、倫勃朗、魯本斯等偉大的畫家并列在一起,特意用一個小節來描述他的藝術風格。
除了熱情贊揚像德拉克洛瓦這樣符合自己藝術批評標準的藝術家外,波德萊爾還批判了很多沉迷于再現和模仿,缺乏藝術創作想象力和創造力的藝術家,即使這些藝術家在當時備受贊譽。例如新古典主義畫家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對于波德萊爾而言安格爾只是對古典人像的完美臨摹,他們只是復制者而已”[5]113。
波德萊爾在《論折中主義和懷疑》一文中寫道:“一件從排他性的觀點出發制作的作品,無論其缺點多么大,總是對與藝術家的性情相類似的性情具有一種巨大的魅力。”[6]277他之所以如此強調排他性,是因為他發現了藝術批評的規律:折中主義的藝術評論沒有明確的標準和原則,不能給藝術家任何有益的指導,終將會因為沒有方向而被歷史所遺忘,只有有所側重才能成就偉大的藝術批評。
(二)政治性——藝術批評要立場明確
波德萊爾藝術批評的黨派性原則,還體現在他的藝術批評是帶有政治性的。在《一八四六年的沙龍》的前言中,波德萊爾就明確地表示:這本書獻給“在數量和智力上都是多數”的資產者。這說明,波德萊爾的藝術批評是站在資產者的立場上的(3)這里需要指出:波德萊爾只是在藝術批評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因為相較于封建主義的古典藝術批評,他更傾向于資產階級的新的藝術批評。波德萊爾總體上的政治傾向是一種無政府主義。他反對封建勢力的復辟,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也有著尖銳的批判。這一點皮舒瓦和齊格勒所著的《波德萊爾傳》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了。。這就是波德萊爾藝術批評的政治性。
波德萊爾之所以強調藝術批評的政治性,并且站在資產者的立場上,是因為他已經意識到資產階級的強大力量,預感到資產階級將成為更加先進的社會治理者,將更能促進藝術的發展。而以“壟斷者”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已經腐朽,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著藝術的繁榮。波德萊爾對資產者們說:“你們在數量和智力上都是多數,因此,你們就是力量,這是理所當然的。”[6]212還對他們說:“你們是藝術的天然的朋友,因為你們由富有者和博學者組成。”[6]214在當時,代表社會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的確在努力地促進社會文化與藝術的發展。他們建立了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公共文化設施,讓原本上流社會和貴族們才能獲取的知識與藝術能夠面向所有的民眾開放。
波德萊爾不僅從藝術批評理論上主張藝術批評的政治性,也在藝術批評的實踐中遵循藝術批評的政治性原則。從《評〈悲慘世界〉》以及《對同代人的思考》等評論文章中,都可以看到波德萊爾的藝術批評在政治方面的黨派性原則。他在《評〈悲慘世界〉》這篇文章中,站在資產階級的藝術批評立場上,將《悲慘世界》中法國復辟政府的一個爪牙——警察沙威視為絕對的敵人。這不僅僅因為沙威為了維護腐朽的法律而陰魂不散地追捕冉阿讓,冷酷無情地將芳汀送進監獄,還可能因為沙威曾作為密探去共和派革命者的街壘中刺探情報,企圖扼殺革命。波德萊爾曾參加1848年法國革命的街壘戰,與革命者同處一個陣營。這樣的經歷讓他更加厭惡沙威這個人物形象。
雖然,波德萊爾并沒有非常鮮明的政治觀點,但是,在他的藝術批評中,讀者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這種傾向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偏袒,是一種對數量和智力上都是多數的資產階級的偏袒。這種偏袒不僅是一種單純的喜好,也是一種在藝術批評中謀求更長久發展的表現。
二、波德萊爾藝術批評的詩意性原則
在批評實踐方面,波德萊爾主張批評的詩意性原則。波德萊爾在《一八四六年的沙龍》中寫道:“最好的批評是那種既有趣又有詩意的批評,而不是那種冷冰冰的、代數式的批評,以解釋一切為名,既沒有恨,也沒有愛,故意把感情的流露都剝奪凈盡。”[6]215波德萊爾強調批評的詩意性,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自己就是藝術創作的主體,在藝術批評中常常會以藝術家的視角看待問題。詩人的才華讓他在討論、鑒別、評判藝術作品或藝術現象時,從批評語言到批評方法都充滿詩意性。另一方面,在審美現代性思想的指導下,波德萊爾認為“浪漫主義是美最新進、最現時的表現”。浪漫主義強調自由,強調情感和想象的巨大作用。這導致他不僅要求藝術創作必須充滿情感和想象力,還要求藝術批評應該富有激情和詩意。
波德萊爾反對那種針對藝術作品的創作方法進行枯燥分析的藝術批評。在他的批判實踐中,秉持詩意性原則,對藝術作品進行富有激情的評論。他的藝術批評不僅是一個批評家對一部藝術作品的品鑒與評點,還是一個藝術家與另一個藝術家的心靈碰撞。具體而言,波德萊爾藝術批評的詩意性原則體現在情感的流露和詩意的隱喻這兩個方面。
(一)情感的流露——藝術批評要富于激情
波德萊爾藝術批評的詩意性原則,首先體現在他的藝術批評帶著許多情感的流露。這種情感的流露,在波德萊爾的藝術批評實踐中是處處可見的。《論〈包法利夫人〉》一文就充滿了強烈的情感色彩。當時,福樓拜(Gustave Flauber)因為出版《包法利夫人》而被起訴,理由是破壞了公序良俗。最終,經過律師的努力,福樓拜打贏了官司。波德萊爾的這篇文章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出來的。波德萊爾在文章中充滿激情地痛斥了那些指責福樓拜的批評家們。那些批評家認為,《包法利夫人》一書沒有一個人物是能夠代表道德,說出作者良心的。還認為,作品的主人公包法利夫人愛瑪太過淫蕩、傷風敗俗。波德萊爾直言他們荒謬至極,提出了與之針鋒相對的看法:“作品的邏輯足以表達道德的要求,得出結論是讀者的事。”[6]57換言之,波德萊爾認為,文學作品不是道德勸誡書,無須在作品中樹立一個道德模范,明智的讀者是懂得分辨是非的。通讀《論〈包法利夫人〉》,我們可以發現:波德萊爾的情感流露從來都是有增無減,從最開始為福樓拜勝訴而喜悅,到中間為批評家們的詆毀而氣憤,到最后贊揚書中的愛瑪,始終都滿懷激情。這種激情讓整篇文章變得生動,讀起來有一種快感。而且,波德萊爾的藝術性批評語言充滿了感染力,讓這種激情的表達更富有詩意。
此外,在《論幾位色彩家》《論埃德加·愛倫·坡的生平及其作品》以及《評〈悲慘世界〉》等一些評論文章中,波德萊爾的激情與情感流露都十分明顯。因為,波德萊爾不僅作為批評家介紹著藝術家們的作品與風格,而且作為詩人與藝術家們進行著心靈的溝通。尤其是《論埃德加·愛倫·坡的生平及其作品》這篇文章,波德萊爾作為批評主體的欣賞與喜愛之情溢于言表。他將愛倫·坡(Edgar Allan Poe)視作創造美的天才,稱贊愛倫·坡的詩精雕細刻,透明、規則如水晶的首飾;稱贊愛倫·坡的藝術風格純粹而怪誕,緊湊如盔甲的鎖扣,自得而細密[6]187。可以說,波德萊爾與愛倫·坡形成了強烈的共鳴。他對愛倫·坡的藝術批評是這兩位天才詩人思想碰撞形成的火花。
(二)詩意的隱喻——藝術批評要有形象性
波德萊爾藝術批評的詩意性原則,還體現在他的藝術批評有許多巧妙的隱喻,批評語言形象生動,給人以藝術的美感。波德萊爾的研究者金心亦就曾指出:“波德萊爾除了是一位藝術批評家還是一位詩人,因此,詩意的隱喻在他的批評寫作中比比皆是,這是他批評寫作修辭的一大特點。”[7]30例如,在《論幾位色彩家》一文中,為了向讀者說明德剛先生繪畫作品帶給人的強烈刺激和吸引力,波德萊爾用“最開胃的菜肴”和“加了最辛辣的調料的食品”,來說明德剛畫作帶給欣賞者的那種野性的快感。本來所有形容詞都難以描述清楚的風格與美感,被波德萊爾輕松地表現了出來,讓讀者有了最切身的體驗。同樣的,還有一個關于愛倫·坡的例子,波德萊爾在《再論埃得加·愛倫·坡》中寫道:“我們經常從那些整夜守著古典美學神圣大門的沒有謎語的斯芬克斯們口中聽到這種空話,并且還伴著一種夸張的哈欠。”[6]190這處批評用“沒有謎語的斯芬克斯們”來隱喻保守的古典主義者們,立刻讓人聯想到固執又乏味的老生常談。這樣隱喻式的評論形象而又精準,讓讀者通過文字就能感受到古典主義者們毫無性情、無視自然、充滿學究氣而顯得迂腐的風格。
除此之外,波德萊爾還曾說:“對于一幅畫的評述不妨是一首十四行詩或一首哀歌。”[6]215-216在他的詩集《惡之花》中,確實有一首藝術評論式的詩歌,它就是我們之前提到過的《燈塔》。波德萊爾在這首詩中使用極具形象性的詩句,分別概括了八位畫家畫作的美學風格。其中,對于德拉克洛瓦的評述是:
“德拉克洛瓦,墮落天使出沒的血湖,
掩映在常綠的樅樹的陰影里。
在憂郁的天空下,吹奏樂隊過處,
奇怪的樂音像韋伯的悶塞的嘆氣。”[8]28
后來,波德萊爾在《論1855年萬國博覽會(美術部分)》中解釋了這節詩歌:其中的“墮落天使出現的血湖”是隱喻德拉克洛瓦畫作中的鮮艷紅色,而“常綠的樅樹”是隱喻畫作中作為紅色陪襯色的綠色,“奇怪的樂音”是隱喻與韋伯的浪漫主義音樂風格相和諧的浪漫主義繪畫風格。總而言之,波德萊爾以詩歌式的隱喻評述了德拉克洛瓦獨特的藝術風格。這種形式讓藝術評論變得形象又富于詩意。
從波德萊爾的藝術批評實踐以及藝術創作實踐中,我們都可以看出,他的藝術評論充滿了形象性的隱喻。這正是他藝術批評詩意性原則的又一個表現。
三、結 語
在西方藝術批評史中,波德萊爾的藝術批評理論和藝術批評實踐是獨樹一幟的存在。他的藝術批評原則直到今天仍然極具啟發性。在藝術批評愈加繁榮且越來越商業化的今天,受到市場經濟弊端的影響,許多藝術批評都有商業炒作的嫌疑,為了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喪失了原則和立場。面對這一傾向,堅持藝術批評的黨派性原則,將幫助我們“堅守文藝審美和陶冶情操的底線,同時使用好資本運作的商業效應”[9]35,從而讓文藝批評的藝術屬性與商業屬性達到平衡,構建起更加合理的藝術批評的價值體系。此外,在藝術批評中,也要防范過度學術化,表達越來越艱深難懂的現象。遵循藝術批評的詩意性原則,一方面有利于創作者與讀者更好地接受批評者的觀點,另一方面也能讓藝術批評變得更加生動透徹,避免文藝批評的枯燥乏味與千篇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