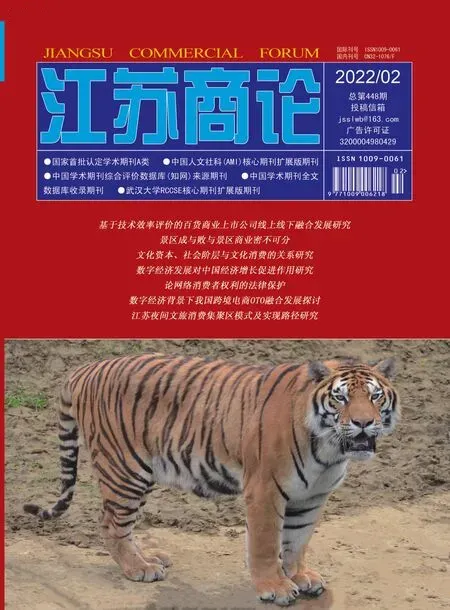數字經濟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研究
——基于中國省域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王彥軍,孫 軍
(江蘇海洋大學 商學院,江蘇 連云港 222005)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由高速度轉變為高質量發展階段,在人民需求與經濟發展方向的共同作用下,數字經濟應運而生,成為國家GDP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經濟助推經濟增長這一事實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驗證,主要表現為疫情期間數字經濟為線下實體經濟正常運行提供了保障。比如封閉期間的線下消費大部分轉換成線上消費,有效緩解了需求緊縮危機;線上協同辦公、網絡教育等也在疫情的刺激下開始了全新變革,隨后可能會成為人們的慣性需求;而像無人超市、服務型機器人等“無人與人接觸”數字服務型場景的新業態也由于疫情的推動而快速發展。可見,本次疫情倒逼數字經濟進行飛躍式的發展,傳統行業與數字技術融合加速,激發出多種新模式、新業態。消費者對數字消費慣性加大,對數字消費方式更加認可和追隨。疫情后,各行各業都開始了顛覆性的數字化變革,可以說,后疫情時代,數字經濟將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能,大力推進數字化革命是國家經濟復蘇以及高效高質發展的重要一環。
一、研究回顧
當前學者主要從三個層面對數字經濟進行研究,分別是從國家層面和地區層面出發探究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以及從產業層面出發探究數字經濟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
第一個層面上。白謹豪(2020)、韓晶(2020)牛文科(2020)等人對當前疫情時期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情況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時也對后疫情時期數字經濟發展建言獻策,在培育科技創新能力、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產業深度融合、加強政策支撐等方面幾人不謀而合。牛文科(2020)還強調了生產要素質量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李艷艷(2020)根據對近十年來美國數字經濟減輕美國次貸危機消極影響這一方面的情況,對中國數字經濟城鄉發展、網絡安全等方面的發展進行了分析,在政策規劃,創新機制以及政府效應等方面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出對比建議,有很強的借鑒效用。宋洋(2019)從經濟發展質量理論視角,從“外在表現”和“內生動力”兩個維度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在多個維度和多個層次上都會對經濟高質量發展起促進作用。張輝(2019)系統整理分析了數字經濟的基本內涵,并結合全球和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現狀,提出中國用戶規模以及政策優勢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開辟良好空間,也指出中國在數字經濟創新、數字人才等方面的欠缺,值得進一步探究。
第二個層面上,吳春華(2020)、金將軍(2020)、郭啟光(2020)等學者分別對山東、福建、內蒙古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進行綜合評估,并指出發展存在的問題。其中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創新驅動性不強、數字人才匱乏等方面與國家層面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基本相同。
第三個層面上,李英杰、韓平(2021)、陳曉東、楊曉霞(2021)等人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以及階段性特征,對產業數字化轉型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的積極影響予以充分肯定。基于研究結果提出構建現代產業體系,進一步優化經濟體系的建議。張艷萍、凌丹、劉慧嶺(2021),余姍、樊秀峰、蔣皓文(2021),何文斌(2020)等人采用實證分析模型論證了數字經濟發展與中國制造業發展存在線性相關關系,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了中國制造業發展得到檢驗,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有利于中國制造業躋身世界制造業高端領域。
通過對已有文獻進行梳理發現,對數字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比較豐富,但對各個要素影響力大小的研究只有較少數的學者進行實證比對,而且評定數字經濟發展測度與指標在現有理論研究中并沒有完全統一。基于此,本文采用實證分析法利用面板數據模型評定數字經濟各子要素發展對地區經濟發展影響力的大小,評定結果將對國家及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起到決策建議作用。
二、變量介紹與數據說明
(一)變量介紹
1.被解釋變量。本文被解釋變量是國民經濟,選取的代表性指標是人均地區生產總值(lnpgdp),其中為消除物價和通貨膨脹的影響,地區生產總值是以2013年GDP為基準進行平減后的實際數值,地區生產總值是最重要的衡量國家經濟發展的宏觀指標,黨的十九大將經濟總量或人均國民收入較2020年增長翻一番作為國家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可量化標準。同時,在繼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致力全面小康建設的基礎上,十九大對全面小康建設也提出了新要求,在民主、科教、文化、社會、人民等方面豐富了全面小康建設的內涵,國家當前以及未來較長時期內都將把民生問題作為國家發展問題的要義之一,基于此,本文選取人均實際GDP作為衡量區域經濟變化的指標。
2.解釋變量。據已有研究,衡量數字經濟發展規模的衡量標準沒有完全界定。黃文金、張海峰、葉少莉(2018),萬曉榆、羅焱卿、袁野(2019)等學者通過構建數字經濟評價模型DEEP,評價地方數字經濟的發展程度。本文對現有研究結果及數據的可獲得性兩方面進行綜合考慮,選取4個解釋變量,作為本文衡量數字經濟發展規模的研究變量:第一,基礎設施建設水平(lnpinf),選取地區人均擁有光纜電路長度為代表指標,光纜是數字信號傳送的物理媒介,用于傳送數據、視頻、語音等,是數字化建設過程中最基本的要求。第二,數字經濟與產業化融合水平(lnptcl),選取地區人均軟件收入量為代表指標,表示電子信息行業研究成果產業轉化的量化反應。第三,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水平(lnpeco),選取地區人均R&D經費投入為代表指標,研發經費投入直接反映某地區數字高科技發展水平。第四,數字人才需求水平(lnpedu),選取地區常住人口每百人中普通本專科擬招生人數為代表指標,這是政府等社會發展部門在對當前社會數字經濟發展狀況的有效評估后,對數字經濟型人才做出的需求預測的量化反應。
3.控制變量。本文主要研究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但是影響區域經濟變動的因素有很多,某地區房地產業、建筑業、進出口貿易等行業的發展也會影響地區整體經濟發展。為控制其他因素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本文選取區域房地產開發人均投資額(lnpest)、區域建筑業人均產值(lnpbui)、區域進出口人均值(lnptra)作為控制變量,具體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表
(二)數據來源與說明
限于數據可獲得性與完整性,本研究所涉及的數據均來源于2013—2019年《中國統計年鑒》與各地方統計年鑒,其中個別數據是根據二次計算所得,具體數據說明見表2。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計量模型構建與分析
(一)計量模型構建
根據對以往研究結果的整理以及本研究的數據特點,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基本數據模型如后:

其中,i表示1,2,3,···,n,表示個體數量為N個;t=1,2,3,···,n,表示時間為T年;rit表示控制變量集合,μi表示固定效應,λt表示時間效應,εit表示殘差項。
(二)變量的穩定性檢驗
1.單位根檢驗。為保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避免偽回歸,進行平穩性檢驗。在進行一階差分后,結果顯示變量P值均在5%水平下顯著,能過平穩性檢驗,見表3。

表3 HT單位根檢驗結果
2.協整性檢驗。以上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變量均滿足一階單整,滿足協整性檢驗條件。可以采用KAO檢驗以確認各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對原值和一階差分值全部進行KAO檢驗。結果顯示,原值與一階差分結果均有部分統計量P值顯著拒絕原假設,見表5。即原值與一階差分值均存在長期協整關系,由于原值也滿足協整關系,故在進行模型估計時可以使用原值進行估計,無須使用經濟意義復雜的一階差分值進行估計。

表4 協整性KAO檢驗結果
(三)計量結果分析
1.面板。面板數據模型估計方法有三種,分別是混合回歸、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混合回歸模型與固定效應模型的選取常用Wald檢驗,與隨機效應模型的選取常用LM檢驗,若檢驗結果均優于混合回歸模型,則要對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通過Hausman檢驗再次進行分析,選擇適合數據估計的模型。本組數據三種分析結果如表5。Wald與LM檢驗結果均表示本組數據不適合混合回歸模型,需要再采用穩健Hausman檢驗。由表5中F值和P值可以得出,本組數據應該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

表5 估計方法選擇結果分析
2.實證結果分析。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模型(1)(2)為未進行異方差消除的結果,模型(3)(4)為采用PCSE法消除異方差影響后的結果,模型均控制省份變量。采用STATA.15分析結果見表6。

表6 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作用的回歸結果
根據實證分析可以得出下述結論:在模型異方差修正與嚴格控制相關變量情況下,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其中數字經濟人才需求水平、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水平和數字經濟與產業化融合水平四個解釋變量均在1%的水平下與地區經濟增長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影響系數依次為0.412、0.111和0.057和0.054。從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間的影響系數來看,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影響程度不同。數字經濟人才投入水平的影響力度最大,每增加1個單位普通本專科招生人數,地區整體經濟增長0.412。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影響次之,每增加1個單位光纜電路鋪設長度,地區整體經濟增長0.111。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水平與數字產業化水平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相當,每增加1個單位的R&D投入與軟件收入,地區整體經濟分別增長0.057和0.054。
四、結論與建議
根據以上實證分析不難看出,數字經濟發展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數字經濟的各要素對于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果有所差異,具體表現如下:
(一)人力資本投入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為顯著
當今社會數字時代下的競爭實際上就是人才的競爭,所以充分利用中國科教基礎雄厚這一優勢,繼續推行“產學研”相結合的人才培養理念,充分發揮數字技術領域“產學研”協同創新長效機制作用等措施是提升中國居民整體數字素養的必要之舉。提高國家整體教育水平,提升民眾數字素養對于全面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重視數字化教育更有助于社會形成一個萬眾創新的局面。
(二)基礎設施建設的貢獻度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次之,與數字型人才投入相比影響程度相差較大
其在前期較為顯著,但隨著基建投資力度逐年增大,設施建設完善程度不斷提高,逐漸接近飽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沖擊作用也隨之減小。原因在于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支撐,當達到一定程度后,利用程度達到飽和,作用會受到限制。而中國經濟發展也由高速度發展轉變為高質量發展,經濟發展在于充分利用各項技術。因此,各地區在完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投入充足的前提下,應將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發展的重點方向放在新基建上,即提升現有通信基礎設施使用質量。積極推動5G通信基礎設施建設與新建建筑物建設同步,實現設計同步、建設同步、驗收同步、監管同步的5G通信基礎設施新方式,同時完成對現有基礎設施升級改造工作,構建完備的城市“數字底座”,以此提升基礎設施建設的經濟效益。
(三)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水平影響相對較弱,但是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正向影響
這表明創新發展這一生產要素在推動地區經濟快速發展作用效果還未顯著,但是據以往研究表明科技創新對經濟是有較強正向推進作用的,如果推進不明顯,不排除研究指標選取的精準性不夠。同時,政府及企業也應加大對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投入力度,使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要素逐步發展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頂梁柱。
(四)數字經濟與產業融合創新成果對地區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較小
其中,一方面是由于目前中國數字經濟總體發展正處于蓬勃期,從研發資金投入以及研發人才投入來看,數字技術的研發力度和研發產出率一直在不斷提高,但研發工作中很多數字技術專利成果仍沒有形成數字產品進行規模生產。另一方面,數字產品創新與應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數字技術創新速度和市場需求程度的雙重支撐。因此,作為政府和企業,在提高數字技術創新能力的同時,更應重視對專利成果轉化率的提高以及對民眾數字產品消費意識的培養,將數字技術轉化成可應用的產品投入市場,以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整體的數字融合發展。
本文綜合利用了面板數據分析模型中的固定效應模型,從四個角度分析了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并根據實證結果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為后疫情時代數字經濟更快更好地推進國家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在理論方面,為數字經濟與區域經濟之間的效應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實踐方面,為中國省(市、區)進一步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進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方向。但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譬如研究中的數字經濟指標的選取可以再多一些,多指標分析時,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對指標進行因子提取,但由于數據較難獲取,因此沒有采用本方法對研究進行評估;同時各個地區和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速度相差較大,未來研究可以利用區域或省域面板數據進行更加有針對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