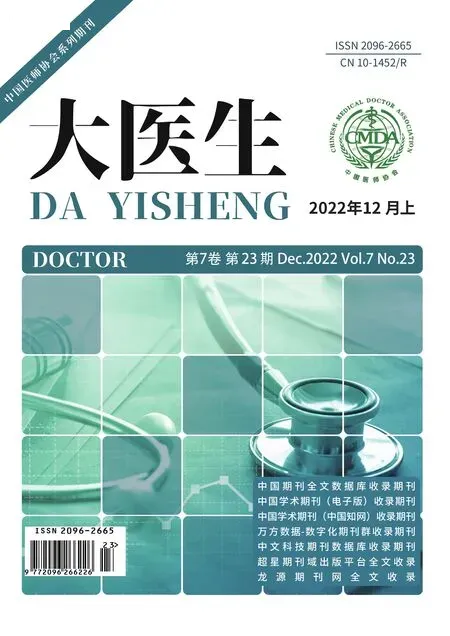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發病機制的研究綜述
黃貴龍,丁保華,許賢茂
(1.中信惠州醫院消化內科;2.中信惠州醫院肝病科;3.中信惠州醫院心內科,廣東惠州 516006)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慢性肝病的一種,發病率逐年上升,正逐漸成為最為常見的慢性肝病[1]。NAFLD是指在沒有過量飲酒或其他特定慢性肝病的情況下,肝臟中脂肪積累≥5%,病理特征為彌漫性肝細胞大皰性脂肪病變,呈現慢性進行性加重。近年來,NAFLD的發病率不斷升高,成為危害人體健康的三大肝病之一[2]。臨床認為NAFLD 的發生與肥胖、胰島素抵抗、血脂異常和遺傳易感等有關,其中胰島素抵抗是影響NAFLD 發生的關鍵因素[3]。治療NAFLD 首先要降低體質量和改善胰島素抵抗[4]。
1 肝臟與巨噬細胞
巨噬細胞是一種位于組織內的白細胞,在肝臟免疫穩態和肝臟內環境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顯示,“二次打擊”學說是目前被廣泛接受的NAFLD 的發病機制[5]。“首次打擊”是指脂肪在肝臟內過度聚集,“第二次打擊”是在首次打擊的基礎上,由活性氧誘導的發生在肝臟實質細胞內的炎癥反應[6]。NAFLD 的發病機制常被認為是“多重打擊”模式,其中對細胞、分子機制、環境與遺傳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為NAFLD 的診斷標記物和靶向治療藥物研發提供方向[7-9]。正常肝臟中,肝巨噬細胞通過上調抗炎基因的表達和降低抗原的呈遞能力來耐受內毒素。而在慢性炎癥脂肪肝中,盡管有免疫調節,肝巨噬細胞在抑制免疫介導損傷方面的作用仍會降低。因此,持續性肝損傷引起的耐受性喪失可能是導致NAFLD惡化的一種機制[10]。肝巨噬細胞參與脂肪肝發病機制的異質性和多種模式,包括Toll 樣受體(TLRs)、NOD 樣受體熱蛋白結構域相關蛋白3(NLRP3)炎癥小體、脂肪毒性、糖毒性、代謝重編程與肝臟周圍細胞的相互作用和鐵中毒。已有實驗表明,巨噬細胞極化是脂肪肝進展中一個高度可塑的生理過程。肝巨噬細胞可以將其表型轉換為促炎(典型激活巨噬細胞,M1樣巨噬細胞)或抗炎(選擇性激活巨噬細胞,M2樣巨噬細胞)表型以應對各種信號,如細胞因子、脂肪酸、內毒素、代謝物和危險/病原體相關分子。肝臟巨噬細胞包括不同細胞群的亞群。在這些亞群中,庫普弗(Kupffer)細胞起源于胎兒肝臟中的卵黃囊源性紅髓樣祖胞,是一群生活在肝臟中的巨噬細胞,進行局部增殖和自我維持[11]。Kupffer 細胞占人體定植巨噬細胞的80%~90%,是調節肝臟免疫的關鍵細胞,其獨特的極化對NAFLD 的影響越來越被科學家重視[12]。Kupffer 細胞作為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吞噬細胞,很少從肝臟中的生態位遷移出來,在調節和維持內穩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肝損傷后,Kupffer 細胞將被激活,釋放出大量的炎癥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13]。在肝損傷早期,骨髓中存在表達淋巴細胞抗原6C+(Ly6C+)高的炎性單核細胞(Ly6Chi)和中性粒細胞被Kupffer 細胞招募到肝臟,并分化為CD11
b+F4/80+M1樣巨噬細胞。在急性炎癥期間,Kupffer 細胞可以降解細胞外基質、修復組織損傷。在修復期間,巨噬細胞選擇性地分化為M2樣表型,通過分泌白細胞介素-13(IL-13)和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促進纖維化進展。總之,這些發現強調了Kupffer 細胞在脂肪肝的進展中發揮著復雜的作用,并表現出功能可塑性[14-15]。
2 肝臟釋放外泌體
外泌體是一種微小膜泡,含有細胞特異的蛋白、脂質和核酸,可以用于基因治療,也可以用于癌癥的診斷和治療,主要參與細胞間信息傳遞和物質運輸,發揮細胞間聯絡作用,同時可影響NAFLD 的發生。不同組織細胞來源的外泌體攜帶的蛋白質、脂質及核酸不同,所發揮的生物學效應也不盡相同。肝細胞和膽管上皮細胞,既可釋放外泌體,又是肝臟內源性外泌體和其他器官細胞來源外泌體作用的靶細胞[16]。微小核糖核酸(miRNAs)為含有19~25 個核苷酸的小核糖核酸分子,參與脂肪細胞分化、膽固醇代謝、胰島素抵抗、線粒體損傷等過程的調節。有研究發現,小鼠脂肪組織巨噬細胞的外泌體miRNAs 可增加胰島素抵抗[17]。另有研究表明,外泌體miRNAs可作為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脂肪肝、NAFLD 和肝細胞癌的潛在生物標記物,外泌體miRNAs 或蛋白的表達隨著NAFLD 的進展而變化[18]。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表明,外泌體對肝臟細胞炎癥反應、脂質變性和肝纖維化的發生也有顯著的影響,包括脂質的合成、運輸和降解,其中就包括NAFLD的發生和發展[19]。
多種細胞來源的外泌體通過靶向釋放蛋白質、miRNA 及長鏈非編碼核糖核酸(lncRNA)等生物活性分子介導細胞間信息傳導,在NAFLD 的發生發展中有重要作用。因此,阻斷致病性外泌體的分泌及其內容物的釋放可能在NAFLD 的治療過程中獲益。此外,外泌體也可作為藥物運送的載體參與疾病的治療,這得益于其雙層脂質結構。在診斷方面,外泌體所包含的miRNAs 與疾病進展呈正相關,可作為診斷肝臟疾病的新型標記物。但目前,外泌體的生物活性分子及其與受體細胞的作用機制尚未完全闡明,作為新的診療工具處于開發階段,要從動物實驗發展到真正用于臨床,需進行更多研究。因此,監測外泌體miRNAs 及其攜帶的蛋白對探索NAFLD 的發病機制有重要意義。
3 NAFLD 和腸道微生物群
人體微生態系統包括口腔、皮膚、泌尿、胃腸道4 個部分。其中最主要、最復雜的是腸道微生態系統,該生態系統由腸道正常菌群及其所生活的環境構成,腸黏膜結構及功能很大程度影響腸道微生態系統的運行。腸道微生物量占人體總微生物量的78%,腸道菌種類多樣[20],其最顯著的特征是穩定性高,若失衡則會發生各種腸內、外疾病。雖然人類宿主和腸道微生物群的關系是互惠互利,但腸道微生物群的紊亂與許多慢性疾病有關[21]。因此,保持腸道微生態平衡可抵抗腸道病原菌感染導致的疾病。有關研究表明,NAFLD 病情進展與患者機體腸道菌群的改變有關[22]。腸道微生物菌群通過多種方式與NAFLD 建立密切聯系。首先,通過炎癥途徑和健康的野生類型小鼠的遺傳修飾表明,易發展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的小鼠在實驗中微生物群共食后導致野生類型小鼠發生肝臟脂肪變性和炎癥。另有研究表明,在常規治療的基礎上腸內營養與腸道益生菌治療非酒精性肝病肝纖維化療效顯著,可抑制肝纖維化,改善患者肝功能、營養指標及凝血功能,能調節機體氧化應激及炎癥反應[23]。在一項有關益生菌與熊去氧膽酸聯合用藥治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研究中表明,服用益生菌后,能調節腸道菌群,抑制菌群有害代謝物的產生,改善機體癥狀[24]。健康機體中,腸黏膜屏障能阻止細菌與毒素經門靜脈進入到肝臟中,而NAFLD 患者大多腸黏膜屏障受損;服用益生菌后,能有效保護腸黏膜屏障,并加速腸道上皮細胞修復,減少痛苦程度,遏制疾病進一步發展。NAFLD 患者腸道菌群失調后,產生大量炎癥物質,促進脂肪肝病情發展,加重病情;采用益生菌治療后,能有效改善炎癥因子水平,抑制α 干擾素(INF-α)等炎癥因子的生成,繼而減輕炎癥因子進一步損害患者肝臟,改善癥狀。
4 非酒精性脂肪肝與糖尿病的密切關系
1 型 糖 尿 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患者通常合并胰島素敏感,但患有T1DM并不能預防超重。有證據表明,越來越多的T1DM患者由于久坐等生活方式、熱量過剩和強化胰島素治療導致超重,NAFLD 患病率在該類人群中也在增加[25]。NAFLD 與代謝紊亂密切相關,如2 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高血壓、高脂血癥和肥胖。NAFLD 與T2DM 具有某些共同的病理生理途徑,包括胰島素抵抗、代謝、細胞死亡、炎癥及纖維化等。T2DM 使NAFLD 的病程惡化,使疾病進展的風險加倍(即從單純的脂肪變性演變為晚期纖維化、肝硬化,甚至死亡)。T2DM 中胰島素可抵抗NAFLD 的發生,其促進脂肪組織的脂解,導致生成游離脂肪酸,并沉積于肝臟,最終導致脂肪性肝炎[26]。胰島素抵抗在NAFLD 發病機制中的潛在機制還包括線粒體脂肪酸氧化、脂肪生成增加和脂聯素水平降低。T2DM 患者發生NASH 和肝臟相關并發癥的風險更高,如肝硬化相關死亡率和NAFLD相關死亡率比非T2DM 患者高3~5 倍[27]。NAFLD會導致T2DM 的代謝失代償,NAFLD 患者T2DM的發病可能是通過幾種肝細胞因子損害代謝控制而介導的。T2DM 和NAFLD 存在相互的、緊密的及雙向的聯系。進一步了解這種雙向關聯發病機制,可能實現通過阻止NAFLD 的進展來預防T2DM 的發展。
胰島素抵抗和NAFLD 被認為存在于一個自我延續的致病周期中,胰島素抵抗被認為是NAFLD 的基本協調者[28]。在胰島素抵抗的背景下,NAFLD 的進展可能是由隨后的高胰島素血癥的致病作用及不同程度的胰島素缺乏導致,特別是在糖尿病中。胰島素抵抗不僅發生于T2DM 患者中,在許多T1DM 患者,特別是高齡患者中,胰島素抵抗也越來越被認為是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T2DM 的存在與NAFLD進展為晚期纖維化、肝硬化和肝細胞癌(hepatic cellular cancer,HCC)相關,T2DM 患者的肝纖維化患病率顯著高于普通人群。此外,T2DM 和NAFLD 患者發生肝纖維化的概率為17.02%,而在T2DM 人群中脂肪肝的發生率高達57%~80%,T2DM、NAFLD 和肝纖維化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復雜的[29-30]。高血糖會對肝細胞產生有害影響,并引發NAFLD 從單純脂肪變性發展為NASH 和纖維化。此外,T2DM 患者會因NAFLD 更易引發肝纖維化,未經治療的肝纖維化將轉變為不可逆的肝硬化和肝癌,從而導致死亡。
5 非酒精性脂肪肝與睡眠的關系
晝夜節律是身體各種內分泌過程的一個完整的調節器,包括睡眠-覺醒周期、激素調節和新陳代謝。除了代謝、遺傳和環境因素外,由生活方式的改變導致的晝夜節律失調也與NAFLD 的發病機制有關。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NAFLD 和代謝紊亂之間的相關性,其發病機制與激素穩態的周期性波動有關。很明顯,內分泌與晝夜節律是緊密聯系的。一般來說,晝夜節律調節生理功能的通量模式。晝夜節律對身體過程的調節,與瘦素和相關激素對NAFLD 的調節有關[31]。
晝夜節律影響睡眠質量,而睡眠質量差也可導致NAFLD 的發生。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會因睡眠質量降低而被激活,從而增強應激激素的分泌,如皮質醇和兒茶酚胺,進而增加代謝綜合征的發生率。睡眠質量差與下丘腦分泌食欲素之間存在聯系,下丘腦分泌食欲素控制著食欲調節激素瘦素和胃饑餓素的分泌。這些激素可有效調節葡萄糖代謝。也有研究表明,睡眠質量差會增加T2DM 患者的胰島素抵抗[32]。因此,睡眠質量差與肥胖有關,是NAFLD 的發病機制。這種關聯的機制還可能是炎癥細胞因子如白細胞介素-6(IL-6)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的作用,這些因子因睡眠障礙而增加,促進脂肪細胞的脂解,進而導致肝臟游離脂肪酸溢出[33]。此外,睡眠不足可能會影響HPA 軸和皮質醇代謝,導致肝臟脂肪儲存[34]。因此,睡眠時間短也會促進NAFLD 發生和發展。
6 小結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生成發展與巨噬細胞密切相關。肝臟巨噬細胞在肝臟免疫穩態和肝臟內環境發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疾病與NAFLD 有重要的關聯,如慢性病毒性肝炎和酒精性肝病。在肝臟疾病的不同階段,駐留的Kupffer 細胞和新招募的單核細胞來源的巨噬細胞在炎癥、纖維化和纖維溶解的調節中起著關鍵作用。miRNAs 為非編碼單鏈RNA 分子,調節脂肪細胞分化、膽固醇代謝、胰島素抵抗、線粒體損傷等過程。NAFLD 與T2DM是互為前提的關系。
綜上所述,NAFLD 與巨噬細胞、外泌體、腸道微生態、糖尿病、睡眠密切相關。但深究其內因,脂肪和膽固醇是否協同加重NAFLD 尚不明確,有待進一步研究考證。在臨床應用上,尚無推廣的指標可直接預防、診斷和評估NAFLD。在探究NAFLD 發展機制同時,既要重視本綜述上述提及的細胞、代謝性疾病,還有待將相關靶向指標應用至臨床,如巨噬細胞標記物等,從而以科研力量推動臨床治療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