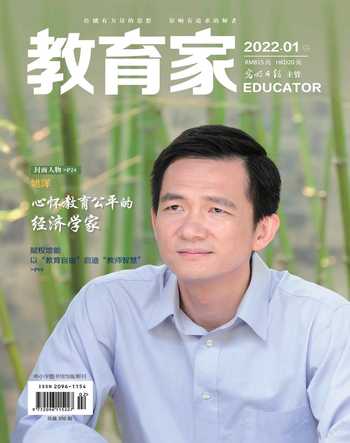在教育變革時代,重申教師自主權
徐莉

教師在工作中享有自主權是教育中的基本問題,它常常與“如何調動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如何激發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在動力”“如何提高教師的創新能力”“如何提升教師的工作滿意度和幸福感”等問題關聯在一起。所有強調專業性的工作,從業者都應享有自主權,從而提高自主性。具體到教育行業,教師自主權喪失,自主性低下,可能導致工作消極被動、責任心低下、創造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研究表明,提高和保障教師自主權對學生的學業發展具有積極的預測性,能提高教師對工作的滿意程度,降低教師工作壓力,增強教師的責任心,有益于教師的專業化發展。但研究也顯示,在世界范圍內,教師自主權正呈現喪失的趨勢。
從教師自身來說,教師自主權喪失,究竟是教師的“不能”還是“不愿”?由教師身處的環境來看,學校的組織架構和制度、相互關聯的一系列政策法規、持續發生影響的社會文化與傳統又是如何發生作用,最終導致教師的“不能”或“不愿”呢?
警惕專精化追求中教師自主權的喪失
筆者親身經歷過一次某校的備課方式改革。源起是教師們覺得備課時花了不少時間、精力寫詳案,實際上課時卻大多不會按照預先的設計來實施。為了解決問題,學校管理者召集各學科帶頭人和資深教師一起討論“如何備課才能提高其實效性”。經過多輪研討,最終形成了一份遠比之前的備課制度更為復雜、嚴苛的新方案。作為制訂者和執行者,參與研制的教師們一面感慨負擔更重了,一面又覺得少了哪一點都不行。
在規范、方案的制訂中,歸納法的使用十分常見。從課程標準的研制、修訂,教材的編寫、修改,到一地一校制度、規章的訂立,都常將行業專家們的“最好”匯聚在一起,反復調整優化,極盡周到細致。條分縷析這些規范、方案,會感到十分完備且有理有據,但落到實踐中,一旦將這些“最好”絕對化,就容易導致教師不堪重負,教學難以為繼。
香港地區的學校及教師團隊可以自由選擇教科書。各家出版社為了讓自己出版的教科書被選中,便邀請行業專家編寫面面俱到、一本在手便能直接上課的教師指導用書,以減輕教師工作壓力。其中不僅有精心設計的教學過程,還有學生的課堂練習以及課后練習,一并附上清晰完整的答案、配套的電子講稿、不定期的增潤修訂……無微不至的支持讓教師不再需要自己花時間去分析教材、設計教學、拓展資源。然而,實踐表明,完備的教師指導用書、精心設計的每一個環節,反而導致日常教學拖沓散漫,陷入一堆瑣碎。過度的支持導致教師自主性低下,這樣的支持也是一種限制和剝奪。
與歸納法相對的另一種路徑是演繹,即直接引入經典的理論、架構,讓教師來完成轉化落地。在理論優先的認識下,以行政權強力推進,讓教師的實踐作為案例來驗證理論。這種單向的理論指導實踐,不斷貶低甚至徹底否定教師的實踐智慧。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哲學教授舍恩就對當時占主導地位、強調理論優先的實踐認識論提出批評。因為在教育中,人們面臨的問題情境通常是復雜的、模糊的、不穩定的、獨特的,乃至相互沖突的,僅靠直接應用現有的科學理論和技術是不可行的。舍恩建議,對于常規性問題,實踐者可以憑借嚴謹、專精的科學知識去解決問題,而對于那些開放、復雜的問題,實踐者只能憑借直覺、個人經驗、嘗試錯誤以及實踐中的摸索來解決問題。這并非否定教育的專業性,而是說在教育實踐中一味追求系統、嚴謹、專精化,可能既不適切也不實用。人們在利用理論為實踐提供指導、啟發的同時,也需要透過實踐對理論模型、流程和架構進行不斷調整。
不論是歸納還是演繹,不恰當的專精化追求,容易侵奪教師的自主權,阻礙教師的自主發展。長此以往,教師只會走由權威劃定的最佳道路,自然既“不能”也“不愿”自主。因此,重申教育行業和教師工作的不確定性,警惕專精化追求中教師自主權的喪失,就顯得尤為重要。
對教師支持的適切性,必須透過教師有意識的行為來體現。既然教育是一個需要在復雜情境中不斷快速做出決策的工作,具體到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以什么樣的方式、學習什么內容、如何處理各類信息和沖突,都應由教師與學生合作完成。那么,在現場的教師可以被啟發、被指引,但絕不應做教育專家及管理者的提線木偶,也不應將經典理論模型絕對化。諾貝爾獎獲得者西蒙說,“最好”是“好”的敵人,這句話也可以作為教育中對所謂“好”和“正確”絕對化傾向的警醒。
濫用外部激勵會降低教師自主性
教師的專業晉升,就像電子游戲中的打怪升級:在各類培訓中學習知識技能以獲得學分,執教公開課、競賽課,做課題研究、寫論文、參加論文評比,發表文章、出版專著,甚至編寫教材、開展教材教法的培訓……一位教師完成學校、區、市、省乃至全國及國際的各類比賽或展示之后,各項榮譽會被折算成不等的分數,經過累計,在各類評比中換取榮譽和晉升機會。這個龐大而精細的外部激勵機制,很容易讓教師把各種利益與專業發展、教育工作的價值意義畫上等號。這種外部激勵機制,雖然為教師指出了一條職業生涯的發展道路,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壞了教師的自我價值感和職業價值感。因為這種行為主義色彩極為強烈的機制,以外部激勵干擾了教師的自主探索。當強大的外部動機抑制了教師的內在動機時,教師就會陷入被動的努力,這對教師自主性的破壞顯而易見。
筆者遇到過不少教師,一旦熬到一定職級或獲得某項榮譽,就再也不上公開課,不寫一篇文章,一心盼著退休。因為在他們的邏輯中,一切的努力就是為了獲得獎賞,然后就該指點年輕人去重走長征路了。還有一些教師,從一開始就選擇放棄,他們放棄的不只是所謂的名和利,還包括專業上的發展和追求。他們同樣缺乏自主性,不愿探索解決問題的新路徑、新方法,不愿承擔變革帶來的壓力與責任。
此外,績效考核這類激勵制度,是在教師晉升制度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外部激勵的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以算是強化結果評價的問責制度。一位教師在學校里教了多少課,交了多少篇學習筆記,參加了多少次專業學習,缺席了幾次全校大會,學生考試合格率多少,教案是否寫得詳細……如此將一位教師在學校里的所有工作和取得的成績換算成分數和報酬,表面上看起來是在評價教師的工作質量,實際上則意味著教師自主權的進一步剝奪。因為教師只有做賦分的事情,才能得到肯定和酬勞;做自己擅長或喜歡的事情,可能無法得到任何支持與肯定。
教師的委屈,可能是整天忙于“非做不可”的事,自己的興趣、想法無法得到支持;或許是漸漸在合作和競爭的拉扯中,陷入深深的職業倦怠;也可能是感到自己已經很努力,但教學效果、學生表現無法與自己的付出相匹配。注重結果評價的績效考核,變相鼓勵教師唯分數論,偏離育人本質。教師身不由己的背后,是自主性日益喪失的無奈。當教師“不能”也“不愿”爭取自主權時,如果教育管理者為了激發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只是一味強化外部激勵,顯然是負薪救火,事與愿違。
缺乏“共同相互”的過程導致自主權喪失
作為一名多年致力于爭取教師自主權的從業者,筆者常常面對來自兩個方面的質疑——教育專家和管理者們說,不是所有教師都既有能力又有行動力,一線教師最想要的是盡可能詳細且好用的行為指南;教師們也說,工作壓力很大,沒有時間研究琢磨,最好是直接說清該如何做。一方面,因為感到許多教師能力不足、耽于事務不愿思考,教育專家和管理者們盡可能細致地做好設計與安排,具體到人和事,時時檢查督促,事事與績效、晉級掛鉤;另一方面,因為教師不愿擔責,難以主動、獨立地完成實踐并進行優化,又導致越來越缺乏自主性。
教育專家和管理者不敢放權,同時教師們似乎也不愿要自主權——雙方之間的不良互動關系需要改變。解決的辦法是賦權增能,“賦權”的關鍵在于為教師“增能”,即提高教師專業能力。在提高教師專業能力的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若教師的能動性和責任心并未真正被激發,教師的自主權依然會不斷喪失。這要求教育專家及管理者與教師之間應保持開放的多方對話。行業中的每個人都要自己去思考、判斷和選擇,并為之承擔責任,而絕不是認為只要爭取了自主權就可以隨心所欲。一個有很強自主性、愿意承擔更多責任、致力于教育創新的教師,只有十分珍惜自己已經獲得的自主空間,才可能贏得各方信任,獲得更大的自主權。因為,給予自主權的管理者,與教師共同承擔著風險和責任。
著名教育家、哲學家保羅·弗萊雷說:“自由不是一種恩賜,也不是自我的成就,而是一種共同相互的過程。”用這句話解釋教師自主權,即教師必須對他們所作出的所有決策負有責任,全然的奉命行事是對權利的讓渡,也是對責任的消解。在新管理主義邏輯下的教育發展思路,追求高度確定性、高質量、高效率、強秩序,加之簡單化和絕對化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教師自主權更容易被侵犯。
2021年,重大教育政策密集出臺,涉及學前教育改革、義務教育質量提升、教育評價改革、高中育人方式改革、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意見、高校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等等,對教師工作提出進一步明確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強調教師自主權這個教育中的基本問題,應成為這場教育變革中不容忽視的重要部分。唯其如此,我們在理解、執行這一系列政策時,才能避免簡單化和絕對化,堅守教育的初心,讓政策發揮出實實在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