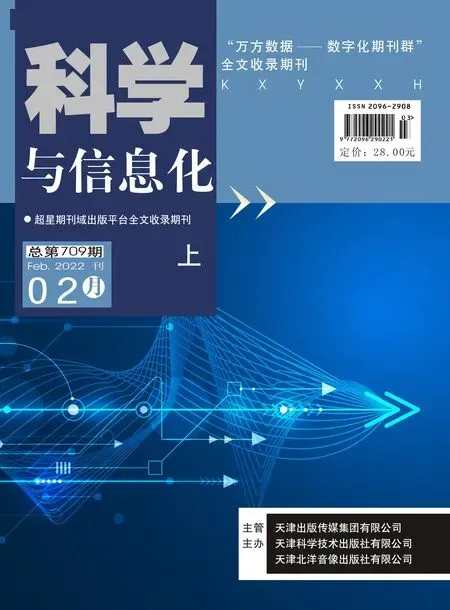大數據空間觀邏輯的楚青銅紋飾寓意研究*
張鈺 肖書浩
武昌首義學院 藝術設計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64
引言
楚國的青銅紋飾排布形式表現了楚人獨特的空間觀念,其觀念被映射到紋飾形態構成和其在青銅器中的相應位置上。如:以饕餮紋為主紋的動物紋飾,一般出現在青銅器的腹部和足部較為醒目的位置,表現楚人對龍圖騰的崇拜。但鳳鳥紋在青銅器中出現也較為頻繁。龍虎形態紋飾常被鳳鳥踩在腳下,乾坤顛倒可推測為楚人與姬周的矛盾關系。楚國與中原諸國之間的微妙關系,可以通過不同時期的青銅紋飾空間變化得到一定印證[1]。
我們往往喜歡通過相關文獻史料,對研究對象進行定性分析,希望能夠在文字上找到學術依據,然而從古墓中挖掘出土的文字資料一般是片段式的,我們只能在這些文字中斷章取義,尋找論證的依據,然而縱觀整個時代,我們很難復原當時的情境,藝術作品所反映的是巫鴻的創作動機和直觀意圖。
進入21世紀,大數據既不是一種新的技術也不是一種新的產品,大數據只是一種出現在數字化時代的現象。20世紀中葉,數據的存在方式只停留在文件之中,人們只能對數據進行簡單的調用和管理;在后來的10年間,隨著科技的發展,出現了數據庫,人們可以根據數據間的關聯構建模型;到了20世紀末,人們構建了數據倉庫,方便用戶分析數據,隨著網絡的普及,數據網絡化傳播成為可能[2]。
現在,隨著手機智能化的發展,社交網絡平臺呈現出迅猛的增長態勢,傳統數據庫的發展已經無法滿足其需求。大數據技術為解決此類問題應運而生。其優點在于調用數據庫數據極為便捷,處理非關系型數據更加效率化。因此該技術被廣泛運用于IT行業,但是被運用到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案例相對較少。
“空間轉向”作為人文學科中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得到了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從而使得“空間轉向”這一趨向具有了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建構的“知識型”的意義和價值。
1 研究的主要內容
首先,按照同一青銅器,不同裝飾紋樣主要分成4個不同的類別,建立圖片數據庫,為數據分析提供圖片基本研究素材對象[3]。如下圖所示:
2 基本思路和方法
其次,根據已有研究圖片素材,進行數據間的橫向對比,對不同楚國青銅器,相同紋樣不同空間分布情況進行數據分析,總結出楚國人紋樣空間分布的規律性現象,找到圖案空間分布的指代意義。按照這個邏輯,本研究分為3個層次,如下圖所示:

圖2 楚紋飾空間層次寓意圖
這3個層次彼此邏輯關聯,在空間形成了一種獨立的敘事語境,“楚青銅裝飾紋樣”在空間中的這3層關系相互關聯,卻又相對獨立[4]。如下圖所示:

圖3 楚紋飾空間層次邏輯圖
3 本課題研究的重點和難點
如果沒有豐富的考古經驗,對于案例進行細致的空間細節分析,很容易造成研究者對于形式語言的誤讀。每個研究者會根據自己的固有知識背景,進行形式上的解讀,從而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
作為動物紋飾代表的龍紋,代表著陽剛之美,作為先秦時期的隨葬物品,起到了聯系人與天地之間的紐帶作用。通過紋飾的附著,讓青銅器更具有象征意味,傳遞楚人對自然的敬畏之情[5]。
4 主要觀點及創新之處
本研究旨在通過傳統美術考古文獻研究法和空間研究法比較,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相比,有自己的獨特性。楚地周圍有蠻族相鄰,苗人、巴人與楚人文化相融,逐漸形成了以曲線審美為特征的繁復裝飾風格。這種靈動的曲線自由奔放、活力四射,與中原中規中矩的風格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