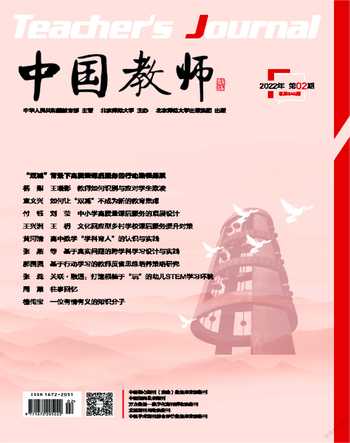一位有情有義的知識分子
檀傳寶
我最早見到王逢賢老師是讀博士的時候。在此之前,我們當然對先生早已心向往之。那時在德育領域里,幾乎所有研究生都知道王老師等國內幾個大腕級的人物。所以,我老早就知道他、讀他的文章。但是真正見到他,是我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1996年6月,我們幾個學生舉著牌子到南京火車站接王老師和黃濟老師來南京師范大學主持我們的博士論文答辯。遵照導師魯潔教授的指示,我們把先生們從南京火車站一路接到南京師范大學的南山專家樓。那一年,我們同門一共有三個人畢業,雷鳴強博士、張樂天博士,還有我。非常榮幸,王老師是我的答辯委員會主席。我對王老師非常美好的回憶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作為我的前輩、我的老師,王先生給我留下了許多深刻而感性的印象。如果讓我對這個印象做一個概括的話,我想這樣表達:王逢賢教授是一位有情有義的知識分子!
比如,王老師對我們這些后輩學生非常有感情。只要是他的學生,他都關懷備至。記得在答辯會上,他反復肯定我們的學術成績,也發自內心體諒我們學習的艱辛。他認為,在大家都熱衷于“下海”賺錢的時候,我們這批甘受清貧的“傻博士”(王老師原話)非常了不起!現在博士生的待遇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們當年讀博士時是非常艱苦的,助學金一個月只有兩百多塊錢。像我,還是已經成家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可謂困難重重。王老師總是基于學生的立場考慮學生的問題,他一邊對我們耳提面命,指出我們研究的不足,但是更多的是對我們極其熱情的鼓勵和褒揚。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研究還稚嫩得很。老師褒揚我們,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我們確實努力了,更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對我們懷有深切的同情,更希望對我們在逆境中求上進的精神予以最大的肯定和鼓勵。
1996年博士畢業后,我回到母校北京師范大學(以下簡稱“北師大”),跟從黃濟教授做教育學博士后研究。其間,在北師大也見過王老師很多次。印象最深的一次,當是在我一居室的寒舍里請王老師吃飯。
我知道,在北師大或者北京市,王老師的好朋友很多,因此吃飯的應酬也很多,而且一般學術活動的食宿也都會安排周到。我一開始擔心請不到他,沒想到我忐忑地說“王老師有時間我請您吃飯吧”,他馬上就說行。很爽快,還反過來讓我說什么時間合適。博士后的住房非常小、非常窄,飯桌就在床與書桌之間。但就是在那種非常局促的環境下,王老師跟我們一起大快朵頤、談笑風生。那頓午餐,雖然非常局促,但是非常非常愉快。一起用餐的除了我的妻子、孩子,還有現在在浙江工作的王健敏博士(王老師就是來參與她的博士論文答辯的)。在工作特別忙的情況下,王老師還能夠欣然造訪我那個非常非常狹小的房間,對作為小輩的我來講,是一份莫大的情誼與鼓勵。
說王老師是一位有情有義的知識分子,當然不僅僅是說王老師和我們這些后輩有著美好的私人情感。最重要的,是說他有那種憂國憂民的品質,有著對整個中華民族發展、人類文明未來的悲憫情懷。他的社會關懷意識強烈而真誠,常常禁不住溢于言表。有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電話里和我討論我在《中國教育報》上發表的一篇論文。那是一篇短文,主張要建立教育的“第三標準”。因為我覺得迄今為止的教育,比較多地考慮了“真”的標準,如教育要符合規律之類;也比較多地考慮了“善”的標準,如我們要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等。但是在教育實踐中,相對來講,我們是比較忽略“美”的標準的。因此我們不光要加強美育,還要建立教育活動的“第三標準”,即教育的“審美標準”。文章剛剛發表,我還沒有拿到樣報,有一天在家里就接到王老師的電話。王老師在電話那頭滔滔不絕地跟我討論那篇文章的觀點,講了好長時間!我想,如果沒有真切的熱情、不是發自內心地關心中國教育事業的話,對一個剛剛畢業的年輕博士、一個晚輩,他根本不可能打長途電話過來與之做如此細致的研討。因此,我覺得王老師不僅是一個在學術上有杰出貢獻的學者,而且在事業、生活中也是一個特別有情有義的人、有悲憫情懷的人。也許正是有了這種人格品質和精神境界,才能成就他比較厚重、比較有成就的人生!
形成王老師這種悲憫性的學養、修養,離不開兩種重要的內在品質:一是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二是克服困難的勇氣跟意志力。
像王老師那一代人,遭遇的國家苦難比我們多,個人的苦難更比我們多。王老師顯然是那些不僅沒有被苦難擊垮,而且能夠在困難中奮力前行的人。以他的人格,讓他沒有國家意識、沒有社會擔當都很難。這固然一方面是社會環境使然,但是另一方面也與王老師本人對這個世界發自內心的關懷有關系。很多時候,只要打通他的電話,幾乎不需要再說什么,他就會滔滔不絕地把他對這個世界的關切,對現實教育問題的憂慮,對我們年青一代的由衷期望,非常非常坦誠地反反復復地叮囑。而這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珍貴的精神營養。我們從先生身上學到的,不僅僅是他實體的學術觀點,實體的教育智慧,更多的是他學者的人格魅力以及這一人格魅力帶給我們從事教學與研究的無限動力。
王老師所具有的堅強意志也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我第一次見到王老師的時候,感覺王老師很健康—高高的、瘦瘦的、神采飛揚,并不知道他的身體也有許多問題。直到1996年我即將辭別南京師范大學的時候,魯潔老師囑咐我要注意身體,說:“不要像王逢賢一樣—胃都切除了三分之二!”那一刻,我十分震驚。難以想象,每一天他要克服多少困難才能從事他最心愛的教學與研究啊。因此我一直在心底非常欽佩王老師的頑強意志。先生一生奮斗不止,一直到他去世,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思考,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工作。也就是說,他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在荊棘中努力前行!
在我們的研究領域,即德育原理、教育學原理領域,以我所了解的情況看,王老師當之無愧是我國現當代最重要、最杰出的教育學家之一。王老師對教育基本理論,尤其是對德育論學術研究、學科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關于德育研究的成果,有時他用理性的形式表達,如發表論文、出版專著等,有時他也會以非常幽默、感性的形式予以表達。記得有一次,為了肯定、鼓勵我從事德育美學觀的研究,他認真地跟我說:“你看現在社會上有人買智育,如家教;有人買體育,如學習跆拳道;有人買美育,如學鋼琴。但是,從來就沒有見到有人買德育!為什么?因為智育好吃、體育好吃、美育好吃,唯獨德育不好吃!”王老師關于德育與人生的聯系,關于社會發展關系的很多論述,對我的啟發都非常大。此外,王老師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德育主體性、德育實體性的諸多論述也是非常精彩的。
如果以王老師為典型案例,我覺得一位“好的學者”的“好”,必須具備三條最重要的標準:第一,有對學術和社會最深切的關懷。王老師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具有悲憫情懷的人,他對教育事業有發自內心的關切。而他的成就,實質上出自內心對于這個世界的由衷關懷。第二,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要有批判精神。王老師常常有非常獨到的學術成就,拒絕人云亦云,哪怕看報紙、看電視的時候也能保持自己對人與事最清醒的判斷。他在研究上所樹立的獨立探索的風范,也是給后學者非常好的榜樣。第三,具備理性分析問題的學術能力。王老師的理性思維是非常發達的。仔細斟酌不難發現,當他滔滔不絕地講他自己某個想法的時候,他的“滔滔不絕”都是基于事實、有非常嚴密的邏輯的。以這三個標準來衡量,王老師是我的榜樣,也是所有中國教育學人的榜樣。
以上三條,第一條最重要。也就是說,未來的青年學者如果要有所成就的話,一定要有一個比較高的人生境界。王老師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他的憂國憂民,他對后學的獎掖,他的不懈奮斗,都是基于對國家教育事業的真切關懷。青年人應該學習這種大的人生境界。因為有多大的境界就有多大的出息。
本文原為王逢賢老師去世(2013年12月13日)后依據東北師范大學有關老師對作者的訪談加工而成,訪談后收入該校編輯出版的紀念文集。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