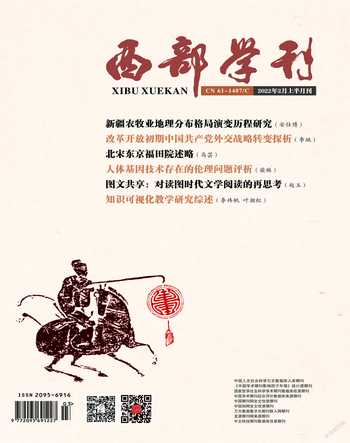影視解說類短視頻的合理使用問題探析
林威宇 林威光
摘要:近年來,影視解說類短視頻風靡網絡,極大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然而此類視頻卻有侵犯相關電影著作權的風險,谷阿莫侵權糾紛案就是其中的典型。就作品本身而言,谷阿莫的短視頻作品雖具有獨創性,卻因素材來源非法以及營利目的而侵權;就創作行為而言,在創作影視解說類短視頻時,作者要遵守合理使用的底線,其作品才會受到法律保護,而合理使用邊界的判斷,宜遵循“四要素檢測法”;就制度完善而言,要從比較法、概念法學、司法實踐及價值衡量等多方面入手,實現著作權保護與合理使用之間的利益平衡。
關鍵詞:影視類短視頻;著作權保護;合理使用;二次創作
中圖分類號:D923.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03-0067-04
一、問題緣起:兩岸三地關注的谷阿莫案
自第三次科技革命爆發以來,人類社會進入信息化時代,網絡自媒體行業蓬勃發展。近年來,網絡上一類主題為“××分鐘帶你看完電影”“××電影解說”和“××電影吐槽”等的系列短視頻風靡。這類短視頻截取某部電影的片段,并配上制作者別具一格的解說,通過視頻剪輯的方式合成一部僅有5—10分鐘的短視頻。此類視頻中包含了電影故事的主要脈絡,包括制作者對該電影劇情、人物構造、鏡頭拍攝等的主觀評價。因此,筆者稱該類視頻為“影視解說類短視頻”。此類視頻中的佼佼者,莫過于因創作“××分鐘帶你看完××作品”的電影解說短視頻而爆紅,來自我國臺灣地區的視頻制作者——谷阿莫。
2014年前后,谷阿莫的影視解說視頻開始在大陸、港澳臺的互聯網上流行。2017年,谷阿莫遭到動畫片《哆啦A夢》、電影《腦漿炸裂少女》《近距離戀愛》、韓國電視劇《W-兩個世界》以及影音串流平臺KKTV等多家影視版權方起訴。原告訴稱:其一,被告谷阿莫未經影視版權方授權,擅自使用盜版影視作品進行改變重制,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其二,部分影視作品在被告制作的視頻中被評價得“一文不值”,以致于相關影片的社會評價降低,影片無法如期在影院上映,致使版權方損失達數百萬元,片商損失逾千萬元,上述經濟損失一定程度上由谷阿莫制作的相關視頻造成[1]。谷阿莫對上述指控辯稱,其所制作的視頻皆為著作權法上的合理使用,不存在侵權問題。2018年,我國臺北“地區檢察署”在對谷阿莫侵權訴訟進行調查之后,認定其制作的短視頻存在侵權行為,正式起訴谷阿莫[2]。
雖然目前谷阿莫在大陸尚未遭到起訴,但該案亦引發大陸輿論關注。就作品本身而言,谷阿莫發布在大陸網絡平臺上的影視解說類短視頻,是否因違反大陸《著作權法》而涉及侵權?就創作行為而言,在創作影視解說類短視頻時,作者要遵守哪些底線,其作品才會受到法律保護?就制度完善而言,今后的制度設計要從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更好地在著作權保護與合理使用之間,尋求利益平衡?本文旨在回答以上三個問題。
二、性質界定:谷阿莫影視解說短視頻之侵權屬性分析
依據大陸《著作權法》,欲探討谷阿莫制作并發布影視解說類短視頻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則首先要考察三大命題:其一,谷阿莫制作的短視頻是否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其二,谷阿莫制作短視頻所使用的素材是否來源于正規渠道;其三,谷阿莫制作并發布短視頻是否具有營利之目的。
(一)短視頻屬性之分析
《著作權法》第三條規定了作品具體的八種類型和一項兜底條款。通說認為,構成作品應具備三項構成要件:其一,該作品是人類的智力成果;其二,該作品具有獨創性;其三,該作品具有可復制性。因影視解說類短視頻固然屬于人類的智力成果,故而該要件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對《著作權法》第三條進行法教義學解讀,可知可復制性和獨創性是評價某種作品是否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的核心要素。可復制性是指作品能夠以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并能為他人所感知且可得以某種形式之載體進行復制的特性,最重要的是,這些作品可以通過特定的傳播媒介進行傳播。谷阿莫所制作的視頻自然符合作品可復制性之要素,需進一步考察的是,其制作的視頻是否符合獨創性之標準。
我國學界對于獨創性之判定標準存在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以吳漢東和王毅教授為代表,以傳統大陸法系著作權為基點。他們認為,獨創性是判定某一成果是否成為作品的最低判定要件和標準,只要一項作品體現了作者的智力成果并且反映其人格,具有作者獨有的思考,就應該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3]。劉春田教授亦認為,作品的構成要素對于作者而言,是付出了勞動,體現了作者個人的思想和情感[4]。第二種觀點以李明德、李偉文等學者為代表,主要借鑒英美法系的版權法理論進行解釋,其認為,獨創性僅要求作者獨立創作,并具備最低創造性即可,但并不是簡單地適用“額頭流汗規則”,而是在付出勞動的基礎上有一定的創新。第三種觀點是上述兩種觀點之中和,一方面既承認作品是作者智力成果的集中體現,另一方面又將“一定的創造性”列為作品的評判標準[5]。而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多將獨創性定義為作者獨立創作的觀點。比較典型的案例為“《宰相劉羅鍋》著作權糾紛案”,該案中,電視劇《宰相劉羅鍋》版權方被小說《劉公案》的著作權人起訴,法院認定該案原告所稱的整體故事情節來源于民間故事,而非原告所創,因此不具有“獨創性”,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我們可將影視解說類短視頻切割成兩個相對獨立的部分:第一部分中的素材來源于原電影中的各種鏡頭和畫面,第二部分是視頻制作者對該素材進行的一種主觀的解讀。對于第一部分而言,其主要的鏡頭都來源于電影的原始畫面故而當然不存在獨創性的問題。接下來探討第二部分視頻著作者的解說是否具有獨創性,這是判斷整個短視頻是否具有獨創性的關鍵。通過考察此類短視頻便可知,其雖然基于原始電影畫面進行創作,但是該創作出的成果已經超過原影片所要表達的內涵,主要是因為視頻制作者在其中添加了自己對于影片獨特的、主觀的見解。正因如此,不同的視頻制作者對同一部電影才有不同的解說范式和解說風格。在谷阿莫的系列短視頻中,谷阿莫通過其具獨特的口音聲調、極具個人特色的解說文案對原始影視作品的畫面進行別具一格的編排剪輯之后,所形成的“新”作品已經突破了原始作品的界限,并且能夠明顯為外界所區分,所以谷阿莫二次創作的短視頻具有獨創性,應當被評價為《著作權法》意義上之作品,故可納入《著作權法》第十三條演繹作品的保護范疇。
(二)短視頻素材來源之解讀
通過上述分析縱然得出谷阿莫制作的影評類短視頻屬于演繹作品,但此并不能當然導出其制作的短視頻可得侵權豁免的結論,仍需探討谷阿莫制作短視頻所使用的原始電影的素材來源,才可進一步確定其行為的性質。
谷阿莫在制作有關電影《唐人街探案》《鯊灘》《荒野獵人》等影視類短視頻時,出現了相關影片仍未公開于影院上映或上映時間過于短暫之情形。有些電影甚至尚未將相關畫面公之于眾,就被谷阿莫從不明渠道獲取相關片段,并制作短視頻公布于網絡。依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三條規定:“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其著作權由改編、翻譯、注釋、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谷阿莫在在未取得相關影片版權人意思表示同意之情形下,擅自將特殊渠道獲取的電影片段制作成解說類的短視頻并在網絡上公開傳播,在這些電影尚處于法律保護的情形下,此舉顯然侵犯了權利人的著作權。進行二次創作的作者應當堅守的首要底線,就是所采用的素材畫面必須通過合法的途徑所取得[6]。因此,筆者認為,縱使谷阿莫制作的短視頻本身已經超出了原始電影畫面所傳遞的要素,但只要其使用之素材是通過非法手段下載而得,且謀取了商業利益,則依據我國版權法之規定,該行為就應當評價為侵犯著作權之行為。
(三)制作短視頻目的之檢討
探討谷阿莫制作的短視頻是否構成侵權,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其是否具有營利之目的。盡管谷阿莫聲稱制作該視頻出于公益目的,屬于合理使用之范疇,但考察其背景便可知,他已經通過影視解說類短視頻的制作與發布賺取了豐厚的商業收益。首先,谷阿莫是YouTube網站的簽約視頻制作者,這意味著他在網站上發布的視頻的點擊量和觀看人數與自身收益成正比例關系,理論上,谷阿莫的視頻觀看的人數越多,其收益越大。據我國臺灣地區三立新聞網刊登的數據,2017年谷阿莫因在網絡上發布視頻而獲得的年收入為1413萬元,該量級的收入水平是我國臺灣地區YouTube視頻網站的頂流。其次,谷阿莫的賬號擁有眾多流量粉絲,關注對象的增多意味著傳播面的廣泛,廣告商紛紛尋求合作,短視頻中被插入了許多商業廣告,谷阿莫亦因此獲得收入。在大陸Bilibili視頻網站,谷阿莫可通過網友們的點贊投幣積攢流量,在“流量為王”的網絡自媒體環境下,谷阿莫通過來路不明的電影原始素材制作視頻,賺取了大量收益。故而,他制作該類短視頻并在互聯網上傳播的行為顯然是著作權侵權行為。
綜上,縱使谷阿莫創作的短視頻系具有獨創性的作品,可由于短視頻素材來源的非法性,以及隱藏在該視頻背后的商業利益和營利目的,他發布在大陸網絡平臺上的短視頻作品無疑具有侵權屬性。但這又引申出另一個問題,影視解說類短視頻一定具有天然的侵權性嗎?作為該類視頻的創作者,要遵守哪些底線,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受到到法律保護?這就涉及《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制度。
三、底線思維:著作權合理使用之邊界
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了合理使用制度,并列舉了十二種合理使用的情形,凡符合這十二種情形之一的,均無需著作權人的同意即可使用該作品,且無需向其支付報酬。這些情形分別是:為個人學習、研究或欣賞;為介紹、評論或說明某一問題;為報道時事新聞而再現或引用;媒體刊登或播放其他媒體已發表的時事性文章;媒體刊登或播放在公共集會上的講話;為課堂教學或科學研究;為執行公務而使用;為圖書館等為陳列、保存版本需要而使用;為免費表演;復制陳列在室外的作品;將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改成盲文。關于本文所討論的影視解說類短視頻可納入到《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第2項所規定的形式,即,“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即“適當引用”。因此,合理使用要以適當引用為標準。
可當追問要如何精準地判斷合理使用時,就會發現我國著作權法律體系尚缺乏相關規定,于是本文轉向借助國際先進經驗。國際通行的判斷標準,主要有“三步檢驗標準”(Rule on Limitation of Copyrights)和“四要素檢測法”(Four-element Method)。“三步檢驗標準”濫觴于1886年的《伯爾尼公約》,其具體內涵是,必須在特定情況下否則不得與作品正常利用相沖突,不得不合理地損害權利人的合法權益[7]。“四要素檢測法”源自美國的《1976年版權法》,這一判定標準從四個層面對合理使用做了界定,分別是使用目的(Purpose of use)、受版權保護的性質(Natur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使用比例(Proportion)和價值影響(Influence of value)。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知識產權法體系的發展,主要是建立在對美國知識產權保護先進經驗的吸收借鑒上。因此下文采用“四要素檢測法”對合理使用之邊界進行厘定。
其一,從作品使用目的這一要素進行考察,探討二次創作中使用的作品是否用于商業目的。在谷阿莫案中,被告二次創作的作品與原始作品之區別可為外界所區分,從形式上看,觀眾觀看谷阿莫上傳至網絡上的短視頻時,并未向其支付任何費用,因為觀眾可以在相關視頻網站免費觀看谷阿莫的短視頻。但從實質角度觀察,谷阿莫在制作視頻時,主觀上沒有營利之目的,但是通過視頻獲取的點擊量和流量客觀上仍然為其獲取了巨大的商業利益。一言以蔽之,谷阿莫雖未直接從觀眾處收取費用,但通過流量和廣告收入,他仍然賺取了收益,而對原作品的使用在客觀上是否可得獲利,則是判定是否納入合理使用制度保護的重要衡量標準之一。
其二,檢討受著作權保護作品的性質這一檢測要素,該要素指被合理使用的作品應當為業已發表的狀態,至少應當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可以任意接觸到該作品。反之,尚未公開發表的作品是不能適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原則上,判斷某一作品是否納入合理使用制度的保護范圍,應當采取不同的判斷標準。
其三,檢視使用比例,該要素指引用的原始視頻素材與二次創作形成的視頻會形成一定之比例,而這一比例是否可替代原作品則需要進一步探討。一般而言,引用的比例與原作品的替代率成正比,引用原視頻的比例越高,越容易對原作品產生替代。只有對原作品非核心部分的少量引用才能評價為合理使用,谷阿莫通過二次創作形成的短視頻,畫面幾乎均來自原作品,其中還有對電影經典畫面的摘取,但從比例上看,引用對原視頻而言所占之比例甚少,并不會當然發生原作品被二次創作的作品替代的情形。
其四,對價值影響考察,其中的“價值”為影片的商業價值。該要素著重考慮使用行為對著作權人的經濟利益所造成的影響。在谷阿莫案中,原告訴請的理由之一,是被告谷阿莫進行二次創作的素材并未得到原告方的授權,而擅自使用影片素材,給后續影片的上映帶來了困難,給原告造成了經濟損失。谷阿莫二次創作可以歸結為介紹或評論,但涉及引用數量,我國著作權法律制度中缺乏可操作的具體標準,給當前著作權糾紛案件審判實踐帶來了困惑。
四、制度完善:合理使用制度之修訂
著作權的限制直接關系到著作權人、作品的使用者和社會公眾三者之間的利益[8],故而是著作權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網絡數字技術的發展,我國《著作權法》面臨著諸多挑戰,而合理使用制度是平衡表達自由和著作權保護的杠桿,修訂完善合理使用制度是更好指導司法實踐之因應,亦是著作權法律制度回應現實需要的應有之義。
首先,從比較法層面入手,遵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充分借鑒國外著作權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的精華和有用元素。其次,從概念法學的視角入手,對相關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填補我國著作權法對滑稽模仿、二次創作的概念缺乏之空白。再次,從司法實踐入手,完善著作權法實施細則以及相關司法解釋,為司法實踐提供指引。最后,要進行必要的價值衡量,尋找到著作權保護和表達自由間的平衡點,兼顧二者之動態平衡。
在當代,關于著作權糾紛的案子愈發增多,一定程度上體現人們版權保護意識的提升。著作權的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權人合法權益和二次創作利益的“平衡點”,如何完善該“平衡點”,兼顧上述二者之利益是法律制定者和司法工作者應當考慮之事。應當看到,通過修訂、完善現行著作權法律制度實現兩者利益的平衡,能夠實現既保護著作權人合法權益,又尊重表達自由之價值。實施知識產權強國戰略需要民眾的智力支持,創造出一部又一部的優秀作品,這里的“創造”既包括“原創”,亦包括“原創”基礎上的“二次創作”,我們要在二者間尋求平衡。
五、結語
應當看到的是,《著作權法》本質上屬于私法,而在私法慈母般的眼神里,每一個主體皆為一個國家。在著作權法中確立“合理使用”制度,是法律追求人文關懷的應有之義。在當今的數字化時代,立足于時代的特殊性,對作品適當引用的合理限制,應當成為著作權保護的有效制度供給,這樣才能保障影視市場的正常運行并推動科學文化事業的創新和發展,使公眾利益和著作權人利益始終維持在價值衡量中尋求動態平衡。
參考文獻:
[1]程麒臺.影視解說視頻的著作權侵權問題——從谷阿莫被起訴說起[J].中國電影市場,2019(5).
[2]江宇琦,馬晨歌.谷阿莫被起訴,“×分鐘帶你看完電影”到底侵不侵權?[Z\OL].壹娛觀察,(2018-06-09).
https://mp.weixin.qq.com/s/pSfCyOh-U9xamfE4WIiwVw.
[3]吳漢東,王毅.著作權客體論[J].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0(4).
[4]劉春田.知識產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57.
[5]陳亦凡.影評類短視頻是否會侵害影視作品著作權——以谷阿莫案為切入[J].河北企業,2019(7).
[6]董天策,邵鑠嵐.關于平衡保護二次創作和著作權的思考——從電影解說短視頻博主谷阿莫被告侵權案談起[J].出版發行研究,2018(10).
[7]張曼.論TRIPS協議中“三步檢驗法”存廢之爭和解決途徑[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1).
[8]吳漢東.知識產權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83.
作者簡介:林威宇(1997—),男,壯族,廣西南寧人,單位為中南民族大學法學院,研究方向為民法學。
林威光(1995—),男,壯族,廣西南寧人,廣西科昌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研究方向為行政法學。
(責任編輯:馮小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