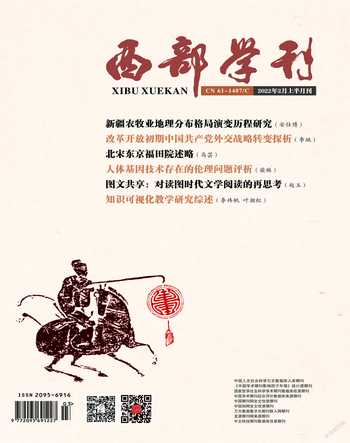從郭店楚簡《五行》篇“惪”字看先秦儒家心性論
摘要:“德”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德”字在古文獻中寫作、(甲骨文)、(金文)、(竹簡文)等,大體上是從殷商時期的“無心之德”到兩周時期的“有心之德”,再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直心之惪”。從“德”字的演變過程可以看出不同的時代所關(guān)注的不同問題。在郭店楚簡中,“德”字都寫為,即“惪”字。從字形來看,從直,從心,當理解為“直心之德”。據(jù)郭店楚簡《五行》篇有關(guān)“惪”的論述,“惪”可以引申出“誠”意,由此開啟了儒家以“誠”為核心的心性之學(xué),其主要代表即思孟學(xué)派的《中庸》,以及后世宋明理學(xué)對于“誠”的繼承與發(fā)展。
關(guān)鍵詞:《五行》;德;惪;誠
中圖分類號:B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03-0097-04
一、德字源流
(一)無心之德
“德”字在殷商時期甲骨文中寫作,左邊,表示道路或在道路上行走,右邊,即古“直”字——。一個明顯的特點是,此時的“德”字中尚未有“心”字出現(xiàn)。對于目字上方是一豎,還是一“十”,有不同的說法。《說文解字》說:“直,正見也,從,從十,從目。”認為目上為一“十”。對此,商承祚先生認為,“直”字在甲骨文中寫作“”,“象視線平直之形”,段氏“其說附會”。徐中舒先生在《甲骨文字典》中說:“(直)從目上一豎,會以目視懸(懸,懸錘),測得直立之意。金文作(《恒簋》),豎畫已訛為,小篆乃訛為十,與十由丨訛為十同。”[1]認為目上當為一豎。從直字的本義來看,理解為目上一豎,表示直視更為合理。若理解為十目,則與直義相去較遠。對于“十目”之附會或許從曾子那里就開始了:“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①。這里“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必有出處,“十目”則自然會讓人聯(lián)想到“直”字和“惪”字,故而曾子這里所論“十目”很有可能就是從“惪”“直”的字形聯(lián)想闡釋而得。
郭店楚墓竹簡是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出土的,郭店一號楚墓M1發(fā)掘出竹質(zhì)墨跡竹簡共804枚,其中有字簡730枚,共計13000多個楚國文字。楚簡包含多種古籍,其中三種是道家學(xué)派的著作,其余多為儒家學(xué)派的著作,所記載的文獻大多為首次發(fā)現(xiàn),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郭店楚簡《五行》篇中說:“中心辨然而正行之,直也。”《說文解字》說:“直,正見也。”直即有直視、正視、端正的意思。《孟子》中有“浩然之氣,以直養(yǎng)而無害。”的說法,即以“正”養(yǎng)氣。《周易·系辭》曰:“敬以直內(nèi),義以方外。”即敬以“正”內(nèi),與“方”互文而言。故此在甲骨文中,最早的“德”字即表示“直視前方行走之義”[2],引申義為“依正見而行”。可見這里的“德”側(cè)重的是一種純粹外在的行動、行為。劉寶俊說:“‘德’的古字作‘徝’,本義當指人的行為舉止所體現(xiàn)的品行,與‘心’相對而異。”[3],如:
“克明厥心,哲厥德。”②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③
“朕心朕德,惟乃知。”④
“而《詩·邶風(fēng)·雄雉》‘百爾君子,不知德行’,《詩·大雅·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周頌·敬之》‘示我顯德行’,均將‘德’與‘行’聯(lián)言,都可證明‘德’的本義不從‘心’、重‘心’而從‘彳’、重‘行’。”[3]可見,此時“德”只表示外在的一種正直的行為。
(二)有心之德
到了兩周時期,“金文中的‘德’字,大都在‘徝’字上增加了‘心’符,寫作‘德’‘’‘’‘惪’()諸形。”[3]由殷商時期的“無心之德”到兩周時期的“有心之德”,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改變。大多數(shù)學(xué)者認為,這是從殷商尊鬼神到周朝尊禮德之轉(zhuǎn)變的具體體現(xiàn):“周取代殷之后,周人深感‘天命靡常’,想要長久地占有天下,僅靠天命是不行的,進而開始了對天的懷疑,逐漸意識到要長久保有社稷,就必須盡人事,于是西周人發(fā)展了德的概念,體現(xiàn)在字形上,就是在西周初期的金文中,德字已寫作,加了心符。”[2]這一點體現(xiàn)在《尚書》中,就是出現(xiàn)了“敬德”“明德”“慎德”“惟德是輔”等概念。“德”字由更偏重外在行為的概念,逐漸向人的內(nèi)心深處引入,開始探究知行、內(nèi)外之間的關(guān)系,更加注重人的內(nèi)心精神世界對于外在行為的引導(dǎo)和控制作用。可見當時的人已經(jīng)認識到,行為最終是由人的心決定的,開始把內(nèi)“心”與外“行”兩個方面結(jié)合起來思考問題。
(三)直心之德
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了大量的無“彳”旁,只有“心”符的“惪”字,這應(yīng)是“具有明確的指向性和目的性”[3]的。隨著周朝禮樂制度的崩壞,禮樂愈來愈淪為一種形式,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為了尋求救世之策,此時的儒家學(xué)者更加專注于人的內(nèi)心,想去探尋解決之道,于是就直接使用去掉“彳”旁的“惪”字,由此開啟了儒家心性論的深入發(fā)展。
在郭店楚簡《五行》篇中,“惪”字與內(nèi)心的緊密關(guān)系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所謂仁、義、禮、智、圣五者,“形于內(nèi)謂之惪之行,不形于內(nèi)謂之行”。這里明確區(qū)分了“惪之行”與“行”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惪之行”是仁、義、禮、智、圣五者“形于內(nèi)”,即“形于心”,也就是真誠地發(fā)自內(nèi)心,是內(nèi)心真正具有這種德行,擁有堅實的內(nèi)在基礎(chǔ)。王中江說:“它旨在強調(diào)一種真正的道德行為是發(fā)自內(nèi)心并有具體結(jié)果的行為。”[4]“行”則更側(cè)重外在行為,不一定有內(nèi)在基礎(chǔ),即不用真誠地發(fā)自內(nèi)心,同樣可以表面上做到。因此,相較而言,“惪之行”是更加強調(diào)內(nèi)在基礎(chǔ)的一種“行”。帛書《五行》說部在解釋“得則不忘”與“形則不忘”中的“不忘”時說:“不忘者,不忘其所思也,圣之結(jié)于心者也。”這種“不忘”是主體內(nèi)在具有了“仁”“智”“圣”等“惪之行”,將其“內(nèi)結(jié)于心”,達到了一種真誠的、非常穩(wěn)固的狀態(tài)。
另外,《五行》篇中還將“樂”的內(nèi)心情感體驗與“惪”聯(lián)系起來:
“不樂無惪。”
“和則樂,樂則有惪,有惪則家邦興。”
“聞道而樂者,好惪者也。”
這里把是否產(chǎn)生“樂”的情感體驗,作為檢驗“有惪”還是“無惪”的標準,是值得重視的一個觀點。“樂”的情感體驗在孔子那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比如《論語》中提到:
子曰:“學(xué)而時習(xí)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⑤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⑤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⑥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⑦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⑦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⑧
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⑧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jié)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矣。”⑨
可以看出,在孔子那里,“樂”體現(xiàn)出的是一種境界或狀態(tài),如“不亦樂乎”“未若貧而樂”“長處樂”“不改其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山”“樂水”“樂在其中”“樂以忘憂”“益者三樂”“損者三樂”等,可以體會到在“樂”所表現(xiàn)出的達觀、智慧和仁愛的道德境界。但是在孔子那里并沒有將這種“樂”的情感與是否有“德”直接掛鉤,《五行》篇中的“不樂無惪”可以說是對于孔子“樂”論的進一步發(fā)展。當真正達到“樂”的境界的時候,也就是達到了一種真實不虛的體認的境界,完全發(fā)自內(nèi)心,毫無牽強與虛偽,這樣才真正能夠被稱為“有惪”。
“惪”與內(nèi)心的緊密關(guān)系,還體現(xiàn)在鄭玄注《周禮》中。鄭玄在注解“敏德以行本”⑩一句時說:“德行,內(nèi)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直接將“德行”做了內(nèi)外之分:“德”內(nèi)“行”外,這也是秉承了兩周以后,尤其是春秋戰(zhàn)國以來人們對于“惪”字的理解。
在《說文解字》中,對“惪”字的解釋為:“惪,外得于人,內(nèi)得于己,從直,從心。”段玉裁注:“內(nèi)得于己,謂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謂惠澤使人得之也。”這里“內(nèi)得于己”“身心所自得”,都是講的“惪”與內(nèi)心的直接關(guān)系,不過這里聯(lián)系儒家“內(nèi)圣外王”之學(xué),加上了“外得于人”,繼承了《大學(xué)》八條目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由內(nèi)而外的學(xué)術(shù)理路,其中“充盈著道德義務(wù)感和社會責任感,帶有濃厚的儒學(xué)色彩。而且也是對‘德’的‘內(nèi)在意義’或‘內(nèi)在價值’的確認。”[2]可見一直到漢朝,人們對于“德”的理解,還是保留著緊密聯(lián)系“內(nèi)心”的理解。
二、天道之“惪”與天道之“誠”
通過以上關(guān)于“惪”字的討論,如“形于內(nèi)”“不忘”“樂則有惪”“不樂無惪”“內(nèi)得于己”等,可以說最能體現(xiàn)“直心之惪”這些特點的就是一個“誠”字。所謂“形于內(nèi)”“內(nèi)得于己”,就是達到了一種“誠”的狀態(tài),是主體的真實體認,是相對比較穩(wěn)定的,所以才會“不忘”,所以才能產(chǎn)生真正“樂”的體驗。真正產(chǎn)生了“樂”的體驗,就是達到了“誠”的境界。雖然先秦儒家關(guān)于“德”的條目有很多,如“三德”:智仁勇;四德:仁義禮智;五德:“仁義禮智圣”;六德:“圣智仁義忠信”等,都未將“誠”列入其中,但“惪”字本身就內(nèi)含著“誠”的意蘊,可以說“誠”是所有這些德的條目的根基,失去了直心之“誠”,這些德的條目就都會淪為虛設(shè)。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失去了“誠”的根基,則條目越多,人偽就越多,徒具形式,而無實情。“君子養(yǎng)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所有的道德原則,都要建立在“誠”的基礎(chǔ)之上,這是“惪”字本身內(nèi)在規(guī)定的。
對于“直”字,我們今天也還經(jīng)常用到“直腸子”“直性子”等詞,表示一個人有什么說什么,真實地表現(xiàn)自己內(nèi)心的想法。“直心”之“惪”也可如此理解,即真誠地遵照自己的內(nèi)心,毫不虛偽。然而“真誠地遵照自己的內(nèi)心”依然需要尋找一個合理的根據(jù),因為不論行善或作惡都可以“真誠地遵照自己的內(nèi)心”。這個根據(jù)的合理性正是來源于它的超越性,于是儒門后學(xué)便又回到了那個自殷商以來的具有超越性的“天”的概念,認為這種“直心之惪”是來自于上天的“天道”“天德”。
郭店楚簡《五行》篇中有:“善,人道也;惪,天道也。”把“惪”提升到“天道”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庸》中,相應(yīng)地把“誠”也提升到了“天道”的高度: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zhí)之者也。”
孟子繼承了《中庸》的這種思想:
“居下位而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于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從“天道之惪”到“天道之誠”,是對“惪”的進一步明確,“誠”就是對“形于內(nèi)”而“不忘”的“惪之行”的另外一種表述,所謂“誠于中者,形于外”①,“至誠無息”。由此開啟了儒門“誠”論: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jīng)綸天下之大經(jīng),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依?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茍不固聰明圣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達到了“至誠”的境界,就可以“與天地參”“能化”“如神”“不息”“可以前知”“能經(jīng)綸天下之大經(jīng),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所謂“至誠”的境界,就是一種“形于內(nèi)”的境界,一種真實“自得于己”的境界,唯有達到這種境界,方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進一步動己、動人、動物;進而化己、化人、化物,從而參贊天地之化育。同時這種“至誠”的境界是不容易達到的,“茍不固聰明圣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5]
故此,我們認為,“惪”與“誠”之間本身就存在著內(nèi)在的緊密關(guān)系,正是由“惪”字出發(fā),才發(fā)展出來先秦儒門思孟學(xué)派的“誠”論,由此開啟了后世宋明理學(xué)關(guān)于“誠”論的濫觴。邵雍和周敦頤就非常重視“誠”。邵雍說:“至理之學(xué),非至誠則不至。”[6]154“先天學(xué)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6]171。周敦頤認為“誠”乃“圣人之本”“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認為“誠”是所有德行的根本和源頭。程頤、程顥進一步發(fā)展出了“誠”“敬”的功夫:“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朱熹繼承了二程關(guān)于“誠”“敬”的思想,將“誠”理解為“實”,將“敬”理解為“畏”,他說:“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誠只是一個實,敬只是一個畏。”王守仁則直接說:“誠是心之本體。”
三、結(jié)語
“德”字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國人自古以來都非常重視一個人的德行。考察“德”字的原始字形,及其后世字形的演變,對于更好地理解什么是“道德”,理解中華先民對于“德”字認識的階段性轉(zhuǎn)變,以及理解古代儒家學(xué)派思想的演化過程都有很大的幫助。“德”字的字形從殷商時期的“無心之德”,到兩周時期的“有心之德”,再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直心之惪”,是一個逐漸由外至內(nèi)的過程,從開始的側(cè)重表現(xiàn)外在的行為,到聯(lián)系內(nèi)心的行為,再到更為專注于內(nèi)心的“惪”,可以看出不同的時代人們因其所關(guān)注的不同問題而探索不同的解決方法。通過對郭店楚簡《五行》篇所揭示的“惪”字內(nèi)涵的分析:“形于內(nèi)”“不忘”“惪天道也”“樂則有惪”“不樂無惪”等,我們發(fā)現(xiàn),“惪”字本身即內(nèi)涵著“誠”的意蘊,故而先秦儒門之“誠”論即來自于“惪”字所蘊含的直心真誠之意。
注釋:
①語出《禮記·大學(xué)》。
②語出金文《師望鼎》。
③語出《尚書·泰誓》。
④語出《尚書·康誥》。
⑤語出《論語·學(xué)而第一》。
⑥語出《論語·里仁第四》。
⑦語出《論語·雍也第六》。
⑧語出《論語·述而第七》。
⑨語出《論語·季氏第十六》。
⑩語出《周禮·師氏》。
語出《禮記·中庸》。
語出《孟子·公孫丑章句》。
語出《五行》。
語出《六德》。
語出《荀子·不茍》。
語出《孟子·離婁上》。
語出《二程集》。
語出《傳習(xí)錄上》。
參考文獻:
[1]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1385.
[2]汪鳳炎.“德”的含義及其對當代中國德育的啟示[J].華東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06(3).
[3]劉寶俊.戰(zhàn)國楚簡“惪”字形義考辨[J].語言研究,2014(1).
[4]王中江.簡帛五行篇“惪”概念的義理結(jié)構(gòu)[C].國際儒學(xué)聯(lián)合會.國際儒學(xué)研究:第十九輯(上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210.
[5]楊天宇.禮記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711.
[6]邵雍.邵雍集[M].郭彧,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17.
作者簡介:史逸華(1988—),男,漢族,天津人,單位為天津商業(yè)大學(xué)寶德學(xué)院,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xué)。
(責任編輯: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