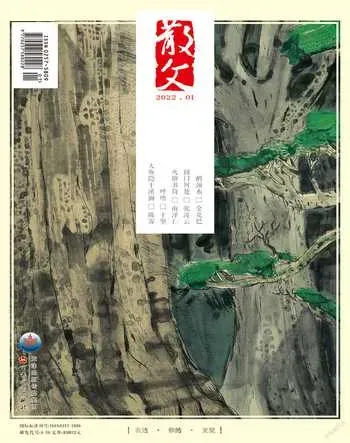陪病記
蔡舒曉
學生公寓總共二十層,我和李菲的宿舍在第十九層,是朝北背陰的兩人間,兩張床豎接著挨墻靠在一起,占據(jù)了房間一半面積,床對面另外兩張高砌至天花板的書桌填滿了另一半,中間留下一條窄窄的過道,寬度剛好可以鋪開一張瑜伽墊。去年開學初搬進來的時候是夏末,假如沒有打開前門窗,即便是天黑以后,仍然能感覺到鋼筋水泥緩慢散發(fā)出白天儲存的光照熱量,被關在昏暗房間里的空氣迅速膨脹擴張,用李菲的話說,是“你有沒有感覺到熱到血管和心臟都要停跳了”。
好在我們還擁有一個視野敞亮的北陽臺,雖然,倘若兩個人一起出現(xiàn)在陽臺眺望遠方的五角場或者觀察樓下的籃球場,無意間互相觸碰到的胳膊肘,就會提醒我這是個不足一平方米的空間,但是從這里能看到灰撲撲的高樓大廈、地鐵口魚貫而出的人群和正在繼續(xù)填鋪擴張的城市高架,是我和李菲晚飯后站立消食的第一選擇。
李菲去俄羅斯旅游已有兩周,一個人在宿舍時,我時常在瑜伽墊上將自己扭成各種形狀的結(jié)來活動肌肉與骨骼,在每個動作的靜止保持階段,我的眼睛無事可做,只能反復捕捉李菲的藏書封面。《第二性》《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和《閣樓上的瘋女人》,它們封皮的邊角翹起,可以想見李菲曾捧著它們在圖書館苦讀、與同學進行專業(yè)辯論,用花花綠綠的印刷字圍筑起一個清涼美妙的世界。
走去學校需要經(jīng)過一條梧桐大道,太陽從樹蔭間隙投射到皮膚上,仍然帶來灼燒的感覺,李菲卻發(fā)來消息說她的行程已經(jīng)到了西伯利亞,很快就回來了。選擇短暫逃離9月份的上海是一個明智的決定,西伯利亞,僅僅是聽到這個詞都能想象到連綿的寒雨與藍色的冰河,還有鼻頭凍得通紅的人們。
這天早晨我還沒有醒透,在房門口響起一陣丁零當啷的鑰匙碰撞聲后,我看到一只巨型行李箱被推進來,李菲輕聲地喊了我一聲,把臉忽地湊過來。隔著蚊帳密集的菱紋,能看到她的小雀斑隨著笑容舒展開,長途旅行后的眼下長出一條深色的疊紋。她放下背包就開始急切地脫靴子脫衣服直奔浴室,皮質(zhì)棕色短靴的鞋面上比從前多出了褶皺和泥點,軟軟地搭在椅子邊。水聲結(jié)束后,她扒拉開蚊帳坐到我的床沿上,一個伴隨著短暫喉擦音收尾的名字帶著沐浴露的香氣出現(xiàn)在我耳邊:奧勒格。
李菲帶給我的特產(chǎn)巧克力上印著一個包裹著頭巾的嬰孩,純度很高的黑巧克力在嘴里慢慢化開伴隨著奇妙的發(fā)熱感。李菲說她和同伴,高中同桌的女生小波,一到俄羅斯就遇到了連續(xù)五個雨天。對于體重不到九十斤的她來說,除了牛肉紅湯和大列巴面包外,還需要通過攝入這些便宜大塊的巧克力支撐自己拖著行李箱走在風雨交加的街頭,鉛鐵一樣厚重的云塊和俄式建筑物上層層疊疊堆砌的花紋帶給她巨物恐懼癥一樣的壓迫感。對刷成磚紅色的墻壁、鎦金吊頂?shù)奶旎ò搴突ㄉ彪s的床單桌布的審美疲勞以及日漸干癟的錢包,讓她們決定從來到莫斯科伊始,就住進價格便宜的青年旅社,正是在這間旅社略顯陳舊和雜亂的公共廚房里,她遇見了那個叫奧勒格的俄羅斯人。
當李菲和小波用本地生產(chǎn)的巨型土豆和青椒炒出一盤酸辣土豆絲慰藉思鄉(xiāng)之情時,奧勒格忽然出現(xiàn)在廚房里,對異香撲鼻的新奇菜式和兩位中國女生展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在用蹩腳的英語進行簡單溝通后,他立刻坐下來自來熟地分享起這道中國菜,然后手舞足蹈地將她們夸上了天。李菲說奧勒格是一個工程師,估摸三十來歲,因為他的年假與她們的行程在時間上完全重合,因為他對以中國菜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強烈興趣,奧勒格提議接下來的三天由他為她們提供義務導游服務。
“遇到奧勒格后,天氣忽然就好了起來。9月份的俄羅斯整體是一種色飽和度很高的感覺。莫斯科是他上大學的地方,哪里是隱蔽的地鐵入口,哪里可以買最便宜的套娃,他都知道,每個犄角旮旯他都熟悉,我和小波忽然覺得這次旅行有趣起來。”李菲輕聲細語的描述,像小眾電影里搖搖晃晃的開場鏡頭一樣,讓我眩暈而神往,僅是對著這些美妙的畫面和詞匯,就能設身處地、自然而然地補充起故事里的諸多細節(jié)和主人公的細碎心情。莫斯科不下雨的天空大多數(shù)時間呈現(xiàn)出一種遙遠的藍灰色,和本地人的瞳孔顏色相近。灰藍色瞳孔的奧勒格帶她們坐長長的下行扶梯感受前衛(wèi)的、充滿藝術(shù)沖擊力的地鐵站,參觀鮮艷明快的、金碧輝煌的克里姆林宮和紅場,拐進生活區(qū)的小巷子,向坐在路邊擺攤的老大爺買自制果醬和牛肉漢堡吃,味道純粹濃烈。他們一路聊兩個國家的歷史和現(xiàn)在,聊中國菜的主要菜式和做法,聊大學生活和就業(yè)打算,就這樣打發(fā)了兩天。
“然而這種輕松友好的氣氛終于在第二晚我們?nèi)ズ染坪髲氐淄呓饬恕!眾W勒格帶她們?nèi)チ怂髮W時代常去的酒吧,糖漿冰龍舌蘭酒下肚后,一首爵士樂響起來。“那是我很喜歡的一首英文歌,我忍不住搖頭晃腦起來,奧勒格露出了吃驚的笑容,然后用手指指酒吧中間的小舞池。”奧勒格眼神亮晶晶的,用磕巴的英語告訴李菲他很愛這首歌,于是他們離開座位走進舞池和其他年輕人一樣拉著手跳起了扭扭舞,旋律結(jié)束后他們意猶未盡,趁著熱度又跳了兩首。兩個人喘著氣大笑著走回座位的時候,感覺四周發(fā)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順著小波閃爍的眼神向下看去,李菲發(fā)現(xiàn)她和奧勒格的手還是牽在一起。
我看向李菲,作為室友客觀地說,她確實很有東方美人的特色,黑色的齊耳短發(fā),白凈面孔上幾粒小雀斑,笑起來的時候丹鳳眼和薄嘴唇格外迷人。按照之前的計劃,后天她們就要啟程去西伯利亞,在莫斯科的時間還剩不到二十四小時,奧勒格和李菲開始后知后覺地珍惜且規(guī)劃起來,喝過酒后的兩個人首先想到的緊要事情是讓奧勒格下載了微信。第三天的旅程成了李菲和奧勒格的專場,他們站在人來人往的街頭爭分奪秒地對視、互相講述著當下的心境,小波略顯尷尬地跟在不遠處。“我覺得小波還是有一點不開心吧,可能是因為我在異國把她撂在一邊,也可能是因為別的。”雖然此刻李菲已經(jīng)洗去了從莫斯科帶回來的所有塵埃和氣味,放松地靠在我旁邊,但是她的眼睫毛在宿舍白熾燈的照射下快速跳動著,濕漉漉的眼睛告訴我她仍沉浸在那時那刻的幸福感里,同時也友善地對沒有充分關注小波心情這件事進行了自我檢討。
李菲回來了,我與她的和諧舍友生活重新啟動。她在學業(yè)上仍然是那么用功,在對著沉重的專業(yè)書挑燈苦讀的間隙,甚至還給自己添了一項學習俄語的額外任務,時不時對著借來的俄語入門書發(fā)出一兩個難以捉摸的顫音。李菲另外一個顯著變化是睡前對著手機的時間明顯長了,我們開始打哈欠的時候,處于東三區(qū)的奧勒格在那一頭應該才剛下班。可能是因為兩個人都要字斟句酌地拼寫英語單詞,拖慢了互訴衷腸的進度。有時我半夜醒來,還看到她蒙眬著睡眼搗鼓手機,以至于白天她偶爾有些沉默和恍惚。在晚飯后站在陽臺消食時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中,李菲又鼓起熱情與我談起未來的打算,比如近期攢夠錢買飛去俄羅斯的機票,比如現(xiàn)在學好俄語去當?shù)刈x個博士的可行性,比如科學研究表明文科和工科的情侶組合是最有利于感情發(fā)展的,比如下次可以請奧勒格在冬天帶我們?nèi)タ簇惣訝柡加鲎匦堋!皧W勒格”這個名字逐漸成為我們黑白日常生活快速放映時的一幀彩片,成為沉悶空氣里可以探出頭看看遠方放飛思緒的北陽臺,成為一根時常跳動、提醒自己與遙遠的東三區(qū)存有聯(lián)系的敏感神經(jīng)。
轉(zhuǎn)眼已經(jīng)是10月末,空氣中的熱度逐漸消退,當自來水管流出的水觸手微涼時,這個城市一年中最愜意的季節(jié)到了。
遇見小波實屬偶然,那天我早早下課,路過宿管辦公室的時候被眼尖的阿姨叫住,說我們宿舍有訪客在這里等著。小波是個自來熟,沒聊幾句我就驚訝地得知,她不僅是李菲的同桌,兩個人還是遠房表姐妹關系,她手里提著的蝦干魚干特產(chǎn)就是李菲媽媽帶給她的。我把小波帶到宿舍,等她放下手里東西后,宿舍就顯得更加小了,于是我只好領她去陽臺透透氣。我想聊聊俄羅斯旅程應該是個不錯的話題,于是自顧自地開頭了,9月是個好時候,天氣不冷不熱,莫斯科的地鐵站個個特色不同確實值得多去幾次之類。當我說到奧勒格的時候,小波也露出了詫異的表情,她問我怎么會知道奧勒格這個人,我只好說李菲跟我詳細講過他們認識的過程,回國后也一直在聯(lián)系。小波哦了一聲,說奧勒格是莫斯科青年旅社的老板,確實很熱情友善,入住的晚上煮了熱騰騰的紅菜湯給她們吃,八十多歲的年紀還非要帶著她們兩個中國女生上旅社旁邊的街區(qū)轉(zhuǎn)轉(zhuǎn),但是沒想到回國后老爺爺還在和李菲聯(lián)系。是打電話嗎?我忽然感到一陣眩暈。小波止住話頭伸出胳膊指向樓下,李菲邁著輕快的步子,正在梧桐樹蔭間影影綽綽地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