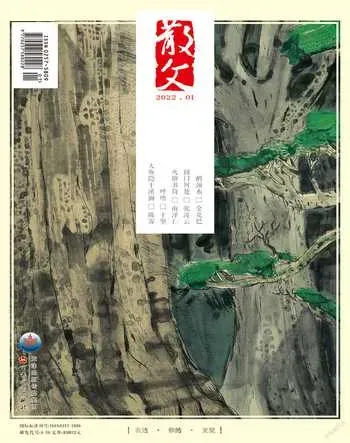重疊的影子
曉寒
我不知道祖母長什么樣子。當我知道有這么一個女人在家里停留過的時候,她已經習慣了天堂里的生活,我相信那里的日子和塵世中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照樣要忙著對付接踵而來的柴米油鹽。家里人很少談起祖母,小時候跟著去掃墓,父親和祖父也只是在一座墳墓前燒紙錢時說一聲:這里葬著你的奶奶。
后來,在漆黑的夜里,我躺在床上勾勒過祖母的樣子,試圖穿過時光的叢林,以此牽出一些蛛絲馬跡,還原那些支離破碎,讓祖母銹跡斑斑的過往重見天日。我在想一個二十九歲失落在夢中的女人,有怎樣的臉型,長著怎樣的眉眼,留著什么樣的頭發,喜歡穿什么樣的衣服。我勾勒的影子,在黑暗中晃來晃去,我不止一次給她換過臉型,更改過眉眼,梳不同的發式,穿各種顏色的衣裳。我看見她從黑暗中脫身而來,對著我笑,向我招手,喊我的名字。我以為這就是我的祖母了,突然又覺得這只是個陌生的女人。這時,我為祖母感到莫名的悲傷。
很長一段時間,祖母就以這樣的形式活在我的世界里,她忽遠忽近,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像是故事書里飄出的一個影子,等我剛要捕獲它時,它又飄進了那些漫漶的詞語中。才上學沒多久的那年,我去樓上找東西,無意中打開了一個箱子,沒刷油漆的小箱子里,裝著些零散的木頭。木頭的形狀各不相同,有的如拳頭大,有的比拳頭小,除了不規則的方形,大多數像誰的腳踩下的印子,只是不是整只腳的印子,是大半只,小半只,三分之一只,前圓后方,或者前方后圓 。
它們聚集在一起,悶頭悶腦,猶如一群乖巧的娃娃正在酣睡。和周圍那些臟兮兮的壇壇罐罐相比,這些木頭顯得干凈多了,沒有一點灰塵。我信手拿起一塊摸了一下,清涼和光滑像水一樣流過指尖。我對著樓板敲了敲,篤,篤,篤,聲音加劇了周圍的寂靜,讓我想起一只啄木鳥在黑夜里啄著一棵老樹的情形。我左看右看,還是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琢磨了一陣后,我覺得這有可能是玩具船上的部件,山里的孩子沒地方買玩具,也買不起玩具,一些簡單的玩具,像陀螺、水槍、彈弓、鐵環、三輪車、高蹺、風箏之類,都是家里人或自己一手一腳做的。祖父就擅長做這些小玩意兒,家里舀水的勺子、小時候躺的竹床,還有我去學校帶飯的飯桶,都是他做的。這些東西十分精致,看上去跟專門以此謀生的手藝人做的沒多少區別。
我拿了其中的兩塊下樓,沒多久,母親光著腳從菜地里回來,看到我拿著那兩塊木頭坐在門檻上,臉拉了下來,讓我放回原處。她說,你怎么什么東西都翻出來玩,這是楦,你奶奶留下來的。這次,我順從了母親的意思,飛快地把它放回了原處,雖然仍不知道楦是做什么用的。這是祖母留下的東西,以前我從沒聽說她留下過什么,仿佛她除了把自己帶走以外,連同她留在這個家里的腳印、影子、氣味以及夢中的囈語都一股腦兒帶去了另一個地方。她的生命短得讓人嘆息,像雷雨前的閃電,在眼角一晃就消失了。她留下這些楦,或許是想證明她在這個家里的存在,也或許只是一個無意的行動,就像一個人出遠門時,無法把某件東西帶走,就隨手丟在了那里。
很小的時候,我只記得腳上的舊鞋,鞋底脫落,鞋幫子翻了起來,鞋尖上露出的腳趾,像好奇的眼睛,探頭探腦地打量著外面的世界。我對唯一的一雙鞋子付出了一個孩子足夠的深情。夏天,雷聲碾過頭頂的烏云,暴雨開始清洗村莊,騰起的煙霧里,萬物都是飄浮的,搖搖晃晃從眼底淌過。風住雨歇,浮塵、淤泥、草屑、枯枝,都被沖進了水溝和河流。山路露出堅硬的筋骨,濕漉漉的石子散在上面,擺出一副慵懶的姿態,它們是雨水的遺物,懷抱著內心的寂靜。我們把鞋放在書包里,光著腳走在上面。石子還是像躲在暗處的敵人一樣,不時偷襲我的腳板,送來尖銳的刺痛。
我寧愿冬天快點到來,天地變成廣大的沉默,雪花像是大地放牧的羊群,隨風席卷而來,把山路鋪成軟綿綿的鞋底,供我健步如飛。剛把腳踩在雪地里時,就像遭到了寒冷的電擊,連牙齒都在痙攣。走一段后腳板變得通紅,就適應了,不冷了,或者說麻木了。到學校后,那個頭發花白的老人會用一個木桶給我們打來溫水,他是學校唯一的老師,他說,水不能太熱了,要不會把腳上的皮燙掉。洗過腳穿上鞋子,整整一天,我們都是屋子圈養的孩子,在里面歡笑、哭泣,臺階以外白茫茫的世界,成為我們不可逾越的禁區,似乎屋內外豎著一道看不見的樊籬。
有一年剛入秋,我腳上的鞋就油盡燈枯,充滿了分崩離析的征兆,母親見了說,過幾天丟了吧,給你做雙新的。她從席子下拿出一張壓平的竹殼,對著我的腳剪了個鞋樣,熬了碗濃稠的米湯,然后拿出一個竹籃子,籃子里裝著不同顏色的布條,那是平時做衣服時留下的邊角料,她把那些布條在門板上鋪一層,然后用棕刷刷上米湯,再鋪一層,用手壓緊,再刷米湯。這樣一層層往上鋪,直到厚厚的一沓,在底面分別蒙上整塊干凈的白布。放到太陽底下曝曬一天后,她從老書桌的抽屜里拿出一把刀子,刀鋒順著鞋樣的邊沿泅過,布屑紛紛揚揚地跌落,像風吹落樹上的雪條。
夜晚,母親開始搓麻線,她把兩腿并攏,上面擱塊凹面朝下的瓦,腳下放一碗水,身邊的竹籃里,是一個個漬好的麻線團。她隔一會兒在掌心里蘸點水,在手掌和瓦片的摩挲聲里,麻線變成一根根細細的繩子,勻稱,柔軟,歲月一樣悠長。接下來開始納鞋底,她把鞋底夾在一個木夾板上,雙腳把底座踩牢,食指戴上頂針后,從容地飛針引線。屋子里,煤油燈的光在風中影影綽綽,母親的額頭漸漸冒出汗珠。妹妹趴在墻角的竹床上酣睡,剛學會走路的弟弟躺在她身邊的搖籃里。外面,月光如雪,照亮了半邊臺階,草蟲在臺階下的石頭縫里低低地吟唱。
納好的鞋底,平整,結實,被細小的麻繩分成整齊的菱形的格子。那些格子,被一雙手賦予了不同的內涵,儲藏著斑駁的夜晚,星光、月色、犬吠、鳥啼,還有一個女人不曾命名的秘密。
鞋幫通常是青色的,這種顏色耐臟。用米湯漿過后,平貼在門板上,像一只攤開翅膀保持著狩獵姿勢的鷹。母親對著它輕輕一揮手,它扇動翅膀,唰的一聲從門板上飛了下來。在夾板上一針一線绱好后,母親將楦拿下樓來,從里面反復挑選,大小合適的話,就往鞋幫子上噴一口水,先在鞋尖上塞一塊,再塞鞋跟,接著又在中間加一塊或兩塊,用小鐵錘敲緊,然后放在太陽底下曬。楦過的鞋平展,順暢,如一個女人尚未出現皺紋的臉。
其實,新鞋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好穿,硬邦邦的,甚至還有些硌腳,穿過十天半月后,才逐漸感受到它的柔軟,一腳下去,像踩著一朵溫柔的云。洗過曬干拿在手里,還能聞到草木的清香,氣味來自棉、麻和水稻。土地養活的草木,總是以最原始的姿態抵達我們,貼近我們的肌膚,進入我們的身體,像母親的愛和慈悲,在我們的身體里形成一條河流。這條河流,不僅穿越個體,穿越族群,也穿越漫長的時間和遙遠的空間。
從此以后,我經常看到母親在燈火里忙著做鞋,那些誕生在母親手里的布鞋,依次穿到家里十幾口人的腳上,去打發一個個平常的日子,對付生活的作梗和非難。在一個冬天的夜晚醒來,我看到母親還在煤油燈下納鞋底,她弓著身子,雙腳擱在火籠上,不時伸手擦一下眼睛,將錐子在頭發上摩挲幾下,繼續飛針走線。月亮向著西邊的山頭奔去,風把蒙著窗戶的薄膜吹得嗚嗚響,霜打白了屋邊的草垛,對面山上,貓頭鷹咕咕地叫著,家里的狗冷不丁汪一聲,像是對它做出的回應。我如同陷入了一種濕滑且捉摸不定的夢境,突然覺得母親的樣子就是心目中祖母的樣子,她們有一樣的動作,一樣的神情,一樣的期待、歡喜和悲傷。母親的那雙手,看上去焦黑、笨拙、粗糙,形同蒼老的松枝,仿佛來自一個古老的年代。
有一年,下屋的鄰居把楦借去,還回來時少了兩塊,她跟母親說,是在烘鞋子的時候燒了。母親一聲不響地接了過來,祖父當時很不高興,黑著張臉,說了聲以后再也別想借了。鄰居走后,祖父把箱子里的楦一塊塊拿出來擺在地上,目光在上面一遍遍逡巡。隨后,他找來一根干燥的桎木,拿出斧頭、鋸子、刨子,忙碌了大半天后,兩塊楦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把那兩塊楦在磨刀石上磨得光滑,拿在手里左瞧右瞧,嘆息了一聲,說,可惜了,顏色對不上。
大姐和二姐還未出嫁時,就學會了做鞋,她倆是按照母親的意思,從打鞋墊學起的。那些平常的夜晚,母親坐在燈下做鞋,大姐和二姐坐在旁邊,手里拿著薄薄的鞋墊,針拖著長長的線,在她們手里穿梭,從鞋墊的一面穿過去,又從另一面穿過來,像是從一個夜晚走向另一個夜晚。剛開始最簡單,就是在鞋墊上打一個大大的“米”字。針像頑皮的孩子,一不留神,就戳破了她們的手指,血滲了出來,在指尖上形成一顆紅色的珠子,她們便把手指伸進嘴里吸一下。這時候,母親會側過頭看一眼,又繼續忙她手里的活兒,我只看到她的眉心皺了一下,仿佛那針尖正戳在她的手指上。剛開始打的鞋墊針腳稀疏零亂,東歪西倒,如同爬著群醉酒的螞蟻。慢慢熟悉后,針腳就變得細密、均勻,這時就可以打中等大的“田”字和“回”字,一雙鞋墊上,布滿了密密麻麻的格子,像一座沒有出口的迷宮。再后來,便隨心所欲地打一些花朵,這些花朵燦爛生動,有的來自地上,有的來自天空,還有一些,來自她們的想象。
大姐出嫁后,母親的腰板不再筆直,白發開始在她頭上興風作浪。她的視力已大不如從前,但還是會戴上老花眼鏡給我們做鞋。我們穿著她一針一線做的鞋,踩著密密的針腳,一個個走向了山外,而她的一生,卻被腳下的鞋牢牢地禁錮在巴掌大的村莊里。日子來來去去,花樣沒有翻新,母親也像以前一樣,把每一件事情完成得風風火火。大姐想得周到,她把那一箱子楦要了過去,說她喜歡楦的樣子,母親笑著大大方方給了她。逢年過節,大姐回來的時候,籃子里除了肉、面條、油餅這些東西外,還有一雙雙的布鞋,用一根橡皮筋箍著。
二姐出嫁后,又從大姐手里把楦接了過去。節日回來的時候,籃子里也有一雙雙的布鞋。我上初中那年的寒假,去二姐家小住,她看到我的鞋子破得不像樣了,說,我給你做雙新的吧。那幾天,我看到二姐每晚都在燈下忙碌,影子打在灰蒙蒙的泥巴墻上,那一舉一動,那專注的神情,就是另一個母親。恍惚間,我又看到了從未見過的祖母,她投下的影子,和母親的影子、二姐的影子,慢慢重疊在一起。那是幾個影子,又似乎只是一個影子。從祖母到母親到大姐和二姐,一代又一代,這些生長在山旮旯里的女人,都在沿著同一條路徑走著。從帶著最初的啼哭來到這個世界,就開始和木頭打交道,坐的搖籃是木頭,砍的柴火是木頭,陪嫁的桶子、腳盆、柜子是木頭,切菜的砧板是木頭,楦鞋的是木頭,夜晚躺著的床也是木頭。在命運的手里,她們也跟木頭一般,聽憑歲月一刀刀刨刨削削,直到把自己刨光削盡,再殮入棺木中,由一棵樹帶往泥土深處,若干年后,從青草覆蓋的墳堆上長出另一棵樹來。
我參加工作那年的清明節,二姐特意把楦帶了回來。她說,楦是祖母的,還是還給祖母吧。我們在祖母的墓前堆了些干燥的蘆箕和松針,把楦擱在上面。父親劃燃火柴,火苗躥起,傳來呼呼的響聲。云淡天闊,青山如岸,噼里啪啦的鞭炮聲,縱容了荒野的寂靜。火星飛舞,像燦爛的星辰,大大小小的楦,化作光,化作煙,最終化作一地灰燼。遠處傳來幾聲鳥叫,頭頂,燒焦的顆粒在空氣中起起落落,緩慢地墜降,成為一個漫長的鏡頭,仿佛道別。
那天,我們腳上穿的是皮鞋,已經很多年沒有用過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