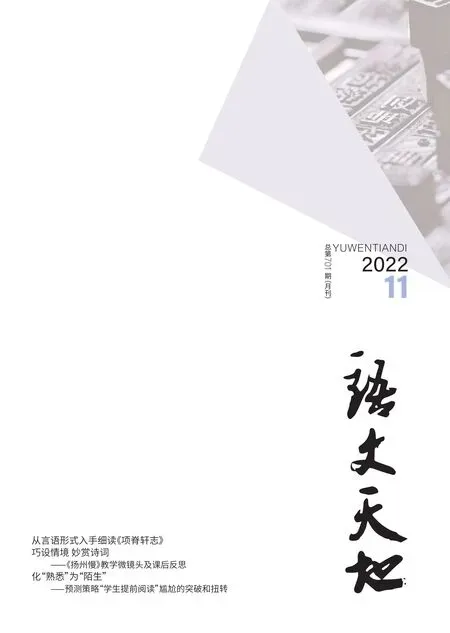多維融合將詞語理解落于實處
——以部編版四上《繁星》中的一組詞串教學為例
張童蘭
詞語,是語言的基礎單位。詞語的積累與運用,是訓練學生語文能力的基石。但常態的詞語教學,基本都是讀讀而已,或者置放于文本情境中,稍加點撥,了解大體意思,也就“鳴金收兵”了。事實上,詞語教學的價值不僅僅是為了消除閱讀障礙,解決生字詞,還可以綜合性地關聯多項思維,這是夯實學生語文能力和推動核心素養發展的重要渠道。
《繁星》是部編版四上第一單元的一篇略讀課文,筆者在學生整體性感知課文之后,設置了“學習詞串,想象畫面,積累詞語”的教學板塊,設置了詞串教學的策略。筆者所設置的第一組詞語是:密密麻麻、星群密布、半明半昧、搖搖欲墜。這是一組很鮮明描寫星星的四字詞語。筆者就以這一組詞語的教學為例,談談本人在這一方面的實踐和思考。
一、試讀與理解相隨,越讀越熟練
從整篇文章,到一組詞串,看似是篇幅的減縮,但在遴選、甄別的過程中,蘊藏著執教者豐富的教學思維,是基于易錯生字詞、課文內容、能力訓練點等多維角度,精心研制的成果。對于四年級而言,詞語教學不是重點,但完全不教,肯定不行,這就需要把握好分寸。
鑒于此,教師教學這一組詞串時,還需要依循學生的認知規律,將讀正確、讀熟練、讀流利作為基礎性目標。為此,教師可以設置這樣的教學板塊。
首先是該放則放。給學生自主朗讀訓練的機會。每個學生的原始經驗不同,可能遇到的障礙也就不同。放手讓學生自主讀,就是給予學生面對障礙,而又能夠克服障礙的契機。其次是該撥則撥。指名朗讀,不該是機械重復。學生聆聽一次,也是學習,所以再次指名朗讀,要求就應該水漲船高。教師延續從“正確”到“流利”的順序,讓學生越讀越自信,越讀越放松,越讀越流利。最后,組織學生全體朗讀,從指名讀時的針對性點撥,到全體朗讀時的強化印證。
此時,瑯瑯書聲,就成了詞串教學第一環節的成果,整體性反復朗讀縈繞在每個學生心中。語言的質感,無形之中滲透到每個學生的意識之中。
二、想象與理解交融,越思越明晰
教學詞語,理解是關鍵,更何況還是并不常用的詞語生活語言。但理解不能依葫蘆畫瓢。我們常用的查閱工具書這一方法,只能針對完全陌生的詞匯,即便是聯系上下文,也不能陷入就詞解詞的尷尬之中。
教師在學生朗讀的基礎上,首先,要做到“對象有格”。詞語表達的內容非常廣泛,適用的對象也絕非一個。將詞語從課文中提取出來,以詞串的形式出現,脫離了具體的語言情境,容易將詞語架空在浮層上。在學生熟讀詞串后,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回憶課文內容”,以一唱三嘆的方式,反復追問、強調“密密麻麻、星群密布、半明半昧、搖搖欲墜”都指向于——星星。隨后,再組織學生反復讀這一組詞串——這一遍的朗讀,意義發生了重大改變,不再基于正確、流利的層面,而是緊扣定格的對象,利用滲透進內心的詞語質感,初步建構感性的畫面積淀。
其次,要做到“想象有度”。緊扣詞語展開想象,與創作天馬行空的想象類作文完全不同。想象習作,雖有“合理”的要求,但仍以“新奇”“大膽”為要,而詞語想象,則是對詞語所裹挾內涵的形象性釋放,是對其高度概括之后的“膨脹化”再現。而這種“度”,主要體現在對詞語的理解上。
例如,教學詞串中的“半明半昧”時,學生想象星星像活了一樣,在對我眨眼睛。教師不能僅僅應付式地贊賞“想象形象,富有童趣,非常棒!”就直接了事,還可以相機追問:為什么“半明半昧”,就讓你覺得是星星在“眨眼睛”呢?看似追問原因,實則回歸詞語理解,引領學生用說明性思維,將“半明半昧”這個詞語,“時亮時暗”的畫面,與星星眨眼睛的狀態關聯起來。
面對學生精彩生動的想象,教師及時捕捉動態生成的資源,以追問的方式,為學生開辟思維的岔道,再現思維過程,達成了“理解和想象一色”的境界。
三、反芻與理解結合,越品越有味
我們所理解的詞語解釋,是由詞到語句的延展過程,是單向的。事實上,詞語的理解應該是從詞到句、再從句到詞的回環過程,是雙向的。
以“密密麻麻”為例,基礎學情下,學生都將其理解為“多”。這肯定是對的,但教學不能止步于此,需要教師鼓勵學生大膽想象,用自己想到的畫面,具體展現“多”的狀態。在學生暢所欲言后,教師不忘“撥轉馬頭”,殺出一招“回馬槍”:“多的樣子,所以作者用了一個詞,那就是——密密麻麻”。
在常態化的教學中,我們常遇到“撒出去,收不回來”的尷尬:有時候,步子邁得越大,走得越深,反而迷失了前進的方向。基于這一理解,重新審視這一板塊的教學,就不難發現鼓勵學生大膽想象,用自己的語言描述“看到的畫面”,悄然之中,將詞語的理解,融進了語言體系,但并沒有讓學生大而無當地伸展下去,而是通過“回環”的方式,重新回歸目標,明晰如此想象、表達的最終價值。
四、內化和理解對接,越用越靈活
教詞語,理解是基礎,內化是關鍵,運用是目標。內化的過程,最忌死記硬背。否則,存儲在語言倉庫中,也只能是一潭死水,無法與原始經驗形成聯系,更不能融為一體。
這就給后續學生遇到匹配情境,游刃有余調動認知儲備帶來了障礙。有了通透的理解,內化就能水到渠成,但這一過程,仍需要教師大道無痕地點撥和引導。
在想象了這一組詞語之后,教師可以再次安排“讀”的環節,是融入想象成果的讀,“要體會文字中的畫面美”:這是一次鞏固之讀,將學生的交流,鐫刻在意識之中;這是一次融合之讀,將描寫繁星不同詞語的畫面,交織成為一幅完整的畫卷;這還是一次審美之讀,給原本機械僵硬的語言文字,賦予濃郁的美學元素。
經歷了這一輪多重意義的讀,學生真正達成內化之目的了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這一組詞串,有共同的表達指向——星星,所以教師可以統整而抓;而四個詞語,又是從不同的維度和側面,來描繪形象的,更需要在統整之后各個擊破。
教師可以轉變視角,幫助學生積累。如“作者寫多,沒有用多,用的是什么?”引導學生對應詞串中的“密密麻麻”和“星群密布”;“作者寫星星眨眼睛,沒有用眨,用的是什么?”引導學生對應詞串中的“半明半昧”;“作者寫星星在動,沒有用動,用的是什么?”引導學生對應詞串中的“搖搖欲墜”。
在想象中學生理解了詞語,教師反其道而行之,從作者表達的維度,借助“想要表達……,卻沒有用……,而是用……”的反差句式,觸發學生的思維火花,以回應的方式,強化了詞語感知,悄然之間達成了內化詞語的目的。最后,教師直接奉上30秒,要求學生讀一讀,記在心里。很顯然,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再加把火,“燜”一下,詞語的內化,即可順勢而成。
縱觀這一板塊的教學,教師不僅用理解成果,幫助學生記憶,將成果轉化成為內化的原動力,同時又在記憶內化的過程中,鞏固、強化了學生理解效果。如此一來,學生對詞語解讀更加豐厚,更加通透。
五、拓展與運用契合,越展越豐富
當學生理解了詞語之后,這些詞語儲存在學生的意識之中,就不是一塊僵硬的石頭被擱置在記憶深處的角落里,而會與原始經驗體系中相匹配的內容,形成自主性關聯,甚至會產生“化學反應”,產生“1+1>2”的效果。因此,理解內化后,就需要切切實實地“用”起來。唯有用,才能讓理解和內化的價值凸顯出來。2011版《語文課程標準》明確指出:語文是一門關于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語文教學的關鍵性目標,就是要“學以致用”。語言的運用,一直與感知理解相輔相成。有著怎樣的理解,就有著怎樣的運用;運用的質態,取決于理解的效果,又能促進理解的深化。
在學生將這四個詞語記在心里之后,教師沒有戛然而止,而是緊扣文本情境、課堂情境,直接“拿來主義”,通過描述情境、選擇詞語的方式,進一步掌握詞語。這一教學設計,對詞語理解的層面改進而言,形式上大致相同,但感知的主體,卻悄然間發生了轉變:從原本的作者寫作視角,轉化成為“如果是我來寫作”的維度。
一次視角的轉變,給學生帶來的是對詞語感知著力點的置換:從原本品味、借鑒的維度,轉化成了自我創作、運用的維度。同時,形式上的照應與關聯,使得前后教學板塊遙相輝映,形成了思維合力,讓學生的思維超越了感知理解、就地運用的雙重之境。在這一過程中,借助文本情境,打開表達思維,與此同時還形成了動態化的生成。
例如,引導學生嘗試運用“半明半昧”時,教師設定的引導語是:表示星星一會兒亮,一會兒暗,你會用什么詞?學生依循常規性思維,首先想到的是這組詞串中的“半明半昧”,但很多學生并沒有局限在這個詞語上,而是創造性地拓展了其他相關的詞語:若隱若現、一閃一閃、閃閃發光。
面對學生豐富而積極的動態性生成,教師沒有止步于語言信息的呈現,而是順勢引導學生說出自己的理由,捕捉這些詞語與“半明半昧”之間的相同點。此時,學生言語之中所描述的畫面,就與原本理解詞語的過程形成了巧妙地融合,再次夯實了對于詞語的感知。
運用的本質,就是在理解之后,基于情境轉化下的再度嘗試。在老師情境描述和渲染之下,學生能夠迅速從蓄積形成的語言倉庫中,積極調取已經貯存的資源,以同類素材的方式,拔出“蘿卜”帶出“泥”,使類同的詞語匹配而出。這種匹配,是原始積累與情境不斷契合的過程,更是簡約而高效的運用過程。
總而言之,詞語的教學,應該以理解為要。但理解的過程,不能硬著陸,需要緊扣學生的思維特點和認知規律,將畫面想象、感知內化、實踐運用與理解巧妙地融合起來。通過這串詞語的教學,在學生初步閱讀課文,準確流利朗讀課文的基礎上,學生經過思維的回環、印證和強化,由此將詞語的理解得到最高效地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