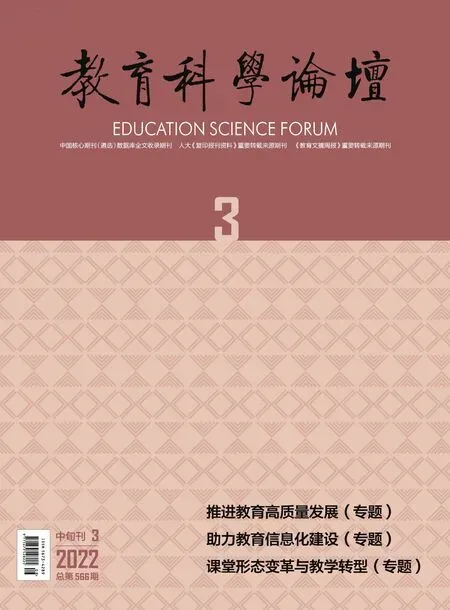師生關系對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一項追蹤研究
■鄭研
近年來,隨著我國新型工業化的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以及提高流動人口生活質量相關政策(如提高社會保障、完善醫療保險和解決子女就學等)的出臺,由農村進入城市務工的流動人口規模迅速增長,家庭式流動的比例越來越高。與此同時,隨父母進入城市生活和接受教育的未成年兒童也越來越多,成為中國社會中一類不可忽視的弱勢兒童群體——流動兒童。
一、問題提出
(一)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受到廣泛關注
根據1998年國家教委、公安部發布的《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流動兒童是指隨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流入地暫時居住半年以上有學習能力的6至14周歲(或7至15周歲)兒童。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指出,2019年跟隨父母進城的流動兒童數量達到1472萬。2016年12月30日,國家衛計委等22個部門共同印發的《關于加強心理健康服務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要“全面加強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尤其要關心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心理健康”。2021年4月29日,山東省教育廳、山東省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全省大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體系建設的意見》進一步提出要在全省加快推進心理健康教育體系建設,促進大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發展。因此,關注流動兒童,開展流動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的相關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流動兒童面臨著較高的心理健康問題風險
流動兒童正處于身心發育和接受教育的重要時期,這些兒童從農村來到城市,他們不僅必須學會應對成長的壓力,而且要適應新的學校、家庭和社會環境帶來的挑戰。因而,他們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較高,尤以內化問題行為(如焦慮、抑郁等)最為明顯。焦慮和抑郁是反映兒童心理健康狀況的兩大重要指標。研究發現,與處境正常的兒童相比,流動兒童具有較高的歧視知覺和較低的自尊水平,這使他們更易體驗到較高水平的焦慮和抑郁[1-6]。焦慮和抑郁情緒的困擾會導致兒童出現許多不良的心理與行為反應,如心境低落、睡眠障礙、食欲下降,嚴重的甚至會導致自殘、自殺等行為,嚴重影響兒童的正常學習和生活[7-9]。因此,考察引發流動兒童焦慮和抑郁的相關因素,對于采取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緩解流動兒童焦慮和抑郁情緒,促進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三)學校是影響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環境
布朗芬布倫納(Bronfenbrenner)的生態系統理論[10]指出,學校是影響兒童發展的最直接、最近端的微系統環境因素之一,對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師生關系作為學校微系統的重要因素,與兒童心理健康發展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相關研究大多考察了師生關系與處境正常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系[11-13],鮮有研究考察師生關系對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狀況的影響。隨著當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落實落地,隨遷子女低齡化特征比較明顯,小學流動兒童越來越多。2020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19年小學流動兒童人數(149.15萬)顯著多于初中流動青少年(101.30萬)。與處境正常的兒童相比,流動兒童在新的城市生活和學習環境下,往往需要調動更多的心理資源來應對環境改變帶來的壓力。在此情況下,當流動兒童在學校環境中經歷了不良的師生關系后,他們更可能因壓力事件的增加和自身心理資源的不足而表現出高水平的焦慮和抑郁等心理健康問題。也就是說,不良的師生關系作為一種學校壓力事件,極易與生活壓力和學習壓力共同作用,對流動兒童產生風險的累積效應。相反,良好的師生關系則可能成為流動兒童發展的一種保護因素,幫助流動兒童在新的社會和學校環境中更快更好地適應,進而促進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此外,僅有的關于師生關系與處境正常小學兒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大多采用橫向研究設計,考察二者間的相關關系[14-15],鮮有研究對二者間的縱向因果關系進行考察。
鑒于此,本研究擬采用追蹤研究設計,對師生關系與流動兒童這一特殊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之間的縱向關系進行探討。對于這一問題的探討,不僅有助于加深人們關于師生關系與流動兒童心理健康之間特殊關系的認識,而且對于學校教育實踐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可以為改進師生關系進而減少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提供一定的心理學實證依據。
二、方法
(一)被試
采用整群抽樣法,從山東省濟南市某小學選取361名三、四年級小學流動兒童為被試。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對被試進行連續兩次(間隔半年)的追蹤測查。剔除作答不完整的無效問卷3份,最后獲得有效問卷358份,有效率為99.17%。其中,男生206名,女生152名,第一次測查(T1)時被試平均年齡9.87歲,標準差為0.66。
(二)研究工具
1.師生關系的測量
采用屈智勇(2002)修訂的師生關系問卷[16],由兒童報告其與老師的關系。該問卷共包含24個項目,由三個積極維度(親密性、支持性和滿意度)和一個消極維度(沖突性)組成。問卷采用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的五點計分方法,得分越高,表明師生關系越積極。本研究中,該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7。
2.兒童心理健康的測量
以焦慮和抑郁作為兒童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標。
采用Spence兒童焦慮量表中文版(SCAS)[17],由兒童在第一次測查(T1)和第二次測查(T2)時分別自我報告其焦慮狀況。該量表包含44個項目(含6個填充項目),分為分離焦慮、社交恐懼、強迫-沖動行為、恐慌障礙、軀體傷害恐懼和廣泛性焦慮六個維度。采用0-3的四點計分法,得分越高,表明兒童焦慮水平越高。本研究中,T1和T2的兒童焦慮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均為0.95。
采用兒童抑郁量表(CDI)[18],由兒童在第一次測查(T1)和第二次測查(T2)時分別自我報告其焦慮狀況。該量表共包含27個項目,采用0-2的三點計分方式。得分越高,表明被試的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T1和T2的兒童焦慮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88和0.90。
3.施測程序及數據處理
以班級為單位進行連續兩次,間隔半年的集體施測。將問卷分發給兒童,由主試向兒童宣讀指導語,介紹研究目的、信息保密性及問卷作答的相關要求。主試由經過嚴格培訓且有多次施測經驗的心理學專業碩士生和博士生擔任,量表當場全部收回。采用SPSS22.0和Amos17.0進行數據的處理與統計分析。
三、結果
(一)師生關系的基本特點
以師生關系為因變量,兒童性別和年齡(T1)為自變量,進行2*4的方差分析。結果發現,兒童性別(F=0.40,p>0.05)、年齡(F=0.09,p>0.05)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F=0.84,p>0.05)均不顯著。這一結果說明,流動兒童的師生關系不因兒童性別和年齡的差異而不同。
(二)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狀況的基本特點
分別以T1、T2的兒童焦慮為因變量,以兒童性別和年齡為自變量,進行2*4的方差分析。結果(見表1)發現,T1、T2的兒童焦慮均存在顯著的兒童性別差異(T1:F=9.94,p<0.01;T2:F=9.43,p<0.01),女孩的焦慮水平 (T1:M±SD=37.56±28.41;T2:M±SD=32.41±21.84)顯著高于男孩(T1:M±SD=23.76±25.10;T2:M±SD=19.69±19.30)。T1、T2的兒童年齡差異(Fs<2.48,ps>0.05)、兒童性別和年齡的交互作用(Fs<2.57,ps>0.05)均不顯著。

表1 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狀況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分別以T1、T2的兒童抑郁為因變量,以兒童性別和年齡為自變量,進行2*4的方差分析。結果發現,T1、T2兒童抑郁的兒童性別(Fs<2.59,ps>0.05)、年齡(Fs<1.54,ps>0.05)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Fs<1.55,ps>0.05)均不顯著。這一結果說明,流動兒童的焦慮和抑郁水平不因兒童性別和年齡的差異而不同。
(三)師生關系與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的相關分析
對師生關系、流動兒童焦慮與抑郁狀況進行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結果(見表2)發現,T1的師生關系與T1、T2的兒童焦慮和抑郁均呈顯著負相關,T1、T2的兒童焦慮和T1、T2的兒童抑郁兩兩間均呈顯著正相關。這一結果說明,師生關系越好,兒童的即時焦慮和抑郁水平越低,兒童半年后的焦慮和抑郁水平也越低。

表2 師生關系與流動兒童心理健康之間的相關
(四)師生關系對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
建構如圖1所示的結構方程模型,在控制兒童性別的基礎上,檢驗T1時的師生關系對T1時兒童心理健康的即時影響,以及對半年后(T2)兒童心理健康的延時性影響。其中,師生關系是外源潛變量,是模型中的自變量,分別以親密性、支持性、滿意度和沖突性四個維度為觀測指標。T1和T2時的兒童心理健康為內生潛變量,是模型中的因變量,分別以T1和T2時的兒童焦慮和抑郁為觀測指標。兒童性別(虛擬化,男=0,女=1)為控制變量。考慮到兒童心理健康發展的穩定性,允許T1時的兒童心理健康和T2時的心理健康相關。結果發現,模型擬合良好,χ2/df=1.48,RMSEA=0.04,CFI=0.996,TLI=0.988。T1時的師生關系對T1時兒童心理健康的預測路徑顯著(β=-0.63,p<0.01)。T1時的師生關系對半年后(T2)兒童心理健康的預測路徑也顯著(β=-0.18,p<0.05)。這一結果表明,在控制了兒童性別之后,師生關系既能對兒童的心理健康產生即時性影響,又能對半年后兒童的心理健康狀況產生延時性影響,良好的師生關系能夠減少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
四、結論
第一,師生關系與流動兒童的焦慮和抑郁癥狀呈顯著負相關,即師生關系越好,兒童的焦慮和抑郁癥狀越少。
第二,教師對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良好的師生關系是兒童心理健康發展的保護性因素,它既能即時地減少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又能對兒童心理健康狀況起到長期的保護作用。
五、討論與建議
(一)關注流動兒童心理健康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一環
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兒童的心理健康關系到民族的未來能否健康發展。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兒童青少年群體在學習、環境適應和人際關系等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隨之也呈現出心理健康問題逐漸增多的趨勢。兒童心理健康問題越來越受到家庭、學校和社會的重視。《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指出,“改善國民心理健康水平,首先應該從孩子抓起”。《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明確指出,要將“關心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為學生提供及時的心理干預”作為中小學健康促進行動的行動目標。
流動兒童是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產生的一類新群體。雖然近年來隨著流動兒童義務教育政策的進一步修訂和完善、城鄉二元體制的逐步破解,流動兒童入學就讀、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緩解,但流動兒童進入城市生活,仍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貧窮、高質量教育缺乏和健康的風險。此外,流動兒童發展環境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遭到破壞,他們需要適應新的生活和學習環境,需要在新環境中重新建構人際網絡和社會支持。這一過程也給流動兒童帶來了較大的心理壓力,使其產生文化適應困難、受歧視、被邊緣化、被接納度低和融入度低的問題[19-20]。較強的歧視知覺和被邊緣化處境,導致流動兒童產生高焦慮、高抑郁、低自尊和高孤獨感等心理健康問題。因此,關愛流動兒童,關注流動兒童心理健康是提高社會和諧,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一環。
(二)良好的師生關系是兒童心理健康發展的保護性因素
發展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兒童期存在心理問題的個體在其后的發展中也會面臨著高風險的適應問題[21]。為預防或緩解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研究者們不懈地對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的相關因素進行探究。基于生態系統理論,師生關系是兒童發展的學校微系統環境中的主要人際關系,與兒童心理健康發展關系密切[13-14]。基于流動兒童群體,本研究發現,師生關系對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具有即時性和延時性的重要影響。具體而言,良好的師生關系是兒童心理健康發展的保護性因素,它既能即時地減少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又能對兒童心理健康狀況起到長期的保護作用。
(三)構建高質量的師生關系可以提高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素養
良好的師生關系促進兒童心理健康發展的原因機制可能有三。首先,與同伴相比,教師作為學校環境中的成人,心理成熟度高,他們更能公平、平等地對待流動兒童,在生活和學習中能真誠關心、幫助和尊重流動兒童,從而為流動兒童創造積極發展的情感環境。其次,良好的師生關系能夠讓流動兒童體驗到來自長輩的溫暖,緩沖親子關系缺失給流動兒童帶來的消極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流動兒童垂直關系的缺失,為流動兒童創造積極的人際環境。最后,教師作為學校和班級中的權威人物,能夠通過塑造非歧視性的、合作互助的學校或班級氛圍,給流動兒童提供平等、積極的發展機會,從而為他們創造積極的學校或班級環境。
美國社會學家哈吐普(Hartup)的人際關系理論指出,兒童生活中主要存在垂直關系和水平關系兩種不同性質的人際關系[22]。其中,親子關系和師生關系屬于垂直關系,二者具有互補性。在這兩種關系中,成人與兒童分別處于主導和服從的地位。垂直關系的主要功能是為兒童提供安全的發展環境,促進兒童更好地生活和學習。同伴關系屬于水平關系,同伴之間地位相當,主要功能是以平等互惠的方式為兒童提供身心發展和交流互動的機會。對于流動兒童而言,他們從農村來到新的城市環境中,尚未建立起充足的社會支持,此時父母往往是他們最初的依賴,親子關系便是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際關系。然而,流動兒童的父母來到城市中工作、生活,往往面臨著較高的經濟和社會壓力。他們為了給家庭和子女更好的生活而疲于工作,因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孩子,忽視了家庭教育。此時,學校作為兒童發展的主陣地,成為流動兒童生活和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境。在重構人際關系的過程中,流動兒童首先需要建立的就是學校中的人際關系,即垂直的師生關系和水平的同伴關系。關于流動兒童同伴關系的研究發現,流動兒童在城市學校中受歧視水平較高、友誼關系質量較差,同伴接納程度較低,常常被忽略,導致其學校適應性較差,焦慮和抑郁水平高、孤獨感較強[23-25]。在親子關系和同伴關系有缺失的情況下,良好的師生關系便成為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護性因素。因此,構建高質量的師生關系,增強師生關系的親密性、合作性和主動性,是提高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素養的有效途徑。
六、理論貢獻和實踐意義
提高兒童心理健康素養,尤其是流動兒童等特殊群體的心理健康素養是“健康中國行動”建設的重要內容。兒童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對于國民整體的心理健康促進工作具有更為長遠的意義。本研究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豐富關于學校微系統環境與兒童心理健康發展間關系的本土化理論研究,深化人們對于師生關系影響兒童心理發展的科學認識,而且對于改進師生關系狀況,進而有效預防和減少流動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促進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