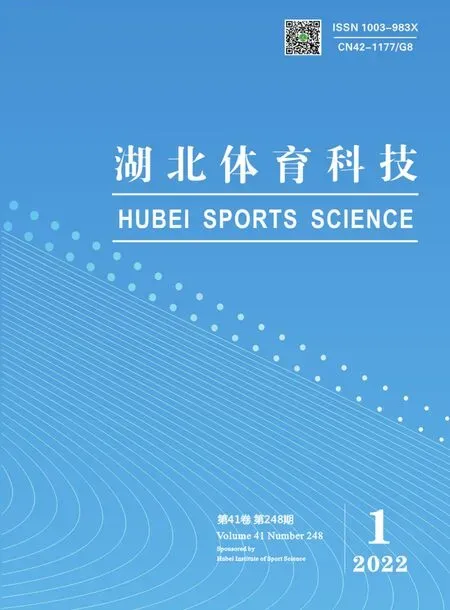天塔獅舞運動的文化符號闡釋
郭佳佳,宿繼光,陳 融
(中北大學 體育學院,山西 太原030051)
塔爾山下孕育的民俗體育活動——天塔獅舞, 在全國各地乃至世界范圍內得以廣泛表演,以驚、奇、絕、美、險號稱為中華一絕。 民俗體育活動通常與一定的儀式相結合,也被稱為儀式化[1]的體育活動。 天塔獅舞也不例外,表演前進行一套程序化的祭祖或祭神儀式,儀式的舉行對于社會結構、秩序和群眾心理[2]會產生重要意義。三國時期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章》中提到:“觸類可為其象,含義可為其征”[3]。 天塔獅舞的表演者通過舞蹈、 武術動作和樂器演奏等形式構建富有獨特意義的情景,它由多種象征符號組成。 象征符號以一種文化形態所呈現,基于符號學視角,通過深描,透過獨特的情景儀式,挖掘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的邏輯結構和社會現實, 剖析其文化符號的發展之路。
本研究以天塔獅舞的文化符號為研究對象, 選擇襄汾陶寺為田野調查地點,陶寺距離襄汾縣城約至10km。 距今約10萬年前,“丁村文化” 在這里誕生, 孕育出燦爛文明的黃河文化,也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天塔獅舞的發源地。 陶寺是天塔獅舞的發源地,而且具有濃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是田野調查地點的不二之選之地。 為此,本人于2020 年5 月深入陶寺,對其展開參與式觀察,并對天塔獅舞的傳承人、表演者、表演觀眾和當地居民做了詳細的訪談。
1 天塔獅舞的文化溯源
自古,人們祈求通過某種方式或方法與神明溝通,以求解答心中疑惑, 而距今約1 700 余年的天塔獅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不斷發展并豐富了自身的文化內涵與表現形式 。 據漢代班固《漢書》記載:“郊祭,有常從象人四人”[4]。 何為象人? 簡言之,就是戴著獅子面具舞蹈的人,這一舞獅起源論述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 此后,“儺舞與獅舞”得以結合。 獅子被人們賦予神學色彩,成為祈禱和敬重的對象。 追溯歷史,天塔獅舞具有濃厚的宗教屬性,包含有宗教觀念:賦予獅以超自然能力,成為祭祀和尊敬的對象;宗教體驗:表演前會進行一系列的儀式活動;宗教行為:按照當地習俗,香火、放鞭炮、燒銀錢等必不可少,用于祈求風調雨順等;宗教制度:獅舞的表演具有程序化、規范化和制度化。 伴隨歷史發展,受當地農民勞作和民族風情的影響,天塔獅舞由原先“青獅子擺象”衍變為以6 只獅子和領獅人的“家文化”表演,表演形式具有地方特色,天塔獅舞運動被賦予“家文化”的理念。
卡西爾從文化哲學的高度論述道:“人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5]。 語言、神話、藝術和宗教是這個宇宙的各個組成部分,構成符號之網的絲線,成為人類經驗交織之網。 從原始社會的圖騰標識到如今的國旗和國徽,都是不同形式的象征符號。 舞獅的源起深受獅文化的熏染, 在中國傳統宗教信仰的影響下得以發展。 當前,衍化而來的天塔獅舞以祭祀、祈禱和追求和諧為,通過板凳、繡球、獅子被和樂器等道具,完成表演,每個環節都具有獨特的蘊意。
2 天塔獅舞的象征符號體系
隱喻符號在獨特情景儀式中的使用被稱為象征方式。 在交流過程中,要想真正實現符號到意義的轉變,必定離不開使用者——人。 歸根結底,人也是“符號的動物”,人的精神、人的社會、 整個人類世界沉浸在一種很少能被人感知的符號世界中,德李達曾在其文中提到:“從本質上講,不可能有無意義的符號,也不可能有無所指的能指。”[6]文化是一個社會意義活動的總集合,“文化”全部由意義活動組成。 錢鐘書論述到:“‘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謂‘文明事物’;‘文學言論’則形而上,所謂‘文化事物’。”[7]實際上,符號就是意義,無符號即無意義,符號學即意義學[8],也可以說,在人類社會中,傳遞信息的象征符號必須獲得所在社會群體的認可和理解, 一般為其所熟知和理解的習俗規范。 以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為載體,就此對天塔獅舞的象征符號蘊意展開論述。
2.1 天塔獅舞的語言符號
在人類活動中,語言符號作為溝通的媒介,具有較強的應用性和專屬性。 各語言符號之間形成的聚合關系,是符號指符的鮮明特征[9]。 替代物和所指事物形成的聚合關系通過隱喻、轉喻和雙關達到一種“超模擬”的語境。 在民俗體育活動中,以語言形式呈現特定語境的符號有很多, 每一個都有其特定的術語符號。
語言是象征蘊意表述的交流方式, 身體動作也是領悟象征蘊意的主要方式。 天塔獅舞運動的語言符號包含有:動作名稱(天塔獅舞動作術語)、獅種類型、語言口令等,在天塔獅舞演藝過程中這些特定的語言符號, 不僅可以反映出民俗體育的性質和特點,也規范了天塔獅舞活動的技術特點和眼球,使之與其它舞獅運動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區別。
天塔獅舞以“家”為核心,由早期的“青獅子擺象”逐步演變為“母獅下崽、闔家歡樂”的場景。 天塔獅舞的表演動作包含有六大步伐:行步、跑步、蓋步、錯步、跑步、碎步和顛步。 動態動作包含有:踺子、旋風腿、后空翻和魚躍前滾翻等,其中,較為經典的動作名稱有水中撈月:即位于塔頂峰,兩只雌雄獅相互托舉交換位置, 身體向斜下方傾斜完成撈月動作; 金雞獨立:領獅人處于最高層,將一條腿抬離至頭頂上方,使身體處于平衡穩定的狀態,維持大約10s;蓮子花開:4 只小獅子攀爬至它的中央位置,側身面向四方的觀眾,將遠離板凳的同側手和腿擺向空中;登高望遠:6 只雌雄獅分別來至自身的最高處,統一面向公眾眺望遠方;空中到福:領獅人在塔的最頂端,完成倒立動作, 并用毛筆書寫祝福語……每一經典動作都具有獨特的指符蘊意(如表1)。 在天塔獅舞的整個活動過程中,領獅人的口令牽動整個表演節奏, 在口令的指引下6 只雌雄獅完成一系列的形態動作和神態動作。 整個表演過程及情節的設計表征出表演者的競技精神和品質,同時身體動作的演繹,“突破”僵硬的肢體動作,構建獨特的情景韻味,無疑充滿豐富的趣味。

表1 天塔獅舞動作術語的符指蘊意
2.2 天塔獅舞的非語言符號
人們通過聽覺、視覺、觸覺和其他感覺在體育活動中所表現得動作具有符號的意義,也稱為體育符號的非語言系統[10]。民俗體育天塔獅舞的非語言符號主要表現在6 只雌雄獅運動時的神情、動作技術和服飾等方面。 登塔的成功離不開每個雌雄獅表演者的相互配合。 在聽覺觸動下,以領獅人和音樂鼓點為主要節奏,扮演者依靠聽覺來完成同時起跳等相同動作。 除專用的手勢語、哨點和鼓點外,扮演者神態和肢體動作的交流也是作為指符傳遞信息的重要方式。 每一個動作的完成,都需要隊員之間通過長時間的磨合方可成功。
2.2.1 天塔獅舞運動中的聽覺音響符號
聽覺上的音響指符包含大自然的各種聲音, 這些聲響直接觸動民眾心理,顯現出特定聲響的聯想。 比如:電閃雷鳴聲和山崩地裂聲會給人心理帶來一定的恐懼感; 狂風暴雨聲會給農民祈求穰穰滿家的心理上增添焦慮感;田徑跑道上,裁判員的鳴槍聲成為運動員開跑的標準。 天塔獅舞運動的音響指符主要以哨聲和鼓點聲為主。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說明在當時“俗”與“樂”已經有了較為明顯的結合[11]。 鼓點聲最早出現于原始部落時期,用木鼓和獸皮鼓發出的聲響制定鼓語編碼,用以傳遞信息,彌補手勢語和吶喊聲的不足[12]。 天塔獅舞的整個音樂鼓點往往突出喜慶、歡快的主題,以京劇劇團鑼鼓聲編制鼓點,鈸、木魚和鑼樂器加以結合用來作為信號使用。 在訓獅人“哨語”和鼓點的指引下,舞獅運動員或是緩和、或是急促、或是親昵、或是顫巍的完成一系列高難度動作,使整個表演過程的“驚、奇、絕、美、險”變現的淋漓盡致。
2.2.2 天塔獅舞運動中的視覺神態符號
天塔獅舞運動中更多體現出一種含蓄美, 大部分動作蘊意是需要隱藏在隊員的神態表情中向觀眾傳達, 給予人一種含而不露、開而不達和耐人尋味的隱秘美感。 在天塔獅舞舞獅運動中神態亮相動作主體主要包含訓獅人和6 只雌雄獅兩個部分。 訓獅人通過靜態動作和動態動作傳達神情蘊意 (如圖1),靜態動作眼神溫和中帶有威武之氣包含有弓步探球、仆步抱球等;動態動作以跑和跳躍為主,訓獅人雙眼炯炯有神,節奏較快,緩慢將全場的氛圍帶動至高潮,傳達歡快、喜悅之情。舞獅運動的神情主要通過獅子頭、眼睛、耳朵、舌頭和尾巴5個細節部分來傳達,通過一些機關控制,幾只大小獅相繼完成愣相、驚相、美相、怕相和急相等。 愣相是獅頭向斜上方45°方向搖擺,眼睛睜大一動不動,給人一種呆萌的感覺;驚相是獅頭由右肩向左下方擺動,腿部左右跳躍,表現出驚恐、怪異的樣子;美相是獅頭自上而下、自左至右的做回旋動作,將力量美與靈活美感展現出來;怕相是身體重心逐漸來至最低點,獅頭自右向左緩慢抬起,眼神左右擺動,眨眼頻率變快;急相是獅頭前后交替,雙腳快速震動,眼神盯住一方不動。 在展現舔、啃、吻、撓、擺尾和伸腰的神情動作時潛移默化的表現出人世間的喜、怒、哀、樂 ,將更多的“家文化”思想和歡快帶給觀眾。

圖1 天塔獅舞神態符號
2.2.3 天塔獅舞運動中的視覺物化符號
在民俗體育的符號構成中, 實物作為表現體形成以物化為代碼的指符特點。 此實物非圖像物品,是實在的物體,物化象征符號文化意義的傳達需要一個轉喻的“超模擬”過程[13]。天塔獅舞的物化象征符號包含有三牲、餞盒、繡球、獅子頭、獅子被和樂器等。 天塔獅舞中的諸多物化符號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 其中以表演者頭帶獅冠面具、身披獅被獸皮、登上9m多高臺、口中發出“儺儺”之聲為特點。 伎樂曲《獅子舞》記載:“伎樂中的獅子舞不久就歸屬于祭禮神事和散樂(猿樂)等,甚至影響后來的田樂、能樂、歌舞伎、民俗藝能獅子舞、太神樂獅子舞,建造了日本藝能史上的獅子舞蹈系列。 ”[14]總的來說,天塔獅舞中“獅”的形象被民眾賦予圖騰寓意,多寓以驅邪避災,且從“獅子”發音音色分析,與古漢語“賜子”音色相諧,預示“多子多福”的美好期盼。 在天塔獅舞儀式前,民眾會通過三牲、餞盒等物品供奉神明,以求好運連連。 天塔獅舞的物化符號自身具備其自然屬性,但伴隨表演者及民眾的設計和期盼,一系列表演過程傳達了民眾的內心情感。
2.2.4 天塔獅舞運動中的視覺色彩符號
在象征符號的外部形態中, 表現最為突出的是某些物質所表現出來的形狀, 與形狀密切相關的是人們通過視覺思維進行類比聯想[15]后所呈現的顏色。 伴隨歷史衍進,色彩觀念體系被逐漸形成, 人類從視覺色彩變幻逐步感知到人間的真善美惡的區別。 變化中不同的形狀與顏色被賦予了各自的文化基因,并形成與陰陽五行相對的赤、黃、青、白、黑五色觀(如表2)。 五色觀在民俗體育的研究中,逐漸豐富了其文化內涵。 天塔獅舞“繡球”是由紅色、綠色和黃色的3 種不同顏色布料組成的圓形球體。 中國古代尚有“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念,圓形球體多被用于表述天穹、和和滿滿等蘊意。 人們對特定事務的好惡感直接決定色彩[13]被賦予的象征意義。 “繡球”綠色多被用于表述希望、青春和生命;紅色蘊意喜慶、熱烈和熱情;黃色蘊意豐收、富裕和高貴。 在咚咚咚……咔嚓咔嚓……的音樂刺激下男性表演者身著白唐裝襯衫、黑馬褂、下為藍色褲子,女性表演者身著粉唐裝襯衫、 大紅馬褂完成一系列情景高難度動作。 白色唐裝給人以純潔無瑕之感、藍色褲子給人以幻想忠誠之感,結束之時的祈禱詞寄托人類的完美夙愿。 人們用顏色的象征來代表“力量”和“憧憬”,這樣,人們會認為他們為了社會的目的而控制了這些力量。 人們正是在這種象征思維的導向下, 充分利用色彩和形狀與其意指對象之間存在的相似性和聯系性來賦予其特定的象征意義, 通過視覺思維更可以直觀地認識和理解天塔獅舞感覺象征符號所傳遞的文化信息。

表2 五色觀
2.2.5 天塔獅舞運動中的其它感覺符號
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中論述道,“辟邪獅子,引導其前”[16]。 天塔獅舞一般會選擇在黃道吉日當天表演,以幻象的心理狀態給予舞獅象征意義。 當地老百姓利用這種活動形式來進行禱穰和娛樂,以進一步烘托節日的氛圍。 在我國農耕文明時代,人們對于萬千世界存在一種敬畏的心態,對于一些自然現象、生老病死無法給予合理的解釋,生產力、生活水平較低,求雨、祈福、消災等成為民眾農耕的頭等大事。 相傳,獅子最早從西域傳入的,是文殊菩薩[17]的坐騎,受佛教思想的熏染,獅子逐漸被賦予人文品格特質。 天塔獅舞深受宗教思想影響,表演前會由眾多象征符號組成一定的儀式空間,借助獅崇拜、面具和祭詞等一系列象征符號,迎請各界神靈,向神獻祭,以求驅逐疫鬼、風調雨順。 張華在中國民間舞與農耕信仰中也論述到,舞獅一般是在天降疫情或祭祀[18]時才會表演的節目,有一種消災辟邪的功效。 據卜辭闡釋, 古時祭祀活動極為頻繁,凡三、五日一祭[19],通過祭祀等一系列活動祈求實現一定的目的和物質利益,一直以來民眾大都祈求穰穰滿家、風調雨順。 因此祭祀活動與當時民眾的生活與生存戚戚相關,由古至今,地位也變得尤為重要。 天塔獅舞的起源地——陶寺一帶民眾信奉自由、認為“萬般皆由命,半點不由人”[20],圖騰崇拜在此具有較為明顯的特征。 在當地民眾心里認為萬物都是有靈性的,而且神靈是無處不在的,尊重祖先,設立神龕也變得尤為重要。
3 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的表達
3.1 由“此”及“彼”身體實踐的隱喻
隱喻是實現文化符號性轉換的重要手段, 符號意義的傳達需要基于“隱喻”,實現“此”與“彼”的轉化[21]。 天塔獅舞隱喻中的“此”是其文化符號的實踐,包含身體動作和儀表形態等,“彼”的指向是天塔獅舞文化符號隱喻下所傳遞的意義。 康納頓認為,“在現存經驗模式階段中,在感知某一事物時,人類大腦會呈現出一個預前判斷, 在先前脈絡認知的基礎上冗雜自己的個別經驗,將認知放置到一個預期期望中。 ”[22]總體分析,“預前判斷”“先前脈絡”“預期期望”都在論證一個“傳統記憶”的問題。 基于此視角分析,天塔獅舞文化符號是可被感知的,整個儀式活動都是參與者在有意識的情況下完成的, 身體實踐及配合它完成動作的服飾道具融合了陶寺一帶先民的歷史生活,身體指向緬懷祖先、追憶家庭酸甜苦辣的美滿。 整體動作和形象已超越其本身,成為一個與民眾溝通的重要符號。 天塔獅舞文化符號“彼”的傳遞意義,是通過“現有經驗”的基礎上,運用一系列的身體動作和形象追溯過往“傳統記憶”,實現文化符號由“此”及“彼”的隱喻。
3.2 以身體實踐語言表述陶寺居民的精神世界
天塔獅舞運動主要是通過身體動作的操練視覺傳達給觀眾,實現符號的隱喻性傳遞,但在符號體系中,語言的身體實踐也發揮著重要功能。 天塔獅舞語言符號的記載包含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字收錄、動作術語、口頭傳承、敘事概述等。如:儀式開始前頌文、蓮子花開、水中撈月、訓獅人口令等都傳遞出一種祈福和規范集體意識的用意, 用語言的方式生動記載傳統與儀式的目標指向。 天塔獅舞語言身體實踐產生于生產生活,融匯于各大節慶日,對天塔獅舞語言符號的考察,要將其置于陶寺特定的歷史背景。 陶寺一帶居民“精神世界”的形成深受陶寺文化的熏染,據陶寺文化遺址面積等級分析出,陶寺一帶歷代屬于相對聚集的聚落群體, 是臨汾地區的中心地帶。 據歷史考證,陶寺一帶居民規模較大,數量群體多、人流交往頻繁、物質資源豐富由以手工業為主、地理位置優越[23]。天塔獅舞文化符號利用得天獨厚的歷史資源優勢加儀式化特征和身體實踐記載著陶寺一帶居民特有的歷史文化底蘊、精神信念、價值理念等。
3.3 指引“社會行為”及“社會場域”的力量支撐
天塔獅舞的文化屬性包含物質文化、 精神文化和社會文化3 個層面。 實際上,無論何種文化形態,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符號屬性,只是顯現的文化符號功能略有強弱。 社會文化符號屬性雖不及精神文化符號屬性更直接的去反饋民眾的思維意識和精神信仰, 但相較于物質文化符號屬性而言潛移默化的成為我們社會行為的重要指針,具有更為重要的價值。 我們將天塔獅舞的衍變置于陶寺一帶歷史社會發展進程中考量時,不得不審視國家宏觀政策指引、 宗教儀式和身體實踐的重要性。 天塔獅舞的起源與宗教、節慶等密不可分,圖騰、祖先祭祀活動通過一系列身體實踐活動而展開。 對于其文化符號的社會功能不可以孤立看待,在提高參與者速度、力量、柔韌、耐力等身體素質的同時也起到了教導社會規范、 培養社會角色的重任。 天塔獅舞主要是在當地的生產生活實踐下為滿足群眾需求而產生,具有相對獨立性,并潛移默化的對當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產生影響。 天塔獅舞的文化符號體系在傳遞的過程中具有雙重的作用,從表層上來講,是一個體育身體實踐的傳承,從深層次來說,傳承的內涵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社會行為的指引方針和社會控制場域的重要力量, 符號化的建立是進一步推動符號變遷的過程。
3.4 “儀式化”與“體育化”的博弈
在原始社會時期,由于生產生活的落后,以及被“大自然”神秘外衣籠罩,大都倡導自然崇拜,人類用無形的身體方式表達著對大自然的敬畏。 社會的發展,圖騰崇拜步入人類視野,天塔獅舞的源起就受到圖騰崇拜的影響, 伴隨科技社會的進步,受鄉賢文化的影響,由圖騰崇拜開始向先賢崇拜轉變。 天塔獅舞是一個典型的受先賢崇拜而成功的一個民俗體育案例。 鄉賢即鄉里有一定威望、品德好、才學高、可以得到鄉民認可的人[24]。 綜合分析,天塔獅舞文化符號歷經“模糊-清晰-模糊”過程的衍變,由最初的圖騰崇拜到“體化實踐”與“宗教”結合的“儀式化”傳播方式,但目前宗教文化符號對體育文化符號的發展存在一定的解弊,使天塔獅舞邁向體育化、世俗化的道路模糊。 早期的天塔獅舞文化符號就是單一的“體化實踐”與“宗教”一時的結合,在第六代傳承人李登山當上村支部書記后,不斷對表演內容和形式進行深化,由原先的敬神娛神逐漸向家文化、娛樂化方向轉化,但由于目前傳承人李登山的退位及為謀取金錢變味發展的山寨“天塔獅舞”的出現,也進一步阻礙了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的傳承與發展, 使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的表達變得越發模糊。
4 天塔獅舞可持續發展的文化符號學思考
4.1 天塔獅舞文化符號身體實踐的傳承
習近平主席說:“保護好、 傳承好歷史文化遺產是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 ”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的傳承有很多方式,除師徒傳承、 言語傳承等, 還有一種特殊化的傳承——身體實踐。 身體實踐的傳承包含由“此”及“彼”身體實踐隱喻意義的傳承和身體實踐體化記憶的傳承。 天塔獅舞運動員的身體動作節奏、身體形態的編排是符號能指構建的過程,通過“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的方式追溯著“傳統記憶”。 天塔獅舞活動的儀式感,促使身體實踐得以重復演練,進一步強化對過往記憶的記錄。 從理論角度分析,這并非是一種機械性的重復與粘貼,是一種模擬性的認知過程,在身體實踐表達與陳述的背后是民眾內心承載的信仰。 就體化記憶而言, 每次的實操重復,使運動員的身體具備了生理學與社會學的傳承屬性。 這些身體動作需在大腦皮質控制下,作用于肌肉和骨骼而產生,運動員運動技能的學習進程包含于泛化、分化、鞏固和自動化4個階段,在此之后運動員會形成“習慣性記憶認知”。 這一“習慣性記憶認知”能夠促使運動員在操練中“回憶過往較為重要的分類體系”[25],它具備一定的穩定性和存儲功能,在某一特定的場景可以得以提取和傳承。 其次,身體具有一定的社會學屬性, 身體動作在規范技術要領的同時也培養了以運動員集體意識感等, 天塔獅舞文化符號承載的并不僅僅是我們所看到的炫酷驚險的身體動作或威武霸氣的服飾, 而是其背后表達與傳承的陶寺一帶居民對“家”傳統的理解與繼續。
4.2 “精神支撐”是推動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發展的關鍵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涂爾干指出,如果社會沒有象征物,那么其存在就是不穩定的。 象征物是社會獲得自我意識所必需的,也是確保這種意識長期存在所不可或缺的[26]。 視覺、聽覺,看似簡單的一看、一聽,無形中卻隱喻了民眾的思想情感。天塔獅舞活動中的身體實踐、 實踐形象和實踐指向共同構成了一個隱喻體系, 每一個身體動作及配合它完成的服飾道具都共同指向同一主題,即“精神支撐”。 事實上,追溯歷史,縱觀奧林匹克發展史,每一項身體運動都是具有祭禮性質,都是在一定的理念信仰之下完成的。 “天塔獅舞”無形的“精神支撐”即是這一代大眾的民俗信仰與信念, 天塔獅舞所在陶寺一帶的社會文化背景促就了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發展的信仰, 早期的傳統舞獅儀式信仰,孕育了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發展的雛形。隨著時代變遷,原始的宗教信仰已經發生了衰落與變異,其精神文化蘊意已轉換為不畏危難、超越自我、祈求安康的良好愿望,展現其敢于拼搏、迎難而上的精神,是陶寺一帶民俗體育文化的一顆明珠。 天塔獅舞精神文化符號是對客觀世界與社會的反映, 以一種觀念的社會形態記錄天陶寺一帶人的思維意識和情感態度,可以將最本質的符號屬性展現大眾,強化天塔獅舞的精神信仰是十分必要的。
4.3 追隨時代步伐,助推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的發展
天塔獅舞驚險刺激、扣人心弦,具有獨特的吸引力,是優質的文化產業資源其文化符號是社會行為的重要指針, 文化符號的發展必須緊隨時代步伐。 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的發展需與管理、政策融合,2018 年,原國家旅游局和文化部合并,組建文化和旅游部,進一步促使用旅游彰顯文化創建價值,用文化提升旅游創建內涵。2021 年7 月8 日國務院印發《全民健身計劃(2021—2025 年)》、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為鄉村振興規劃提出《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等,政策保駕護航,為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的發展奠定基礎。 政扶持是地基,最為主要的還是要創新出群眾新聞樂見的模式。 為適應時代發展,本著“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文化理念,堅持多效并舉, 進一步減弱神秘儀式文化外衣, 給予新時代精神,演繹新的時代故事。 天塔獅舞的神秘色彩還是相對濃厚,可嘗試在天塔獅舞的演繹故事中融入精準扶貧的艱苦創業、甘于奉獻的典型故事,創作出符合時代精神,講述時代故事的優質文化產品。 創新旅游產品體驗,引爆市場賣點,如:豐富產品供給,創意求學塔獅等、個性化服務、推進智慧文旅,可利用AR 或VR 虛擬現實技術等。
4.4 鄉賢推動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的發展的發展之路
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的發展處于 “模糊-清晰-模糊” 的階段,作為脫胎圖騰祭祀,祖先崇拜的天塔獅舞,在弘揚科學精神的今天,要進一步剝除神秘外衣,向人們傳遞健康向上、和諧美滿、頑強拼搏的精神價值,達到“提升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的目的。 白晉湘論述道:民俗體育非遺保護停留在國家熱,民間冷的發展態勢,也就是說,國家在行政給予很大的支持,基層政府卻處于一種被動局面,創新力度欠缺,運行方式死板[27]。 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可借鑒李登山為村支部書記時期發展模式,發揮鄉賢的模范帶頭作用。 農村鄉賢的特質在于情感在鄉,貢獻突出,是村民較為敬重之人,這里不僅僅是指土生土長的本地人,而是將其擴充為心系鄉。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也說到,在中國的鄉土社會中“情感在鄉”被視為特質[28],在鄉村振興發展戰略中也涉及到基層治理新主體為新鄉賢。 目前,由于“城市化”的推動,致使大部分農村人才流失,為推動天塔獅舞文化符號的反展之路,可拓寬多方路徑,制定合理合規的用賢機制,提供必要的生活保證措施,優化設備環境, 吸引更多的年輕的具有相同圖情懷的新鄉賢人才回歸農村。
5 結語
原始農耕文明時代的舞獅, 在中華兒女心中具有較強的文化認同感。 對天塔獅舞象征文化的研究,在一定意義上為認知其文化提供了一種思維方式。 當今象征文化符號的研究已“突破”學科限制,成為研究文化蘊意的一種基本視角。 天塔獅舞常常與祭祀、祭神相聯系,是古代一種重要的巫術儀式,其擁有較為完整的象征符號體系,以娛神和祈福為主要目的。 現階段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民俗體育項目的發展處于改革階段,天塔獅舞管理方法、運行模式、天塔獅舞的文化等應當如何傳承,是我們應當考慮的問題。 天塔獅舞的傳承與發展不應局限于表現形式,更重要的是挖掘文化內涵,發揮文化象征符號的作用。 天塔獅舞的創作理念取自自然,來源于生活,最終的目的依然是為生活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