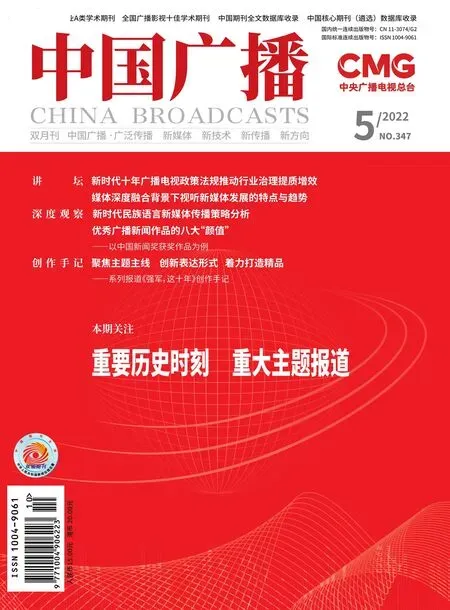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流廣播媒體重大主題宣傳的特點、邏輯及價值
☉李 晶
重大主題宣傳一般是指新聞媒體“圍繞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重點工作、重要事件進行的宣傳活動”。①換言之,重大主題宣傳的核心在于“重大”,有別于新聞媒體對一般事件的宣傳,是針對關乎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國計民生的主題“所進行的力度大、投入多(時間精力多、版面時段多、人力物力多)的新聞宣傳(通過新聞報道和新聞評論實現,往往報道和評論齊上,形成互補效應)”。②這其中,主流廣播媒體責無旁貸,其以權威性和時效性肩負著重大主題宣傳的意識形態陣地鞏固、輿論引導、上情下達等重任。
伴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和媒介環境的變遷,主流廣播媒體必須積極踐行媒介融合,推動其走向縱深化發展已是大勢所趨。同時,媒體融合實現縱深化發展也被寫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要求“推進媒體深度融合,實施全媒體傳播工程,做強新型主流媒體,建強用好縣級融媒體中心”。③可以說,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探討主流廣播媒體的重大主題宣傳的特點、邏輯和價值,有助于促進該領域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一、主流廣播媒體重大主題宣傳的特點呈現
重大主題宣傳是主流輿論引導和主流價值觀傳播的重要途徑,呈現出中央與地方聯動、宏觀與微觀平衡敘事、接近性與交互性配合的人文主義關懷等特征。
(一)中央與地方聯動
重大主題宣傳是主流廣播媒體領會和傳播中央精神、提升政治站位、匯聚全民話題和社會議題的重要戰場,以高度和深度體現其核心競爭力。這種競爭力不是媒體單打獨斗或一家獨大的結果,而是以“中央—地方”的合理化布局形成巨大合力。中央級主流廣播媒體與地方媒體聯動,體現了“既接天線,又接地氣”——既為國家政策方針疏通傳達路徑,又為其有的放矢地實施找到了重要抓手。例如圍繞“建黨百年”這一重要議題,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聯合全國各地廣播電臺及新媒體共同推出365集特別報道《中國共產黨百年瞬間》,節目以拼圖形式展現中國共產黨百年波瀾壯闊的歷史征程。在中央級主流廣播媒體的牽頭下,充分挖掘地方資源,讓地方元素有了跨地域傳播的渠道。可以說,中央與地方聯動盤活了全國一盤棋的策略,以頂層設計有力引導,激活了地方廣播媒體參與的活力,為其供給豐富的養料,讓重大主題宣傳之“樹”愈加茂盛。
(二)宏大敘事與微觀敘事結合
重大主題宣傳一般從大處著眼,在宏觀維度體現主題事件的歷史脈絡,在時間線索中鋪展歷史畫卷,力求事件的完整性以凸顯歷史價值,進而達到傳播核心價值觀,為大眾提供行為的標尺。例如中國之聲推出的《70年趕考成績單》系列報道,節目開頭涉及大量數據信息,直觀易懂地展現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各個領域的成就。同時,宏大敘事離不開微觀層面的支撐,因為諸如政策落實、藍圖描繪和社會變化離不開個體的理解、執行與反饋。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在日常生活空間中動態記錄著個體、群體、社會的發展,并在身體實踐中結成各種各樣的關系以促進空間生產與再生產,從而讓國家宏大敘事有了落地的保障。所以,“小切口”的微觀報道有效地補充了國家宏大敘事。例如中國之聲推出的《百年黨史,我家的故事》,從個體故事的講述中展現家國情懷,“將普通民眾家族史與黨和國家發展史相結合,達到交相輝映、凝聚人心、同頻共振的目的”。④
(三)接近性與交互性配合
重大主題宣傳是靠(系列性)故事或事件組成,但核心在人。人是宣傳報道的主角,因此,接近民眾,貼近民心,才能獲取民意。人始終是重大主題宣傳的寶礦,其生活的細節,構成事件的情節,編織社會關系的過程,都應成為宣傳主題策劃、內容生產、效果研判的來源。江西廣播電視臺的生態主題廣播融媒體作品《十年,我們的山江湖》,以“講述人”的角度入手,通過河道清潔員、水渠建設者、護林員等人的親身經歷讓聽眾感受江西的生態保護情況。他們的事跡引發的共情讓節目可聽、可信、可感。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重大主題宣傳還充分利用媒介技術的賦能,強調交互作用,以此擴大人文關懷的范圍,既能關照節目中講述的人,也關切到有表達訴求的聽眾。2022年湖北省兩會期間,湖北廣播電視臺湖北之聲聯合武漢“1+8”城市圈9地廣播電視臺共同推出系列廣播“快閃”活動——《2022秀出圈》。該節目挖掘出“邊走邊說”的趣味性特色,“吸引聽眾和網友在直播時間、直播地點、直播頁面聚攏,成為直播的一部分”⑤,讓他們具備了聽眾、嘉賓、城市發展見證者的多重身份,激發了其參與互動的主體性,是以交互性體現重大主題宣傳接近性的優秀案例。
二、主流廣播媒體重大主題宣傳的生成邏輯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流廣播媒體重大主題宣傳在傳播主體、傳播渠道和內容生產方面都產生了深刻變化,使其更具權威性、典型性、廣泛性。
(一)參與主體拓展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重大主題宣傳,超越了曾經以媒體為宣傳主體的單一性,進而規避了傳統媒體線性傳播的單向性。換言之,主流媒體積極引導,以大眾思維考量宣傳的主題謀劃、細節抓取、場景布局等,讓大眾參與宣傳報道,才能真正抓住其所思所想所需,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進而達到以話題促進公共討論和引導公眾輿論,以內容傳遞核心價值觀和樂觀向上精神的傳播效果。

北京體育大學體育賽事解說班學生參與中國之聲《一起向未來·冬奧之夜》節目
2022年北京冬奧會期間,中國之聲打造《一起向未來·冬奧之夜》節目,邀請北京體育大學體育賽事解說班的學生走入直播間,同主持人一起進行賽事播報、冬奧知識講解、復盤當天比賽等。青年大學生的參與,既為節目注入了年輕、激情和活力,與體育賽事的緊張與刺激相得益彰,也強化了節目互動。再如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之聲推出的互動活動“給你一支麥克風,中國之聲邀你提問兩會”的H5海報,用戶可以掃碼進入錄音間獲取發言權,向兩會代表提問。同時,節目設置熱詞使話題細分,方便用戶留言。這實際上是中國之聲傳播平臺功能拓展的一種大膽嘗試,其不僅承擔信息傳播的功能,還積極搭建平臺,以用戶驅動內容生產的模式帶來信息增量和內容聚合,“成為聽民聲、察民情、聚民智、解民憂的服務平臺,為廣大受眾‘參與’兩會提供新穎的路徑”。⑥
需要注意的是,重大主題宣傳傳播參與主體的拓展,的確為曾經略顯單一且單調的宣傳話語空間注入了新形式和新觀念,但是若沒有統一且規范的標準作為約束主體的話語行為,會影響媒體的權威性和內容生產的嚴肅性。中國人民大學欒軼玫教授認為眾聲喧嘩之下,做好重大主題宣傳的傳播邊控至關重要。她認為:“為確保主流聲音始終被彰顯被傾聽,行動者們亟需探尋新的標準統一媒介場內多元主體的傳播行為”。⑦所以,新媒介技術的使用,意味著新的傳受關系形成,進而需要新的傳媒規制進行引導與約束,才能保證重大主題宣傳主體的內在有機統一。
(二)媒介技術賦能
傳統媒介環境下重大主題宣傳的內容分發渠道相對單一,這導致把受眾固化在特定的時空內,受眾的主體性受到限制。而媒介融合造就了全新傳播環境,可讓宣傳內容轉化為用戶的“隨選”信息,用戶可在非固定時空內對信息進行接收、理解、認知與反饋,以“拉”出信息的方式發揮主體作用。同時,主流廣播媒體積極拓展內容分發渠道,深耕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和全效媒體,提升重大主題宣傳的影響力和傳播力。
廣播是以調動聽覺進而刺激人體其他感官的傳播媒介,音頻節目成為主要傳播樣態。隨著媒介融合向縱深化發展,音頻節目有了跨平臺的路徑。例如《中國共產黨百年瞬間》節目,不僅在全國廣播電臺播出,還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和各地廣播電視臺所屬的“兩微一端”播出,同時還加載到學習強國客戶端、共產黨員微信公眾號、共產黨員網等新媒體平臺。如此一來,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了節目傳播呈現出立體化形態,使其產生協同共振效應。

除了節目的跨平臺分發外,可視化的廣播模式打破了“只聞其聲”的節目傳統。不但“聞其聲”,還要“觀其人”,成為廣播節目樣態創新的重要突破口。例如重慶市涪陵區融媒體中心的《方言說美食》節目,兩位主持人各司其職,一位負責解說美食,一位負責錄制,把地道的美食以可視化的方式呈現給大眾,讓“色香味”“美食盡收眼底”。再如,吉林市經濟廣播電臺也是通過廣播可視化的方式進行國際馬拉松比賽轉播,“直播室與戶外直播進行聯動,變換多個場景,集中、全面、立體地呈現廣播和活動現場的交流實景”。⑧可以說,多渠道內容分發和多樣態節目傳播能夠多觸點地與用戶的生活時空發生交集,在短時間內產生匯聚范圍廣泛的用戶,最大限度地釋放用戶參與熱度,提升用戶黏性。
(三)敘事空間創新
敘事空間是對事件發生的現實空間的文本表述,是在盡可能完整、真實還原現實而對事件的再創作過程。主流廣播媒體在重大主題宣傳中比較常見的創新方法是“主題—并置”,是指“構成文本的所有故事或情節線索都是圍繞著一個確定的主題或觀念展開”。⑨簡言之,每個文本的敘事都統一圍繞一個主題鋪展,它們之間不是按照時間線索排序,而是體現了空間并置的特點。
例如,《70年趕考成績單》節目選擇了30位涉及不同年齡段和職業領域的人共話10個關乎國計民生的議題。其中《小小讀書郎》中的受訪人蘇明娟,以堅強的毅力學有所成,詮釋了知識改變命運的真諦;《車輪上的濃縮歲月》中的受訪人司機師傅李隆舉,回憶幾十年來中國公路的顯著變化時感慨萬千;《面朝大海》中的50后受訪人莫華,以親身經歷描述中國旅游業的巨大發展……這些鮮活生動的案例表明,對中國故事的再創作,應立足時代主題,以百姓的視角,展現百姓生活空間的種種變化,體現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非凡成就,體現了宏觀著眼和小切口支撐的平衡,正所謂“細微之處見真情”。
主流廣播媒體對中國故事敘事空間的再創作還表現在話語范式的變遷,具體表現為“新聞成為集信息、輿論、監督、教育于一體的產品,語態方面形成以新華語體為主導,通訊、深度報道等其他多元新聞話語為補充的格局”。⑩簡言之,話語的貼近性為重大主題宣傳報道所青睞。在系列報道《我們村里的年輕人》中,主持人展現了拉家常的功力,用百姓聽得懂的話聊百姓聽得懂的事,用百姓說的話聊百姓說的事,樸實無華、通俗易懂讓宣傳報道充滿人情味,有力地拉近了節目與百姓的距離。
三、主流廣播媒體重大主題宣傳的重要價值
主流廣播媒體重大主題宣傳的價值體現在傳播能力立體化、報道效果優質化,進而在更加廣闊的層面有力推動基層社會治理。
(一)以協同生產增強立體傳播能力
媒介融合對主流廣播媒體帶來的最為顯著的影響之一,就是傳播渠道的擴展和內容的協同生產,從而形成傳播矩陣。立體傳播體系的建設使有序的資源優化配置產生“1+1>2”的效應。這種協同生產既表現了傳統廣播媒體向內開掘,強調重大主題宣傳的系列性,例如浙江寧波新聞綜合廣播積極響應中央提出的“一帶一路”發展理念,策劃推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始發港城市紀行》系列報道,通過“歷史的回望”“現實的夢想”“未來的思考”等三個層面,采制27篇報道,形成整體和諧的系列報道框架;同時,主流廣播媒體重大主題宣傳又向外探索,注重視覺元素和平臺媒體的嵌入,例如西藏廣播電視臺在圍繞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這一主題宣傳中,不但在其王牌廣播節目《新聞早世界》推出《共產黨來了苦變甜——慶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的專題節目,而且“‘共產黨來了苦變甜’這一策劃主題產生了電視、廣播、專題網頁和晚會等多種形態的內容產品”。?西藏廣播電視臺此舉是在統一思想、統一主題、統一協調的前提下,既發揮傳統優勢,又凸顯不同媒介的特色,從而生產出符合用戶喜聞樂見的節目產品。
(二)以精心策劃優化宣傳報道效果
主流廣播媒體重大主題宣傳若要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除了激發用戶主體性和拓展傳播渠道外,“內容為王”是始終如一需要秉持的金科玉律,而精心策劃是實現這一原則的必由之路。宣傳報道借助描述、采訪、敘事、議論、抒情等手法,達到引人入勝,才能啟人心智。例如中國之聲推出的特別策劃《我們村里的年輕人》中的《在希望的瓜田上》,通過采訪讓受訪人描述主人公黃有生:
族叔黃徐林:我眼中的黃有生,從小就很誠實,家里比較貧窮,為了改變家里的生活,就去種大棚瓜,現在生活慢慢好起來了。
哥哥黃順生:他做事又勤快又吃得苦,對父母也蠻有孝心的。
蘭盤村村支書鐘平根:他個子不高,瘦瘦小小的。通過這幾年種西瓜,他賺了一部分錢,現在比以前更自信了。
這種借他人視角呈現主人公形象,避免了自說自話而導致的信息差,同時可以更加細致入微地展現主人公的口碑,進而豐滿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采訪內容與故事核心相契合,切中題中之義也易于引發共鳴,從而增強傳播效果。
(三)以觸點多元推動基層社會治理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流廣播媒介可以最大限度擴大用戶增量,同時以大數據和算法為技術支持,深入挖掘用戶的喜好,生成用戶畫像,促進內容分發的精準度,以此深達社會的各個領域和用戶的生活空間。如此一來,主流廣播媒體所進行的重大主題宣傳就有了上情下達的起錨方向和落地抓手,就有了把國家大政方針同基層社會實踐聯系在一起的中介和樞紐,把中央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家風、家教等道德觀念與百姓生活融合在一起,在橫向和縱向中開辟信息高效傳播的通道,進而有力推動基層的法制和道德建設。同時,這種宣傳報道方式有助于最大限度調動大眾參與的積極性,集思廣益且廣開言路,為社會創造“恒溫層”。簡言之,重大主題宣傳成為“‘跨平臺、跨圈層、貫層級’多方聯合的融媒體社會化生產,有利于連接屬性作用的最大發揮”?,促進基層社會治理網絡的構建。
四、結語
媒介融合是時代之需和大勢所趨,促使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積極整合社會資源以強化和鞏固社會主流輿論的綜合優勢。借助媒介融合,主流廣播媒體重大宣傳報道的參與主體更加豐富,傳播渠道更加多元,內容生產更加多樣。在未來,或許其應在縱向上做到“中央統領、省市兼容、縣域縱深的層級布局”?,在橫向上觸及不同領域,覆蓋不同平臺,連接不同用戶。總之,主流廣播媒體的重大宣傳報道若以點帶面、由內而外——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相通,國家政策與大眾生活相連,必有利于獲取豐富生動、啟智潤心的效果。
注釋
①田麗:《新媒體時代的重大主題宣傳探析》,《青年記者》,2020年第4期,第48頁。
②丁柏銓:《重大主題宣傳:特點、現狀與優化》,《新聞與寫作》,2020年第10期,第74頁。
③《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網,http://yuqing.people.com.cn/big5/n1/2020/1104/c209043-31918159.html.
④陳怡:《多維度拓展重大主題報道空間——中國之聲“建黨百年”報道的實踐與思考》,《新聞戰線》,2021第17期,第86頁。
⑤周漫、金若晗、向秀:《隨行廣播互動貼近 守正創新融合傳播——湖北之聲2022全省“兩會”全媒體報道這樣“秀出圈”》,《新聞前哨》,2022年第9期,第25頁。
⑥周宇博、楊可:《與時俱進推動重大主題報道模式創新——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22年兩會報道的創新探索》,《新聞戰線》,2022年第7期,第36頁。
⑦欒軼玫、徐雪瑩:《融媒體時代重大主題報道的傳播邊控》,《當代傳播》,2020年第4期,第94頁。
⑧《時代驅動下的廣播可視化發展》,聽見廣播微信公眾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367733686262908&wfr=spider&fo r=pc.
⑨龍迪勇:《空間在敘事學研究中的重要性》,《江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8期,第49頁。
⑩趙曼、李林青:《重大主題報道融入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教育研究》,《傳媒》,2022年第9期,第95頁。
?王鳳:《全媒體時代主流媒體重大主題報道的守正創新——以西藏廣播電視臺為例》,《傳媒》,2022年第14期,第44頁。
?欒軼玫:《重大主題報道:媒介化治理的傳播實踐》,《編輯之友》,2022年第3期,第9頁。
?欒軼玫:《信息傳播與公共服務: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雙融合”》,《視聽界》,2018年第5期,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