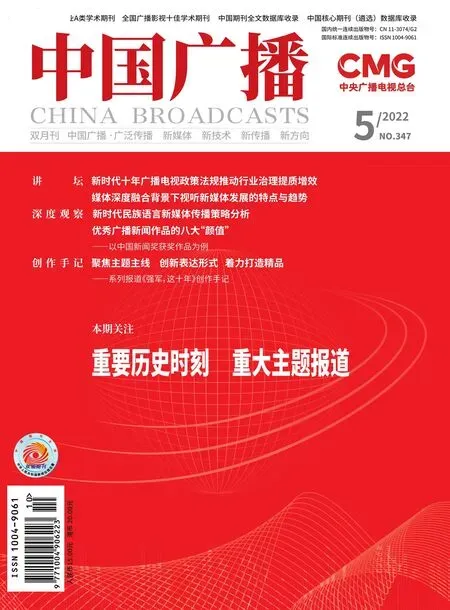AI主播發展背景下播音主持創作革新
☉仇婧楠 丁治鋼 時璟呈昕
任何科學技術的誕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1955年AI(人工智能)由于當時的計算機還達不到大規模的數據處理和運算能力,相關技術研發陷入低谷。直到2006年,英國科學家杰弗里·希爾頓(Geoffrey Hinton)等人首次提出了“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概念,才使AI技術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如今AI技術在廣播電視領域的發展和成熟,已經可以讓一個“克隆”真人的AI主播獨立完成新聞播報工作。人工智能技術為播音主持創作帶來了形式與內容的雙重變革。
一、從智能朗讀到AI主播
無論是智能手機里的語音朗讀,還是活躍于喜馬拉雅、微信讀書等知識類App上的智能有聲讀物,AI朗讀的語言傳播形式已經出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托于科技的發展,人類把每個字的聲音錄入機器,芯片根據錄入的文字匹配播放相應的讀音。隨著技術的不斷更迭和發展,大數據、云計算的出現給予了智能朗讀更為先進且更加接近真人聲音的語言表達方式。如今,AI技術已經可以通過一個視頻來“克隆”出一個主播,依靠動態捕捉技術,機器能夠根據主播的面部動作表情學習播音狀態,同時大數據的深度學習讓語音變得連貫流暢,更加接近真人。
(一)“形”“神”兼備:應用優勢凸顯
如果說早期的智能朗讀是還原再現真實的人類聲音,那么現今在大熒幕上與受眾進行互動交流的AI主播形象已經做到了“形神兼備”。2018年5月,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直播長江》節目中,以康輝為原型的AI主播“康曉輝”,無論從外形還是從聲音上,都實現了對康輝本人的高度還原,并且準確無誤地完成了主持播報工作。AI主播對真人主播栩栩如生地仿真呈現,與“藝術形式和內容相統一”的藝術創作規律十分契合,在符合節目形式創新的同時,也滿足了受眾對電視藝術的審美需求。

以康輝為原型的AI主播“康曉輝”
在實際應用過程中,AI主播效率優勢明顯。AI主播是通過采集真人主播的聲音和圖像,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對虛擬形象進行合成,在系統中輸入文本就可以進行新聞播報工作。AI主播可以實現全天候無差錯播讀新聞。成熟的智能技術使其數據庫不斷更新進步,因此即使在不斷變化的語境下,如網絡用語、多音字、變調輕聲,AI主播也能夠應對自如。并且,機器處理文字稿件更為快捷,一旦文稿形成就能及時播報,十分契合新聞的時效性要求。
除了效率優勢明顯以外,AI主播收益優勢也比較顯著。北京電影學院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教師王秋碩和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博士、編劇魯昱暉認為,AI主播是媒介產品,具有典型的初始成本高、邊際成本低的經濟特性,一旦完成首輪開發,就能依靠增加產出獲得利潤。AI主播工作的機會成本遠小于真人主播,亦能減少人力資本投入。①AI主播作為技術產品,前期研發投入相對較大,不過,合成后的AI主播能夠穩定持續播報,維護成本較低,相對于真人主播具有更好的延續性,同時節省時間和人力投入,優化資源配置,長遠來看,應用周期更長,收益周期更短。
(二)“藝”與“技”的碰撞:應用壁壘頑固
AI 主播作為真人主播的仿真品,是一次技術對藝術的高度模仿,是“藝”與“技”的碰撞。AI 主播可以模仿真人主播的“技”,卻很難跨過“藝”的鴻溝。AI主播是基于大數據庫和編程系統來創作文稿的,在實際應用中很難突破個性化的壁壘,也無法具備同真人一樣的主觀能動性,所以,更無法為節目和觀眾搭建長期穩固的情感橋梁。AI主播雖然在推出的前期可以迅速“吸睛”,在大數據的幫助下集合大多數主播的技術優點,但它無法塑造個人形象和建立情感紐帶。
二、AI技術與播音主持創作的融合
早在2010年美國敘述科學公司(Narrative Science)就已經推出了機器新聞寫作工具,約每30秒就能輸出一篇新聞報道。它的基本操作模式為,先通過系統的搜索引擎收集大量高質量的數據,并從中尋找新聞要素,之后決定新聞的角度和風格模式,最后按照“元作者”提供的詞匯來組織句子。②由此可見,AI技術與創作的“采編”部分已經實現了“技術與藝術”的融合。如今,日趨智能化的大數據信息抓取、語音識別、圖像識別等AI技術對播音主持創作中的“播”更是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助益作用。
(一)AI新聞主播加持新聞稿件播音創作
AI新聞主播對新聞稿件進行了精準的“二度創作”,提高了新聞節目的傳播效率。新聞稿件分為消息、通訊、評論等類型。消息類稿件篇幅較短,詞匯簡單明了,語言節奏快,采寫迅速,十分適合智能語音技術進行識別處理。AI新聞主播可以很精確地對文本稿件中的停頓、語氣、重音等外部表達節奏進行分析、檢索。由于新聞對時效性要求高,結合AI主播穩定、高效的特點,不難看出AI主播在新聞類節目的創作中更具優勢。
但是,目前AI主播還只是對主持人聲音、形象、動作的簡單模仿,而對于新聞事件中的觀點評論及情感表達還需要人為介入。
(二)AI讀物賦能文學作品播音創作
隨著手機App的廣泛使用,像蜻蜓、喜馬拉雅、微信讀書等文化類App需要大量的有聲作品來吸引流量。AI讀物對文學作品進行創作,可以快速越過人工創作需要的備稿步驟,利用智能大腦快速分析文學作品,轉化為聲音作品投入市場,雖然在表現稿件情感方面依然略為機械和生硬,但是已經可以滿足一部分受眾對了解文學作品內容的需求。另外,AI讀物中聲音的可變性更多,切換更為迅速,作品的制作成本也更低。
AI讀物能夠提高文學作品的創作效率,但缺少情感融入。以《斗破蒼穹》這本小說的有聲讀物為例,雖然有AI主播的錄制版本,但在播放量上有很大差距。根據喜馬拉雅手機App上的顯示數據,AI版的《斗破蒼穹》作品并沒有顯示播放數量,而真人版的《斗破蒼穹》作品的播放量達到了9.69億次,每集評論在200條以上。AI主播的作品整體非常流暢,但是整段聲音語調單一,不能突出人物情感和個性。藝術創作本身具有主觀性,真人會在文本基礎上產生獨特的風格,從而演繹較為生動,而AI讀物不具備這樣的功能。
三、AI主播發展背景下播音主持的創作革新
法國文學家居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對藝術和技術的關系做了闡述:“藝術愈來愈科學化,科學愈來愈藝術化,兩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會在山頂重逢。”③藝術與技術融合的成功案例已經頻繁出現在多個藝術領域,因此,在AI主播發展背景下,真人播音、主持創作應做出革新,積極擁抱AI技術,促進AI技術與播音主持的創作革新與融合。
(一)創作形式智能化革新

央視新聞冬奧會AI手語主播
藝術創作需要藝術形式與內容的統一。AI智能主播給真人播音主持的創作帶來新的挑戰與機遇,依托AI主播聲音的多變、數據庫豐富等優勢,對提高節目視覺觀感和促進AI與真人互補具有重要意義。
播音主持創作形式智能化革新體現在優化“人機協同”上,無論是新聞稿件還是文藝稿件的創作都面臨著形式革新的時代需求,AI主播和真人主播優化組合,從宏觀角度上說是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合作共贏,兩者合作的前提是基于“優勢互補”原則,AI主播可以承擔更多固定環境下的信息篩選、播報,真人主播則需要進一步加強自身專業技能、情感表達、人文關懷等。正如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楊嘉儀所說,人工智能正在顛覆人類傳播,新聞業需要接受技術的鍛造,在維護人類權力的基礎上,更好地實現人機耦合,促進信息社會的發展。④
(二)創作內容人文化革新

搜狗聯合新華社推出的3D-AI合成主播“新小微”
AI主播發展背景下,真人播音主持對內容的創作顯得尤為重要。無論AI技術如何更新迭代,真人主播始終是創作內容的主體和主導者。在冰冷的機器面前,人類擁有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情感,播音主持創作內容的人文化革新是要關心人民群眾、貼近人民群眾,現如今越來越多的主播從臺前走到幕后,參與節目的策劃和制作,通過采編播一體化參與增加節目的深度,引起受眾的共鳴。根據事件的事實進行合理的調查和分析,在此基礎上形成有理有據并且旗幟鮮明的觀點,實現推動社會進步、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目標。⑤當下,播音主持創作的藝術作品如何引領新時代受眾的審美,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真人播音主持在創作內容實現人文化革新方面要重視專業技能的培養。一個節目主持人或主播是否具備專業技能,語言表達和情感運用是標準之一。AI主播可以做到語言表達,但卻無法實現情感交融,這一點與真人主播無法比擬。例如,我們熟知的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新聞周刊》欄目主持人白巖松,因其犀利、一針見血的新聞評論風格讓大家熟知,同時新媒體端的《康輝的Vlog》《剛強的Vlog》等新聞評論,都離不開主持人本身的政治主場、專業知識、新聞素養以及適當的情感融入等。期望在AI主播發展的背景下,真人主播在創作內容和人文化革新方面有很大提升。
四、結語
顯而易見,AI主播在廣播電視領域中的應用,有助于提升播音主持創作工作的效率,創新了受眾群體與傳播媒介的信息互動與交流模式。同時,AI主播為播音主持創作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加速了播音主持創作形式和內容的革新,也對當下真人主播在專業技能方面提出新的要求。播音主持創作依附于技術發展和社會文化更迭,全新的媒體格局和技術運用勢必會帶來播音主持創作形式的嬗變,但是藝術創作有其客觀規律,堅守專業精神和人文情懷,是發揮AI主播對播音主持創作的重要前提。
注釋
①王秋碩、魯昱暉:《智媒時代播音主持藝術的創作嬗變與價值考究——以“AI合成主播”為例》,《中國電視》,2021年第4期,第86~91頁。
②胡曉巧:《人工智能技術在新聞傳播業中的場景應用——以百度大腦為例》,《新媒體研究》,2020年第6期,第23~24頁。
③趙廣遠、田力:《技與藝的博弈:人工智能語境下主持人職能重構》,《當代電視》,2019年第10期,第93~96頁。
④楊嘉儀、楊雅:《不止是“傳聲筒”:AI合成主播的特征、趨勢與進化邏輯》,《教育傳媒研究》,2019年第6期,第28~32頁。
⑤李惠文:《虛擬播音主持與傳統播音主持的發展創新》,《傳媒》,2021年第13期,第44~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