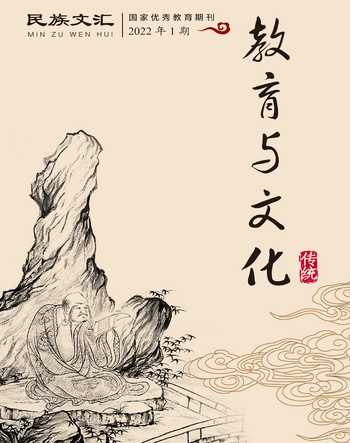繪畫性在油畫創作中的運用
張媚
摘 要:繪畫一直是伴隨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語言。而油畫作為繪畫中的重要門類由于他在繪畫語言上的豐富性和強大的表現力,支撐了西方國家近一個世紀的繪畫歷史。攝影術的出現對繪畫造成了巨大沖擊,人們開始質疑它存在和繼續發展的必要性。在質疑的同時‘繪畫性’一詞被提出來用于強調繪畫存在的獨特性。油畫在中國的落戶真正意義上僅有百年時間,而那時正是西方現代藝術興起的時代,國內畫家用這一百年時間理清了油畫的發展脈絡,但對‘繪畫性’的問題卻始終含糊不清,或是避之不談。
關鍵詞:繪畫性 創作實踐
第一章 概念界定
“繪畫性”一詞是黑格爾提出,一般是指繪畫語言的相關問題,即純手工繪制的特性,與攝影照片有一定的區別。繪畫的思維方式因個人個性和風格的各不相同,觀察或表現的角度不同,思想自然也會產生一定的差距。因而作品的效果往往相差甚遠,甚至有觀念上的根本差異。
從某種程度上說,“繪畫性”只是一個大致的稱謂,其內涵在一定意義上具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分。從廣義上說,“繪畫性”通常用于描述或解釋除了繪畫這一藝術門類之外的其他藝術,例如雕塑、攝影等其他藝術形式,這些藝術形式近似于繪畫又不同于繪畫。從狹義上來說,有關繪畫性的界定,要比廣義上復雜的多。
第二章 “繪畫性”在東西方繪畫史上的發展
1.東方
與西方相比,中國傳統繪畫一直具有豐富的繪畫性,這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首先,中國文化受到儒佛道思想的影響,追求協調統一兼容并蓄、注重意境,講究筆墨的運用,擅于通過“書寫”的方式來描繪心境。它所描繪的物體有具體的形象,但不完全是現實中所存在的真實,它的真實在于尊重藝術家心靈感受的真實。
其次,中國傳統繪畫一直重視畫面趣味性的表達,這其中包含了“意境”和“筆墨”,“意境”是藝術的靈魂,是作畫的動機和最終效果;“筆墨”是表現手法,強調書寫性是它的特點,而書寫性的側重點就在于“寫”。因此可以說,整個中國傳統繪畫就是一個“寫的藝術”,而中國講的“寫”和西方的“繪”又可被視為同一個概念。所以對中國傳統繪畫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
2.西方
在20世紀以前并沒有提出有關“繪畫性”的概念,但是繪畫性一直存在于繪畫的歷史中。早在舊石器時代的壁畫,用簡單的幾筆就能生動地概括出動物的靜態特征;中世紀人物比例被拉長,色彩和明暗的純粹化呈現出宗教的肅穆感;文藝復興時期把科學性和以人為本的觀點融入了繪畫中等;直到進入19世紀,攝影術的出現,繪畫的地位遭到了威脅,達達主義首次挑戰了繪畫性;1917年,杜尚把小便池放在博物館,徹底挑戰了傳統的繪畫藝術。此后,直接利用現有產品和大眾媒體,對繪畫的存在產生了巨大沖擊;1960年極簡主義出現,主張將繪畫語言簡化到清晰明確的抽象形狀和平整光滑的色塊,排除了藝術家的主動性和感情表現;在這之后繼續出現的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多媒體藝術等成為了那個時代的主流,繪畫慢慢淡出了藝術舞。70年代到80年代,許多新鮮的媒體進入了繪畫,表現的內容和手法越來越自由。至此,繪畫性在繪畫作品中再次突出了重要性。
第三章 繪畫性在作品中的傳達
1.技術美感傳達繪畫性
洛佩斯,西班牙寫實畫家。熱衷于描寫城市的街景、寬闊的郊區、熟悉的家庭小場景等。他把看似平凡卻無法融入畫面中的景色描繪得很感人。對比古蘭街的實景圖,可以發現一條看似涼颼颼的街道風景在他的畫筆下面反而變得溫情。他的作品雖然屬于寫實,但并不是模仿真正的現實,而是增加畫面的繪畫性,傳達某個時間凝固的永恒感。洛佩斯的畫具有鮮明的鏡頭感,細膩的程度與照片相似,但處處都有畫家的創意。
在我看來,畫家技藝嫻熟,制作精巧和繪畫性是不矛盾的。并不是說那種看似筆觸極強的畫面才具有繪畫性。技術實際上豐富了畫面語言的開拓表現性,只有精湛的技藝和精巧的制作才能更好地傳達繪畫性。畫家通過技術將感情融入畫面,正確地表現畫家的觀念,并表現出具有美感的對象。以繪畫性為前提條件,拓展表現手法和技藝。如果花很多時間在如何復制對象的技術上,畫面就會僵化、沒有生氣,且嚴重喪失繪畫原有的意義。
2.形式美感傳達繪畫性
厄格羅,英國畫家,作品嚴謹、簡潔、莊重。為了追求更好的平面感,將色塊進行了充分的概括,并對顏色的明暗對比進行減弱。在人體重要的轉折點,才有大的反差色調,身體其他的構造處是塊面般等微小顏色的變化。這些大小的色調都是硬邊的刀切般的不規則的幾何形狀,與整個畫面的幾何形式相呼應,形成了簡單的理性美感。他的作品將“形式美感”在繪畫性中充分體現了出來。
繪畫性豐富的形式需要畫家主觀的發現和創造,對物象進行高度概括。這是內在的感情和外在形式的統一,主客觀的統一。如果擺脫畫家的感性和創造性進行創作,就會像電腦PS效果一樣,在形式上機械地用“個人化的筆法”或與裝飾畫的圖案類似,繪畫也將失去原有的意義。
2.材料美感傳達繪畫性
夏禹,青年藝術家,他的畫里經常出現病態人物和片段式的場面,仿佛舊照片靜靜地訴說著過去的歲月。他使用坦培拉材料來達到技法方面的突破,通過把顏色一層層疊加,色層相互透疊后產生微妙的變化。微微的灰色調稍微明亮,帶有一定的光澤感。特別是用柔軟的布或干筆揉搓,更像古代陶瓷的表面釉質層的瑩潤溫和,形成了他獨特的,含蓄內斂的畫面語言。新材料的運用也給繪畫帶來了重要的視覺體驗。
雖然材料進入繪畫并不新鮮,但繪畫并不是為了材料,而是為了明確其繪畫性,也不是盲目追求媒體材料的效果。媒體發掘只有在基于畫面的內容形式、題材觀念來體會畫家的表現意圖和感情時,它的表達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夠創造性地實現繪畫表現手法的多元化,強化畫面的感染力和繪畫性。
總結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也是知識不斷更新的時代,同樣藝術也是如此,在多種藝術形式的沖擊下,藝術語言、藝術形式在不斷的發生著變化不斷,畫種與畫種之間相互學習,融會貫通。架上繪畫已經不是一個唯一的藝術表現形式,但這不代表架上繪畫的消失,眾多的繪畫大師足以說明架上繪畫有無限的延續性,繪畫作品依然以其真誠的情感和高超的技藝打動著觀者,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注釋:
[1]楊揚. “境生象外”美學思想對油畫創作的影響[D].大連外國語大學,2021.
[2]魯士秀. 《孤獨》系列油畫創作思考與實踐[D].云南藝術學院,2021.DOI:10.27777/d.cnki.gynxy.2021.000009.
[3]陳宇陽. 我對都市題材油畫的思考與創作實踐[D].云南藝術學院,2021.DOI:10.27777/d.cnki.gynxy.2021.000125.
[4]胡婕. 對王克舉的繪畫語言藝術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21.
3420500338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