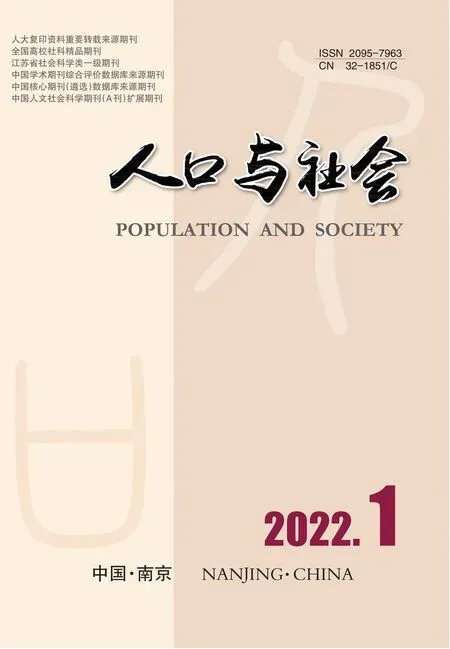后扶貧時代農村青年消費的新特點
——以陜西關中城郊B村為例
邢成舉,魏曉麗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發展學院,陜西 楊凌 712100)
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1],表明當前我國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但脫貧摘帽并不代表反貧困斗爭的結束,而意味著我國減貧實踐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指出,要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共同富裕方向,將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建立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幫扶機制,健全鄉村振興領導體制和工作體系,加快推進脫貧地區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全面振興[2]。可見,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這兩大戰略實施的交匯期,對農村低收入人口的社會幫扶,不能僅停留在物質層面,更要關注其發展能力。
筆者在調研中發現,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民的收入快速增長,與此同時他們在城市買房、買車、餐飲、休閑娛樂等方面的消費也在不斷增長,出現了一批“消費貧困”的農村青年。從年齡結構來看,以“85后”“90后”和“00后”為主;從學歷來看,普遍為初中或大中專技校畢業;從工作類型來看,多為城市中的藍領技術工人或缺乏技術的普通勞動者。這批農村青年的消費觀念與父輩有明顯差別,不同于父輩婚后將資源向子代傾斜以謀求家庭的再生產,婚姻對農村青年人的約束力下降,他們更傾向于將資源向自己傾斜,追求自我生活品質的提升,從而被消費主義裹挾。他們對房、車、吃穿用度的要求較高,消費水平超出了自身需求以及承受能力,呈現出非理性特征。這導致了他們的經濟積累能力下降、家庭脆弱性增強、因消費返貧的風險增加,甚至形成了一種新類型的貧困。僅從絕對收入來看,他們并不一定是貧困者,但從消費和收入支出結構來看,他們往往是月光族甚至是負債族。消費貧困背后深層次的含義是消費主體的非理性行為導致其發展能力不足。
一、文獻綜述
(一)消費貧困及其成因
在消費貧困的相關研究中,部分學者認為,商品與服務的消費提高了人類福祉[3]。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生活區域對其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有顯著影響[4-5]。收入較低以及社會保障的不健全抑制了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6],因此要通過各種手段來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刺激經濟增長。這些研究重視消費的經濟價值,卻忽略了消費的社會影響,預設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是純粹的經濟理性行為。
與以上觀點不同,另一部分學者指出高消費正在成為農民返貧的重要誘因。在齊格蒙特·鮑曼看來,隨著物質產品的不斷豐富,西方國家迎來了消費社會,此時的窮人不再是物質產品極度匱乏者,而是指不具備消費能力且在精神層面喪失尊嚴的“新窮人”[7]。結合我國現實情況,在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后,“新窮人”感受到的不再是生存層面的貧困,而是消費層面的貧困[8]。因此,消費貧困在本文中被定義為“個體的非理性消費行為擠占了自身和家庭再生產資源,收支結構失衡導致其發展能力不足的狀態”。
在消費貧困的成因方面,主要有兩種解釋。其一,消費貧困與現代社會的轉型高度相關。現代性的擴張帶來了經濟的增長,而經濟增長在部分程度上擴大了低收入人口的規模[9]。現代消費方式更加復雜,商品的實用價值被削弱,人們的消費欲望不斷提升[10],現代消費文化極大地增強了低收入人口的剛性需求[11],導致其基礎性消費增加[12]。另外,消費不只是為了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它還區分著社會階層[13],農村居民的面子競爭導致其容易過度消費,返貧風險增加。其二,消費貧困與婚姻家庭高度相關。失衡的性別比使女性在婚姻市場中更具優勢,城市對農村的婚姻擠壓導致農村傳統婚姻圈被打破[14],農村婚姻市場出現了高價彩禮、結婚花費過高的現象[15],這也使農村家庭容易返貧。這兩種解釋對理解消費貧困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同時我們也應該發現消費行為不只是個人行為,不同年齡段的群體有不同的社會經歷和社會心理,即便處在相同的時空下,他們的消費行為也會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所以本文嘗試從代際差異的角度探討農村青年的消費貧困現象,分析消費貧困的發生機制與其所產生的社會影響。
(二)代際差異與農村青年的消費貧困
代際差異有兩層含義:一是屬于個人特征且與生命周期高度相關的年齡層差異;二是屬于群體特征且與生命歷程高度相關的時代差異[16]。根據生命周期假說,個體的消費行為與其年齡密切相關,不同年齡段的人由于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不同,消費行為也有所差異[17],比如個人成家之后會傾向于經濟積累,增加家庭預防性儲蓄[18]。年齡對消費的影響反映了個體自身的成長變化,但同時由于人是處在社會環境之中的,也應考慮到時代變遷對個人消費行為的影響。社會制度的轉型、消費政策的轉變以及個人的境遇等都會對其消費行為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19]。以代際差異為切入點來理解農村青年的消費貧困,是假設青年人的非理性消費行為不僅受到個體年齡(生命周期)的影響,而且受到時代背景(生命歷程)的影響。
從個體的生命周期來看,每一代青年人都有一段利己主義消費時期,但綜合時代背景及群體的生命歷程來看,當下的農村青年與過去的農村青年相比,在消費方面出現了較大差異。當下農村青年的消費結構日益復雜,消費邏輯從“主動攢錢”轉變為“意外余錢”,“主動攢錢”是在家庭利他主義的驅動下,個體更多追求家庭的發展而產生的計劃性行為;“意外余錢”是在個體利己主義的驅動下,個體更多追求自身生活享受而產生的隨意性行為(消費代際差異的其他方面詳見表1)。

表1 消費的代際差異
二、調查情況與農村青年的消費特點
(一)田野調查情況
B村位于西安市郊區,縣道、鄉道橫穿村落,交通便利,是典型的城郊村。全村有6個村民小組,467戶,1 917人。村域面積3 789畝,耕地面積2 317畝。村民通過種植甜瓜、相棗、櫻桃以及生產羊奶獲得收入,村莊農業產業發展勢頭較好。
根據“咨詢估算”和“抽樣調查”所得數據,將村民的家庭收入類型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私營企業主,其家庭年收入在50萬元左右,人數約占B村總人口的5%。圍繞甜瓜、相棗、櫻桃和羊奶,B村發展了羊乳廠、紙箱廠以及農產品加工銷售方面的企業,部分農民成了老板。第二類是種植大戶和進城務工技術工人,其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左右,人數約占B村總人口的40%,種植大戶承包著20畝以上的土地用于種植甜瓜或櫻桃,技術工人的學歷一般在大專及以上,掌握了電焊、汽修等技術。第三類是小農戶和缺乏技術的普通打工者,其家庭年收入七八萬元,人數約占B村總人口的45%。第四類是勞動力不足的老弱病殘群體,他們家庭年收入一兩萬元,人數約占B村總人口的10%。以村莊為范圍來確定低收入人口,則第三類和第四類人群均屬于低收入人口,從比例上看,低收入人口占比超過村莊總人口的50%。本文所關注的青年群體主要出現在這兩類家庭中。
目前,農村居民的家計模式出現了明顯的代際分化——中老年人主要在村務農,青年人大多進城務工。除去隨遷家屬與子女,B村在外務工的人數約為530人,務工地點集中在西安、咸陽等周邊城市,以“85后”“90后”“00后”為主。這批農村青年的人生經歷有很多相似之處:從經歷上看,他們大多在畢業后直接進城務工,沒有太多農村生產生活經歷;從職業來看,他們并不愿像老一輩進城務工者一樣從事建筑工、保潔、保姆等辛苦的工作,而是傾向于自主創業,想通過創業在城市迅速過上理想的生活,又往往因為自身能力不足、缺乏資金以及激烈的市場競爭等原因以失敗收場;從消費水平來看,他們穿著高檔,用著新款的手機,開著私家車,沒事就去下館子……吃穿用度等方面毫不吝嗇;從居住空間來看,他們生活在城市,其中70%的青年人結婚時在父代的幫助下有了自己的住房,但是由于在城市中沒有穩定的工作和社會保障,仍然需要農村父母的經濟補貼。
(二)當前農村青年的消費特點
1. 個體本位
一般而言,農村家庭的消費因家人所處年齡段的不同而具有周期性特征,農村家庭的消費需求取決于農村家庭再生產所處的階段[20]。農村的中老年人在其青年時期,中國市場經濟和城市化進程緩慢,在消費時更關注商品的實用價值,尤其是結婚成家、生兒育女后,他們普遍會為了滿足家庭再生產的需要抑制自身的消費需求,主要以維持生活為主,消費呈現出家庭本位的特點。
而今,消費成了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消費主義營造出一種自由平等的幻象,消費者看似可以自由選購商品,但商品的背后卻被貼上了社會地位的標簽,一些人為了獲得他人的認同就特意去消費特定品牌的商品。來自農村的青年先賦性社會資本不足,同時受制于學歷、資歷等,在職場中通常所處級別較低,自我價值感較低,于是想要通過消費來獲得存在感。“形象要走在能力前面”“人要學會包裝自己”“錢攢著就是個沒有意義的數字”等話語被這批農村青年廣泛認同。即便是結婚后,他們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費支出仍然居高不下,追求個人高消費的生活。
總之,農村家庭在消費觀念上存在著明顯的代際差異:中老年人把家庭再生產當作人生目標,消費呈現出家庭本位的特點;而青年人更加注重自我享受,消費呈現出個體本位的特點。
2.過度支出
農村中老年人不管是在其青年時期還是當下,都普遍表現出“重儲蓄、輕消費”的特點,他們將勤儉節約視為一種美德,在日常生活中能省則省,絕不輕易消費。
而今的農村青年卻表現出透支消費、過度消費的特點。一方面,農村男多女少、城市對農村婚姻的擠壓使商品房、私家車和彩禮成了農村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場中提升自身競爭力的籌碼;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農村青年的日常消費水平也不斷提升。以B村為例,農村家庭除了需要一次性支出80~100萬元幫助青年人順利結婚以外,有的父代還要負擔青年人日常生活中吃飯、加油、通信等方面的開銷,一個由年輕夫婦和兩個孩子組成的四口之家一年需要5~6萬 元才能維持日常生活。子代日常生活的高消費使家庭無法積累經濟資源,而絕大多數農村父代自身也無力承擔子代進城買房、買車和彩禮等一系列費用,不得不因此背負債務。農村居民一般傾向于向親朋好友借錢,但是當大多數親朋好友也面臨相似狀況,資源有限時,他們就需要向金融企業借貸,因此催生了大量的本地貸款公司,信貸手續越來越簡單快捷,這也刺激了農村青年的消費。“吃了今兒就不顧明兒”“只想著錢多、舒服、干活少”“攢不下錢”是B村中老年人對青年人的普遍評價。
總體而言,農村中老年人傾向于主動攢錢,自給自足,而青年人則傾向于主動消費,甚至透支未來收入。
3.消費金融化
在農村中老年人的青年時期,網絡技術尚不發達,又受制于自身知識水平和學習能力,目前他們仍以紙幣為媒介的線下消費為主,呈現出消費方式傳統、消費內容單一、消費心理保守的特點。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農村青年的消費方式、消費內容和消費心理都發生了巨大轉變。第一,消費方式的便利化。相比于農村傳統的“廟會”“集市”等固定時空場域的消費方式,網絡購物成了當前農村青年消費的重要方式。這種方式打破了時空限制,使他們可以隨時隨地利用碎片化的時間挑選和購買商品。同時,花唄、白條、信用卡等便利借貸方式的出現也減輕了他們的消費顧忌。第二,消費內容的多樣性。一方面,商家通過“簽到領券”“拉人砍價”“愿望清單”等各種形式實現與消費者的互動,擴大購買需求;另一方面,商品類型不再受地域限制,發達的物流可以把全球各地的商品送到消費者手中。質優價廉的商品在滿足青年人不同需求的同時,也提高了他們對線上消費的依賴程度。第三,消費心理的畸形化。當前消費方式已經不再是傳統的“人找貨”,而是在廣告營銷、媒體誘導、大數據精準推送下的“貨找人”。通過微博、抖音、快手、微信、QQ等新媒體平臺的宣傳推廣,商品的符號價值不斷被放大而實用價值被忽略,激發了人們的好奇心和購物欲,影響了人們消費的目的和意識。
線下面對面的貨幣交易方式使人們對自己的花費有重量、觸覺方面的感知,而當消費金融化之后,在消費方式便利化、消費內容多樣化、消費心理畸形化的共同影響下,貨幣對于農村青年來說只是一組抽象化的數字,但它換來的商品卻能帶給他們實實在在的快樂。消費金融化一方面放大了消費帶來的快樂,另一方面又麻痹了人們對于貨幣流失的感知,因此,沉浸其中的農村青年在消費過程中極易失去理性。
三、消費貧困的生成機制
(一)需求轉型與收入支出失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現了三次消費需求轉型,經歷了從“解決基本溫飽問題,滿足生存需求”到“追求非生活必需品”再到“青睞高質量服務,滿足心理需求”的變遷[21]。居民收入提升的同時,消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表明,在收入方面,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 189元,去除價格因素,比2019年實際增長2.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 834元,比2019年實際增長1.2%;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 131元,比2019年實際增長3.8%。在消費方面,全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 210元,去除價格因素,比2019年實際下降4.0%;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7 007元,比2019年實際下降6.0%;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3713元,比2019年實際下降0.1%[22]。根據這組數據,可以計算出:第一,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收入比為65.9%,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收入比為61.6%,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收入比為80.0%,說明農村居民消費占收入的比重遠遠高于城市居民;第二,全國居民人均收入消費增長幅度差值為6.1%,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消費增長幅度差值為7.2%,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消費增長幅度差值為3.9%,表明農村居民邊際消費能力不僅遠低于城鎮居民邊際消費能力,而且遠低于全國居民邊際消費能力。
綜合上述兩點可以看出,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比城鎮居民消費支出比重大,主要是由于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農村居民消費意識大大增強,但收入卻沒有顯著增加。
(二)參照群體的變化與生活方式的現代化
隨著打工經濟的興起,農村中老年人普遍經歷過從農民到工人的身份轉變,但對他們來說,城市只是掙錢謀生的地方,農村才是真正的歸屬地,所以農村中老年人表現出在城賺錢、回鄉消費的特點,他們的消費參照群體是本村的村民。而農村青年普遍從學校畢業就開始進城務工,到一定年齡后返鄉談婚論嫁,幾乎沒有農村生產的經歷,城市便利的生活方式、多樣的娛樂場所、便捷的交通以及眾多的就業機會讓他們對在城市定居與生活充滿渴望,只是逢年過節回村莊短住。在此背景下,農村青年養成了城市的消費觀,在消費時他們往往會向城市居民看齊,以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為參照標準。
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導致了農村青年消費行為的巨大變化。首先,結婚花費增加。由于農村青年普遍學歷較低且專業技能不強,他們獲得的收入不足以支撐其在城市中買房定居。在當前性別失衡的現實背景下,女性在婚姻市場上占有相對優勢,農村男青年為了順利結婚則需要滿足女青年的要求。同時,男女雙方均有在城市生活的愿望,女性青年提出進城買房的要求與男性青年的發展目標相契合,加上幫助子代結婚是父輩認為的人生責任,因此兩代人會盡最大努力在城市購買商品房、私家車等。其次,家庭消費的貨幣化程度提升。在村莊中生活,農民可以部分依靠種植莊稼和飼養家畜自給自足,而在城市中生活,農村青年生產生活的各項需求均需要通過市場消費來滿足。最后,身份標簽激化了消費攀比。城市不同于村莊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信息不對稱,對他人的認知首先是對其外在的判斷,因此個體有了自我包裝的空間。由于先賦性資本不足而處于弱勢地位的部分農村青年希望通過購買高檔商品等來包裝自己,建構名不符實的身份標簽,進而實現滿足自身虛榮心、獲取他人尊重的目的。
(三)收入方式轉變
根據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說與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說,個體的消費需求不僅取決于當前的收入,還會受到未來預期收入的影響。當未來預期收入較差時,個體會預防性地降低當前消費支出,而當未來預期收入較高時,個體消費顧慮較小,消費支出較大[23]。
從實地調查情況看,B村中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收入方式有著明顯的差別。中老年人的收入方式是兼業式的,其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基本各占一半。以B村為例,村民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種植甜瓜,至今從事農業種植的人口中有90%都在種植甜瓜。受代理銷售方式的影響,農民成了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獲得的收入較低。因此除去種植甜瓜的4~5個月,B村中老年人農閑時期還會外出務工,但是受制于文化水平、技能水平和時間不穩定等,他們從事的工作多為流動性較大的兼職工作。而青年人的收入幾乎全部來自務工收入,以“90后”“00后”為代表的農村青年不再像父輩一樣半工半耕,他們在城市中大多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可見,農村中老年人的收入穩定性較差,且缺乏保障,“半耕半工”導致的收入不確定性塑造了其“重儲蓄、輕消費”的消費觀念;而青年人的收入相對穩定,這使他們敢于透支未來的收入提前消費。
四、消費貧困對家庭的影響
(一)代際剝削
部分農村青年的非理性消費行為導致其經濟積累能力不足,無法進城買房以及在城市中維持體面的生活。在家庭責任倫理與村莊地方性規范的影響下,子代的經濟壓力傳導給了父代。首先,“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對廣大農村居民影響深遠,父代普遍認為若子代不能娶妻生子,家庭就無法順利完成繼替,自己的家庭任務就沒有完成。其次,父代對子代有著深厚的代際親情。兒女健康成長、成家立業、生活幸福對于父母來說是一種心靈慰藉。最后,地方性規范也在深刻影響父代的行為。“一切為了孩子”是B村村民的共識,這一共識細化為“父母要為兒子買房”和“父母要撫養孫輩”等具體行為。如果父母不能滿足這些角色期待就會受到地方輿論的壓力,被其他村民認為是“不合格的父母”。在這些因素的共同影響下,父代會主動延長勞作時間、抑制個體消費,將家庭經濟資源投向子代,保證子代家庭的正常運轉。即便是喪失了勞動能力,父代也要盡可能自養以減輕子代的經濟壓力,而子代消費能力與積累能力之間的不平衡使其給予父代的資源反饋十分有限,呈現出“父代低消費、子代高消費”的特點。父代對子代付出時間長且內容多,子代對父代的代際反饋微弱,父代生活質量和養老保障存在較大隱患。
(二)婚姻不穩定
農村青年個體本位的觀念和過度消費的行為導致家庭整合能力下降,婚姻的脆弱性上升。一方面,相比于農村中老年人長期持“家庭本位”的觀念,農村青年更多講求“個體本位”。在農村中老年人的觀念里,家庭重于個體,當個體的追求影響到家庭發展時,他們會抑制自我意愿以保全家庭;而農村青年更多關注自我享受與發展,婚姻家庭對其消費意愿的抑制作用降低,個體為了家庭發展犧牲自身利益的意愿大大下降。另一方面,由于過度消費,農村青年小家庭的經濟積累能力不足,但他們又想追求體面的生活,因此夫妻雙方因為經濟壓力發生的矛盾越來越多。與此相伴的是,農村青年的婚戀觀也發生了轉變:在農村青年看來,婚姻的締結更多是個人的事情而非家庭的事情,他們不認為穩定的婚姻是個人生存與發展的根本,更看重個體情感的體驗,如果個體情感在婚姻中得不到重視,就會選擇離婚。
(三)生育意愿降低
農村中老年人的生育觀可以概括為“多子多福”“養兒防老”,他們對孩子的數量和性別有所期待,覺得家庭不僅要有多個孩子而且至少要有一個男孩,這樣才能對得起祖輩,未來養老才能有保障,才能在村莊中得到他人的尊重。而農村青年的生育觀更具經濟理性,家庭少子化趨勢十分明顯。B村有已婚育齡婦女397人,零孩家庭12戶,占比3.0%;一孩家庭186戶,占比46.9%,其中獨男戶126戶,占一孩家庭總數的67.7%;有兩個孩子的家庭180戶,占比45.3%,其中雙女戶40戶,占兩孩家庭的22.2%;多孩家庭19戶,占比4.8%,有多孩的婦女年齡在45~49歲之間,無青年女性。從數據可以看出,1~2個孩子是農村青年家庭最為普遍的孩子數量,而從日常訪談中我們也發現絕大多數25歲及以下的已婚婦女偏好只生育一個孩子,30歲左右的婦女在一孩是兒子時不愿生育二孩,在一孩是女兒時才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幾乎沒有生育三孩的意愿。究其原因,與農村青年的非理性消費行為有關,非理性消費擠占了自身和家庭再生產資源,收支結構的失衡導致他們無力承擔養育孩子和孩子結婚的經濟壓力。在家庭經濟積累不足的情況下,減少生育孩子的數量可以提高家庭生活質量,所以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不愿意生育多孩。
(四)返貧風險增加
隨著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當前農村青年感知到的貧困,并非由于低收入而產生的生存方面的貧困,而是在消費金融化影響下,個體過度消費所造成的貧困。消費主義增長了這類群體的虛榮心,膨脹了消費欲望,他們希望通過消費彌補先賦性資本不足,找尋生活的樂趣。部分農村青年用未來的收入規劃當前的消費支出,消費需求與消費能力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一方面,現實落差使他們面臨著社會排斥、自我污名和自卑感,這容易造成其精神層面的信念消極、生活麻木、缺乏志向;另一方面,收支的不平衡使他們經濟積累能力下降,很可能無力應對突發事件和重大疾病,又無法為以后投資、擴大再生產。精神層面與經濟積累層面的弱勢提高了農村青年家庭返貧的風險。
五、結語
作為貧困的一種形態,消費貧困值得深入研究,同時也需要針對性的治理思路[24]。本文將消費貧困定義為“個體的非理性消費擠占了自身和家庭再生產資源,收支結構的失衡導致其發展能力不足的狀態”。在消費需求轉型、生活方式現代化以及收入方式轉變的背景下,缺乏城市生活能力卻依舊希望在城市生活的農村青年表現出個體本位、過度支出、消費金融化的消費特點。消費貧困也帶來了一系列消極的社會后果:第一,子代的經濟壓力通過責任倫理傳導給了父代,由此帶來了父代生活質量較低和養老保障的隱患;第二,家庭收支結構失衡造成農村青年夫妻的婚姻脆弱性上升;第三,對于日常生活質量的追求降低了農村青年的生育意愿;第四,非理性消費使農村青年精神層面和經濟積累層面弱勢累積,最終導致其家庭返貧風險增加。
因此,當前的幫扶工作應轉變思路,一方面要注意到城市也是社會幫扶的重要場域,應關注城市中進城務工農村青年的生活狀態;另一方面也要在精神扶貧上下功夫,警覺消費主義對農村青年思想觀念的沖擊,引導農村青年樹立健康適度的消費觀,將消費理念從享受型消費轉向發展型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