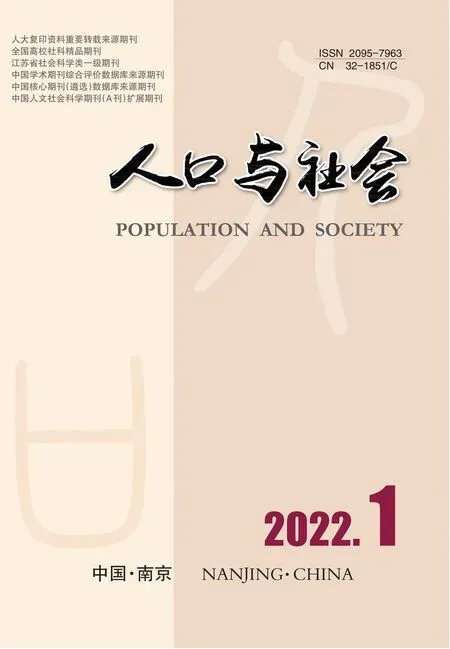關于數字鴻溝問題的若干思考
李 梅,陳友華
(南京大學 社會學院,江蘇 南京210023)
一、研究緣起
數字鴻溝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也是一種現代性危機。隨著人類進入到工業與后工業社會,越來越多的新技術、新發明噴涌而出,并持續不斷地應用于社會生產與生活的各個領域。與此同時,技術發展與社會變遷之間的問題也隨之產生。盡管互聯網和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為社會變革與社會進步帶來了諸多益處,但其引發的社會矛盾與不平等問題也愈發突顯,數字鴻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具有高度獨特性、本土性、社會性的問題。根據不同的社會發展狀況,數字鴻溝又轉化為具體的、相應的、特定的社會問題,并且與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和福祉緊密相關。在中國,加速數字鴻溝顯現的外部壓力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數字化社會的轉型。以信息通信技術(ICT)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影響,中國也不例外。在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實現了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互聯網普及率由2010年的34.3%增長至2021年的71.6%。(1)數據詳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網址為http:∥www.cnnic.cn/hlwfzyj/hlwzbg/hlwtjbg/202109/9020210915523670981527.pdf.截至2021年6月,中國網民數量增長至10.11億,占全球網民總數的五分之一左右,(2)數據來源于Internet World Stats,網址為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htm.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數字社會。
二是人口結構的老化。早年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國的人口結構轉型[1]。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逐步延長,老年人口比重快速增加。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2000年的71.4歲(3)2000年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網,網址為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逐步增長至2019年的77.3歲[2]。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也在快速上漲,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高達2.64億,占總人口的18.7%。盡管目前我國的生育政策在逐步放開,但人口結構老化和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中國已經面臨由勞動力過剩轉變為勞動力不足的嚴峻形勢[3]。
三是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的暴發。世界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使得數字鴻溝問題的嚴重性更為凸顯。我國有相當一部分社會群體被排斥在數字社會之外。無法熟練使用網絡通信工具、移動支付軟件、健康碼等引發的“數字鴻溝”“數字貧困”甚至“數字難民”等社會熱點問題不僅給個體帶來了一定的心理影響與社會脫離感,也引發新的社會分化與社會不平等,為社會整體的平穩發展埋下了一定的隱患。
上述幾方面原因的交相作用成為加劇數字鴻溝的重要推手。為了解決這一社會問題,2020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4)文件來源于國辦發〔2020〕45號,名稱為《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的通知》,網址為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24/content_5563804.htm.該方案中正式指出老年人面臨的數字鴻溝問題日益凸顯,并聚焦老年人出行、就醫、消費、文娛與社交等高頻事項提出了具體的指導意見。2021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再次發布《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產品和服務的通知》,(5)文件來源于工信部信管函〔2021〕18號,名稱為《工業和信息化部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產品和服務的通知》,網址為https:∥www.miit.gov.cn/jgsj/xgj/wjfb/art/2021/art_f34ef0284e164abbb3c6ef193aa20586.html.重點督促工業和信息部門開展互聯網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專項行動,圍繞老年人獲取信息的需求,優化界面交互、內容朗讀、操作提示、語音輔助等功能,切實改善老年用戶在使用互聯網服務時的體驗,提高其信息無障礙水平,助力老年人等特殊群體跨過“數字鴻溝”。
盡管政策層面就數字鴻溝問題給出了具體實踐方向的指導,但有關數字鴻溝的本質、數字鴻溝何以形成以及數字鴻溝的未來走向等問題尚未得到學界的充分研究。此外,已有研究大多圍繞老年數字鴻溝問題展開。不少學者都意識到了老年群體可能面臨數字鴻溝問題,但這些研究更多是一種對于老年數字鴻溝現象的描述,有關數字鴻溝問題本身及其可能引發的社會后果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在探討如何應對數字鴻溝之前,本研究更期望能夠回歸到數字鴻溝問題的本源性上,并就該領域內的相關問題進行討論與反思。
二、數字鴻溝:溯源與發展
(一)概念溯源
數字鴻溝是現代工業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面臨的一種社會問題,它與互聯網技術的興起和普及密不可分。
對于數字鴻溝這一概念最早的認識與爭論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有觀點認為美國《洛杉磯時報》的兩位記者Jonathan Webber和Amy Harmon最早公開使用數字鴻溝一詞,他們使用數字鴻溝這一概念來描述社會中那些熱衷于使用信息通信技術與不太使用該技術的人群之間的社會分化現象[4];也有學者認為,時任克林頓政府馬薩諸塞州眾議員的Ed Markey和《紐約時報》記者Gary Andrew Poole使用數字鴻溝來形容當時美國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相關報道更早[5];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聲音認為數字鴻溝最早由Markle基金會名譽總裁Lioyd Morrisett提出,他將數字鴻溝喻為一種在信息富人和信息窮人之間所存在的差距[6]。
但由于缺乏足夠的資料佐證,目前仍然不能確定“數字鴻溝”一詞真正出現的時間。盡管對數字鴻溝這一概念的溯源尚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數字鴻溝概念的出現與20世紀末互聯網的快速興起以及當時美國國家信息管理局發布的一系列報告相關[7-10]。自此,數字鴻溝這一概念開始被社會各界接受并得到了廣泛使用。
(二)概念演進
在互聯網普及的早期階段,學界對于數字鴻溝概念的認識和使用是寬泛、模糊的。它不僅被視作一個技術領域的關鍵話語(例如被用于區分對IT技術的擁護者與反對者,用于指代數字技術行業內部的不兼容性問題),還具有政治性與社會性的意涵(例如曾被用于指代美國義務教育過程中信息技術資源的不公平分配、高科技行業內部的種族歧視與就業機會的不公平等現象)。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國家信息管理局的相關報告發布,(6)美國國家信息管理局(NTIA)1999年發布的報告:Falling through the Net: 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 網址為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fttn99/contents.html.數字鴻溝這一概念才開始得到正式確認。“數字鴻溝”也被定義為:能夠獲得新技術的人與沒有獲得新技術的人之間的差距。這種二分法的認識通常體現在物理層面上的接入,如私人電腦的擁有狀況、寬帶網絡的連通等[11-12]。
然而,這種接入方式的差異隨著互聯網的快速普及正在逐漸縮小。當互聯網、寬帶和數字設備變得更加普遍時,基于“接入”的數字鴻溝概念已無法反映現實社會發展。盡管數字鴻溝概念起源于互聯網的接入技術,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關于數字鴻溝的研究應當超越物理接入的層面,有關個體的數字技能、數字技術的使用以及不同的使用狀況帶來的差距等內容逐漸成為后續研究的方向[7,11,13-14]。數字鴻溝這一概念也隨著研究取向的變化而不斷地得到外延。這一點通過經合組織(OECD)對數字鴻溝的定義就能體現出來:數字鴻溝是指處于不同社會經濟水平的個人、家庭、企業和地區之間在獲得信息通信技術的機會上,以及在互聯網的使用上所存在的差距。(7)OECD.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 http:∥www.oecd.org/dataoecd/38/57/1888451.pdf.這種差距通常被概括為個體的數字技能、數字素養等方面的差距,一般根據使用信息通信技術所需的技能類型和人們在線開展的活動類型進行區分[15]。
所以目前在學界,數字鴻溝這一概念已不單是指物理層面上的接入,個體對于數字技術的使用情況成為數字鴻溝這一概念新的研究內涵。也正是如此,數字技術的物理接入問題常常被稱之為第一道數字鴻溝(the First-level Digital Divide),用戶對于數字技能的掌握情況被稱為第二道數字鴻溝(the Second-level Digital Divide)[16-18]。
然而,隨著資本的全球化擴張、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普及,一系列數字不平等現象被催生。原有的數字鴻溝概念已經不再能解釋相關的社會現象,數字鴻溝這一問題也變得更具有挑戰性。因此,學界對數字鴻溝的認識也開始變得復雜,第三道數字鴻溝(the Third-level Digital Divide)的概念與相關理論開始得到學界的注意[19-20]。與前兩道數字鴻溝不同的是,第三道數字鴻溝面臨的問題是交叉與多元的,更加關注數字技術接入和使用后帶來的社會影響和社會后果。該理論觀點所持的假設:即便互聯網用戶都擁有高質量的網絡接入和熟練的互聯網操作技能,他們在獲取數字資源時也存在巨大的差異[21]。因此,除了以往的技術性因素以外,社會學相關的因素開始被納入到數字鴻溝領域的研究視野中。學者們開始對使用數字技術獲得的不同結果以及從數字化社會中獲得數字紅利的能力進行研究[22]。在這個層面上,數字鴻溝不僅表現為對計算機的物理連接和訪問的差異,而且表現為利用信息技術獲取資源的差異。關于這種數字資本的生產與獲取,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布爾迪厄的社會資本理論等都曾被用于進行相關探究[20,23-24]。至此,有關數字鴻溝這一概念的發展脈絡已逐步清晰。對于數字鴻溝問題不同層次的探究也構成今天國內學界對于數字鴻溝現象的基本認識。
三、關于數字鴻溝問題的若干思考
(一)數字鴻溝是一個技術問題嗎?
數字鴻溝這一問題的產生來源于新技術的發明與應用,但它同時也反映出一個核心的問題,即技術的發展如何落地,如何更好地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站在技術社會學的視角,數字鴻溝問題本質上是在技術與社會互動中出現的,因此,并不能單純地將其視為一個技術問題。
關于技術與社會的互動,過往研究中始終存在著兩種代表性的解釋框架:技術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這兩種不同的解釋框架形塑了現代社會對于技術及其造成的社會后果的認識與態度。前者認為技術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有機體。技術能夠驅動社會變革,對社會發展造成沖擊,可以決定和支配社會的發展狀況[25]。后者強調技術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關注社會性因素對于技術發展的影響,諸如政策、制度、文化等。有豐富的經驗研究證明技術進步與社會發展之間具有復雜關系[26],數字鴻溝問題的產生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國家與社會對技術發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一系列數字治理、智慧城市等相關政策的提出迫使我國加速進入了數字化社會,這就使得當前國內的技術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
因此,技術社會學意義下的數字鴻溝問題已不再停留在技術層次,諸多研究表明數字鴻溝已逐漸成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下的綜合性議題。
從社會層面來看,數字鴻溝更多體現為數字不平等問題。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物理接入差距,個體使用數字技術的差距以及從中受益的程度是數字不平等研究領域關注的重點內容。來自這一領域的學者認為,數字鴻溝在互聯網社會中不會因為互聯網、智能設備等信息通信技術的普及而逐漸消失,相反,可能會變得更加隱蔽并且持續存在[27]。已有研究表明,數字鴻溝放大了線下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原有的社會不平等問題[21,28-29]。這種不平等主要體現在經濟、政治、社會、教育等方面[22]。這一觀點認為“互聯網用戶之間的不平等”主要是由于人們在使用數字技術時獲益的程度不同[30]。研究表明不同社會階層的互聯網使用慣習也呈現出明顯不同的特征[31]。低社會階層的個體更傾向于與同齡人在社交網絡上進行橫向交流與關系活動,例如消遣、娛樂[32-33];高社會階層的個體更關注與社會化相關的縱向的、增強社會資本的活動,例如獲取信息、商業交易等[34]。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數字鴻溝是原有的社會不平等在互聯網場域中延續與固化的結果。馬太效應在數字鴻溝領域內日益凸顯。數字鴻溝的社會屬性也在不斷增強,個體如何通過使用信息通信技術來獲得更好的回報是數字鴻溝這一現象需要回應的現實問題。
(二)數字鴻溝與老年數字鴻溝的關系
數字鴻溝是一種所有年齡階段人口都可能面對的風險,不局限于某些特殊群體。盡管目前老年數字鴻溝問題比較突出,但需要意識到的是,這一問題并不專屬于老齡社會群體,在其內部也不存在絕對的弱勢群體與優勢群體。因此在面對數字鴻溝問題時,要謹防落入“年齡陷阱”,唯年齡是論,避免對老年群體的標簽化與刻板印象。
年齡這一變量的確對于解釋數字鴻溝這一現象起到了顯著的作用。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年齡對數字鴻溝現象的產生有著較強的預測作用[35]。相較于年長的人群來說,年輕人對于新技術的接受程度更高,使用程度更好。更重要的是:年輕人更可能知道自身的不足與學習的重要性,而年長者卻相反。因此,在有關數字鴻溝的研究中,老年人口所面臨的數字鴻溝問題更加突出,與此相關的研究也較為豐富。
然而,除了年齡變量以外,數字鴻溝也與其他人口學變量緊密相關。個體的性別、受教育程度、工作狀況、家庭收入、居住地等同樣是造成數字鴻溝現象的重要因素[19,27,36]。已有研究表明,性別差異對數字技術使用方面的影響在逐漸縮小,但男性相較于女性來說在互聯網的使用以及獲益過程中仍然更具有優勢[37-38]。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個體受數字鴻溝的影響是不同的,通常來說,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意味著個體面對數字鴻溝的可能性更低。然而,也有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在面對數字鴻溝的第二道溝和第三道溝時,教育程度對于數字技術使用的影響可能是不同的,低學歷的個體對數字技術也具有較好的使用能力,但更多是參與游戲娛樂、社交互動[21,37];而擁有較高學歷的個體使用數字技術更多是用于獲取信息、線上資源等[35]。就個體的工作狀況而言,未就業、退休人群相較于就業人群來說面臨數字鴻溝的風險更高[38]。家庭收入水平依然是造成數字鴻溝的一個關鍵因素,其不僅能夠影響個體對數字技術的物理接入,而且會延續到數字技術的使用層面[37]。居住地反映了所在地的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生活在偏遠鄉村的個體相較于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來說,遇到數字鴻溝的可能性更高,這與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高度相關[39]。
所以,通過前文梳理的數字鴻溝相關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發現,個體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社會經濟地位等都是造成數字鴻溝的重要原因,老年群體、女性群體、低學歷群體以及居住在城市化水平較低地區的群體都有可能成為數字困難群體。
(三)數字鴻溝會逐漸消解還是會持續存在?
如前文所述,數字鴻溝不僅是一個技術性問題,更是一個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社會性難題。
對于數字鴻溝未來走向的判斷取決于我們如何認識數字鴻溝的本質。技術派觀點的學者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更加樂觀,他們認為隨著技術的進步與更迭,數字鴻溝這一問題終將會得到解決;但更多的聲音認為數字鴻溝在未來會持續存在,并且根據社會發展狀況轉化為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18]。數字利維坦、技術利維坦、算法利維坦等概念的出現其實就反映了這種擔憂。這些有關技術與社會的關系、數字技術異化等相關問題的研究在不斷深化學界對于數字鴻溝問題的認識[40]。它不止是一種數字技術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能夠被簡單歸因于個體的選擇偏好差異或者其原有的社會經濟地位差距,其背后所映射的國家-社會關系的重構是值得學界思考與研究的。
因此,數字鴻溝這一現象在未來很可能會持續存在。當技術在不斷進步、社會在不斷發展的時候,技術與社會的互動就會持續發生,原有的數字鴻溝不斷地被消解與新數字鴻溝不斷地被建構,進而形成一種常態化的社會現象。誠如前文所溯及的發展脈絡一般,數字鴻溝這一現象在過去的幾十年間經歷了不斷地拓展、外延與更新。當前學界對數字鴻溝現象的解釋力度非常有限,它可能既不適用于過去,也未必適用于將來。因此,對數字鴻溝這一問題的認識也應隨著社會變遷的節奏而不斷深入與持續更新。
四、結論與討論
數字鴻溝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層面上的難題,更是一個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技術的發展始終無法規避當代中國面臨的艱難社會轉型,因此,數字鴻溝問題的產生是一種必然。盡管近年來有關數字鴻溝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逐漸豐富,但事實上有關數字鴻溝的本質、數字鴻溝何以形成、數字鴻溝的未來走向等問題尚未得到學界的充分探討。本研究嘗試對以上問題進行回應與分析,以期增進學界對于數字鴻溝這一問題的理解與認識,并提供一些值得反思的方向。數字鴻溝作為一種誕生于信息化社會中的現象,其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必然性。此外,對于數字鴻溝這一現象還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是對于數字困難群體的認識要避免割裂性的誤區。數字鴻溝不是一種絕對的差距,大多數數字技術使用者面臨的困境與不平等更多是一種相對的不平等[7]。在技術使用層面,有些人可以更快地采用新技術,而另一些人使用這些技術的程度較低。因此,我們對于數字鴻溝的認識要保持一種發展的眼光,避免對其進行簡單的二元劃分,既沒有處于絕對困難的弱勢群體,也沒有處于絕對優勢地位的群體。以往研究認為數字鴻溝兩端的群體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二是對于數字陷阱的警惕。諸多文獻在對于數字鴻溝問題的研究中都使用了“消解、彌合、跨越”等字眼,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已經落入數字陷阱中:試圖將數字技術視作一種必備的生活要素,并希望用數字技術來解決一切問題?是否已經陷入了技術對于社會的反噬過程中?在政府大力推動數字社會、智慧城市建設的同時,技術治理擴張的負效應卻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視和研究。
三是數字包容型社會的構建。無論是學界還是實務界在面對數字鴻溝這一問題時,要謹慎、規范、盡量避免使用“數字難民”“數字窮人”這樣一些帶有歧視性與污名性的術語。正視其存在的合理性,弱化其污名性。相較于“跨越數字鴻溝”,保持一種開放、包容和發展的態度,并努力構建一個數字包容型的社會才是解決數字鴻溝問題的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