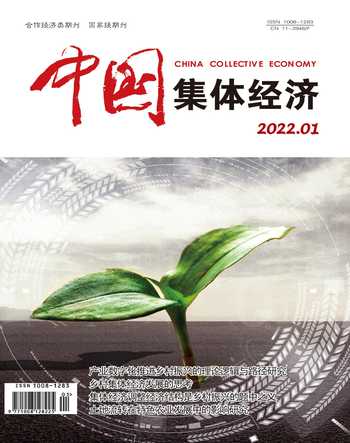共享經濟視閾下網約車平臺公司與司機用工關系的司法認定
徐鑫
摘要:勞動法的調整對象是勞動關系,而勞動關系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為了實現社會化勞動過程中形成的特定的社會關系。勞動法的產生與發展與工業化革命如影隨形,換言之,勞動法是對工業革命的立法回應,勞動關系的基本范圍會隨著社會經濟、科技創新的需要而不斷變化。就目前“智能革命”的發展趨勢而言,人類正在擺脫“從屬勞動”的傳統束縛,用工關系的內涵也將發生顛覆性的改變,與此同時也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關鍵詞:共享經濟;網約車;勞動關系;法律性質;司法認定
一、問題的提出
“智能革命”又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的“4.0革命”(Industrie4.0),指以智能制造為主導的人類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此新興的生產模式下,要求企業生產的核心必須建立在數字化和個性化的基礎之上,傳統的行業邊界正在日益模糊,各種全新的生產模式、生產活動及生產合作方式在不斷涌現,給傳統產業帶來了嚴峻的挑戰。隨著“智能化”社會的到來,傳統的用工關系已經不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勞動關系的“從屬性”關系似乎正在被弱化,靈活就業等多元化的就業方式已經孕育而生。例如,在互聯網技術的強烈沖擊下,為企業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特別是共享經濟模式下的網約車行業更是顯示出其獨特的魅力,不僅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也給從業者帶來了更多靈活就業的“面包”,也就意味著很多勞動者可以擁有更多額外的勞動收入,從而為社會創造了更多的財富。在人們為網約車行業進行肯定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困惑和現實問題。網約車平臺公司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向社會招聘的門檻較低,用工前的審查不嚴,應聘者可以同時在多個平臺注冊并接受指派,從業風險難以估算。由于互聯網平臺用工形式和時間安排比較靈活,甚至沒有任何約束,因此與傳統行業的用工形式存在很大的差異,加大了網約車司機與平臺公司用工關系認定的難度。
人民法院對網約車司機與平臺公司之間用工關系的認定同樣存在較大的分歧,全國各地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判斷標準,主要集中在“依附性”審查標準和“從屬性”審查標準兩個主要的裁判要點之上。由于網約車司機數量的不斷增大,網約車司機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不斷增強,加之司法審判實踐中構建相關審查標準和體系的滯后性,已經嚴重影響了網約車平臺的健康發展。行政職能部門,抑或司法實務部門應當對網約車行業進行調查研究,傾聽網約車司機的聲音,獲取第一手真實的資料,構建一種與時俱進的“傳統勞動關系”與“新型勞動關系”相結合的互聯網用工關系。詮釋一種“類勞動者”的概念,對網約車司機量身定做一種契合行業發展現狀和特點的“類勞動者”身份,以促進網約車平臺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有必要對認定網約車司機與平臺公司之間的用工關系的法律性質展開研究。
二、我國勞動用工關系法律制度的變遷與愿景
任何法律制度的變革和相關理論創新,必須基于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就法律歷史的演進而言,勞動法是從民法中分離出來的一個新部門法,二者之間有著天然的關系,但相互獨立、各成體系。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勞工關系法律制度大致經歷三個階段:一是計劃經濟時代。由于是計劃經濟,并沒有形成真正的勞動力市場,因此主要是以國家意志力為主導的用工法律制度來進行調整,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二是1995年《勞動法》頒布實施階段。主要形成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用人單位與國有企業職工為勞動者的單一性勞動關系。隨后,《勞動法》于2009年、2018年經歷了兩次修訂,至此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用工制度基本形成。三是“智能時代”的到來。“互聯網+”、技術革新、數字化等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智能社會”使得靈活就業成為常態化,某些高端的行業人群(教師、律師、法官、醫生等)也或將受到影響,其中也包括共享經濟模式下的網約車司機,勞動者的身份逐步變得多元化,勞動地點和勞動時間變得更加靈活,大量的勞動者已經實現了“在家辦公”、“線上辦公”、“平臺辦公”、“微信辦公”等相對不固定的模式,以從屬性為基石而產生發展的勞動法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以網約車為代表的新興行業打破了傳統單一化的用工方式,司機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上班時間和行駛路線,甚至駕駛的車輛也可以由司機自行提供。
相比之下,我國實務部門(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向來以勞動者人格從屬性為主的判斷標準已經不適應當前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2016年11月《網絡預約出租車經營服務管理辦法》正式實施,雖然專門對網約車司機和平臺公司之間的勞動關系認定進行了規定,即“勞動合同或者協議以多種形式簽訂”,但并沒有明確二者之間用工關系的法律性質。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針對當前形勢確立的非標準化勞動關系類型較少,也無法滿足互聯網模式下靈活就業等新型勞動用工方式的需求,受制于傳統工業革命背景下的“從屬性”審查標準,必將使得網約車行業用工關系的法律性質難以認定,網約車司機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進而言之,我國勞動法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必將涉及到如何處理勞動者穩定性和靈活性、勞動法的放松管制與再管制的問題以及是否承認以網約車司機為代表的主體的勞動者身份等。
三、我國網約車用工勞動關系認定與重構
(一)雇傭關系與勞動關系
所謂雇傭是指受雇方以契約為基礎,為雇傭方提供不定時的勞務,并獲得一定報酬的行為。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是指以勞動合同為基礎之報酬行為。簡而言之,雇傭關系具有單純的私法性質,強調意思自治和平等協商;而勞動關系身兼公法和私法性質,既強調平等屬性,又強調從屬屬性。因此,勞動關系必須考慮勞動紀律、固定的上下班時間、工資關系等識別因素。在現代經營方式下的網絡時代,傳統的識別要素已經很難準確定位是否屬于勞動關系,越來越多的工作并不需要在單位和辦公室完成,也不需要在固定的時間進行,傳統的“從屬性”標準,已經失去了一部分的價值。司法機關有必要防止用人單位濫用“雇傭關系”以規避依法應當承擔的法律風險責任。因此,以營利為目的的用人單位,只要有償使用了勞動力從事市場經營活動,從業者在勞動過程中所遭遇的勞動風險就必須由受益人(用人單位)承擔。可見,盡管網約車司機與平臺公司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甚至難以判定,但絲毫也不影響平臺公司作為受益人的客觀事實,其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二)網約車平臺與司機之間用工關系法律性質的認定
共享經濟帶來的新的市場并不只有一個密不透風的維度,現行勞動關系判斷標準也不是完全過時或者完全不適應,我們必須在現有法律基礎上引入新的判斷因素。《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的用工形式為全日制用工(每天工作8小時)和非全日制用工(每天平均工作不超過4小時),網約車司機也可以分為全日制網約車司機和非全日制網約車司機。全日制網約車司機與平臺公司直接建立用工關系,一般爭議不大,勞動關系認定不復雜。實際上,全日制網約車司機還可以分為以下三類:一是獨享模式,即網約車平臺要求網約車司機只能和其建立用工關系,禁止建立多重用工關系,且與網約車司機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網約車司機全面接受平臺公司的管理,嚴格遵守其勞動規章制度。二是包容模式,即平臺公司原則上要求網約車司機只能接入自己的平臺,但并不與其簽訂勞動合同,二者之間的關系并非《勞動合同法》意義上的勞動關系。這種用工方式,平臺公司為司機提供訂單,由司機自由進行選擇,平臺公司從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費用。二者關系較為復雜,需要具體分析進行認定。三是兼容模式,即平臺公司允許網約車司機與多家公司建立用工關系,且并不是與公司直接建立用工關系,而是與第三方租賃公司建立合同關系。這種用工方式更為復雜,雙方之間的關系很難界定為勞動關系。而非全日制網約車司機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即有主業工作,同時又與網約車平臺建立用工關系(非正式關系,不簽訂勞動合同),這樣的用工方式一般爭議較大,需要綜合判斷,具體而言。
(三)我國網約車用工關系認定標準的重構
靈活就業的發展,不僅使原來的“標準勞動關系”發生了變形,而且使多重勞動關系有了建立的基礎。“多重勞動關系”的發展,打破了“一人一職”的傳統觀念,讓更多的從業者享受到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同時也為社會創造了更大的價值,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型經濟形態、新的從業模式形態發展日漸興盛。為了有效保障新生事物的發展,頂層設計者始終保持一種包容審慎的態度,積極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 《電子商務法》),具體明確了“平臺公司”和“個人”的身份分別為“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和“平臺內經營者”,并將二者統稱為“電子商務經營者”。按照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承擔以下法定義務:“登記、核驗、建立檔案、報送登記信息、報送稅務信息、提供原始合同、提供交易記錄、承擔行政責任等”。
1. 設立網約車勞動關系認定新標準
網約車司機與平臺公司之間用工關系的法律性質認定應當采取“要素式”方法進行,綜合考量從業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依附程度、勞動紀律、勞動時間、勞動地點、勞動報酬、接單自由程度等因素,不能拘泥于二者之間的協議。法官應當基于多種要素進行識別,對二者之間的“依附性”程度進行主客觀一致性的考察,而不單單不囿于“從屬性”的范圍,讓認定更加符合事實。
2. 確立網約車用工模式中的“類勞動者”概念
互聯網用工模式給政策制定者找到了一種方式,讓從事零工的工作者能夠更公平地分享共享經濟模式所創造的利益,同時又不損害商業模式本身。傳統的用工模式并不是密不透風的維度,可以探索注入新的元素,引入“類勞動者”概念。在“強資本弱勞工”的現實條件下,可以嘗試對共享經濟視閾下以網約車司機為代表的靈活性較大的從業者,依法給予一定傾斜性的保護待遇。
3. 網約車用工各方權利保障的構建
在未來,隨著互聯網用工新業態的不斷發展和我國勞動者彈性就業需求的不斷增長, “非全日制用工”、“不定時用工”、“雙重勞動關系”“非標準勞動關系”等概念以及法律制度都將走上勞動法變革的完善之道。在“需求即權利”理念指引下,對于非全日制網約車司機,可以傾向性的進行規范和保護,根據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創新社會保險繳費模式,讓靈活就業人員真正享受切實有效的社會保障,從技術層面上實現網約車兼職司機的社會保險賬戶可以分別獲得不同單位的繳費。這一舉措不僅能促進就業,促進和諧的勞資關系,還能避免由于交通事故造成賠償無力承擔的局面發生。更為重要的是,各級勞動行政部門應當加強對網絡平臺公司的監管,檢查勞動法的實施情況,加大簽訂書面勞動合同重要性的宣傳力度,以書面的勞動合同來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四、結語
綜上,與傳統的工業時代相比較,互聯網社會、“智能”時代的產生和發展孕育出了更多的新興行業和就業模式,并呈現個性化和主體化的發展趨勢。在當前的形勢下,勞動法的固有天然屬性與靈活就業屬性格格不入,難以磨合。相形之下,司法實務部門同樣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對“互聯網+”新型靈活就業形態的屬性判斷尚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導致此類勞工爭議案件的判決結果不盡相同。因此,對于共享經濟視閾下的網約車行業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如何認定網約車司機與平臺公司之間用工關系的法律性質的方法和標準顯得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1]謝增毅.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關系認定[J].中外法學,2018,30(06):1546-1569.
[2]李夢琴,譚建偉,吳雄.共享經濟模式下的共享型用工關系研究進展與啟示[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8,35(08):105-115.
[3]柴偉偉.“互聯網專車”勞動用工問題的法律規范——以P2P模式為中心[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5(02):57-64.
[4]錢玉文,張金華.論網約車平臺公司與司機之間用工關系的司法認定[J].常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1(02):31-42.
*本文為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共享經濟模式下互聯網專車服務行政法規制研究”(項目編號:2019J0352)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昆明理工大學津橋學院法學院)
3629501186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