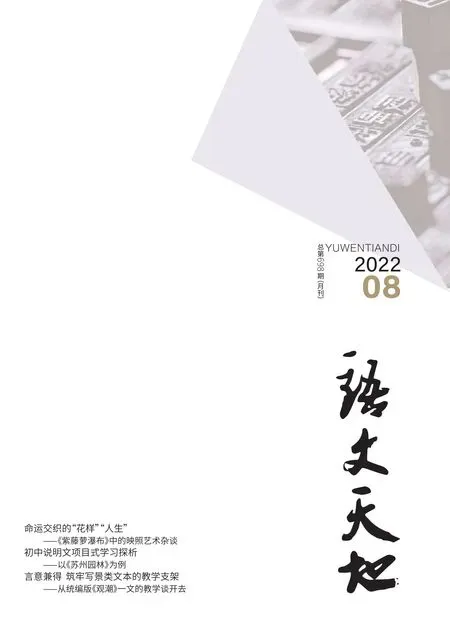一曲悲歌一段情
——細談《琵琶行》中線索的運用
董立平
作為一首敘事詩,《琵琶行》以“我”的視角生動描述了琵琶女的人生境遇。正如現實主義詩歌對底層社會的關注,白居易通過多元化的表現手法揭露了統治者的冷酷,并以“小人物”的悲歡,從“他者”關照“自我”,進而表達自己內心的憤懣之情。其中,多元化的對比“線索”增添了該詩的藝術表現張力。基于此角度的文本分析,對讀者了解現實主義風格敘事詩或許是不錯的新路徑。關于《琵琶行》的敘事解讀,對人物形象、思想主旨、意象意境和藝術特色分析不可或缺。正如現實主義詩歌對底層社會民眾的關切,白居易通過多元化的表現手法深刻揭露了當時統治者的嚴酷和腐化,在“緣事而發”的倡導中見證了唐中期社會的動蕩不安。但是,從詩歌內容的邏輯生成角度對《琵琶行》“線索”應用的挖掘,即文本主旨、藝術特色等是如何呈現的,似乎是更接近作者創作意圖和內心情感的解讀方向,如“他者”與“自我”命運的形象對比、多元敘事脈絡的對比、演奏曲目與命運的交織等。圍繞這些線索對比,可以從更深和更廣的維度剖析作者的敘述特色,感悟敘事詩的藝術魅力。
一、線索及《琵琶行》中的“線索”
所謂線索,指的就是事情發展的頭緒或來龍去脈,多見于敘事性文章或散文之中。在不同的文體中,線索的類型不同,有的以情感為線索,有的以時間為線索,還有的以事情的發展為線索,等等。線索一般會貫穿全文,讓文章結構更加完整和嚴謹,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文章大意和主題思想。線索有明線和暗線之分,如果一篇文章中既有明線,又有暗線,雙線交織使用,相輔相成,可以增添文章內容的豐富性,讓故事情節更加曲折生動,充滿藝術張力。《琵琶行》作為唐代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最具代表性的敘事詩,給我們講述了一個完整而又感人的故事內容,詩歌中通過作者的所見所聞,講述了京城琵琶女的悲慘遭遇,結合自己的經歷,表達了強烈的移情與共鳴,讓讀者產生聞者垂淚的效果,具有很強的藝術張力和文學魅力。該詩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除了故事感人,還有詩歌語言獨特、情感豐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其“線索”的應用。結合詩歌開頭的并序內容,作者使用了明線和暗線相互交織的藝術技巧,兩線相輔相成,共同完成組織詩歌內容與結構的使命。
二、從縱橫對比線索中體會情感共鳴
作為“歌行體”敘事詩,《琵琶行》也摻雜著濃郁的抒情色彩。其中,“他者”與“自我”,即琵琶女與作者的情感共鳴是解讀的關鍵。既然“同是天涯淪落人”,那么對人物形象的把握就是理解情感共鳴的前提。圍繞“他”與“我”,《琵琶行》塑造了琵琶女和詩人兩種人物形象,且靈活運用了多元對比手法。其中,縱向和橫向對比是較為明顯的兩組線索。前者是過去與當下的對比,既包括琵琶女的今昔對比,也有詩人對現狀有感而發的今昔對比;后者是琵琶女與作者人生命運的對比。在橫縱線索的貫穿中,作者以“對比”強化了思想主旨和作者情感。
首先,在縱向對比上,作者在小序中即對被貶之事進行正面描寫,包括被貶時間、地點、生活狀態等命運軌跡的描述。正如文中所言,“嘔啞嘲哳難為聽”“杜鵑啼血猿哀鳴”,寥寥數筆,便將其“心有不甘”的謫居狀態充分展現出來。之所以“心有不甘”,是因為作者自進入仕途之后,便心懷濟世之志,恰逢君王賞識,政治上一片至誠與熱忱,由此便有了改革時弊的政治主張,繼而因觸及權貴利益被誹謗、排擠,最終被貶謫為江州司馬。正是這種凄慘的人生際遇,才導致了作者的悵惘與煩悶,也才有了詩歌第一部分中的“醉不成歡慘將別”。較之京城的繁華與摯友,潯陽的落寞與伶仃給抱有鴻鵠之志的詩人帶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誠然,倘若依小序中所言,“是夕始覺有謫遷意”,詩人并無如此情感落差。但是,自謫居以來,白居易的憤懣和失落之情顯而易見。例如,在《東南行》中,其述“失腳到泥涂”,在《江南謫居十韻》中,其述“俄成失水鱗”,無一例外都體現了這種情感落差。正是這種今昔對比的落差感,才賦予詩歌思想主旨更具穿透性的藝術張力。這是單一的直述形式無法實現的,也是對比線索下情感邏輯的生成。此外,對琵琶女今昔對比的敘述也較為詳細。在小序和正文中,詩人細膩展現了琵琶女青蔥時的風華容貌和歌舞生活,如“名屬教坊第一部”和“妝成每被秋娘妒”。但是,隨著容顏消逝,琵琶女在與商人的“不幸”婚姻中夜夜獨守空船,只能與江水和清月為伴,今昔對比同樣強烈,也更凸顯了琵琶女的凄慘境況。
其次,在橫向對比上,《琵琶行》將琵琶女與詩人自身的人生軌跡并置。前者在年輕時風華絕代,名震京城。然而,以容色事人,終究難以長久維持,隨著容色漸衰,只能“漂淪于江湖”,過著孤獨凄涼的生活。當然,琵琶女的人生境遇并非偶然,而是封建制度下藝伎群體命運的濃縮。作為朝中官員,白居易與琵琶女的懸殊地位顯而易見,卻在看似毫無交集的情況下為知音創作此詩。這是因為,在白居易看來,自己仕途命運的由盛及衰與琵琶女的身世有著相似之處。詩人在入仕后一路擢升,“春風得意馬蹄疾”,卻因小人誣陷被貶謫。當琵琶女演奏完畢,自敘悲慘身世后,詩人便與她產生了情感共鳴,即以詩抒發了自己的滿腔憤懣。“同是天涯淪落人”,琵琶女的悲慘身世與作者的謫居之苦兩相暗合,從而凸顯了“天涯淪落”的怨恨。因此,作為詩歌內容和人物情感的載體,對人物形象的分析固然不可或缺,但要通過縱向和橫向對比強化這種藝術表現張力。
三、從描寫對比線索中把握詩歌脈絡
“行”是一種古詩體裁,正如胡震亨在《唐音癸簽·體凡》中所述,“衍其事而歌之曰行”。因此,“行”兼具抒情和敘事兩種特性。但是,反觀學術界和教育界對《琵琶行》的諸多研究,對抒情性的關注要遠高于敘事性。對敘事性的弱化,導致了教學層面對文本內容的碎片化處理,對人物塑造、音樂描寫、景物描寫和情節結構的粗略化探究。因此,對比故事情節的把握,對景物描寫和音樂描寫的解讀也是理清本詩敘事脈絡的途徑。
首先,在故事情節方面。《琵琶行》的情節是從詩人送客到聽琵琶,再到琵琶女自述身世,最后詩人獨白。需要強調的是,詩人在情節描述上,體現了明顯的詳略得當特征。在整體敘述方面,略寫詩人自身部分,詳寫琵琶女部分。如對“潯陽江頭送客”略寫,對“與琵琶女相遇之事”詳寫。在具體細節方面,關于琵琶女的自敘,作者詳寫其昔日之風華,而略寫當下之落寞;關于詩人的自白,則詳寫當下之憤懣,而略寫昔日之榮華。這種詳略有序的處理,使得情節互補,映襯得當,意在突出、深化主題。
其次,在景物描寫方面。《琵琶行》的故事背景是潯陽江頭的秋日凄冷和清寂,如冷色調的“荻花”和“秋月”。其中,詩人對意象“江”“月”描寫共有三次,如“別時茫茫江浸月”下作者的送客景象,“唯見江心秋月白”下琵琶女曲終的景象,“繞船月明江水寒”下琵琶女自述生平的景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意象的描寫不僅是“寓情于景”,同時也推進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如“別時茫茫江浸月”在作者的離別愁緒下引出了下文的琵琶聲;“唯見江心秋月白”則以靜謐感映襯琵琶女技藝的動態感,折射出技藝的感染力;“繞船月明江水寒”則是將琵琶女的孤寂與“江月”的冷清并置,共同刻畫了人物的內心世界。
再次,在音樂描寫方面。在演奏技巧上,作者從“忽聞琵琶聲”到“轉軸撥弦”,再到“四弦一聲”,最后是“卻坐促弦”,人物情感隨著音樂節奏的變化而變化。在演奏曲目上,琵琶女首先自行演奏了《霓裳》和《六幺》,隨后再應詩人之邀續彈一曲。從這個角度講,音樂是詩人與琵琶女交流的橋梁和紐帶,而正因這些琵琶曲,詩人才在強烈的情感共鳴中導致“青衫濕”。因此,對音樂描寫的分析也能窺見詩歌的敘事脈絡。
誠然,敘事性與抒情性是相輔相成的。詩人的“敘”恰是對兩者“同是天涯淪落人”感嘆的具體呈現。如“夢啼妝淚紅闌干”是琵琶女自敘其身世后伶仃和孤苦的體現,而詩人的“重唧唧”體現了兩者“淪落人”的共同處境。詩歌結尾句“江州司馬青衫濕”,則是詩人最終情緒的傾瀉。因此,無論從故事情節,還是景物描寫和音樂描寫,都是挖掘敘事內涵和文本解讀的路徑。
四、以文本比較線索鑒賞音樂描寫
縱觀詩中人物情感,琵琶女和作者的“心事”均通過音樂形式呈現。因此,鑒賞詩中音樂描寫的藝術價值也是文本解讀的一環。對此,文本對比是一種常用的方法。以元稹的《琵琶歌》為比較文本較為妥帖,這主要源于兩者高度的相似性。首先,作者的經歷和創作背景相似,均作于詩人謫居之時,元稹和白居易私交甚厚,且因詩歌主張并稱“元白”;其次,人物形象塑造相似,琵琶女的悲劇性和詩人的憤懣之情“不謀而合”;再次,藝術表現手法相似,尤其是對琵琶曲的描寫,圍繞正面描述和側面映襯呈現了詩人與琵琶女的今昔對比。但從藝術表現角度,兩者的表現張力則相差較遠,現就兩者的差異做具體分析。
首先,在畫面營造方面,較之《琵琶歌》,《琵琶行》聲畫合一,畫面感強烈,如“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視覺元素豐富,聽覺落差明顯。對比起來,《琵琶歌》中的“冰泉嗚咽流鶯澀”,畫面感則相對較弱,難以充分調動讀者想象形成體驗感。
其次,在用詞方面,疊詞的靈活運用是《琵琶行》的語言特色,如“嘈嘈”“切切”,生動描繪了大弦和小弦的音色區別,充分賦予詩歌音樂美和節奏感。對比而言,《琵琶歌》疊詞“珊珊”則顯得相對刻板。在動詞運用上,白居易對琵琶女的動作描寫細膩而真實。如“猶抱”和“半遮面”,將琵琶女的矜持形象刻畫出來,而在隨后的演奏中,更以“轉”“撥”“信手”“攏”“捻”“挑”“彈”“畫”等一系列動作的連用展現其高超的技藝。而《琵琶歌》“彈”“弄”是主要動作,給人的感覺相對單調。
作為白居易的經典敘事詩,《琵琶行》不僅是其“文章合為時而著”的理論表達,也是我國傳統古詩詞文化的藝術瑰寶,文學價值和藝術價值都值得挖掘和探究。尤其是其多元化的對比“線索”,不僅增添了該詩的表現張力,更給讀者提供了一種新的解讀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