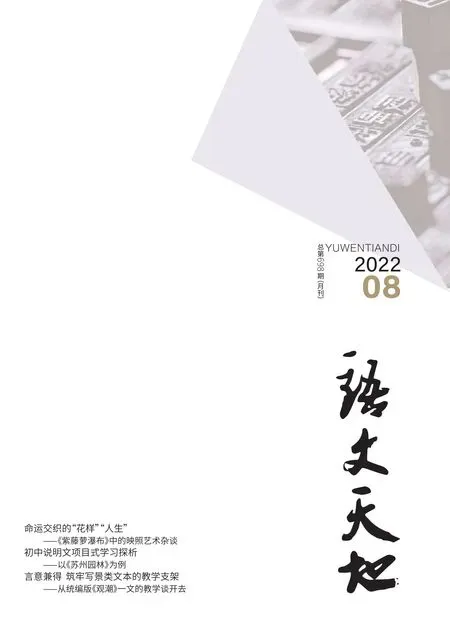小小茶館,人生百態
——談老舍《茶館》的敘事空間構建
王亞絨
老舍是我國近現代文學史上閃耀的明星,也是曾經距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中國作家之一,足見其文學地位。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老舍卻一直生活悲苦,嘗盡了人間冷暖,獨特的人生遭遇激發了他的文學創作激情和靈感,創作出一批優秀的文學作品。老舍的文學創作語言個性鮮明,人物形象眾多,情節結構獨特,并且善于把握矛盾和沖突,從心理和細節洞察人性,具有深厚的人文性和文化意蘊。老舍一生勤奮,創作了大量的文藝作品,小說、散文、話劇等類型眾多,其中話劇《茶館》在其文學創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力。作品以老北京為背景,透過“茶館”這個獨特的空間完成敘事,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文學價值。本文聚焦“茶館”特殊的敘事空間,結合空間理論,從生存空間、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三個層次對老舍的空間構建藝術進行全面探究,挖掘作品背后更為深厚多元的文化意蘊,助力優秀文藝作品的當代傳承與發展。
一、“茶館”的生存空間構建
老舍在話劇《茶館》中給我們構建了一個多維立體的敘事“空間”,在這個狹小的“空間”中為眾人搭建了一個敘事的“場域”,完成情節的推動和人物的塑造以及主題的升華。空間最開始是一個物理性定義,是我們生存和居住的基礎,但隨著文化的演進,空間具有了多重內涵,正如勒魯瓦·古朗指出的一樣,自從有了原始人,空間不再是“實用的操作對象”,已經具備了符號化與表象功能,于是作為文學意義上的“空間”就具備了“空間性”。
老舍先生從小在老北京的環境中長大,對北京的文化和生存空間有著特殊的情感和獨特的感受,他將對生存的“空間”思考應用到自己的文學創作之中,構建起一個獨特的“敘事空間”。茶館首先是一個物理層面的“空間”,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物理體,在位置、空間結構和功能分區上體現出一定的特點。茶館是喝茶的地方,既具有空間的開放性,同時也需要有私密性,并且茶館是以商業盈利為目的的,不論是選址、構造還是布局都有特殊的要求,構成其獨特的生存空間。
老舍對生活有著極度的熱愛,善于發現生活的獨特,因此心思細膩,將現實中的茶館“搬”到自己的文學創作之中。他在《茶館》中對“裕泰茶館”的地理位置、空間布局及功能分區進行了真實的還原,并利用“門”對空間進行了隔絕,區分茶館與外部城市,營造出真實性和立體感,從外部環境為茶館勾勒出一個生存輪廓。做好外部規劃以后,老舍對“茶館”的內部空間進行了劃分,利用空間的劃分將茶館內各茶客的生存狀態展現出來。他巧妙地把內部劃分為上、下、前、后,并且對其進行了細節刻畫,甚至對于家具的樣貌與擺設也進行了真實的還原:“屋子非常高大,擺著長桌與方桌,長凳與小凳,都是茶座兒。隔窗可見后院,高搭著涼棚,棚下也有茶座兒……”如此布局,增添了茶館的空間透視感和立體感,給人更加真實的感覺,不同的茶客坐在不同的位置之上,生存樣貌一覽無余。
總之,老舍將生活中茶館的原貌進行修復和還原,對茶館空間的營造勾勒出茶館的基本樣貌,讓茶館的空間立體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為后文劇情的發展打下了環境和氛圍基礎。
二、“茶館”的社會空間構建
“茶館”中的“空間”是地理與社會層面上的人的生存空間。根據列斐爾的理論可知,空間是人、文化、各類社會關系的集合地,它們均在空間里面得以具備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在《茶館》中除了生存空間以外(日常喝茶消遣),還有著重要的社會空間性,這里是社會大舞臺的縮影,也是社會變化和歷史發展的重要見證。這里的空間不僅滿足了人們日常喝茶消遣的生活需求,還為眾人提供了信息傳播與交流的平臺,成為一個公共空間。茶館與人的生活、生產以及社會和歷史產生了內在的勾連。
首先,茶館是人們生活的公共場所,是一個開放性的公共“空間”。老北京的茶館文化濃厚,茶館的功能齊全,不僅可以喝茶,還可以居住,類似于旅館的樣貌,這里不僅是人們茶余飯后消遣娛樂的地方,還是交流信息和情感的重要場合,具有多功能性。老舍對這些功能雖然沒有濃墨重彩地展現,但是也透過字里行間讓讀者了解到了這些內容。在這個空間我們可以看到人們的生活樣態:“玩鳥的人到這里歇歇腳,喝喝茶……商議事情的,說媒拉纖……有事沒事都可以來。”因此,作為公開場域,茶館最基本的社會功能就是休息,還有專門的廚房和小吃,具備公共休閑空間的所有元素。
其次,茶館的社會空間性還體現在信息的交流上。茶館一般開在人流量較大的地方,各色人等都可以來吃茶說話、交流信息。在這里可以看到最新最火的新聞,聽到荒唐的事情,就像《茶館》中所說的一樣,“簡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這里還體現出茶館的共生特性,在《茶館》中很多人依茶館而生,他們與茶館形成一種共生關系,比如算命的唐先生、拉皮條的劉麻子、兜售貨物的老楊等,形成了穩定的業態環境。
最后,茶館的空間社會屬性還體現在茶館是時代和歷史的縮影。根據話劇中的內容可知,茶館經歷了前后幾十年的跨度,并且經歷了清朝末期、軍閥混戰以及抗戰等幾個特殊的時期,每個時期茶館的裝飾和空間布局都產生了鮮明的變化,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社會生活元素。
三、“茶館”的文化空間構建
茶館作為一個公共場所和開放式的空間,對人們的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尤其是老北京,形成一種獨特的滿清茶文化,脫離了原來的空間屬性,被賦予了更多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內容,成為歷史的見證和社會制度變遷的縮影。老舍利用茶館這個獨特的空間,通過茶館的興亡轉變隱喻社會和歷史,讓茶館有了更多的文化意蘊。
茶館作為社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裕泰茶館”的變遷就是中國二十世紀以來社會的變遷,反映出社會的更迭中制度與人關系的核心問題。不論是“改良”還是“改朝換代”,人們都期望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現實總是事與愿違,因為制度的改變屬于權力階層,不屬于普通勞動人民。在《茶館》中經歷了三次重要的“變革”和制度的轉變,國家和社會以“變革”為由繼續盤剝民眾,他們的利益被忽視甚至被隨意的踐踏,加重了民眾與國家之間的矛盾。在這個過程中,個人和公共空間的關系也相應地發生變化,從而反映出民眾和公共場所錯綜復雜的關系。作品中民眾一直處于權利的缺失之中,常四爺因為一句話遭遇牢獄之災,老板王利發最后自殺身亡,都映射出社會和歷史的荒謬。
在“茶館”這個小的生存空間和秩序背后,是各種政治力量的較量,墻上的“莫談國事”的裝飾顯示出濃厚的政治性,在這個自由的場域中,民眾的言論自由一再受到壓制,處于極其被動的地位。所謂的“改良”也在政治斗爭中不斷地妥協,民眾空間被不斷地擠占,隱喻著政治的蠻橫,最終是制度的消亡和民眾的背離,舊的社會秩序和文化體系崩塌,新的社會和文化空間到來,這就是“茶館”背后更為深厚的政治文化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