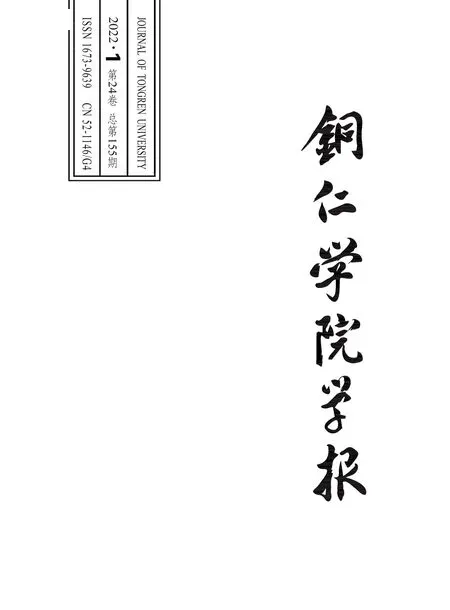試論阿爾都塞的政治形象
羅玉竹
( 清華大學 建筑學院,北京 100084 )
路易·阿爾都塞(1918-1990年),出生于阿爾及爾近郊的比曼德利(又譯稱“比爾芒德”)小鎮,其父是一個銀行的經理。阿爾都塞從小信奉天主教,參加過天主教青年運動。因為家庭殷實,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在阿爾及爾上小學,后又就讀于法國馬賽中學,考入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文學院,師從著名學者巴什拉教授。1948年,他以《黑格爾哲學中的內容的觀念》為題獲得博士學位,隨后留校任教。1980年11月16日,他因精神病發作而誤殺妻子被送進精神病院,出院之后體弱多病無法工作,直至1990年去世。他著作頗豐,代表作有《孟德鳩斯:政治與歷史》《保衛馬克思》《讀〈資本論〉》《列寧與哲學》《自我批評文集》等。
關于阿爾都塞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學術界論說不一,莫衷一是。一說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家;一說他是“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說他不僅是一個結構主義者,而且是一個兼容了多家學說的唯科學主義者;一說他是“極端仇視、蓄意歪曲馬克思主義,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馬克思主義者”;一說他是扮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守夜人”的角色。然而稱“他是一名法共黨內深受結構主義思想影響,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思想家”[1]是比較切中要害的。通觀其代表性著作,其中《保衛馬克思》一書最能體現其政治上的鮮明立場。從書中所反映的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來看,可以肯定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是一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捍衛者和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即“保衛真正的馬克思主義”[2],同時也是一個能夠熟練運用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并能深入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思想家,即“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理論的形態及形象”[2],而非一個純粹的結構主義學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然而需要指出和強調的是,阿爾都塞所要保衛的馬克思主義,乃是科學學術研究語境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流派,即研究論域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理論性問題;換言之,阿爾都塞視界中的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門政治學說、一種分析和行動的‘方法’,而且作為科學,它是發展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哲學不可缺少的基礎研究的理論領域”[3]7,可見他思想深處的馬克思主義則是尤其強調哲學意義或方法論理論向度的科學馬克思主義,而非西方學者視野中的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觀念的單向度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著作本身就是科學,而過去,人們卻要我們把科學當作一般的意識形態”[3]3,乃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和科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的捍衛者,“是為一個特定的學說(或理論)服務,為馬克思的學說服務”[2]。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世界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空前關注、傾注熱情,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與新勢頭,“馬克思哲學不僅成為東方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指導,而且在整個東西方學術研究中占據了重要地位”[4]15-16。如盧卡奇重拾人的主體性價值而強調“階級意識”和“把馬克思主義黑格爾化、人道主義化”[4]19作為改造馬克思主義的努力探索獲得廣泛性認同,“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幾乎席卷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所有代表人物和所有流派”[4]。蘇共“二十大”之后,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倡導的人本主義思潮異常活躍,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重釋和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成為時代強音,并呈現出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和教條主義化的發展態勢,使得馬克思主義朝著庸俗化方向發展。馬克思主義者為捍衛真理,重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靈魂,紛紛反對人道主義化和教條主義化的馬克思主義,在這股力量的推動下出現了科學的馬克思與人本的馬克思之間的思想交鋒,而阿爾都塞就是在這股思潮交鋒中涌現出的一個以科學的精神為標榜來捍衛馬克思的著名“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他曾公開宣稱:“自己是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威脅的正統的捍衛者”[4]4。阿爾都塞對于馬克思著作的重新闡釋,貫穿了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和“認識論斷裂”①觀點。盡管他對馬克思經典文本進行解讀中的諸多觀點頗具爭議性,然而,在重解馬克思和回到真實的馬克思的過程中,尤其是因為在對文本的詮釋和分析采取結構主義的方法而并被授予“結構主義者”之稱號,事實上則是有失公允的。因為運用結構主義研究方法并不意味著就是結構主義者,以標簽式的簡單化一的方式去評價歷史思想人物本身是不科學的。
阿爾都塞是結構主義者嗎?阿爾都塞在其自傳《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中說:“到了‘結構主義’意識形態風行之時,因為它表現出與一切心理主義和歷史主義相決裂的優勢,我似乎也追隨過這場運動。”[5]197阿爾都塞與結構主義有密切之關聯,為此有學者有過這樣的論述,“阿爾都塞的思想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這是阿爾都塞的思想淵源之一”[6]。客觀而言,在法國“結構主義運動”盛行的大歷史背景下,阿爾都塞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中進行“保衛馬克思”的理論闡釋與論辯,因其所處的時代而受到“結構主義”社會思潮運動的思想影響,則在所難免,“將結構主義方法與社會科學某一領域的研究相結合”[4]48和“用結構主義重新‘注釋’馬克思主義”[4]48成為理所當然。雖然他運用結構主義的方法去研究歷史、哲學和社會問題,但是并不意味著其本人就是一個結構主義者,如同社會主義要搞市場經濟,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就變成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有計劃經濟亦不意味資本主義社會變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正如張一兵指出的那樣:“不能簡單地把阿爾都塞的思想稱之為‘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加以貶斥。”[7]
那么,什么是結構主義呢?如何界定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的方法論究竟有何內涵?阿爾都塞如何運用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去進行分析和闡釋歷史哲學方面的諸多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探究,有利于我們辨識和還原其本身并非一個結構主義者的真實面貌。眾所周知,結構主義最早發端于瑞士語言學研究領域,即“狹義的語言學結構主義,開始于索緒爾(F.de Sausure)”[8]65,索緒爾素有“結構主義之父”之譽,是較早將結構主義的方法和思想具體運用到語言學研究上重要的語言學家。他通過長期的實踐探索,在比較語言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見識和新觀點,“他證明語言的過程并不能歸結為語言的歷史性研究”[8]64,如比較語言學將一些孤立靜止的語言事實當作單位或單元對待是有缺陷的,僅注意到語言的歷史維度的比較,而忽視了語言要素之間的相互制約與相互依賴性關系也是不夠的,且忽視了語言本身就是一個綜合且復雜的整體性文化系統。在語言認知上,索緒爾則把具體的語言行為(“言語”)和人們在學習語言實踐過程中所掌握的深層次體系(“語言”)有效區別開來,把語言視為一套有機組合的文化符號系統,同時亦認為語言能夠產生意義的并非語言符號本身,而是在于語言符號彼此間的組合關系及其所構造生成的意義,并且他強調“除了歷史之外,還有一個‘體系’的問題(索緒爾沒有用過結構這個術語),而這樣一個體系主要是由對于這個體系的種種成分都發生影響的平衡規律組成的,在歷史的每一個時刻,這些規律都取決于語言的共時性”[8]64。可見,語言的規律既具有歷史性也具有共時性,是歷史性與共時性的統一,同時也強調“體系”或“系統”的重要性。索緒爾使用的詞雖然是“體系”或“系統”而不是“結構”,但在本質上的意思乃是同一的、無差別的,“種種意義合成的整體,自然地形成一個以區別和對立關系為基礎的系統,因為這些意義相互之間是有聯系的”[8]64。在他看來,語言學是研究符號組合規律的一門學問。他把語言的特點看作是意義和聲音之間的關聯體系或關系網絡圖景,形象地展示了二者之間純粹的相互關系性結構,并把這種關系性結構作為語言學研究的主體性對象,“在語言中起作用的基本關系,乃是符號和意義之間的對應關系”[8]64,這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的主要理論原則之一。索緒爾的語言學結構主義理論在他死后,則由他的學生全面和系統整理出來并冠名以《普通語言學》的書名公開出版面世,對結構主義思潮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較為深遠的社會影響。索緒爾的這些結構主義語言學觀點,后來被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繼承,其《野性的思維》則是直接將結構主義理論運用到人類學的研究,并使之在其他各類研究領域迅速傳播并得以發展,“從而使結構主義正式登上了法國理論舞臺”[4]48。之后,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不斷被擴展到法國的文藝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諸多研究領域,并成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方法論。法國當代學者通過運用結構主義方法探究現實問題,獲得豐碩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戰后歐洲大陸法國曾經一度泛濫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潮。顯然,在這種思潮和思想背景下,阿爾都塞理解和詮釋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那么,究竟阿爾都塞在哪些方面受到了結構主義的影響?檢讀阿爾都塞的著作,尤其是從他與巴里巴爾合著的《閱讀〈資本論〉》中最能反映其對結構主義方法論的運用的嫻熟,他所倡導的“依據癥候閱讀法”,即是閱讀馬克思經典著作的重要方法。按照這一讀書方法,一部著作的閱讀是就文本自身的對癥性解讀,閱讀者關注的不是它闡述的各個具體原理和基本命題,也不是觀察和揣度書作者的主觀意圖,而重點在于把握它的內在思想體系結構或基本的理論框架,“正是理論框架的概念在思想內部揭示了由該思想的各個論題組成的一個客觀的內在聯系的體系,也就是決定該思想對問題作何答復的問題體系”[4]254,“任何理論體系,任何思想結構都能夠還原為各自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條件下,人們可以對理論體系中的某一個成分單獨進行研究,也可以把它與屬于另一個體系的另一個類似成分相比較”[3]41。可見,從體系結構和理論框架出發認知和理解著作繼而把握事物的本質,是阿爾都塞閱讀的關鍵所在和認知的獨特路徑。因為這種理論框架或思想體系作為一種“無意識的結構”隱藏在原文本之中,蘊藏和體現著一本著作所具有的豐富思想內涵與精神實質,因而需從作品的字里行間去把握它的內在聯系,即“要從充實的話語中找出‘空缺’,在完滿的文本中看到‘空白’,從被洞察到的內容中尋出‘失察’,從可見的東西中窺見到‘不可見的’東西”,并且“要特別注意文中那些無意中出現的疏漏和缺失”[9]378,只有進行針對性閱讀和解讀,才能真正理解作者真實思想和企圖,從而實現“思想、思想的明晰以及語言這三者的統一”[5]181;同時他認為,任何閱讀均非“毫無根據的”,它必然是以一定的理論為指導,譬如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則理所當然地必須具備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基礎或思想素養,“我們從認識論和歷史的角度來閱讀這些著作(馬克思的著作)。確實,這種理論只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而不是任何別的東西”[3]23,并強調了在特定的理論框架內就文本對象和問題內在關聯系進行思考與理解的意義。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阿爾都塞強調的對象性關系,“不在于我和一個或一些客觀對象的關系,而在于我和‘對象性的’對象的關系,也就是和內在的、無意識的對象的關系”[5]227,乃是一種潛在的、隱性的內在邏輯性結構,因而“把握總體的思想本身是嚴格而清晰的,才能夠思考整體,這樣的思想才可以反思整體的不同要素的結合”[5]181。
“依據癥候閱讀法”對于如何閱讀提供了讀書之法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僅憑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是不可能真正領會其精神實質的。該方法具有明顯的唯理主義傾向。原文中的所謂“無意識結構”,“顯然是從弗洛伊德主義那里搬來的”[9]378,但是阿爾都塞對弗洛伊德文本研究并沒有更多的興趣,他說:“我卻從來沒有能深入到弗洛伊德的任何文本中去”,可能他使用這一無意識的語言結構,乃可能是靠其傳奇式的“道聽途說”方法而獲得哲學知識所致,他常常自夸說:“我最終以‘靠道聽途說學習’這樣的事情為榮。”[5]174-175那些熱衷于把阿爾都塞稱為結構主義者的學者,則把他的這種“癥候閱讀法”視為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典型案例,認為阿爾都塞就是從這種“癥候閱讀法”方法出發去推論和得出馬克思理論的反歷史主義、反經驗主義、反還原主義和反人道主義結論的;也有學者將他的“問題式”“無主體過程”“認識論斷裂”以及“多元決定論”等思想觀念全部歸結為結構主義的認識論。事實上,“癥候閱讀法”在阿爾都塞的思想理論系統中并不占核心地位,它僅僅是起到了一種沖破思想傳統的催化作用。阿爾都塞《閱讀〈資本論〉》,打破了歷來僅將《資本論》視為經濟學著作來詮釋解讀的思想傳統,而相反的則是可以把它當成是反映了馬克思哲學思想、“實踐狀態的哲學”以及“社會問題”的主要論著,由此為他從哲學和認識論(或“理論實踐”)的視角詮釋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了一種廣闊的理論視野和“自由聯想”的思想基礎。至于其中許多具體觀點的提出與論證,并非以“癥候閱讀法”為參照系,相反,更多地是體現在“換喻的因果性”內涵表達方面,“大家在《閱讀〈資本論〉》里還能找到這件事的痕跡。在我使用這種表達式(‘換喻的因果性’)時”[5]241,盡管阿爾都塞的《閱讀〈資本論〉》在注釋中使用了“結構的因果性”詞匯,但是從避免“剽竊”所謂“換喻的因果性概念”之誤解處著眼。運用“依據癥候閱讀法”,阿爾都塞得出了一系列關于文本深處的思想觀點,“思想家被他的著作所掩蓋,人們通過著作只能看到思想家的嚴謹思想;具體的歷史也被當時的意識形態論所掩蓋,人們所能看到的只是意識形態的體系”[3]50。阿爾都塞涉及的理論性問題很廣泛,如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唯物辯證法等,“因而,如果把阿爾都塞的思想完全歸結為結構主義,就難免以偏概全”[6]。
二
阿爾都塞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嗎?答案顯然不是。有學者研究指出,“從阿爾都塞的整個思想發展來看,他還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固然他的理論表述方法中存在著種種未必合法的理論挪用,他對馬克思的解讀尚有大量的武斷臆想,但阿爾都塞的學術立場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的”[7]。所以,他在政治立場上旗幟鮮明地亮出保衛馬克思的響亮口號。堅持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是其一貫的思想立場。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科學,而過去,人們卻要求我們把科學當作一般意識形態。”[3]3在這里,他區分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與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是兩種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為我們認識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新的參照視野。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和審視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流派究竟是什么的問題?我們又應該如何去對待西方哲學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化的馬克思主義差異性與關聯性。這對于全面系統認識和評價馬克思主義,毫無疑問是有益處的。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是以一個共產主義者戰士的身份向學術界和思想界作出的政治表達,這一表白更是說明了他的政治立場和思想要達到的具體期望,與其說是思想學術的自由表達,還不如說是政治責任感的感召與呼喚,所以他說:“我是以我自己的名義,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寫這些話的;我研究過去,正是為了說明現在和認識將來。”[3]3在阿爾都塞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乃是至關重要的一項研究內容,即探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研究馬克思的關鍵之所在,他認為“要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必須先具備在本質上與各種理論形態及其歷史完全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就是說,必須先具備一種說明認識論歷史的理論,而這種理論恰恰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3]22。而真正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就在于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理論根據。隨著斯大林教條主義的結束,“我們有權正確的重新評估我們自己,坦率承認我們的優點和缺點,公開提出和思考我們的問題”[3]12,所以他主張:“我們今天的使命和任務就是公開提出這些問題,并努力去解決這些問題。”[3]13這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應當予以肯定。
三
是政治上的保衛馬克思,還是思想上的保衛馬克思,抑或還是哲學上的捍衛呢?從《保衛馬克思》一書我們不難看出,在保衛馬克思的運動中他是以哲學批判的思想傾向表現了其政治上的立場和態度。換句話說,阿爾都塞力圖區分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或哲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區別,而實現哲學意義的捍衛他所認為或理解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但事實上他的哲學表達恰好地凸顯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政治立場,盡管他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哲學表達是有缺陷和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誤讀,就像他本人的所說的那樣,“我現在清楚地看到,這種方式和馬克思本人的方式并不完全一致”[5]236,但是他用心良苦,“我所做的只不過是試圖讓馬克思的理論文本就其本身和我們而言都變得可以理解”[5]236,實質上也捍衛了他所理解和能理解的馬克思主義。
他又是如何去實踐這一哲學表達的歷史任務的呢?他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重要的不是理論,而是實踐”[5]177,“我致力于就哲學發展一種論戰的和實踐的觀念”[5]178。他試圖實事求是地去呈現馬克思主義的真實面相。他主張“必須去接觸實際事物,同哲學意識形態相決裂,并著手研究真實”[3]11,但他運用結構主義方法力圖去解讀文本思想,力求回到馬克思,然而他實際上又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的真實內涵與時代意義,還沒有從實踐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質。阿爾都塞指出,在馬克思的思想系統中,阿爾都塞指出,在馬克思的思想系統中,“‘社會主義’是一個科學的概念,而人道主義則僅僅是個意識形態的概念”[3]217—218,他在論證馬克思同人道主義的徹底決裂時說,“從1945年起,馬克思同一切把歷史和政治歸結為人的本質的理論徹底決裂”[3]222,“馬克思同一切哲學人本學和哲學人道主義的決裂不是一項次要的細節,它和馬克思的科學發現混成一體”[3]223。他提出馬克思堅決反對從“人的本質”這一思辨概念中,引申出和演繹出社會發展的必然性。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對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道主義思想的理解以及把它同康德、費希特和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相混同,則是不正確的。他說:“青年馬克思認為,‘人’不僅是揭露貧困和奴役的一聲呼叫,而且是他的世界觀和實踐立場的理論立場。‘人的本質’(不論它意味著自由和理性或是共同體)同樣是嚴謹的歷史理論和連貫的政治實踐的基礎。”[3]218在他看來,早期的馬克思是“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義”,即“歷史只是依靠人的本質,即自由的理性,才能被人理解。自由是人的本質,正如重力是物體的本質一樣”[3]218。人道主義這個概念本來就有多種不同的含義,而從阿爾都塞視界折射出來的人道主義,在馬克思那里蘊含著前人所沒有的極為豐富和十分深刻的內涵,如強調在實踐中重獲人的本質的觀點、無產階級和哲學在人的本質中結成革命聯盟的觀點、消滅私有制的觀點、進入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觀點等等;又如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不斷發展了自身對人道主義的認知與理解,宣揚“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馬克思在歷史理論中用生產力、生產關系等概念代替個體和人的本質這個舊套式的同時,實際上就提出了一個新的‘哲學’觀”,“馬克思不再把人的本質當作理論基礎,因而也摒棄了兩個假定(主體的經驗主義和唯心主義、本質的經驗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全部有機體系。他把主體、經驗主義、觀念本質等哲學范疇從它們統治的所有領域里驅逐出去”[3]224。由于馬克思否認人道主義是理論,作為意識形態的人道主義是被其所承認,即“人道主義的本質是意識形態”[3]227。阿爾都塞認為,在馬克思早期的著作里經常出現的主體、人的本質、異化等有關人道主義思想的哲學概念,在其后來的著作中罕有論及,這也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關于新的真正的人道主義問題,阿爾都塞在其《關于“真正人道主義”的補記》中有所論及,他認為“新人道主義的內容,必須社會、國家等現實中去尋找”[3]240。他以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提綱》為例,論及馬克思提到費爾巴哈關于宗教上的“自我異化”論見,在指出費爾巴哈的不足的同時還專門就費爾巴哈對人的本質的錯誤理解進行批評,特別提出了“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新洞見。但是,阿爾都塞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說:“如果把這句話(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當作完整定義單從字面上去解釋,它卻說明不了任何問題。”[3]241在他看來,關于“人的概念”和“人的定義”(社會關系的綜合)不相符合,盡管不相符合,但是“這種不相符合的關系畢竟是有意義的;它有一種實際意義”[3]241。事實上這種“實際”,是具有實踐行動的隱形邏輯的含義,即“應該進行什么運動,朝什么方向和為達到什么目的地而轉移,以便不懸在抽象的空中,而腳踏實地的地上”[3]242。可見,這是具有“實踐”意義的。馬克思還反復提到實踐是人的實踐、人的感性的實踐,尤其展示了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實踐意義,顯明了“理論實踐”的特性[3]251,如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那樣,“認真地去研究實在。那時候,信號已經起到了它的實踐作用”[3]243。阿爾都塞認為,共產黨人應該踐行真正的人道主義,他說:“共產黨人認真地研究人道主義愿望的真實意義,研究這一實際概念所指出的現實,這肯定是完全必要的。”[3]244
總之,在哲學思想層面的探究上,阿爾都塞的主要理論向度目的是力圖通過對細致、縝密的思想史文獻的重新解讀——他稱之為“按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的解讀方式來回到真實的馬克思原真狀態而實現真正的保衛馬克思之目標,并通過嘗試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形態而形塑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所以,他直接面向馬克思,力圖向我們呈現一個本真的馬克思,但事與愿違,他卻離馬克思越來越遠,誠如他自己所言:“我試圖使馬克思的思想對一切真誠的、有理論需要的讀者來說變得更明晰而嚴密。當然,這樣便使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敘述有了一種特殊的形式,因此有許多專家和戰士都感覺我制造了一個自己的馬克思,與真正的馬克思大相徑庭,是想像的馬克思主義。這一點我愿意承認。”[5]237而恰是如此,他在試圖通過《保衛馬克思》來維護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理論姿態的過程中,并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化的思潮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思想戰士的政治形象,雖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識存在有種種缺陷和偏見,但也掩飾不住他思想的睿智和精神的光芒,“他的作品仍然有著生命力”[2]!
注釋:
① “認識的斷裂”的含義有二:一是科學理論的產生或科學精神的形成,須與直覺自明的事物或明顯之現象所予決裂;二是科學本身的發展是不連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