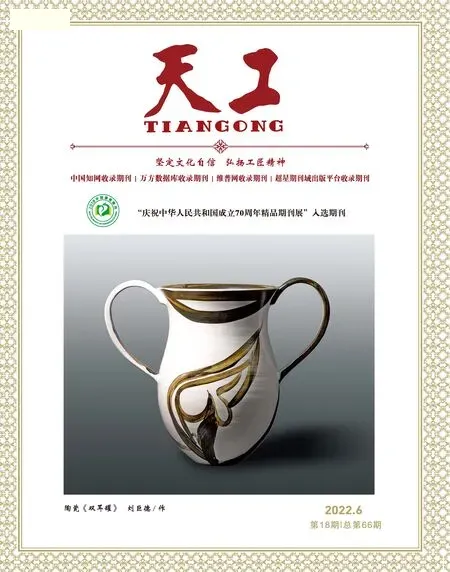淺析杖頭木偶的造型藝術及其文化傳承研究
朱加瑩 東北大學
一、杖頭木偶的概述
(一)杖頭木偶的起源
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有很多文化形式都被保留了下來并且擁有獨特的藝術形式,木偶戲正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也是一個重要的模塊。
木偶的起源很早,最早在《列子·湯問》中出現過綁著皮革的木頭人作為演員,所以木偶有可能在周穆王時期就出現了。我國木偶出現的時間大約在戰國時期,考古記錄表明,早期的木偶雛形是在戰國古墓中發現的。作為漢族獨特的一種戲劇,在古代被稱之為“杖頭傀儡”,這種木偶內部是鏤空的,眼睛、鼻子都是能動的,木偶人物的頸部下面有木棍或竹竿連接,在表演時主要利用木杖進行操控,也稱為“舉偶”。
(二)杖頭木偶的發展
“木偶”這一詞源于周朝,由于當時的喪葬儀式,因而稱之為“傭”,后來也被稱為“傀儡”。木偶戲是由木偶表演者操縱木偶進行一些戲劇表演的一種傳統藝術形式。我國的木偶戲大概起源于漢代,考古工作者在山東漢墓發現過大型的木偶人,有五官,身體關節都可以活動,可坐、立、跪。木偶在唐代有了新的發展和改善,在當時,杖頭和提線兩種形式成為主流形式。到了宋代,木偶的發展迎來全新的變化,無論是制作工藝還是操作技藝都做出了改變,同時也出現了很多著名的表演藝人。明清時期,木偶戲蓬勃發展,在民間越來越受歡迎。
(三)杖頭木偶的特點
杖頭木偶在表演中的主要特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可以獨立操作,在表演過程中,觀眾是全程看不到表演者的,只能看到被操控的木偶,這種表演形式有助于提高觀眾對表演的熱愛;其次,舞臺比較小,杖頭木偶表演不像其他節目那樣需要那么大的舞臺,杖頭木偶表演只需要三面布幔圍起來,給木偶留出表演空間即可;最后,杖頭木偶的表演層次比較分明,不論是靜物還是人物都能夠形成高低錯落的視覺效果,人物也可以在場景中進行穿梭,這樣能夠強化舞臺表演的層次,使木偶表演更加生動、更有靈魂[1]。
二、杖頭木偶的形象特征
(一)杖頭木偶中的五形造型特征
木偶的五官也稱之為“五形”,是指眼睛、鼻子和嘴,眼睛成雙,鼻有兩孔,加上一張嘴。五形基本決定了木偶形象的性格特點及其喜怒哀樂。
最初傳統的用木雕刻的偶頭主要是借鑒了歷史中俑的造型風格,和俑的形象比較相似,還有一部分偶頭受到戲曲表演的影響,其形象參考了戲曲中的臉譜以及妝容。傳統偶頭五官是不能動的,妝面都是預先系在面部的,大約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有些木偶能夠“開口說話了”,還有一些眼睛可以動的木偶,它們通常可以眨眼,更為復雜的可以轉動眼珠表演。
杖頭木偶的臉譜與傳統的戲曲臉譜較為相似。武生通常為國字臉,額頭較寬;文生通常為目字臉,和國字臉相比較瘦長;丑角通常都是滿月臉,是圓圓的頭和圓圓的臉;旦角是女性形象,旦角也有不同,通常鵝蛋臉代表著地位較高的小姐,而丫頭則是較為清瘦的瓜子臉;大花臉通常是田字形,寬額頭和寬下巴;還有一些特殊的形象,如各種動物、妖魔鬼怪等。
不論是什么臉型,都是通過五官的特征來展現的,所以五形的設計至關重要。相較于由人扮演的戲劇形象,木偶的局限在于表情不能隨著劇情發展隨時變化,即便是復雜的木偶可以實現眼睛和嘴的運動,但是也不能如同真人一般表達喜怒哀樂的情緒,因此偶頭雕刻藝術家便會選取角色一瞬間的精彩神態,所以該神態的選擇和刻畫極其重要。不過雖然木偶不能實現面部神態的變化,但是表演者也可以通過操作肢體動作來彌補這一方面的缺失。
(二)杖頭木偶中的角色特征
木偶藝術是民間藝術的衍生,杖頭木偶人物和戲曲人物一樣,基本分為老、中、青三種,既有老生、青衣、花旦,又有武生、丑旦。杖頭木偶大多是按照傳統的造型方式,與戲曲人物的造型基本一致[2]。
木偶形象一般分為生頭、旦頭、凈頭和丑頭。男性角色通常稱之為生角,其中包括老生、武生、小生、紅生以及娃娃生。中老年的男子形象通常叫作老生;武生主要是比較英勇的男子形象;小生主要是一些年輕英俊的男子形象;帶有紅色臉譜的男子形象被專稱為紅生;娃娃生,顧名思義就是在劇中的兒童形象。旦頭是女性角色的頭部造型,其中包括青衣、花旦、老旦、武旦和彩旦。青衣大多是溫柔端莊的女子形象,少女和少婦的形象通常被稱為花旦,老旦是老年婦女的形象,武旦是比較英勇的女性形象,彩旦是滑稽、帶有喜劇色彩的女性形象。凈頭作為具有突出特點的男性形象,有時也稱作“花臉”。丑頭主要用于丑角人物形象,也可以用于家丁、商販、店小二這樣的小人物形象。
三、杖頭木偶的服裝造型特征
(一)紋樣
杖頭木偶表演的很多劇目都來源于戲曲的劇目,在服裝樣式上也與戲曲的服裝有異曲同工之處。木偶的服裝紋樣汲取了傳統服飾、傳統繪畫等藝術形式的傳統紋樣精華,紋樣在服裝造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絕大多數的服裝都有著精致的紋樣,有一些蟒和道袍甚至都是滿繡的樣式,這些精美大氣的線條、絢麗多彩的紋樣不僅起到了美的作用,而且有一定的寓意,其包含了美學、心理學以及民俗學等相關的內容。
紋樣從古至今都起著點綴、裝飾的作用,杖頭木偶的服飾來源于戲曲服飾,而戲曲服飾的紋樣大多都是歷史上傳統的紋樣樣式,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進行提煉、概括,既表現出了日月、龍鳳、水火等藝術特點,又凝聚著民族文化精髓。
杖頭木偶的服裝紋樣中運用最多的便是傳統服飾紋樣。例如,象征著皇帝地位的龍袍中的龍紋樣,經過藝術加工提煉后被作為權力的象征,用得比較多的有十團龍蟒,團龍紋樣整體為圓形,構圖搭配合理、主從有序,形象上動靜相宜,左右紋樣對稱,布局規整嚴謹,生動的紋樣配合華麗的顏色和刺繡,使得蟒袍成為象征身份的服飾。象征性紋樣多為身份或者情感的寄托,如以梅蘭竹菊為主的植物系列紋樣以及以蝶、燕和云蝠為主的動物系列紋樣[3]。
梅蘭竹菊象征著高潔的品質,將這些元素應用到服裝紋樣中,代表了傲幽堅淡的品質,而且將紋樣的意義體現在人的服裝上,其不僅僅是對外貌秀美的贊揚,更多的是對品格的贊揚。像飛蝶、飛燕紋樣運用于木偶服飾中,通常象征此人武藝高強、身手敏捷;而蝠紋則是取其諧音“福”,通常和壽字紋結合使用,寓意福壽延年。
(二)色彩
色彩作為服飾的靈魂,主要分為兩大類:上五色和下五色。上五色也稱為正色,包含紅、綠、黃、黑、白,下五色也稱為副色,包含紫、藍、粉、秋香、皎月。顏色既有著不同功能的文化含義,還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
服裝的色彩不僅可以體現角色的身份地位,而且可以體現角色的性格特征,如紅色多表現比較剛烈、脾氣火爆的人物性格;白色多表現剛正不阿的人物性格;黑色通常表現心思深沉、心狠手辣的人物性格,曹操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墨綠色多用來表現詭計多端的小人。除此之外,也會衍生一些其他的色彩,要結合具體情節細致分析[4]。
杖頭木偶的服飾色彩要根據劇情的需要融入豐富的色彩,讓劇目可以在色彩的影響下呈現出更好的效果,色彩的融入恰好能夠體現民族文化內涵,也能夠彰顯出角色的身份。
四、杖頭木偶戲的文化傳承
杖頭木偶現已演變成為最大的木偶戲群,而其延續至今也形成了具有獨特藝術價值的表演形式。我們也不難發現,木偶戲早已遍布全球各地,很多國家都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木偶表演形式,而我國的木偶戲表演雖源遠流長但卻有些陌生,從歷史角度來看,民國時期的戰爭對木偶戲的發展造成嚴重打擊,民間藝人受到了冷落,很多木偶戲藝人為了養家糊口而另謀其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也集合了很多分散的民間木偶戲藝人,木偶戲逐漸回到正軌。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木偶戲的表演出現了斷層,如老藝人的逝世和傳本的流失導致很多劇目都無跡可尋、很多老藝人的絕活也因此失傳。
另外,隨著木偶戲長期的發展,現已成為民間化的狀態,而一些專心研究木偶戲的學者由于缺乏實踐,所以研究的木偶戲與最原始的木偶戲有很大的區別,并且杖頭木偶與戲曲的融合專業性極強,使得一般學者不能簡單參透。我國杖頭木偶行業的停滯不僅僅是技術上的差距,更多是人為的原因,所以為研究杖頭木偶戲的文化傳承,提出以下幾點。
(一)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從目前杖頭木偶的發展來看,國家正在大力推崇保護和發展此類技藝,將更多藝術形式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一個很好的勢頭。不過,木偶戲屬于一種特殊的藝術形態,給學者帶來很大的研究難度。因此,要不斷地完善藝術保護機制,通過政府進行更大力度的推廣,也要通過各大媒介傳播杖頭木偶,讓更多大眾了解且喜歡這項傳統技藝。自1980年成立了木偶皮影藝術學會以來,學術界開展了大量的學術研討活動,恢復了大量的劇目,接下來需要對其出現的瓶頸加以分析,汲取其他國家的經驗,取其精華,并且與其他國家要有所區別[5]。
(二)培養更多傳承人
一門藝術若想要長久地傳承與發展,傳承人的培養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演員的培養是對木偶傳承和保護的重點。可以多進行一些杖頭木偶藝術團在學校中的宣講,或者設立相關的課程,將杖頭木偶作為一些院校開展教學的一個重點內容,可以請一些資深的杖頭木偶藝術家到學校對學生進行相關知識講座。總之,結合多種形式進行文化宣傳,使學生從小就樹立文化傳承的意識,使越來越多的學生可以了解杖頭木偶的傳統技藝[6]。
(三)建立數字化影像數據庫
隨著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人們可以更快、更高效地獲取更多的信息。杖頭木偶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藝術形式,在傳播其藝術價值和文化價值的同時,通過各種媒介不斷擴大杖頭木偶的受眾群體,讓更多人了解、熱愛這項技藝,并且加入傳承的隊伍中。
除了利用網絡進行推廣宣傳外,也應建立數字化影像數據庫,將一些制作木偶的工藝以及其表演形式記錄下來,使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及時的保存、展示、傳播,加大對杖頭木偶藝術的傳承與保護力度。建立統一的數字化影像數據庫,首先要搭建數據平臺建設,其次在采集大量非遺信息的基礎上,通過對杖頭木偶非遺傳承人的采訪及現場表演進行記載,從而推動杖頭木偶藝術非遺數字化進程[7]。
五、結語
綜上所述,杖頭木偶是我國傳統的文化瑰寶,發揚和傳承傳統文化是必然趨勢。首先,本文對杖頭木偶的起源、發展及其特點進行概述,了解其歷史背景以及與其他種類木偶的不同之處。其次,對杖頭木偶的五形特征進行分析,了解了偶頭制作工藝的重要性,并通過對杖頭木偶服飾的紋樣、色彩以及圖案的研究,探討杖頭木偶藝術與戲曲藝術間密不可分的聯系。最后,通過以上的研究分析,更加了解杖頭木偶藝術的寶貴價值及其文化底蘊。作為流傳已久的杖頭木偶藝術,可以在傳統藝術中加入創新元素,開拓思維,并通過政府加大力度的扶持,培養更多傳承人以及建立數字化影像數據庫,將杖頭木偶藝術更好地發揚、傳承下去,讓更多的人了解。
文化代代傳,優良不可拋。隨著時代的發展,杖頭木偶作為一種民間藝術,擁有著巨大的魅力,同時也是我國其他傳統藝術文化的見證,無論是表演形式還是造型藝術,我們都應當繼續將其保護、傳承并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