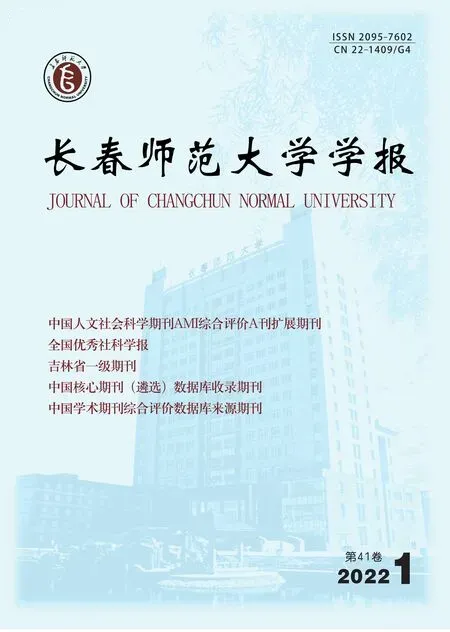人物身份認同視角下《桃花扇》中“情”之探析
李瑞瑤
(香港城市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香港999077)
《桃花扇》作為傳奇戲劇,其中的“情”含義復雜、意蘊深遠。本文嘗試從晚明“情”之概念出發,探析《桃花扇》中的“情”,并采用現代身份認同理論,分析《桃花扇》中的人物由于不同的身份認同而產生的男女之情和家國之情、興亡之情與反思之情。
一、“情”與“身份認同”概念辨析
如果與西方語言比較,漢語中缺少對概念的定義和探析。“中國為確定事物和世界,產生了者……也結構及其簡化形式,構成其語言的非定義特色。”[1]漢語的這種非定義特征,也影響了漢民族的思維方式。
王力等學者站在中國語言學研究角度,力圖論證中國對語言準確性的重視[2],并舉出孔子的正名說、墨子的語文符號論以及荀子和公孫龍的名實論為例。然而后世接受更多的反而是老莊的“道不可名,言不盡意”論。在這種思維模式下,人們并不將語言的精準作為追求目標,而是將目光投射于遙遠的形而上學。
這種傾向使漢語中許多概念呈現出一種龐雜含混的特征,其中也包括“情”。為了追求思維的明晰,對概念的厘清更是現世研究中需要重視的部分。因此,本文在分析《桃花扇》中具體的身份與情之前,先探析漢語中“情”之概念,并解釋“身份認同”的概念。
(一)“情”之概念
“情”之概念龐雜混亂,若依時間順序梳理可從先秦開始,一定浩浩蕩蕩漫無邊際。因此,對“情”概念之討論只能集中于晚明一點。然而,這一點上的情也必不是獨立的,其中也可見前代之影響。總體而言,晚明“情”之概念主要由王陽明、湯顯祖、袁宏道、馮夢龍等人構建。他們所說的“情”可分為三種:感情之情(feeling),欲望之情(desire),男女之情(love)。
1.感情之情
三種定義中,“感情”最龐大卻又最明確。在上述文人中,王陽明基本將“情”之含義概括為“感情”。
在《傳習錄》中,王陽明提出:“喜、怒、哀、樂,性之情也”,可見其將“情”定義為感情。但在王陽明的體系中,情又與心、性、理相統一。他雖然試圖指明心、性、情、理間一種模糊的先后關系,但并沒有給予它們嚴格的區分。而王陽明對情的要求是中和,他曾表示:“情正則中,情修則和”。在這里,王陽明提到的“情”顯然是感情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感情和心性在王陽明處為一體,但他對感情和欲望有明確的區分。如《知行錄》:“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為私欲所蔽。”“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有學者在評述王陽明的理論時表示,“欲不僅僅是生理欲望,也是人類的情感需要”,認為王陽明肯定人欲,形成對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反抗。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因為對欲望的肯定雖盛于明代,但并不源自王陽明。
總體而言,將情定義為感情的代表人物是王陽明,而王陽明的感情又與他看作負面的欲望是完全相悖的,并且他的情體系中沒有提到男女間的愛情。
2.男女之情
男女之情即是愛情。與感情相比,愛情的概念更加狹窄。明中后期逐漸出現對愛情的重視,湯顯祖有相關闡述,但直接將情具體定義為男女之情的是馮夢龍。
湯顯祖并沒有提出成體系的情論,他對情的解釋只能在文學作品中間接體現。如《牡丹亭記題詞》:“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3]這里的情顯然是男女之情,而他的其余戲曲作品如《紫釵記》也將男女之情作為中心部分。
馮夢龍受湯顯祖影響,并將情論體系化。他指出:“六經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婦,《詩》有關唯,《書》序濱虞之文,《禮》謹聘奔之別,《春秋》于姬姜之際詳然言之,豈非化膚始于男女?”[4]馮夢龍將男女之情的地位提升到至高處,認為萬物之情始于男女之情,并將這種情作為情教的基礎。他明確提出自己的目標:“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在這種觀點下,馮夢龍作出許多創作嘗試,特別是在“三言二拍”中大量描寫男女愛情故事。
由湯顯祖和馮夢龍開始,愛情在感情中被突出強調,男女之情也被直接引入情的定義中,但此處之情并不能延伸到欲望。相反,馮夢龍正小心地維護著情與欲的邊界,警惕著情向欲的滑動:“善讀者可以廣情,不善讀者亦不至于導欲。”
3.欲望之情
將情完全等同于欲望,也是晚明對情的一種特殊定義方式。王陽明等人想必會激烈否定這種定義,但這一趨勢已成必然,尤其體現于袁宏道和金圣嘆處。
袁宏道表示:“真樂有五,不可不知。”他對“五樂”有非常具體的描述,如:“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譚。”[5]袁宏道雖然并未直接將情定義為欲望,但如此詳細的場景描寫足以顯示他對聲色耳目之欲的肯定。
真正在理論上將情等同于欲的是金圣嘆。他指出:“人未有不好色者也,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6]美國學者黃衛總總結:“情與欲界限的模糊,情的欲化和世俗化正是晚明情論的一大特性”[7],這種觀點也應當源于金圣嘆。
然而,欲望并不能看作被普遍接受的情的定義。實際上,更多晚明文人掙扎在情與欲關系的統一與矛盾之中,即使袁宏道本人也有對這種觀點的反思。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將情定義為欲望的文人往往會將愛情包含在欲望之中。
至此,對晚明語境下情的概念分析已經完成。然而實際上,三種定義間還是可見明顯的交錯纏繞,如欲望是否隸屬感情、愛情與欲望是否矛盾、它們是否相互包含或有明確的界限,所以更深的問題依然被懸置。本文采取的觀點是將情定義為廣泛的情感,將男女之情包含其中,以進一步探析《桃花扇》中復雜多樣的情。
(二)身份認同的概念
與漢語中情的概念不同,身份認同完全是一種西方概念。關于身份認同的理論更加清晰明確而成體系,因此文章選擇以此為基點進行論述。“身份認同”(identity)一詞來自于晚期拉丁語identitas和古法語identite,然而真正關于身份認同的探討是現代才有的,它的理論開始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后又被埃里克森、霍爾等集中討論。
弗洛伊德對身份認同的解釋被翻譯為“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在《精神分析導論講演新篇》中,“自居”被定義為:“一個自我同化于另一個自我之中(即一個自我逐漸相似于另一個自我),于是第一個自我在某些方面摹仿第二個自我,并像后者那樣處理事務,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將后者吸收到自身之中。自居作用不再不恰當地被比作用別人的人格來補充自己的結合行為,它是一種很重要的依戀他人的形式。”[8]在弗洛伊德主義發展晚期,弗洛伊德將對自居作用的解釋簡化為:“一個人試圖按照另一個作為模范的人的樣子來塑造他自己的自我。”弗洛伊德的自居作用有非常強烈的個人色彩,比如其和本能性沖動的聯系,但我們也應注意到,它包含了非常現代的建構主義特征:將個人身份認同建立在他人與社會基礎上。這在本質主義者處是萬萬不能被承認的,例如笛卡爾和康德。
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學家埃里克森,在其身份認同理論基礎之上進行補充,提出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他將認同危機定義為:“注意外界并與外界相互作用的需要。而個人的健全人格正是在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9]埃里克森繼續強調社會歷史在個人處起到的作用,并提出了“自我同一性”,實際上就是社會與自我的統一,類似于弗洛伊德的“超我”。
另外一個對身份認同理論有集中討論的是霍爾。他繼承了建構主義的基本觀點,提出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概念:“身份正是通過否定的視角確立了其肯定的成分,必須通過他者的視角才得以建構自身。”[10]和之前的精神分析學家一樣,霍爾認為只有在“他者”出現后,主體認知才會覺醒,這類似于拉康的鏡像理論。他后來又提出了“后現代身份”概念,認為后現代身份沒有固定的核心,是矛盾且暫時的,變化著將主體拉往不同的方向:“我們包涵相互矛盾的身份認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們的身份認同總是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這種矛盾變化的身份認同已與前人理想中的統一獨立的自我有很大區別。
可以發現,與情論統一矛盾相交錯的狀況不同,身份認同理論是發展的。除了不再強調弗洛伊德所重視的性欲,后世關于身份認同理論的內在觀點基本一致,都認同社會歷史和他者對個人身份意識的構建作用。尤其是霍爾強調的矛盾流轉的身份,使得對《桃花扇》中“情”的分析有所依據,同時更容易。
二、桃花扇中的人物身份與情
由前文已知,身份認同是在社會群體和他者影響下個人對自我身份的追求。從此角度出發,《桃花扇》中的情可以被看作不同身份認知下產生的變化的感情。本文嘗試忽略作者影響,集中于戲中人物本身,根據他們的身份認知差異將戲中的情分為兩組:男女之情和國家之情,興亡之情和反思之情。
(一)男女之情和家國之情
《先聲》中老贊禮稱《桃花扇》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11],這里的“離合”即形容男女之情,“興亡”則形容國家之情。它們雖都屬于感情,但對象截然不同。當事者面對兩種感情時的身份也不同,即愛人和臣民。在《桃花扇》中,侯李的身份認知在兩者流轉切換,最終形成一個愛人身份與臣民身份一體的自我。
1.作為才子佳人的男女之情
侯方域作為愛情故事的男主人公,帶有典型的才子身份。如《卻奩》一出中他人對他的評述:“羨你風流雅望,東洛才名,西漢文章。逢迎隨處有,爭看坐車郎。秦淮妙處,暫尋個佳人相傍,也要些鴛鴦被、芙蓉妝。”侯方域對這種身份是接受并且有認識的。在與李香君的交往中,他處處以小生自稱:“不消詩箋,小生帶有宮扇一柄,就題贈香君,永為訂盟之物罷。”這種將“小生”作為自稱的現象始于唐代,只用于文士。在其他才子佳人故事中,才子在與愛人閑話時也都如此自稱。如《西廂記》中的柳夢梅:“小生那一處不尋訪小姐來,卻在這里。”在才子身份的自覺下,侯方域才會去選擇尋訪秦淮,并主動與名妓李香君相好。
侯方域作為李香君的愛人身份,是比他的才子身份更晚形成的,經過很長時間才逐漸獨立出來。他對愛情的意識基本是在李香君寄扇后。在此之前,侯方域對李香君的感情還屬于對名妓的欣賞:“香君天姿國色,今日插了幾朵珠翠,穿了一套綺羅,十分花貌,又添二分,果然可愛。”而得知李香君血濺桃花扇時,侯方域哭道:“香君香君,叫小生怎生報你也?”在侯方域意識到李香君對自己熱烈的愛后,也就是認識到自己在他人處的愛人身份時,才真正完成了從社會才子到香君愛人的轉變。也正因此,在重回秦淮舊樓不見香君時,他才會失落痛哭。
李香君也同時具有佳人形象。在養母的影響下,她作為名妓的身份認知在幼年時已經開始建立。《傳歌》一出中有:“(旦皺眉介)有客在坐,只是學歌怎的。(小旦)好傻話,我們門戶人家,舞袖歌裙,吃飯莊屯。你不肯學歌,閑著做甚。(旦看曲本介)”從她和養母的對話可知,李香君本不愿意唱歌討人歡心,但《訪翠》一出中對她的描寫已是:“鸞笙鳳管云中響,弦悠揚,玉玎珰,一聲聲亂我柔腸。”“有趣有趣!擲下果子來了。(凈解汗巾,傾櫻桃盤內介)好奇怪,如今竟有櫻桃了。(生)不知是那個擲來的,若是香君,豈不可喜。(末取汗巾看介)看這一條冰綃汗巾,有九分是他了。”在遇見侯方域時,李香君早已完成了對名妓身份的認同和轉變,舉止言行已是實至名歸的“秦淮八艷”之一。
但與侯方域不同的是,作為名妓的社會身份并不是李香君的底色。她在遇見侯方域后,就已經堅定了自己作為他的愛人的身份,這也是她的愛遠比侯方域更加熾熱濃烈的原因。在故事中,兩人愛情的危機都發生在李香君一側。即使只經歷了極短暫的相處,愈加堅定勇敢的卻也是香君。在《卻奩》一出中,李香君已經展現出對侯方域的忠誠。在《拒媒》《守樓》中,她更是表達了對承諾的堅守:“奴家已嫁侯郎,豈肯改志。”“案齊眉,他是我終身倚,盟誓怎移。宮紗扇現有詩題,萬種恩情,一夜夫妻。”在戲文中,也只有李香君提到夫妻嫁娶之辭。李香君實際已將自己置于侯方域妻子的身份中,將其看作自己終身的愛人。所以在此時,侯李兩人的身份認知并不對等,導致兩人的愛情意識產生某種程度上的錯位。
2.作為臣民的家國之情
侯方域對自己作為香君愛人的身份認知很晚才建立起來,同時,他對自己作為復社文人的政治身份的認知也很模糊。侯方域的開場詞中說道:“小生姓侯,名方域,表字朝宗,中州歸德人也。夷門譜牒,梁苑冠裳。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樹東林之幟;選詩云間,征文白下,新登復社之壇。”強調自己的復社身份,把自己置于東林清流一派,可見侯方域是有對政治身份的認同的,然而并不堅定。如在《卻奩》一出中,侯方域對阮大鋮的評價為:“原來如此,俺看圓海情辭迫切,亦覺可憐。就便真是魏黨,悔過來歸,亦不可絕之太甚,況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見,即為分解。”在得知阮大鋮出資時,侯方域對其稱呼已經轉為“阮圓老”,和同在場的李香君的反應形成強烈對比。
侯方域對自己作為南明臣民的身份認知同樣不突出。在戰火紛亂、國家覆亡之時,侯方域在《沈江》一出中表現為:“我和敬亭商議,要尋一深山古寺,暫避數日,再圖歸計。”在國家破滅時,侯方域作為復社文人的選擇是逃難和保全自身。同樣情況下,史可法的選擇更加壯烈決絕:“你看茫茫世界,留著俺史可法何處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江山易主,史可法作為南明將領死守揚州,最終主動沉江。他對自己南明臣民的身份認知十分明確,甚至將國家與自己的生命相連。這樣的政治身份已經成為他全部的自我,國家的意義已經全然融入個人主體的意義。相較之下,侯方域不會將復社文人、南明臣民等任何一個政治身份作為自己的全部,他徘徊在各身份之間,并保持著不得已便拋棄它們的狀態。
如果說其余人物承載著一種有明確身份認同的理想人格,侯方域就是更為確切現實的化身,他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也更加模糊。出于對理想身份和意義的追尋,人們對這種人的喜愛可能更少,但實際上侯方域更類似日常生活中真真切切的搖擺矛盾的人。
李香君對自己政治身份的認知比侯方域更加明確。如在《卻奩》中,她聽到侯方域對阮大鋮的評價后,怒道:“官人是何等說話,阮大鋮趨附權奸,廉恥喪盡;婦人女子,無不唾罵。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處于何等也?”在《守樓》中,她說道:“可又來,阮田同是魏黨,阮家妝奩尚且不受,倒去跟著田仰么?”可以說,李香君拒婚的原因一方面源于侯方域,另一方面是因為她堅定拒絕和魏黨有所交往,最終血濺桃花扇:“你看血噴滿地,連這詩扇都濺壞了。”李香君有堅定的政治立場,不僅明確自己的身份認同,也不斷提醒侯方域保持氣節,希望強化侯方域復社文人的身份。
然而,李香君作為南明臣民的身份同樣不明顯,這種身份在李香君處可以說是低于侯方域愛人身份的。南明滅亡后,李香君同樣選擇逃難,而這種逃難和保全生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來自對侯方域的愛:“便天涯海崖,十洲方外,鐵鞋踏破三千界。只要尋著侯郎,俺才住腳也。”在國家滅亡后,她并沒有明確表現出對舊國的感情,發出的感慨也都是圍繞自己的愛人:“一絲幽恨嵌心縫,山高水遠會相逢;拿住情根死不松,賺他也做游仙夢。看這萬迭云白罩青松,原是俺天臺洞。”所以李香君對侯方域愛人身份的認同是遠超對南明臣民身份的認同的,她對愛情的態度也超越了對國家情懷的執著。
3.男女之情與家國之情
真正將離合興亡、愛情與國家價值、愛人身份與臣民身份結合起來的是《入道》篇的張道士。在此之前,侯李兩人的國家之情并沒有如此明顯強烈。他們流轉于愛人和臣民身份之間,并且可以將二者有所區分。兩人失散許久再次重逢時,國家已經覆亡,但兩人還保持著對彼此的愛情與思念:“(生遮扇看旦,驚介)那邊站的是俺香君,如何來到此處?(急上前拉介)(旦驚見介)你是侯郎,想殺奴也。”這時,侯李甚至還提到兩人未來的理想:“待咱夫妻還鄉,都要報答的。”兩人還以夫妻相稱,懷有極強的愛人身份認同,并且為愛情的價值辯護:“從來男女室家,人之大倫,離合悲歡,情有所鐘,先生如何管得?”在這里,愛情和國家是各自獨立的,雖然國破但家不必亡。然而張道士對此批評道:“呵呸!兩個癡蟲,你看國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么?”侯李的愛人身份和臣民身份本是兩分的,但在張道士訓斥下,加之兩人本身即有的對政治理想的追求,他們自覺將兩種身份融合成一個整體的自我,認為選擇愛情即是對國家的背棄。兩人最終入道,看似拋棄了對意義的追尋,實際上也是一種對意義的選擇。
(二)興亡之情和反思之情
除了個人的多重身份外,不同人的不同身份也導致了情的差別。侯李作為盛衰的親歷者和歷史的當事人,最終將自己的情與國家和時代緊密捆綁在一起,表現出承擔歷史的極高自覺性。老贊禮也經歷了時代的變遷,卻表現出超脫的旁觀者之情。他講述故事、品評人物,但都帶有一種陌生感。作為旁觀者,他對歷史更多的是敘述和反思,而非肩負與承擔。
1.作為親歷者的興亡之情
作為國家興亡的親歷者,侯李二人并不將南明的興亡看作一種“歷史”,而完全是生活、生命的一部分,他們不自覺地被時代左右。在整出戲中,侯李兩人聚少離多。在剛剛相知相愛后,《辭院》一出中就因為阮大鋮的陷害和戰亂長久分離:“今日清議堂議事,阮圓海對著大眾,說你與寧南有舊,常通私書,將為內應。那些當事諸公,俱有拿你之意。”在南明滅亡之際,因為戰亂,侯李兩人各自逃難,侯方域感嘆道:“這紛紛亂世,怎能終始相依。倒是各人自便罷。”作為興亡的親歷者,處于歷史洪流和混亂之中的侯李對國家的感情和個人在歷史中的身份并不明確,然而他們無時無刻不被動地被潮流推向各自的命運。
侯李兩人主動拾起南明遺民的身份,開始作為歷史的承擔者,是在《入道》一出。侯方域說:“幾句話,說的小生冷汗淋漓,如夢忽醒。”直到這時,侯李才真正意識到國家已經覆亡。在張道士的影響下,兩人將愛情與國家之情捆綁在一起,將愛人和臣民兩種身份統一成一個完整的新身份,也就是選擇成為興亡的承擔者,用自己的半生肩負家國之痛。
2.作為旁觀者的反思之情
與侯李兩人不同,戲中的老贊禮雖然也經歷了國家興亡,但他似乎是一個超脫的旁觀者。興亡在他眼中就是戲文故事中的“歷史”,他沒有表現出像侯李一樣作為當局者的模糊,而是將感情建立在抽離之上,抒發出對歷史的反思性感慨。
老贊禮主要出現在《先聲》和《余韻》中。他說:“老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個贊禮爵位不尊,姓名可隱。最喜無禍無災,活了九十七歲,閱歷多少興亡,又到上元甲子。堯舜臨軒,禹皋在位;處處四民安樂,年年五谷豐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見了祥瑞一十二種。”老贊禮面對的他者是戲外的觀眾,他承擔的身份更多是講述人。也正因如此,他開場點明年齡與年號,有非常強烈的時間感,旨在將故事和現實、歷史和當世相聯系。
在《余韻》中,老贊禮集中抒發情感:“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具體的國家之情絲毫不在老贊禮的回憶之中,他的感慨完全是因為人事的悲歡離合和歷史的盛衰興亡。也正因如此,老贊禮的感情明顯帶有時光流逝后回望追憶的反思感。從第一出《聽稗》的崇禎癸未二月到《余韻》的戊子九月,已經過了六十五年,國家興亡和愛情已成為故事和歷史。此時,在面對觀眾時,老贊禮的身份已經是一個超脫的旁觀者。
三、結語
本文嘗試從身份認同理論出發分析《桃花扇》中的情,希望從這一新的角度使討論更加明晰。這里的“情”即是廣泛意義上的感情,而感情又往往形成于個人身份認同之上。侯方域和李香君作為彼此的愛人和南明的臣民,同時懷有對彼此的愛情與家國之情。最終,他們選擇將兩種身份整合成一個完整的自我,即興亡的親歷者和承擔者。老贊禮則是歷史的旁觀者,這決定了他的“情”中包含了慨嘆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