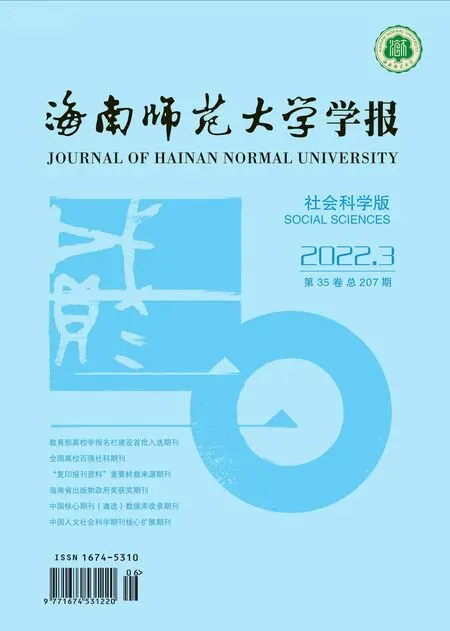南海觀音:海上絲路與文明交流互鑒的共同印記
[馬來西亞]王琛發
(閩南師范大學 閩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363000;馬來西亞道理書院,馬來西亞 檳城11600)
南海生存共同體的共享文化意象
自晉代《法顯傳》的記載,一直到后世各國僧人留下的不少文字,都說明觀音信仰流傳中國的其中一個途徑,是隨著商旅經過南海諸邦傳播中國的。觀音信仰文化的經典,還有各種觀音信俗實踐,不只出現在來往中、印以及南海諸國的船艦中,也影響著海上絲路沿線各處海港城邦,包括流傳在中國沿海各口岸,是南海各民族生存共同體祈求海域安全的精神象征,也是家家戶戶向往富裕康寧的理想意象。古代南海諸國的原來土地上,也就是今日東南亞諸國,至今屢有觀音像出土,也足以說明中國古代典籍所說的“南海”是觀音信仰文化的傳播區域;從印度洋進入馬六甲海峽再到南中國海所經過的土地,是印度南部海濱的補旦洛迦山所面向的南海,也是從中國以南航行到印度所經過的海域。
由玄奘《大唐西域記》可知,至少在玄奘那時代,中國人還是依據《華嚴經》的記載,認為觀音修行道場是位于印度南部海濱的補怛洛迦山。《大唐西域記》形容補旦洛迦山的地理形勢說:“秣刺耶山東有布呾洛迦山,山徑危險巖谷敧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流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匝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游舍。其有愿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1)[唐]玄奘述,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十,《大正藏》第51冊,第932頁上。可見這個地方并不容易到達,但行人若有恒心,又是可以沿著從天池流往南海的大河歷水登山。《大唐西域記》又有記載:“從此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南可三千余里至僧伽羅國”;(2)[唐]玄奘述,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十,《大正藏》第51冊,第932頁上。僧伽羅,梵語名Simhalauipa,是斯里蘭卡的古代名稱。由此亦可知,《大唐西域記》的說法是從印度地理出發,認定補旦洛迦山天池大河奔流出口之處已經是所謂“南海”具體位置的開始,旅人可以從補旦洛迦山東北處的海港出發,往南航行三千余里就到了南海的斯里蘭卡。
其實中國的文獻之謂“南海”,自古以來也通常是指稱從印度大陸南面通往中國的整片海域,包括斯里蘭卡在內,一概統稱“南海”;古籍里所謂南海諸國包括了從南中國海到馬六甲海峽范圍內的諸多城邦小國。以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記》或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為例,他們對于南海的認識,依舊是根據歷史上來往印度與中國之間的航線。民國年間馮承鈞撰《中國南洋交通史》,曾引用元代《島夷志略》的概念說:“今之所謂南洋,包括明代之東西洋而言……大致以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以西,質言之,今之印度洋為西洋,以東為東洋,昔日大食人亦以此兩地為印度與中國之分界。然在元代以前則概名之曰南海或西南海。”(3)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序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頁。換言之,元代以前中印兩地航路之間曾經有過的“南海”概念,是大海域的概念,航路覆蓋的水域面積比現在的“南中國海”大了好幾倍。
也因此,元代以前出現“南海觀音”的尊稱,足以說明信仰菩薩的土地范圍不僅僅在中國,觀音信仰當時是個遍及昔日南海諸國的信仰概念。事實上,在Chutiwongs 與Denise Patry Leidy 合作的書中,曾提到了羅伯?基本尼斯(Robert Kipness)收藏了一尊蘇門答臘(Sumatra)出土的不空罥索觀音銅像,考證其制作年代約在公元七至八世紀之間。(4)Chutiwongs,Nandana,and Denise Patry Leidy Chutiwongs,Nandana,and Denise Patry Leidy.Buddha of the Future:An Early Maitreya from Thailand. New York:Asia Society Galleries,1994. p. 49,plate 26.這說明在印度和中國航路之間,南海諸地在中國唐代期間盛行供奉不空罥索觀音,確實不是陌生的歷史記憶,而且是盛行在鑒真渡海傳教日本之前。在印度尼西亞現在的國土上,由南中國海以南的爪哇群島,到馬六甲海峽西岸通往印度的蘇門答臘,目前能追溯到最早期的不空罥索觀音圣像,幾乎也都是公元七、八世紀之間的遺存,其造型多是手結諸種手印或執拿各種法器,與密教不空罥索觀音信仰流傳唐代中國的時間相近。這似乎還可以說明,在相同時期,唐代出海求法的僧人或當時入唐弘法的天竺僧人,是熟悉這種觀音造型的。
可是,隨著觀音信仰在中國深入傳播,中國本土出現越來越多菩薩應化和顯圣的傳說,如《法華經》等經典又說觀音的方便應化能隨處祈求隨處應,從而助長了菩薩在中國擁有應化道場的理論根據。至遲到了12 世紀,中國本土終于出現結合了“浙江普陀山”“南海”“觀音”三大關鍵概念的說法,中國信眾對觀音修行道場的認識也終于起了極大變化。漢傳佛教不一定需要改變經典上關于觀音道場的說法,還是得承認經上說的補旦洛迦山本在印度南部海濱,但同一段梵文翻譯成“普陀”兩字,看來會比“補旦洛迦”的讀音更讓漢地信眾熟悉;漢傳信眾更普遍相信浙江普陀山是觀音本身的修行道場,甚至有以為經上說的“補旦洛迦山”也是指浙江的普陀山,以至在中國稱呼“南海觀音”。
正如漢傳佛教界歷史以來普遍流傳的說法,浙東佛教早在唐代已經出現《法華》經系的傳承,當然也流傳著本經的《觀音普門品》,而其中鑒真和尚極為出名,是由于他曾因風浪阻攔,客留在天臺、阿育王寺弘教。以后日本平安朝遣唐僧最澄泛海到天臺山求法,則是日本天臺密教的源起。普陀山觀音之盛,則要等到另一日本僧人惠萼于五代后梁貞明二年(916 年)自五臺山請到觀音像。惠萼取道明州港出海回日本受到風勢阻攔,于是在普陀山觀音洞前的紫竹林建“不肯去觀音院”,方是浙東普陀山觀音道場的真正創始。但是,自隋唐以來,漢地大眾所指稱的“南海”畢竟不是以印度地理為主位,而是按照中國出海的地理位置,認為這是從中國海邊往南方以及西南方航行的遠洋海域。
關于浙江普陀山作為觀音道場的緣起,宗教界和學術界已有太多探討,在此不繼續重復。不過,這里得補充一點,佛教在12 世紀以后并不是極短期間在印度驟然失去蹤影,而是經過長期逐漸消亡的過程。而且,如《梁書》所載,中國之前的海上強鄰狼牙修自梁代已經是佛國,曾經遣使朝覲梁武帝,奉表時稱譽武帝“供養三寶”(5)[唐]姚察、姚思廉:《梁書》卷五十四《狼牙修國傳》。原文有說:“狼牙修(Lankasuka)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士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筏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發以吉貝為于縵。其王及貴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磚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又載:“……天監十四年(五一五)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眾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耀亦如月光,諸天善神所供養,以供正法,寶梵行眾僧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陀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于一切國,為極尊盛,天王愍念群生,人民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凈,正法化冶,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榮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忝承先業,慶喜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愿大家曲垂領納。’”,一直到15 世紀,南海諸國雖說此起彼落,也還是佛教勢力旺強之地,在東南亞出土的觀音像,許多正是12 世紀到15 世紀的產物。如此,談到觀音信仰,就不能忽略,中國觀音信仰原來指稱的“南海”,它的海水包圍過許多大小國家和地區;其原型其實不是浙江紫竹林前邊的一小片山水,而是從明州港南下,包括從今日南中國海到孟加拉灣以南諸處海域的大海洋世界。
回歸《華嚴經》第六十八卷原文,瑟鞞胝羅居士告訴善財童子觀音道場所在,其實是以他本人會見善財童子的地方作為地標,由居士告知童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補怛洛迦,彼有菩薩觀自在”,經中并頌揚說:“海上有山眾寶成,圣賢所聚集清靜。”(6)[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十八,《大正藏》第10冊,第366頁。此段經文真是傳自印度,當然也是以印度本土為主位,經中雖未明言觀音神圣道場本在印度本土的“南海”,但已經是說明補怛洛迦山原來的地理位置。至于玄奘的記載,則可視為作者以本身親歷耳聞印證《華嚴經》說法,證明觀音在印度的道場位近南亞大陸西邊接近印度向南航行的海邊口岸。
佛經中的觀音修行道場原本是位處于印度通往南海的出口,它后來會演變成中國東海舟山群島的位置,想來也很有意思。舟山群島雖然位處東海,卻是中國通向南海的門戶之一,因此,浙東普陀山圣跡的出現,其實就是中國信徒在浙東形成觀音在東亞的新興國際道場的同時,也在海上航路兩端的終站之間越洋移植“圣地”,把南海旅人在漢地上岸的其中一個終點代替印度原來的圣地。(7)當代學者根據玄奘和《華嚴經》的記載,認為根據印度原來的說法考據,補怛洛迦山的位置當在目前印度西高止山南段的巴波那桑山,屬北緯8度43分,東經77度22分;見[唐]玄奘述,辯機撰,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62頁。當然,根據這樣的說法是容易把巴波那桑山的存在視為尋找到“神話地點”的原型,反而可能忽視宗教感應的經驗是可以超越出現實中的三度空間世界。
屢現圣跡的說法,正好反映觀音信仰后來由印度而漢地的因緣成熟,以至隨著印度佛教沒落,真有普陀(補怛洛迦)東移之勢。(8)關于普陀山觀音顯圣的諸種說法,可參考煮云法師:《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新加坡:柯華印務公司再版,1981年。本書原是法師在1953年的結集,原文來自他為佛刊《菩提樹》逐期撰寫的文章,后來曾經過多次再版,補敘。這本書在不同時期的版本曾經流傳各地,一再被中國港臺地區以至新馬兩國的各地佛教組織和善信翻印傳閱,視為贈送給公眾人士的弘法善書。正如書名,其時對“南海”的印象已經出現聯系本土地理觀念“南海普陀山”,成為主要定格在眼前中國海門的海域觀。相反地,回到中國歷史上對于“南海”的固有概念,也可以發現中國國內一些說法有待商榷;企圖從普陀山本身地理位置解說“南海觀音”,正好是忽略了“南海”長期以來的通用指稱。(9)如互聯網上即互相輾轉轉載說法,即說,由于中國歷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來,慣稱此山為“南海普陀”。
中國東海出往南海的浙江舟山群島,被視為菩薩道場,在某種程度上足以反映中國古代民間很普遍的認識——從“南海”到“觀音”再到“南海觀音”,早就是很中華的本土概念。但這不影響漢傳佛教認同南海凈土可以同時在人間多處顯跡。
海陸絲路的觀音印象
關于佛教何時傳入漢地的討論,現代人從文字上尋求信史為據,多是根據《后漢書》的說法,認為是在漢明帝時代。在《后漢書?光武十王列傳》說及漢光武帝的兒子、明帝異母弟劉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10)[劉宋]范曄、[唐]李賢等注:《后漢書》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傳》。由此可證明,在當時,佛教已經傳播到漢王朝的上層社會。到永平八年(65),明帝曾下詔說,凡死罪者可繳縑(生絹)贖罪,楚王劉英派遣了郎中令奉獻黃縑、白絹(熟絹)三十匹向明帝謝罪;明帝認為劉英是信佛而忠誠,下詔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11)[劉宋]范曄、[唐]李賢等注:《后漢書》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傳》。“伊蒲塞”原文應念成upasaka,即“優婆塞”,指在家持戒的居士;“桑門”原文應念sramana,即僧人,后人多譯為“沙門”。這段文字提到明帝吩咐將楚王贖罪的生熟絹布賜給“伊蒲塞”和“桑門”,在中國非佛教文字的典籍之間,這是以漢文音譯天竺佛教名詞的極早例證。
可是,在同一個時代,我們還沒有發現中國典籍注意到觀音信仰。
到了三國時代,丹陽人笮融以卑鄙狡詐和崇佛佞佛聞名于史。《三國志?吳書?劉繇傳》載說,笮融聚眾數百投奔徐州牧陶謙,受任廣陵、下邳、彭城三郡運糧監督,大力搜刮民財獲利,“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涂身,衣以錦采,垂銅只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課讀佛經。……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于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12)[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四十九《吳書四·劉繇傳》。這里且不討論笮融的人格問題。單就當時的社會現象而論,其時的笮融可以利用佛教名義標榜招搖和收攬人心,而2世紀末葉的中國寺院也已有能力供奉鍍金銅佛,辦的浴佛會和齋會又是參與者眾,后人即使僅據這段短短的文字,也可以理解后漢以降佛教日盛。從《三國志》所敘的盛況也可估計,當時的漢地大乘佛教內部很可能已掀開觀音信仰進入中國的序幕。
從印度佛教歷史看,觀音信仰在印度興盛是在同一時期。當代學者之間,值得注意的是Chutiwongs的說法,她以中國譯經史上最早的《無量壽經》是在公元148 年到170 年之間譯出,說明觀音信仰中屬于彌陀凈土思想的部分更早在印度興盛,其考證亦一再引用中國材料反證觀音信仰出現在印度的因緣。(13)Chutiwongs,Nandana.The Iconography of Avalokiteshvara in Mainland South East Asia. Ph. D. diss.,University of Leiden,1984. pp. 20-21.另外,Chutiwongs 亦發現在印度的犍陀羅(Gandhara)和秣菟羅(Mathura)地區,一二世紀觀音造像擁有多樣風格。這些貴霜時代結束以前的觀音像,其中不少頂上并沒有彌陀化佛,似乎說明救苦救難的觀音信仰,早期不一定都要結合彌陀凈土的信仰思想體系。(14)Chutiwongs,Nandana.The Iconography of Avalokiteshvara in Mainland South East Asia. Ph. D. diss.,University of Leiden,1984. pp. 26-28.到法顯在公元5 世紀訪問當地,他猶以“摩頭羅國”之譯稱記載秣菟羅當地的大乘信仰,說“摩訶衍人則供養般若婆羅密、文殊師利、觀世音等”。(15)[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4-55頁。法顯在看到人們同時供養般若經論、文殊和觀音菩薩之際,文中并沒有記載西方彌陀信仰。
Chutiwongs 提出中國在2 世紀出現《無量壽經》漢文譯本,相同說法最早源自唐朝智昇的記載。來自安息國的安世高是最早在中國譯經弘法的外來僧人,他于漢桓帝建和二年(148)到達洛陽,以后翻譯的多為小乘經典,其譯文“或以口解,或以文傳”,多達數百萬言。(16)[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據智昇在《開元釋教錄》卷十四記載,安世高也曾譯過《無量壽經》二卷,可是譯本在古代早已亡佚。(17)[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四,《大正藏》第55冊,第626頁下。但實際上,至今流傳的漢文佛經之間,譯于公元2 世紀而出現“觀音”名稱的,最早應該是支曜在漢靈帝中平年間(184-189 年)翻譯的《成具光明經》,其經文說:“明士及上諸天應當成者及當發者,凡八百億萬人皆飛來至佛所”、“次復名觀音,如是眾名各各別異”,“觀音”在眾多被提及名字的“明士”之間奉陪末座。(18)[后漢]支曜譯:《成具光明定意經》,《大正藏》第15冊,第451頁下。《成具光明經》或另名作《成具光明定意經》。這部經可能譯的年代早,后來其他佛經習慣按音譯簡譯“菩提薩埵”(Bodhisattva)為“菩薩”,但本經卻是按梵文詞意一律譯為“明士”,足見“觀音明士”即是“觀音菩薩”。只是,觀音在這部經典所屬的修行系統雖說有地位,并不見得是主尊。
另外,比安世高稍后的支婁迦讖,來自月氏,他于漢桓帝末年(167)到達中國,在漢靈帝光和、中平(178-189)年間譯了不少大乘經典。(19)呂澂:《中國佛教源流略講》,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288頁。《佛說無量清凈平等覺經》據說也是來自支婁迦讖的譯筆,其卷三有曰:“佛言:無量清凈佛,至其然后般泥洹者,其廅樓亙菩薩。便當作佛總領道智典主教授。世間八方上下。所過度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皆令得佛泥洹之道。”(20)[后漢]支婁迦讖譯:《佛說無量清凈平等覺經》,《大正藏》第12冊,第291頁上。根據其他的凈土經文互考,“廅樓亙”肯定是音譯觀音梵名Avalokitesvara。不過,日本的鐮田茂雄在《中國佛教通史》即主張這部經典并非出于支婁迦讖的譯筆。(21)[日]鐮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年,第156頁。因此,在持著否定態度的學者之間,《佛說無量清凈平等覺經》既然并非支婁迦讖所譯,當然不能作證觀音信仰在公元2 世紀傳播中國。
眾多中國文字之間,東晉法顯在自述中極早提及修持觀音名號,并且作了信仰實踐的見證。據《法顯傳》,法顯在獅子國出發回華,原本是上了一艘上邊可乘200 余人的大船,后邊又準備了預防大船毀壞的接應小船。不料,出海諸人在東下兩日之后便遇到大風,原本商人都要下小船,但小船上的人恐怕大船下來的人多,即斫縆斷。法顯記錄當時情景:“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滿。即取粗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君墀及澡罐并余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眾僧:‘我遠行求法,愿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后見船漏處即補塞之。”(22)[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第167頁。
《法顯傳》又記述,眾人是在海上漂泊歷險90 多日,方才到達耶婆提國。(23)[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第167頁。于是,法顯便在耶婆提國停駐了五個月,之后再跟隨另一批商人乘坐一艘也是載了200 余人的大船回華。據法顯載,船上原本準備了50 天的糧開往廣州,可是“一月余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于是又得再念菩薩保佑:“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眾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24)[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第171頁。到后來,因連日天陰,舵師出錯,大船在海上延長超過20 余日仍然找不到方向靠岸,眾人是再花了12 天向西北尋找陸岸,一直航行到青州長廣郡方才安全上岸。(25)[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第173頁。
在《法顯傳》里的觀音,顯然是法顯心目中聞聲救苦的菩薩,所以他在危難時專心持念的是這位菩薩的名號,而不是其他的佛菩薩或者諸天神祗。東晉到宋元之間,曾有許多來往中國、日本、印度等地的僧侶為了傳法、求法來往海上;許多商人也依靠在南海各處航行貿易謀生。在法顯的傳記中記載“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26)[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第171頁。,可見當年耶婆提與廣州之間常有同類船只往來,商人原來就熟悉把握航程時間。而法顯在危急時求助于觀音,很明顯亦是源于他人的經驗和教導。
法顯的經歷,不是罕見的,只不過是他活下來了,也把遇險的過程記錄下來。法顯當時在上岸后還曾經向山東青州官民作過見證,后來閱讀其文字的人們,也會向他人轉述菩薩如何靈驗。傳中既然說“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聞有沙門持經像乘船泛海而至,即將人從來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27)[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第173頁。,相信這位太守也會從法顯的敘述理解到持念觀音名號可以救苦救難。只不過,法顯會持念菩薩名號、祈求觀音救難,到底是本來學自中土,抑或是到了西域之后方才受到當地感召,其傳記中未有說明。
必須明白,昔日南海航路上持念觀音名號的僧人,不僅法顯一人,更不一定是漢族。在公元5 世紀前后,祈求觀音在海上聞聲救難的法門似乎已流傳于來往南海的商人和船員之間,也依靠外地僧侶傳播到中土漢地。例如,在《高僧傳》的描繪中,就有一位天竺人僧人“求那跋陀羅”是“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泛海”(28)[梁]釋慧皎撰:《高僧傳》卷三《求那跋陀羅》,《大正藏》第50冊,第334頁上。,靠著觀音佑護,在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取道南海而到達廣州。《高僧傳》記載求那跋陀羅的事跡說:“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咒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云降雨。一舶蒙濟。”(29)[梁]釋慧皎撰:《高僧傳》卷三《求那跋陀羅》,《大正藏》第50冊,第334頁上。以當時的情況,求那跋陀羅所乘的船半途遇到海上無風,船既不能航行,也因此而不夠食水,如果他祈雨不靈,全船人都可能活活渴死。
《高僧傳》還提到說,求那跋陀羅到達中國以后還是專心菩薩名號,結果留下一段傳奇的事跡:“梁山之敗,大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邛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后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余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30)[梁]釋慧皎撰:《高僧傳》卷三《求那跋陀羅》,《大正藏》第50冊,第334頁中。這在信仰者來說,確實是觀音拯救信徒于水難的證據。
由法顯而求那跋陀羅,正當中國東晉至南北朝,可見那時觀音信仰已經盛行南海諸國,被視為有求必應、靈驗殊勝,來往路客在取經和弘法的旅途上屢受危難,都是依靠專心持念觀音名號,祈求化險為夷。與此相應,南海諸國各地區考古一再發現的菩薩像,多是5 世紀以后的觀音像為主。(31)Jacq-Hergoualc’h,Michel.The Malay Peninsula:Crossroad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100BC-1300AD)(Hobson,Victoria,Trans.).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2.pp.301-337.
以馬來西亞來說,霹靂州和豐(Sungai Siput,Perak)出土的四臂觀音立像和八臂觀音立像,以及1936年在霹靂州美羅(Bidor,Perak)掘到的八臂觀音,都是印度大乘佛教影響東南亞的證據。(32)Devahuti,D.India and ancient Malaya(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circa A. D.1400). Singapore:Published by D. Moore for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1965. pp. 125-126.重要的是這些菩薩像和佛像有很大的差別:佛像都是寫實的人像,而菩薩像則都是夸張地呈現多臂甚至多頭的姿態,各手上又持著不同的物件或結起不同的手印。這反映了人們祈求菩薩聞聲救苦的需要極多,而且需要也各有不同,人們希望觀音隨時伸出不同性質的援手。
南海諸邦的經典實踐
回到經典發現,觀音在世間救苦救難的詳情細節,其實集中在《法華經?普門品》的信仰陳述。它最早走向漢文讀者,有賴于西晉竺法護的翻譯。竺法護所譯出的版本取名《正法華經》,其中有《光世音普門品第二十三》稱“適聞菩薩名者,輒得解脫……光光若斯,故號光世音”。(33)[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十〈光世音普門品第二十三〉,《大正藏》第9冊,第128頁下-129頁上。此外,竺法護在翻譯其他經典時,也一概使用“光世音”名號。
不過,目前較通行的《妙法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的譯本。根據鳩摩羅什所譯,觀音的救苦救難形象極為突出:“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若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求金銀、琉璃、車磲、瑪瑙、珊瑚、虎珀、真珠等寶,入于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剎之難。”(34)[后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七,《大正藏》第9冊,第56頁下。觀音以是因緣名觀世音,菩薩靈驗確實最能符合海上商旅靠天吃飯、望天求生的愿望。
《普門品》接下去說,觀音亦能拯救人們于人為災害:“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剎,欲來惱人,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設復有人,若有罪、若無罪,杻械枷鎖,檢系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赍持重寶經過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于眾生。汝等,若稱名者,于此怨賊當得解脫。”(35)[后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七,《大正藏》第9冊,第56頁下。從天竺入南海而往中國,正如從中國入南海而往天竺,途中可以是長年累月,也不知會經過多少地方、遇上多少災病、盜賊和王難,《普門品》的這段內容亦是從信仰上保障人們長期跋涉的勇氣。
由法顯的經歷可知,漢譯《普門品》出現以前,其說法至遲在東晉已經廣泛流傳于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海域。法顯之前,海上已經流傳了祈求觀音保護海上安寧的法門,以后并且有法顯本身在漢地傳頌的見證。等到《普門品》的漢譯出現,它就不僅是流傳于天竺和南海的大乘信眾之間,而是更為漢地佛教徒所熟悉了。
再檢視Chutiwongs 對于公元一二世紀觀音信仰形態的說明,她是以觀音造像頂上沒有化佛為根據,認為早期的觀音信仰并不一定是附屬于凈土往生思想或者密教行為,以救難為主的觀音信仰和后兩者也沒有必然的密切聯系。(36)Chutiwongs,Nandana.The Iconography of Avalokiteshvara in Mainland South East Asia. Ph. D. diss.,University of Leiden,1984. pp. 26-28.可是,若從爪哇和馬來西亞兩地的出土菩薩造像去思考,當地在7 世紀之后出現的觀音菩薩造像,很多都在頂上裝飾有化佛。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當年曾經有中國-印度航線在南海中途站,在學者的考證中,法顯所到的“耶婆提”若不在蘇門答臘便是在爪哇;(37)[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第170頁。而今日屬于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的地區,也曾是義凈和玄奘等唐代僧人海上求法必經之地,是唐代同期的南海佛國“室利佛逝”勢力所到的范圍。也不能否定,到了印度佛教在南海航道上傳播最盛的時代,彌陀信仰也曾經盛行一時。
在漢文版本的佛典之中,劉宋朝疆良耶舍譯的《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有說觀音“頂上毗楞伽摩尼妙寶以為天冠,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38)[劉宋]疆良耶舍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大正藏》第12冊,第343頁下。化佛,是凈土信仰系統對于觀音造像的區別特征。南海諸國出現天冠上擁有化佛的觀音造像,雖說其頂上化佛坐立不一,但也足于說明當時南海地區盛行過彌陀信仰,因此才會流傳表達觀音作為彌陀脅侍的造像特征。
若翻查在華的古籍,南海流行彌陀信仰,亦有文獻可證。義凈的《大唐求法高僧傳》便記載有僧人常愍師徒兩人,在南海海難中舍己為人,唱誦彌陀而歿。《大唐求法高僧傳》載說,法師和弟子原本是附隨商船往中天竺,可是船載貨過重而沉沒:“當沒之時,商人爭上小舶互相戰斗。其舶主既有信心,高聲唱言:‘師來上舶’。常愍曰:‘可載余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輕生為物順菩提心。亡己濟人,斯大士行。’于是合掌西方稱彌陀佛。念念之頃舶沉身沒。聲盡而終。春秋五十余矣。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許人也,號啕悲泣,亦念西方與之俱沒。”(39)[唐]義凈:《大唐求法高僧傳》,《大正藏》第51冊,第3頁上。
常愍在海難中舍己為人、但求往生,畢竟是較少的特例。以早期南海航程的兇險考慮當地觀音信仰的基礎,不論是依照《法華經》說的觀音隨處現身在塵世救難,或者是依附凈土思想的觀音信仰,其實都符合海商的需要。以馬來西亞霹靂州美羅(Bidor,Perak)1936 年出土的觀音像來說,這尊斷了一只右手的菩薩像目前陳設在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它的造型正是下身圍獸皮、頂上有化佛,其四只左手分別握有經籍、罥索、凈瓶和蓮花,余下三只右手,兩只分別握著念珠和三棱杵,一手結施無畏印。這說明它有著不空罥索觀音的模樣,既是接引死者往生阿彌陀佛世界的觀音,又是以多臂應付心中各種祈求的救難觀音。觀音在現實中兼顧海陸眾生,隨時救苦救難,也照顧遇難者直到無可避免之刻,在未可知的死亡世界接迎往生,兼顧度生與救亡的菩薩角色,構成觀音信仰在海洋社會盛行的條件。
更進一步說,自隋唐以來,中國本土翻譯出不少屬于不空罥索觀音系統的漢文經典,這一個時代,這些經典許多是從南海的海上絲綢之路帶來。而自隋唐以降的南海地區觀音信仰形態,除了繼續是救難與度亡的慈悲,更可能是讓不空罥索觀音信仰走向主流。
以菩薩造型分類,上述1936 年出土于馬來西亞美羅(Bidor)的觀音,既然已示手握不空罥索的特征,當然是“不空罥索菩薩”(Amogha-pasa)。這一造型,在密宗以像說教的義理,是象征人們凡有世間所求必有所得而不落空,也象征鉤取人們出離世間前往解脫彼岸。如此造型,無疑亦能符合海陸商旅跋涉各國的祈求,但愿菩薩保佑水陸平安、不遭王難,生意有成。進一步說,這尊不空罥索觀音現出矯健男兒身,赤裸上身、腰間披掛著獸皮,既是表達出印度佛教史正統的、經典的各種觀音原型常見特征,又反映出印度觀音信仰以至佛教信仰自隋唐以來愈加的民間化與密教化,同樣的菩薩造型也出現在當時猶屬佛教文化區域的馬來半島。
而印度尼西亞雅加答國立博物館收藏的1286 年造八臂不空罥索觀音立像,基座雕刻的古馬來文和梵文文字敘述菩薩圣像由來,據說是爪哇王維斯瓦如帕庫馬拉(Javanese King Visvarūpakumāra)以宗主國身份送給當時蘇門答臘王朝(Sumatran kingdom)的禮物。(40)Soebadio,H. ed.Pusaka:Art of Indonesia. Singapore:Archipelago Press,1997. p 71.文中說,爪哇新柯沙里(Singhasari)國王Kertanegara 贈送圣像給蘇門答臘的末羅瑜國(Melayu,《元史》作“麻里予兒”)國王Tribhuwanaraja,祝愿送像的功德能護持bumi Melayu(末羅瑜土地),使這片土地上的一眾君民皆歡喜贊嘆。這位Kertanegara,即是新柯沙里王朝最后的國王,他沒有兒子,自認本身具備的轉輪圣王地位是以瑪哈噶拉(大黑天)作為修行的本尊,在一項密乘儀式的聚會上與一眾朝臣被叛臣殺害。1293 年,他的女婿Raden Wijaya 聯合了元朝忽必烈派遣南下的海軍擊潰叛臣,為岳父報仇,較后又突襲驅走元軍,成為爪哇人的民族英雄,建立滿者伯夷王朝,從此繼承了新柯沙里王朝控制從爪哇到蘇門答臘水域的國家法統。
同一座不空罥索觀音雕塑背面,后來又添加了蘇門答臘米南家保(Minangkabau)王朝創國遠祖Ad?ityawarman 在1347 年增刻上去的文字。Adityawarman 當年是受命于自己的表姐妹,即滿者伯夷王朝(Majapahit,《元史》作“麻偌巴歇”)的女主,帶軍征服蘇門答臘與鄰近各個原來隸屬三佛齊王朝的屬國,建立侯國,并把王都所在之整片地域命名為馬來亞都城(Malayapura)。他征服當地后,將圣像保留供奉,在原有雕刻以外再添加背面文字,是為了要宣說,自己是以不空罥索菩薩作為護持本尊,也說明本身是以修行菩薩相應替身的因緣,成為統治地區所有人民的福利庇護者。
可見,有好幾個世紀,南海諸國長期流傳著侍奉不空罥索菩薩的觀音信仰形態,其中屢有統治者本身修學不空罥索觀音本尊法,甚至把菩薩視為邦國的保護者。
相應于這段時期,中國正值隋唐兩代,此時中國本土已經出現了一部又一部屬于密教傳承的漢譯不空罥索觀音經典。這其中,唐顯慶四年(659)五月,玄奘于慈恩寺翻譯的《不空罥索神咒心經》文中有說不空罥索觀音的造像“似大自在天”,是在補陀洛迦山上說法。以后,比玄奘較遲出國求經的義凈法師,在公元672 年到過末羅瑜國,當時南海是義凈學法和譯經的圣地。義凈指說:“南海諸州,咸多敬信人,王國主崇福為懷……若有唐僧欲向西方為聽讀者,停斯一二載,習其法式方進中天亦是佳也。”(41)[唐]義凈自注:《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大正藏》第24冊,第477頁下。可見這個宣稱是依靠著不空罥索菩薩護持的南海邦國,當時還是唐代僧侶來來往往的落腳地。
按印度教的信仰,摩酰首羅天(Mahes/vara)或即大自在天是三千界之主,故多供奉在山上,以腰圍獸皮形象造神,其教徒則被佛教稱為“涂灰外道”。到今日還可看到崇奉大自在天的印度教徒在額上涂灰,其祭祀人員赤裸上身主持上供。據密教系統的《不空罥索咒經》,“不空罥索觀音菩薩”其實是采取大自在天的形象:“狀如摩酰首羅天,頭上發悉如螯髻,方作華冠,肩上當畫作黑鹿皮覆在左肩上。”(42)[隋]阇那崛多譯:《不空罥索咒經》,《大正藏》第20冊,第402頁上。由此可見密教化的印度佛教信仰與印度教之間的交流。今天看來,稱呼不空罥索觀音為“圣觀自在菩薩”,或總稱不空罥索觀音密法為“自在王咒”(43)[唐]寶思惟譯:《不空罥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大正藏》第20冊,第421頁中-432頁上。,俱因受到一系列不空罥索觀音經典的影響。
但《不空罥索咒經》說觀音形象義理,不只來自不空罥索菩薩的信仰因緣。它在大乘佛教早有所本,其實也源出于唐譯《四十華嚴》的偈誦文有說觀音的形象“伊尼鹿皮作下裙……眾寶所集如山王”。(44)[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六,《大正藏》第10冊,第735頁上。而且,也正是隋代的阇那崛多于開皇七年(587)五月譯出的第一本漢文《不空罥索咒經》(45)[唐]智升撰:《開元釋教錄》卷七,《大正藏》第55冊,第548頁下。,里頭說明不空罥索觀音是“在逋多羅山頂觀音宮殿所居之處”(46)[唐]義凈自注:《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大正藏》第24冊,第399頁上。,即唐代玄奘同經異譯《不空罥索神咒心經》所指的“布怛洛迦”(47)[唐]玄奘譯:《不空罥索神咒心經》,《大正藏》第20冊,第402頁中。。由此才能確定布怛洛迦山上的圣尊,不是原來印度諸教教義或佛教本身所謂的“大自在天王”,而是應化為不空罥索菩薩的觀音形象,即是玄奘堅持翻譯時尊稱為“觀自在菩薩”的那位。
一旦讀到玄奘《大唐西域記》說布怛洛迦所在的秣羅矩吒國“伽藍故基,實多余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數百,外道甚眾,多露形之徒”(48)[唐]玄奘述,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十,《大正藏》第51冊,第931頁下。,又讀到玄奘說“山下居人祈心請見觀音”,是“或作自在天形,或為涂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愿”(49)[唐]玄奘述,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十,《大正藏》第51冊,第932頁上。,閱讀者當注意到其時當地民間“觀自在”形象的主流印象;也可當知到了唐代,在印度本土傳聞的觀音修行道場原地,人民對于觀音認識已有所演變,布怛洛迦山周遭都在經歷外道興起、佛教消退的過程。而此時南海諸國的觀音信仰,也同樣受到印度布怛洛迦山下的影響:供奉的觀音既是頂上有彌陀化佛,又是回應著外道民眾日常以“自在天形”祈請菩薩保佑,菩薩也就同樣會以大自在天形象出現,亦即不空罥索菩薩的標準形象。這種信仰,是符合法華經系俗世救難的說法,也是符合彌陀經系度亡需要,它也是應機和印度教融合的,是密教的,也是民間的。
如此抑或可考慮,玄奘在《大唐西域記》說“即縛盧枳多譯曰觀,使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為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謬也”(50)[唐]玄奘述,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十,《大正藏》第51冊,第883頁中。,不僅由于他對梵文的掌握與推敲,也可能源自他對印度觀音圣地的實地印象。在梵文,Avalokita(阿縛盧枳多)義為“觀”,稱“聲音”為svara(濕伐羅),后者至今為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地土著語言沿用;而玄奘則根據isvara(伊濕伐羅)原意“自在”,以及梵文口語會把“t”和“i”的連音讀成e,認為菩薩梵名后邊的“esvara”發音本應是“isvara”,即“自在”。法師當年處身印度,親身聽聞布怛洛迦山的印象,也許會讓他更堅持Avalokitesvara 應翻譯為“觀自在”,而非翻譯為“應聲”含義的“觀世音”。
最重要的是,后人翻閱唐代譯出的《不空罥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經上記載了種種密法,有涉及修行的,也有涉及世間福利的,其中有調伏諸龍的密法,即是以亞熱帶或熱帶農業風情作為背景,對南海諸國從統治者到人民,是頗有針對性的吸引力。《不空罥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是說,若有國土旱澇不調,相應的密法能使諸龍下甘雨,“一切苗稼甘蔗稻谷悉皆成熟,又能令彼多諸水牛,彼國眾生因之耕植;由此遠離饑饉、疫病、斗戰、諍論,復無賊盜及以惡獸,衣食豐足,安穩快樂,一切人民皆行善事。”(51)[隋]阇那崛多譯:《不空罥索咒經》,《大正藏》第20冊,第430頁中。這正說明“南海”的觀音,確有應對著南海地理氣候的特征,保護著今天屬于泛馬來文化圈的黎民百姓。
苦海的慈航變相
從“南海觀音”的歷史看南海,唐宋以前的“南海”,比起后來人們單憑宗教文字根據浙東普陀山想象的南海,更有大氣魄。它是中國的,也是國際的,海上經常來往著乘客達200 余人的大船,人們不分種族在海上同舟共濟,也共同崇拜和呼喚著一位隨處祈求隨處現的觀音大士,他管海上的平安,也管陸上的幸福,不分國度也不分族別的聞聲救苦,既拯救生靈也度脫亡者。這就是大慈大悲,相應其大愿的情景,是眾生終能離苦得樂,得大自在。
而到了唐代,根據當時翻譯的系列不空罥索觀音經典,這一形象流播于南海諸國朝野之間觀音信仰形態,按其經典的說法,已經是很具體地表現為兼顧水陸眾生的大菩薩,擁有從護國佑民、保護舟車到回應個人要求的各種感應,讓人感覺菩薩神通照料的范圍真是無邊無際。
現在的馬來西亞,西馬的原來地理區域本來就叫馬來亞半島(Malaya Peninsular)。而回顧古金剛乘的信仰印象,“摩賴耶”(Malaya)原本亦意味著不空罥索菩薩諸經典的早期傳播地區。印度經典最早提到Malaya(馬來亞),是成書于公元4 世紀前到1 世紀之間印度《大史頌》(Maha Bharata),其地點原是印度南部西海岸的一座山脈,中國典籍一般翻譯為“摩賴耶”;到了玄奘法師《大唐西域記》卷十八,又把“摩賴耶”山翻譯為“秣剌耶”,說它產檀香和龍腦。(52)許云樵:《馬來亞的來歷》,載許云樵輯:《馬來亞研究講座》,新加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1961年,第2-3頁。稍后,《高僧傳》的《釋跋日羅菩提傳》提到了這位在中國傳密宗的祖師華名“金剛智”,說他是“南印度摩賴耶國人,華言光明,其國境近觀音宮殿補陀洛迦山”。(53)[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一《釋跋日羅菩提傳》,《大正藏》第50冊,第711頁中。可見,南印度“摩賴耶”國和境中的“補陀洛迦山”,是聯系著的一組地理概念。但是,早在公元5世紀的《風天往世書》(Vayu Purana),摩賴耶洲(Malayadvipa)的地名已經是古印度人眼中的印度南部六大洲之一,屬于“海外”,成為印度文化發展在印度洋以外的一種表現,即是遷徙的民眾以故鄉的原名去形容和命名所到達的新土地。(54)許云樵:《馬來亞的來歷》,載許云樵輯:《馬來亞研究講座》,第3-4頁。如此看來,唐朝玄奘翻譯的《不空罥索神咒心經》提到那位采取自在天形象的觀自在菩薩往來游舍于補陀洛迦山,和Kertanegara 到Adityawarman 數代人先后強調不空罥索菩薩對末羅瑜(Malayu)國的護持,是互有思想上的因緣,顯露金剛乘信仰用詞和印度地方名稱在印度洋以外傳播的痕跡,說明印度佛教文化曾經屢屢受到往昔南海諸國各地方上“復制”,或重構成為當地的本土信仰。根據佛教在南海的歷史,可以追溯南海土地上延續著“Malaya”命名的原初涵義與文化淵源。
尚且不能否認,隨著唐宋兩代造船與航海技術的發展,從印度、南海到中華,密教化的觀音影響,是借助著唐代海上交通促進音訊交流,為古代南海觀音信仰傳播提供新的推力。最佳例子是正當唐代漢傳佛教各宗派紛紛開宗立說的盛況時,唐玄宗時期將密宗從外國傳入中土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開元三大士”,其中金剛智與不空師徒于開元七年(719)第一次泛海到廣州,據唐朝呂向撰寫《金剛智行記》所說,是受到觀音化現指示,到中國找文殊菩薩,所以金剛智在南天竺啟程向中國出發時,才要“向東禮文殊,西禮觀世音菩薩”。(55)[唐]呂向:《金剛智行記》,[唐]釋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正藏》第55冊,第875頁上。可是,金剛智師徒到達廣州之前,顯然經歷了在南海諸國傳教說法的過程,“計海程十余萬里,逐波泛浪,約以三年,緣歷異國種種艱辛,方始得至大唐圣境”(56)[唐]呂向:《金剛智行記》,[唐]釋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正藏》第55冊,第875頁上。,也廣為海路上來往商旅知悉敬重,所以才會發生“行至廣府,重遭暴雨,時節度使使二三千人乘小船數百只,并以香花、音樂海口遠迎。”(57)[唐]呂向:《金剛智行記》,[唐]釋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正藏》第55冊,第875頁上。現在漢傳佛教普遍流行的《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咒本一卷》,當年就署名“大唐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大弘教三藏沙門金剛智奉詔譯”。唐代以來,隨著各種增譯或另譯的觀音經典出現,進一步建構成漢傳觀音認識的整體來源。
某些時候,南海傳來的觀音經典很可能因宗派傳承差別,導致重新翻譯的需要。例如,北天竺僧人般刺若,在德宗建中初,即780 年或781 年扺達廣州,貞元二始屆京師:到四年以后的八月,千福寺講論大德沙門智柔,向朝廷進呈般刺若重譯心經一卷,奉敕云:“般若心經,大乘秘旨。頃者玄奘翻譯,字義已周;其于首從,或未詳備,近因罽賓僧般若來至中華,傳此遺文,足相翼贊。”(58)[唐]釋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正藏》第55冊,第894頁上。
正緣于佛教《法華普門品》提到觀音有“三十三化身”,諸經也多有提及觀音化身無數尋聲救苦,乃至漢傳佛教有“千江有水千江月,隨處祈求隨處現”之說,密宗更延續觀音與其圣境可以隨眾生緣分化現,提出以觀音作為修持佛法之本尊,亦可在契合菩薩相通境界,將周圍實現為觀音之凈土. 于是印度到蘇門答臘都出現名為“末羅瑜”的地理環境,抑或中土“普陀”或吐蕃“布達拉”都是當地語言翻譯“補陀洛迦”,也都不奇怪了,更能反映其信仰傳播歷時悠久、涉及的地理范圍跨山過海。
然而,如按照唐代菩提留志譯《不空罥索神變真言經》,觀世音菩薩頂禮白佛,說起菩薩本身在過去劫中曾獲世間自在王如來傳授“不空罥索心王母陀羅尼”,談到持誦陀羅尼的功德和各種修法,就有提到其護摩增益法可以“復得除滅一切災疫、饑饉、猛獸、他兵謀叛、大臣謀叛、一切斗諍諸惡鬼神;國土豐稔,雨澤順時,滋生一切苗稼花果;大小諸樹、根莖枝葉、藥草等類,皆令茂盛滋味繁多。人民快樂多饒財寶,無諸殃咎而作侵惱,更相贊詠恩愛相向,當知國中不為諸惡天龍鬼神而作災害”;(59)[唐]菩提留志譯:《不空“復得除滅一切災疫、饑饉、猛獸、他兵謀叛、大臣謀叛、一切斗諍諸惡鬼神;國土豐稔,雨索神變真言經”》卷七,《大正藏》第20冊,第264頁上。涉及這類議題的儀式,顯然不屬于平民百姓可以擅自處理的范圍。而在《佛說不空罥索陀羅尼儀軌經》,僧侶和國王請觀音護持、修本尊法,除了提及個人如何修行免災,以及如何臨命終安詳回歸西方極樂,其目標也涉及應付“國土荒亂,大臣謀叛,他兵侵毀,災疫時起”。(60)[唐]阿目佉譯:《佛說不空罥索陀羅尼儀軌經》卷下,《大正藏》第20冊,第436頁上。經典中提及的不空罥索信仰的一些作用,以及相關的儀軌,顯然就不是以個人為目標,是屬于護國保駕之儀軌,要由僧侶或王侯主其大事。
但就傳統佛教經典顯示的觀音思想,重在教導大慈大悲的實踐、大愿與大行的實現,其教義始終圍繞著“大乘”佛教重視“般若波羅密”而展開。因此,不空罥索觀音的形象流傳與經典傳播,既不遠離原來的教義而涉及許多方術,還是《法華經》所謂觀音度人的原則,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觀音即以相應化身救度。南海到中國內部,也不會有人質疑不同名稱與形象的菩薩是否都是觀音。假若依據唐代海上絲路的發達,對比隋唐期間流傳的漢譯不空罥索觀音諸種經典,或可注意,其儀軌所用物事有好些不是中原產品,如白檀木、蘇合、龍腦、白豆蔻等,(61)[唐]阿目佉譯:《佛說不空罥索陀羅尼儀軌經》卷下,《大正藏》第20冊,第438頁上-441頁上。主要都是依靠海上入口的熱帶產物。這除了說明唐代海洋交通比前代發達,足以確保漢地實踐經典內容,也反映了經典傳播對象和實踐者并非一般人家,可能涉及皇家、宗室、貴族、富賈,滿足他們涉及國祚、身家、性命的祈求。
由此或應注意,基于佛教金剛乘主張修持本尊法的影響,南海諸國的國君,如上述來自蘇門答臘的Adityawarman,都在宣稱以信仰觀音和修習觀音法門護持其統治,或宣稱修持其他佛菩薩為本尊,無形中也形成政教結合的論述,鼓吹菩薩護國的社會形態,形成明顯以宗教世界觀結合政權觀念。一方面,佛教教導是要承認世界萬物不斷經歷成住壞空,包括政治權威,一切世俗形態都是無常;另一方面,也得通過因果、信仰、轉世、本尊相應等說法,反過來解說現存王權合法與神圣。這內邊,以因果報應合理解釋財富和社會地位,認為能當上統治者肯定前世擁有大福報,沒有人可以妄議君王前世去質問統治權力。這樣來看,國王目前統治固然受到宗教公認是暫時的,強者或弱者的關系也是暫時;但是,從國君到王公大臣既然靠著前世因果得到地位,國王到大臣也就可以在現世受菩薩戒、修持密法、行菩薩道,積累更多功德福報,繼續統治地位。尤其是國君修行密法強調與本尊身口意相應或合一,又可解釋國王幾乎能以菩薩化身治理國家,具有神圣與權威,唯一擔心就是犯戒報盡。
問題就在,這種結合佛教信仰的政治觀念,以王權源于前生修好,修行人又是依靠前世因果和今世積德在權位實行菩薩道,明顯是在解釋與強化王權,解說等級制度的合理。但是,即使政權公開宣稱統治者修本尊法成為菩薩化身,國王也親自主持宗教儀式表達本身神圣,這并不等于他人會承認,也沒有辦法保證指導僧人、掌權的國王和行政官員不會陷入私欲,導致各種沖突。因此,國君宣稱自己要做觀音化身、或者宣稱自己菩薩轉世,都不見得可保王國永固。只是,雖然后來南海諸國發生了各種事態,各國逐漸去除掉僧人影響,馬來世界普遍伊斯蘭化以后還是把蘇丹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直把統治者認作擁有救世能耐的神明代言。讓君權代理神權,這種態度似乎表明古代南海印度教-佛教的“神人同性”論述尚留痕跡;而中古馬來世界不少蘇丹熱心蘇菲神秘主義,主張從自心合一神圣境界去成為自度度他的“完人”,其實和地區上曾經的“印度教—佛教傳統”有著對話余地,觀念上可和菩薩道理念交流。(62)Milner.AC.Islam and the Muslim State.in M.B.Hooker.ed.Islam in South East Asia.Leiden:E.J.Brill.1983. pp.32-42.
今天,盛唐以后的好些《大悲咒》陀羅尼石經幢還是有保存下來的,例如當初眾多僧侶來往上岸的廣州,光孝寺志大雄寶殿外西南角的大悲心陀羅尼石經幢,石刻尚有模糊文字,代表著它見證過密宗的觀音信仰入華。清朝顧光編寫《光孝寺志》,記錄說“幢以青石為身,高三尺許,形如短柱,下石跌座高二尺許,上寶蓋高一人許。幢身八面鐫大悲咒,字多漫漶殘缺。……東面款一行云:寶歷二年(826 年),歲次丙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天德兼蒲澗寺大德僧欽造。”(63)[清]顧光:《光孝寺志》卷3《古跡志》,廣東省立編印局,1935年影印本。當然,走近文物的游人即使知道這是密宗建壇、灌頂傳法的證據,又有誰知道咒語要感應的那位本尊當年常見的大士形象,不同于現在殿中的貴婦樣貌?從南海諸國到華夏各地,古代各國僧人和航海商旅都曾經崇拜與贊嘆過的觀音大士形象,是陽剛的,赤裸著健美上身,以雙手、四臂、六臂、八臂,乃至千手千眼的姿態,來往海陸救苦救難。
正如中村元《中國佛教發展史》所提及,密宗的東傳,出現了十一面觀音、千手觀音、如意輪觀音、不空罥索觀音等信仰,導致中國觀音信仰的民眾化,是各種觀音特色互相混合,甚至結合道教,發展“娘娘廟”;(64)[日]中村元等撰,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卷,臺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358頁。中國的觀音信仰演變出的民間流行形態,卻不見得全盤按照與延續原來傳入中華的經典文字,而是出現印度和南海本所未有,在中國膾炙人口的妙善公主成道傳奇,讓觀音轉為女身,代替南海觀音原有的印度貴族王子“偉丈夫”形象。觀音變身為婦女禮教可以私下接觸的娘媽相,這樣一位符合中國舊時代婦女文化與審美情趣的女身菩薩,還是符合《妙法蓮華經》所謂觀音以諸種化身對待眾生的教義。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者,即以何身而為說法”,有利漢傳佛教通過傳播觀音信仰推廣教義。
后語
由上述歷史可見,南海諸邦歷史上的馬來語地區長期以來都是梵文影響的地區,也曾是以密乘佛教為主流信仰;不空罥索菩薩的信仰盛行于“馬來亞”的年代,正是金剛乘佛教在南海昌盛的年代。即使到了元朝,滿者伯夷與元朝政府發生過戰爭,兩地后來還是維系著長期的友好關系;而且根據《元史》記載,元朝國師曾經在延祐年間(1314—1320)追隨船隊到滿者伯夷尋找藏經。可見到了元朝,國朝重視密乘,而南海依然是崇尚密乘的求法僧侶往來之處,滿者伯夷曾經是元朝僧人學習、傳抄佛教經典的中心。爪哇史料也記載,Adityawarman 在成為蘇門答臘的統治者之前曾經兩次代表滿者伯夷出訪元朝。中國學者白壽彝的《中國通史》認為他即是《元史》所載的爪哇國臣昔剌僧迦里也(僧迦剌),分別于元泰定二年(1325)和至順三年訪華。
過去提及古代南海諸邦君主制度,有把君王視為神明化身的“神王”說法,以為這是印度宗教的影響。然而,若理解從新柯沙里至滿者伯夷諸王的信仰,則會發現其中多有自認為佛教菩薩之應化;如此,吾人對其原來制度內涵的理解,實應考慮佛教對“轉輪圣王”的諸種說法,以及從金剛乘重視修行本尊相應、乘愿轉世等教義入手思考。
而回顧古金剛乘的信仰印象,可見“摩賴耶”的概念,原本就是不空罥索菩薩諸經典的早期傳播地區。在《不空罥索神咒心經》,那位采取自在天形象的觀自在菩薩就是往來游舍于當地的補陀洛迦山,說法的對象包括“無量凈居天眾、自在天眾、大自在天眾、大梵天王及余天眾”。如此看來,在南海的土地上,原本是以梵文延續的“摩賴耶”或者“末羅瑜”的命名,也是延續了它們本來的涵義;從Kertanegara到Adityawarman 都先后強調不空罥索菩薩對末羅瑜國的護持,也不能單純視為無獨有偶,也不見得純粹是他們數代親戚共同的個人喜好。
可是,當Kertanegara 以眾生平等的姿態祝福末羅瑜土地的四個種姓,文字的表現顯然也是承認了婆羅門種姓制度的存在,而且他也稱呼Tribhuwanaraja 為“一切圣哲的中心”。由此可以發現,在金剛乘佛教流行于南海的時代,它已經在神秘化的同時也出現了認同世俗、為政教結合關系背書的面向。若注意《不空罥索神咒心經》,“各姓”的說法也出現在經中。密乘對待世俗權勢分配及婆羅門習俗抱著寬容與收納態度,一方面固然可以隨順奉行婆羅門習俗的現實環境,對眾生作方便引導;但另一方面也是打開缺口,接受外來知見左右原來的教義。
但漢地的觀音印象,畢竟隨著佛教融入中華文化,發展出漢傳佛教,逐漸轉化出自身民眾更覺親切的面貌。而且,隨著佛教進入中華大地,至今東亞各國的觀音信俗,作為華夏文明對外交流互鑒的見證,也還是呈現著中華文化歷史以來持續在當地的影響和交流的印記。
漢地觀音文化,逐漸產生了有別于印度觀音的特征,最大表現是在思維上和觀念上的特征,其特點就在于中國本土出現在各朝編修的觀音經咒,以及諸如妙善公主等傳奇,都是延續著南海各地觀音信俗的主題,強調不論眾生不論生死都要做到慈悲平等對待。可是漢地信俗,衍生出本土觀音應化的系列教化故事,在延續宣揚慈悲精神之際,又把原有佛教教義敘述融合于本土脈絡,以慈悲的教義印證中華文化仁民愛物的傳統價值觀,真實不虛,因此就會特別注重在強調勸善勸孝,強調印度傳來經典所未傳播的孝女說法或孝道倫理。(65)王琛發:《觀音古佛在瑤池收圓信仰的定位——從青蓮教常用經典探討其道學建構》,“2015年王母信仰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地區花蓮:慈濟大學、勝安宮,2015年11月28日,未正式刊行。
漢文化是經過漫長時間,從海陸絲綢之路文化交流,逐步吸收從西域和南海諸國傳入漢地的各種形態的觀音信仰文化,在漢地兼容并蓄各種觀音信仰形態,并在此基礎上呈現文化交流與融合,卒之是把觀音信仰結合到中華文化內部的信仰觀念與文化內涵中。只是,一旦漢傳觀音信仰使用經典都是以漢文字書寫傳播,在地傳播的結果又流傳著許多印度原所未有的觀音顯圣故事,甚至各種梵文觀音咒語也由漢文翻譯,以后出現讀音演變和串成,連經典上原是印度的普陀山也出現了漢傳信眾在浙江重構的應化圣地,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已不再把觀音看成是外來的。(66)王琛發:《觀音古佛在瑤池收圓信仰的定位——從青蓮教常用經典探討其道學建構》,“2015年王母信仰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地區花蓮:慈濟大學、勝安宮,2015年11月28日,未正式刊行。
昔日觀音信仰從南海諸國傳播入華,從廣州到浙江普陀山,沿海市鎮或村落至今總有自己的觀音廟宇。中國東南沿海的人民如果到了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參觀當地的國家博物院,也能見證祖輩早期接觸的南海觀音。這位菩薩頭頂著化佛、赤裸著上身,伸出許多手臂,保護過法顯、義凈、玄奘及許多來往南海的僧侶和商人。他來自印度的布怛洛迦山,但是早就落戶南海各處,隨處聞聲救苦。
無論如何,歷史的演變畢竟“諸行無常”。今天,在中國的“南海觀音”主要演變為大家熟悉的女身觀音。而原來從印度到南海,密教的興起演變出的不空羂罥索菩薩信仰,幸得在唐代傳入中國,才能有漢文翻譯文獻保存其信仰傳統,在東亞諸國佛教信仰圈內繼續流傳。
但是,佛教在原來南海諸國的土地上最終還是式微,也是隨著伊斯蘭教的興起而失去作為主流的趨勢,先民膜拜的菩薩像最終演變成為走進博物館的歷史文物。而華人世界南海觀音記憶,也就逐漸忘卻玄奘流傳的布怛洛迦山的記憶,又逐漸變化成為大眾以浙江普陀山的記憶作為“南海觀音”印象的主流。可惜,如此一來,人們也會隨之忘卻中華民族在明清以前有過面向一個大海洋時代的“南海”,而且曾經勇敢地把象征“苦海慈航”實踐精神的Avalokitesvara 請了回家,演變成后來的紫竹林記憶。尚且,觀音信仰在中國的流播越趨向漢化,原本的南海觀音信仰的密乘色彩也就越加淡薄,民間對原來“南海觀音”之所以“南海”的認識,包括對“南海”原來的范圍,概念上也越來越模糊。
當然,只要經典存在,后人是有可能從不同角度,討論南海上曾經流行的“觀音”形象,顯現為不空罥索觀音形態,以及帶動的各種議題的影響。例如已故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便提到過《不空罥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最早在7 世紀討論如何主導佛教的童乩程序;(67)Strickmann,Michel.Chinese Magical Medicin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03-204.而到了Frederick Smith 的《自召附身》(The Self-Possessed)一書,則是延續多位前人研究的成果,包括司馬虛所言,認為亞洲地區普遍的神靈附體現象,并非原來在印度吠陀傳統受到認可,卻在中國被接受為合理,彼此的淵源可能互有關聯。(68)Smith,Fred.The Self-Possessed:Deity and Spirit Possession in South Asian Literature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p.417-426.諸如此類討論多國文化現象隔海相似,畢竟以共同的歷史背景為據——曾經有一段很長時間,在波瀾壯闊的大海洋,航路所及各處,廣泛流傳著同一個菩薩的信仰文化,傳播著菩薩相關的系列經典,表述著民族生存共同體海洋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共同愿望;他們會在危難中,以菩薩名號象征的“慈悲”和“平等”,完成“同舟共濟”,在日常生活祈求海不揚波、出入平安,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