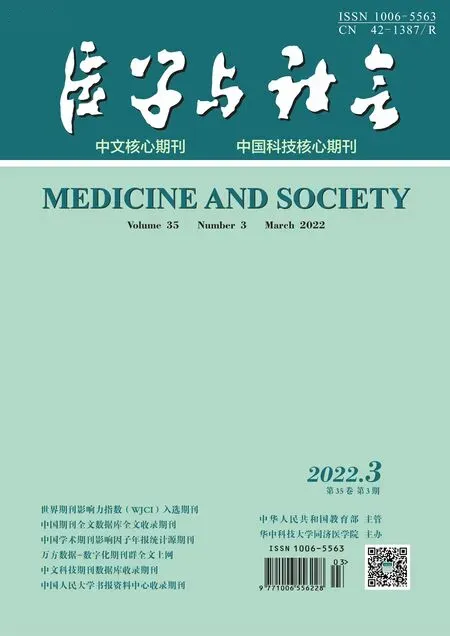中國女性社會工作者的職業心理健康問題研究
胡高強, 沈錦浩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上海,200237
截至2019年底,全國持證社會工作者共計53.4萬人,其中女性社工數量遠超男性,但學界忽視了對女性社工的關注。社會工作是需要性情投入的社會服務[1],而女性社工一直面臨著不公正的情感勞動分工,并在專業過程和組織場域中被建構[2]。她們既要符合一般性的職場規范,又要符合情感勞動的特殊規范,這導致她們的職業心理出現抑郁問題。由此,本研究通過對大樣本數據的分析來探究該問題。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數據使用2019年的“中國社會工作動態調查”,來自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國際社會工作學院和上海高校智庫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研究院的調查。數據涉及57個城市,獲得有效問卷6776份,數據清洗后剩余4501份。
1.2 模型假設
職業心理健康是對工作壓力的特殊反應形式[3]。Demerouti的工作要求-資源理論認為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的不平衡是造成心理壓力和工作倦怠的原因[4],并且個體可以通過工作自由度和工作支持可以抵消工作者的心理壓力帶來的消極心理影響[5]。French和Kahn也指出,心理問題并非單一環境或個人因素引起的,而是二者相互聯系的結果[6]。對社工心理健康而言,當前研究將社工視為整體。陸飛杰通過調查上海420名社工發現,社工的職業倦怠程度較高[7],張大維認為社工的職業耗竭與工作環境和組織支持有關[8],也有研究關注社工的組織支持感與職業倦怠之間存在心理資本的調節關系[9]。
職業心理健康既受到客觀工作環境影響,也受個人心理屬性的影響[10]。其中,環境因素包含工作自主性、機構支持等,而個人因素包含工作認知、自我評價等。因此,從客觀工作規制和主觀工作感知出發,建立一個多因素假設模型。模型設置了兩組假設和一個總假設,第一組是工作規制維度,共計五個小假設,第二組是工作感知維度,共計六個小假設。此外,考慮到某些變量可能存在調節效應,因此設置了年齡和工作情緒對心理抑郁的調節假設。
第一組假設: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工作規制中的工作支持(假設1)、工作自主性(假設2)、工作時間(假設3)、工作倫理(假設4)、工作內卷化(假設5)對女性社工的職業心理抑郁有顯著影響。
第二組假設: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工作感知下的工作滿意度(假設6)、工作宏觀認知(假設7)、職業認同(假設8)、機構集體擁有感(假設9)、職業倦怠(假設10)、自我評價(假設11)對女性社工的職業心理抑郁有顯著影響。
總假設(假設12):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工作感知的影響要大于工作規制。
假設13: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年齡和工作情緒對心理抑郁產生一定調節作用。
1.3 研究方法
1.3.1 工作規制測量。工作規制由多個變量綜合而來,共涉及五個問卷,其中三個為量表。本文將工作支持操作化為兩個子變量:組織文化支持和機構人員支持。前者來自Karasek的工作內容調查[11]。每個題項的回答均為分為5級,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下同)。后者來自House和Wells的社會支持測量量表,每個題項的回答分為5級[12]。工作自主性變量的測量也來自Karasek,每個題項的回答分為5級。日工作時間和工作倫理變量為調查自編問卷,每個題項的回答分別為7級和5級。工作內卷化測量來自Rizzo等人關于角色沖突或角色模糊的問卷,回答均分為5級[13]。三個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分別為0.91、0.87和0.83。
1.3.2 工作感知測量。工作感知測量涉及六個問卷,其中有三個量表。工作滿意度涉及樂趣、熱情、適應等維度,回答分為5級下同;工作宏觀認知涉及16個題項以考察社會工作者對本職業的宏觀認知,并且每個題項均具有否定性,指出當前社會工作的發展問題與不足;職業認同涉及公平、福祉、穩定、和諧、改革等7個題項;機構集體擁有感測量來自組織背景下集體心理所有權的量表,設有7個題項,回答分為4級[14];自我評價測量來自美國社工協會和奧爾巴尼大學衛生人力研究中心的調查,以考察社工的自我評價,每個題項的回答均分為5級[15];職業倦怠測量采用Maslach的職業倦怠三維結構量表[16],共計22個題項,每個題項的回答均分為6級(0=“從未”、1=“一年幾次”、2=“每月一次”、3=“每月幾次”、4=“每星期一次”、5=“每星期幾次”、6=“每天一次”)。三個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分別為0.88、0.79和0.85。
1.3.3 CES-D抑郁量表。它是由Radloff編制的人群自評式問卷[17],由20個題項所組成,回答均分為4級(0=“一周沒有出現”、1=“有1-2天都出現”、2=“有3-4天”、3=“有5-7天”)。該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為0.93。
1.3.4 工作情緒變量。工作情緒變量涉及情緒低落、疲憊、壓力等9個題目,回答均為7級(0=“從未”、1=“一年幾次”、2=“每月一次”、3=“每月幾次”、4=“每星期一次”、5=“每星期幾次”、6=“每天一次”)。
1.4 統計學方法
利用SPSS 20.0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采用描述性統計、回歸和調節效應分析。P<0.05認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Karasek工作內容調查量表、House和Wells的社會支持量表以及Rizzo角色沖突量表的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109.93±19.10)、(98.26±18.30)、(18.41±4.30);集體心理所有權量表、自我評價測量和Maslach職業倦怠量表的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19.19±4.30)、(33.19±4.40)、(46.37±13.00)。本文的因變量是職業心理抑郁,通過CES-D抑郁量表來測量,采用題項分值求和的方式來衡量抑郁程度,其均值為10.14,中位數為8,四分位數為3。
2.1 各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對收入、年齡、學歷、婚姻狀況、是否有社工師證和工作年限等控制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控制變量的統計
對工作規制和工作感知下的各變量以及心理抑郁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工作規制、工作感知和心理抑郁變量的描述統計
2.2 工作規制和工作感知對職業心理抑郁的影響
如表3所示,婚姻和年齡具有統計顯著性(P<0.05),為了簡明表達,將模型8-14的部分控制變量數據省略;由表3可知,模型2到模型6表明工作支持、日工作時間、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內卷化均有統計顯著性(P<0.05),假設1、2、3、5成立。模型7結果與模型6相同;工作滿意度、職業認同、機構集體擁有感和職業倦怠均具有統計顯著性(P<0.05),假設6、8、9、10、11成立。模型14顯示工作感知下的工作滿意度、宏觀認知、機構集體擁有感、自我評價和職業倦怠均具有統計顯著性(P<0.05);模型7和模型14表明工作規制和工作感知的各變量大部分具有統計顯著性。工作規制(模型7)的解釋力為10%,而工作感知(模型14)的解釋力為13.7%,因此工作感知對職業心理抑郁的解釋力要大于工作規制,假設12(總假設)成立。

表3 工作規制和工作感知與職業心理抑郁的回歸分析
2.3 婚姻和工作情緒對職業心理抑郁的調節效應
為了直觀展示婚姻和工作情緒對職業心理抑郁的調節效應,根據多元線性回歸制成調節模型圖,如圖1。

圖1 調節效應模型
模型顯示,工作支持(-0.302)、工作自主性(-0.108)和工作滿意度(-0.261)對女性社工職業心理健康的抑郁的影響受婚姻的負向調節(B<0),而工作內卷化(0.355)和職業倦怠(0.473)受到婚姻的正向調節(B>0);工作自主性(-0.140)和機構集體擁有感(-0.059)對女性社工職業心理健康的抑郁的影響受到工作情緒的負向調節(B<0),而工作內卷化(0.119)和職業倦怠(0.028)受到工作情緒的正向調節(B>0)。因此假設13成立。
3 討論
3.1 女性社工職業心理健康中的抑郁具有普遍性
中國女性社工的CES-D量表均值為10.14>10,并且收入、學歷、工作年限、有無社工證等特征對其心理抑郁無影響,這說明女性社工普遍存在抑郁傾向。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社工職業情感勞動的一般性和性別分工的特殊性。在一般性方面,作為一種職業的社會工作要求女性社工依據專業技能與情感來提供服務,引起情緒耗竭等問題[18]。社工專業要求社工要以理性態度去處理問題,而其過程卻期望社工試圖做到感同身受,這本身就致使社工的情感勞動陷入在專業理念的被動之中,強化社工“情感系統”的矛盾性;在特殊性方面,女性社工比男性社工更多地居于一線,承擔較多的個案、小組工作,這導致女性社工負責更多的情感勞動和專業服務,繼而加重了職業心理抑郁問題[19]。其本質在于女性社工在男權話語體系中被賦予了更多的情感屬性,是整個行業甚至社會對女性社會工作者甚至是對女性群體形象的強行刻畫。可以說,中國女性社會工作者因承受著工作規制、更多的專業服務以及由此強化的主觀感知而產生和加劇了心理健康問題。同時,不可忽視的是,女性社工在家庭中承擔了更多的家務勞動與照顧行為,是促進女性社工心理健康問題面向特殊性的另一種容易被忽視的權利不平等的表征。而女性社工占據了中國社工的大多數,因此她們的職業心理健康問題應該受到重視。
3.2 客觀工作規制與主觀工作感知均產生影響
女性社工職業心理健康中的抑郁問題既受到客觀工作規制的誘發,也受到主觀工作感知的影響,但工作感知的解釋力要大于工作規制。這與其他關于社工相關問題受到非單一因素影響的結論大體相似[20-21],但所不同之處在于,以往研究只是挑選、剪裁和驗證兩至三個因素的影響,忽視了社工職業心理健康中抑郁問題的綜合性,也未考慮到女性社工的獨特性。根據數據分析,在工作規制上,女性社工的工作支持和工作自主性可以緩解心理抑郁,而工作時間和工作內卷化則催生和強化了問題;在工作感知上,工作滿意度、機構集體擁有感和自我評價可以緩解心理抑郁問題,而職業倦怠卻在加劇問題。因此,緩解女性社工的職業心理抑郁可以從兩方面出發。一是從工作規制出發,社工機構應該給女性社工提供更多工作支持,包括組織文化支持和機構人員支持,給女性社工提供更多工作自主性以及適度減少女性社工的日工作時間,使其身體和精神得到充分休息,社工機構應該減少自身的內卷化程度,避免強化女性社工的角色沖突。二是從工作感知出發,提升女性社工的職業認同、重塑機構尊重女性的工作文化、加大賦權女性社工以及科學調整機構的工作安排,以提升女性社工的職業成就感來降低工作倦怠。
3.3 婚姻和工作情緒對職業心理健康的抑郁存在調節作用
調節分析表明,工作支持、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滿意度對女性社工職業心理健康的抑郁的影響受婚姻的負向調節,而工作內卷化和職業倦怠受到婚姻的正向調節;工作自主性和機構集體擁有感對女性社工職業心理健康的抑郁的影響受到工作情緒的負向調節,而工作內卷化和職業倦怠受到工作情緒的正向調節。婚姻和工作情緒是影響中國職業女性心理狀態的重要因素。以婚姻狀況為例,未婚、已婚、離異和喪偶對女性職業心理狀態的影響或沖擊存在差異,未婚的女性社工與已婚的相比,可能會在日常生活中擁有更多的個人時間,而不是將精力和時間花費在照顧家庭、事務或處理矛盾上,因此獲得工作支持和自主性等積極因素的可能性要高一些,因而擁有更好的職業心理健康狀態。同理,未婚同樣比離異或喪偶的女性社工擁有更好的心理狀態,但對工作內卷化和職業倦怠卻與之相反,其原因在于未婚女性社工擁有更高的職業期待、較強的生命意義感以及較多的時間投入[22],也就更易發現工作中的內卷化事實和感受到工作倦怠。而由于女性社工的工作情緒受到專業認同和職業技能的深刻影響,很大程度上引起職業心理抑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