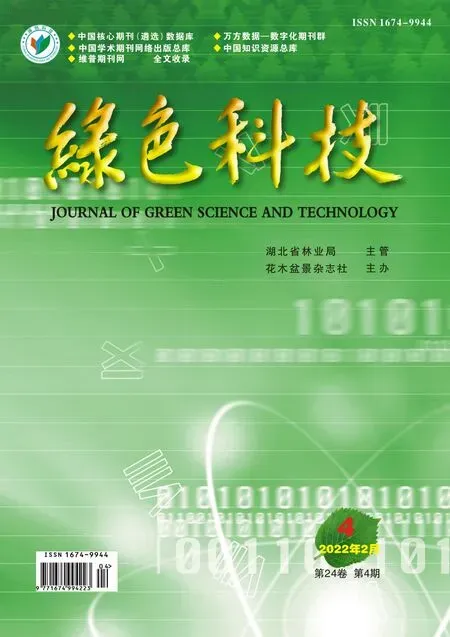長江中下游流域人類活動對濕地生態系統的影響研究
王硯深,竇弘毅,趙麗婭
(湖北大學 資源環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
1 引言
濕地生態系統自然資源豐厚,有涵養水源、調蓄防洪、維護生物多樣性等多種生態服務功能,對流域生態環境的改善有著重要推動作用。但近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力度不斷加大,高強度的人類活動干擾了當地的濕地生態系統現狀,使得濕地功能喪失、面積銳減[1],其中以長江中下游流域形勢最為嚴峻。作為我國最大的人工和自然復合的濕地生態系統(占到全國濕地總面積的20%),近10年其流域濕地面積不斷減少,其中具有標志意義的洞庭湖面積下降了63.4 km2,同時生態功能強大的灌叢、沼澤面積也分別減少了0.38 km2、186.49 km2[2]。人工湖庫坑塘代替自然濕地的現象較為突出,“占優補劣”問題較為嚴重[3]。
國內外學者圍繞著人類活動對濕地生態系統的干擾影響展開了一系列研究。余姝辰等[4]對洞庭湖區通江湖泊進行了研究,揭示了長期人類活動下湖區的時空演變特征;羅建波等[5]對不同類型的湖泊型保護區進行了富營養狀況評價,為保護區管理提供了決策支持;趙軍凱等[6]探討了人類活動對于鄱陽湖水位變化的影響,為湖泊生態治理提供了參考。上述對于濕地生態系統的研究多集中在通江湖泊濕地景觀格局演變、濕地自然保護區的分布與保護空缺等方面,對于人類活動影響及預測其變化趨勢的研究較少。雖然賈艷艷等[7,8]已對1995~2015 年的流域人類活動和濕地景觀格局時空演變進行了綜合性研究,但其研究的時效性滯后。因此,對長江流域濕地現狀、變化趨勢及其對人類活動強度響應進行了綜合分析,旨在為濕地保護提供參考。
基于2000~2020 年土地利用數據,以長江中下游流域濕地為研究對象,利用ArcGIS、Fragstats等軟件對近20 年人類活動強度的變化以及濕地景觀格局的變化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長江中下游流域濕地生態保護、功能恢復和人類活動調控的相應建議和對策。
2 研究區概況
長江中下游通常指湖北宜昌以東的長江流域,西起巫山東麓,東到黃海、東海濱,北接桐柏山、大別山南麓及黃淮平原,南至江南丘陵及錢塘江、杭州灣以北沿江平原(105°30′~122°30′E,23°45′~34°15′N),涉及湖南、湖北、江蘇、上海等在內的多個省市,流域總面積近78 萬 km2。
長江中下游流域是長江流域人類活動最為頻繁的區域[9],流域內擁有全國近1/3 的人口數量,人口密度較大,兩大城市群(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皆位于此。同時,作為長江經濟帶高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江中下游流域與我國其它地區溝通互融,擔負著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雙重責任。
流域內自然資源優勢顯著,河網密集,濕地資源豐富。據統計,流域內濕地面積達5.8 萬 km2,占長江中下游流域面積的7.4%,占全國濕地總面積的15%。研究區有中國五大淡水湖中的4 個,有國際重要濕地10 處、國家級濕地自然保護區20 處、國家級水利風景區163 處、國家級濕地公園209 處等[10]。
3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3.1 數據來源
基礎研究數據為江蘇、浙江、上海、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和陜西等省(市)的2000、2005、2010、2015 及2020 年的土地利用數據(空間分辨率為1 km),參考中國九大流域片,以長江流域為邊界對9 省土地利用數據進行掩膜提取,得到2000~2020 年(以5 年為期)的長江中下游流域的土地利用數據。以上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
3.2 人類活動強度綜合分析
人類活動強度(HAILS,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of land surface)是用以評估區域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干擾程度的重要指標[11]。在分析中,將2000~2020 年所有土地利用類型按照其對應的建設用地當量折算系數(CI,conversion index of construction land equivalent)換算成建設用地當量面積,用以表征該區域的建設用地當量(CLE,construction land equivalent),進一步進行換算得到人類活動強度指數用以反映人類活動強度的變化程度。
人類活動強度指數計算公式及建設當量面積計算公式如下:
(1)
(2)
式(1)、(2)中,CIi為第i種土地利用類型的建設用地當量折算系數,SLi為第i種土地利用/覆被類型的面積,S為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總和,n為土地利用類型的總數目。確定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建設用地當量折算系數表如表1。

表1 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建設用地當量折算系數(CI)
3.3 濕地景觀指數計算
參考李秀珍等[12]對景觀格局指標的相關研究,在類型水平指標上選取斑塊面積(CA)、斑塊密度(PD)、斑塊數目(NP)、斑塊所占景觀面積比例(PLAND)、最大斑塊占總面積比例(LPI)、散布與并列指數(IJI)、凝聚度指數(COHESION),使用Fragstats 4.2進行分析[13]。其中,PD、IJI和COHESION能夠反映流域內的濕地景觀破碎化程度,PD與IJI越大(COHESION越小),濕地景觀破碎化程度越大;LPI用以表征流域內最大濕地斑塊面積的變化。具體計算公式參考鄔建國等[14]學者的研究成果。
4 結果與分析
4.1 2000~2020 年流域濕地面積變化
從表2看出,濕地總面積在2000~2005 年增長較快,而在2010~2015 年略有減少,其中2020 年濕地總面積約為40502 km2,較2000年增長近1660 km2。根據不同的濕地景觀類型來看,在人類活動干擾下,作為生態環境質量較高、服務功能較強的自然型濕地,湖泊與沼澤地的面積在近20 年來不斷下降,降幅分別為9.06%、9.03%,且近5 年湖泊面積明顯萎縮;灘涂和灘地的面積雖然有所波動,但整體上仍較穩定;人類生態活動進一步推動了人工濕地的建設,河渠、水庫坑塘等人工型濕地的面積在不斷增長,與2000 年相比,增幅分別為13.26%、11.45%。在高強度的人類活動下,雖然流域2000~2020 年濕地景觀總面積整體上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但其生態環境質量和功能卻因自然濕地的萎縮而略有下降,人工湖庫坑塘代替自然濕地的現象不斷突出,“占優補劣”問題日益嚴重。

表2 2000~2020 年濕地景觀類型面積變化 km2
4.2 2000~2020 年流域濕地景觀指數變化
近20 年來,CA與PLAND的變化與濕地景觀總面積的變化相統一,呈現不斷增大的趨勢(表3)。但隨著人類活動強度等級的增加,流域土地覆被類型在空間上發生改變,進而驅動濕地景觀格局發生演變。NP、PD、IJI均不同程度地增大,尤其在2015~2020 年IJI的增幅達到了2.56%;COHENSION不斷下降,在2015~2020 年間降幅較為明顯。流域濕地景觀的凝聚度總體上不斷減小,散布程度不斷增大,出現了斑塊破碎程度加劇的問題,即人類活動干擾使得流域內濕地景觀破碎化程度加劇。在2010~2020年,LPI降幅約25.35%,表明流域內最大斑塊、長江及洞庭湖、鄱陽湖等通江湖泊在部分區域破碎程度加深且面積不斷萎縮。

表3 2000~2020 年濕地景觀指數變化
4.3 人類活動強度與建設用地當量變化特征
由圖1可知,流域人類活動強度與建設用地當量呈不斷增長的趨勢且增長速率逐漸升高。根據長江中下游流域2000~2020 年人類活動強度變化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城市化進程期(2000~2010年): 2000~2006 年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第四個階段,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在這一時期城市化進程明顯加速、城市化增長率顯著后趨于平緩,10 年間建設用地當量面積增加約4742.72 km2。在此階段,雖然部分濕地景觀指數受城市化建設影響有所波動,但長江及其通江湖泊的面積占比穩定上升,濕地整體的景觀破碎化程度尚未加深。現代化進程期(2011~2020年):在加速城鎮化、推進現代化的背景下,長江產業帶開發區處于超常規發展期,以工業開發為主導,10 年間建設用地當量面積增加約19716.46 km2。人類活動強度與建設用地當量面積的增長相統一,每5 年均增長約0.8%,2020 年較2000 年增長約3.17%,且在近10 年來進入了快速增長期,流域的人類活動更加頻繁,進而使得長江及其通江湖泊面積銳減,高強度的人類活動導致濕地景觀破碎化程度不斷加深。

圖1 2000~2020年人類活動強度與建設用地當量變化
2000~2020年間各類建設用地面積對人類活動強度及建設用地當量增長的貢獻排序為:城鎮用地>其它建設用地>農村居民點(表4)。2020 年城鎮用地面積較2000 年增長約7949 km2,其它建設用地面積增長約7003 km2,農村居民點的面積變化較為穩定,呈緩慢增長趨勢。尤其在近10 年,流域內城鎮用地的擴張及工業、交通用地的建設使得人類活動強度快速增長,進而導致自然濕地萎縮、人工濕地增長。其它建設用地面積增加5596 km2,城鎮用地面積增長5301 km2,長江流域經濟的蓬勃發展、交通運輸綜合體系的建設完善及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建設使得中下游流域人類活動強度不斷增加,是導致“占優補劣”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

表4 2000~2020年不同類型建設用地面積統計 km2
4.4 人類活動強度空間分布變化特征
對2000~2020年長江中下游流域土地利用類型進行重分類如圖2所示,在該圖中以建設用地表征人類活動強度區域的空間分布變化。總體上,近20 年流域人類活動強度變化主要集中于長江三角洲核心區域,同時在長株潭城市圈、武漢城市圈、合肥、南昌等區域有顯著變化;在河南南陽、江西宜春、湖南益陽及湖南常德等非省會城市強度亦有所增長,人類活動所帶來的城市聚攏效應不斷增強。與濕地景觀指數的分析結果相同,流域內人類活動強度密集區域基本圍繞長江及其支流、大中小型湖泊而變化,使得濕地最大斑塊受人類活動干擾增強;城鎮用地、工業用地、交通用地等建設用地肆意擴張、不斷侵占生態用地,進而導致濕地景觀格局發生演變。同時,長江中下游流域的西、西北、南和東南邊緣起伏較大的秦嶺、巫山、武夷山脈等山地區域始終保持較低的人類活動強度,人類活動強度基本未發生變化。與人類活動強度計算結果相同,2015~2020年流域人類活動強度區域擴散加速,在長三角核心區和長株潭城市圈較為明顯,這也與其區域的現代化高速發展密不可分。

圖2 2000~2020長江中下游流域人類活動強度分布變化
5 討論
人類活動是一個較為廣泛的概念,很難對其變化特征直接進行描述,因此參考徐勇等[15]對陸地表層人類活動強度的計算方法及應用,引入人類活動強度及建設用地當量兩個具體指標對人類活動進行定量分析。同時,對土地利用數據進行重分類并制圖,分析其空間分布變化,有助于系統地描述流域的人類活動變化特征。景觀指數(Landscape Index)是一種最大程度濃縮景觀格局信息的簡單指標, 能夠很好地反映其自身的結構組成及空間格局的演變特征[16-18]。引入景觀指數進行分析能夠更好地反映在人類活動干擾下流域濕地生態系統的時空演變特征,從而為未來濕地的生態保護提供理論支撐。研究表明:近20 年流域內濕地的景觀破碎程度不斷加劇,在近5 年尤為嚴重。在人類活動的干擾下,由于人類活動強度較密集區域基本圍繞長江及其支流、大中小型湖泊而變化,這樣進一步導致人類活動對濕地的干擾增強,從而使得自然濕地面積萎縮,人工湖庫坑塘代替自然濕地的現象較為突出,總體的生態價值有一定的降低。
1996年傅伯杰等[19]提出人類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會改變區域土地利用現狀及景觀格局,使得自然景觀轉變為存在人類活動的建設用地或耕地類型等。針對不同類型流域的研究中,發現不管是濕潤區[20]還是干旱區[21]的流域自然景觀格局都會受到人類活動的干擾進而發生改變,二者存在一定的耦合關系。隨著國家對生態環境保護的日益重視,雖然高強度的人類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流域內自然濕地總量明顯恢復、人工濕地面積不斷增長,但同樣導致自然濕地面積萎縮、景觀破碎化程度加深等問題的產生,不利于長江中下游流域人與自然和諧、兼容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未來流域發展的同時,應盡可能阻礙建設用地對生態用地的侵占,將自然濕地的生態恢復工作放在首位,解決“占優補劣”的相關問題。同時,以長江經濟帶發展、生態文明及國家公園建設為契機,逐步加強長江及其通江湖泊的水域岸線管理,積極修復灘地濕地資源,保護天然沼澤的原真性、完整性[22~24],從而有效緩解人類活動對流域濕地生態系統的干擾。
6 結論
(1)濕地景觀面積增加約1660 km2,河渠、人工水庫坑塘面積增幅11%以上,湖泊、沼澤地面積降幅9%左右,灘涂、灘地面積較為穩定。
(2)人類活動強度增長近3.17%,建設用地當量增幅27.72%。長江及其支流、通江湖泊的人類干擾活動不斷增強,這也是洞庭湖等大型湖泊面積減少的主要原因。
(3)受人類活動的影響,濕地破碎化較為嚴重。如何正確處理人與濕地之間的關系,是修復長江及通江湖泊濕地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