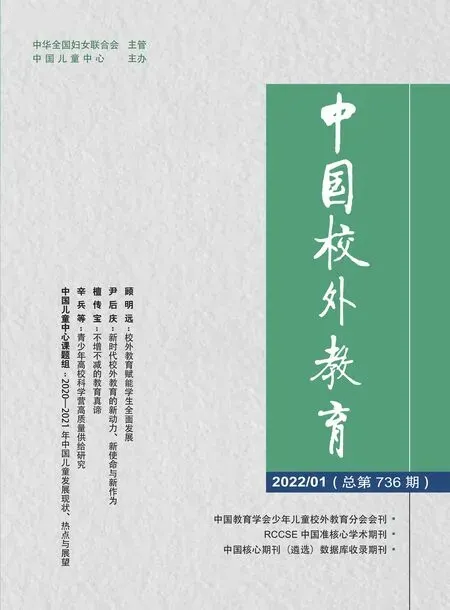校外音樂項目對城市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積極影響①
梅麗莎·L·惠特森 薩拉菲娜·羅賓遜 肯德拉·范·沃爾肯伯格曼迪·杰克遜 著吳揚北 張 莉 時 麟 吳碧宇 鄭紅紅 譯
一、導言
研究表明,兒童接觸音樂項目可以提升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1]。盡管低收入家庭兒童很少有機會參加音樂項目,但研究發現,有機會參加美術項目和音樂項目的低收入家庭兒童與其他同齡人一樣可以從中獲益,有時甚至比同齡人獲益更多[2]。本文采用混合設計法進行探索性研究,評估校外音樂項目對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積極影響。
(一)為低收入家庭的兒童開設的校外項目
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差距在持續擴大。但是,針對校外項目研究的結果表明,高質量的校外項目對提高低收入家庭兒童的學業成績具有重要作用[3],認知層面的學業成績的提高很大程度得益于非學業素養的訓練。例如,有研究發現,參加校外項目獲得的社會支持對提高和維持學業成績和非學業素養至關重要[4][5]。
布蘭達和麥克雷亞收集了一個領導力發展校外項目中低收入家庭非裔美國青少年的定性數據[6]。在調查過程中,這些青少年強調,參與項目最重要的收獲是與同齡人建立了聯系,并得到導師“無條件的積極關注”。因此,他們能夠在學業上與他人保持積極聯系。
薩盧斯基等人研究了青少年通過參加青少年發展項目培養責任感的過程[7]。研究采用開放式定性訪談,調查青少年在培養責任感的過程中經歷的壓力和緊張。研究分析了青少年責任感發展的四個階段:承擔新責任、承諾責任、履行責任和經歷行為變化。調查數據顯示,青少年通常會自愿承擔新責任,在履行新責任的過程中會感到壓力,但仍以積極心態承擔新責任,在校外項目之外的其他場合也更有責任心[7]。
很多研究都提到主要服務低收入家庭兒童的校外項目對學生學業成績和非學業素養的潛在積極影響,當然這些積極影響常取決于多個因素,比如項目的質量。這些研究還調查了關注特定領域或特殊技能的校外項目會對兒童產生怎樣的積極影響。藝術類校外項目已經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對這類項目的評估研究還很有限。
(二)藝術類校外項目
萊特等人對國家藝術和青少年示范項目(NAYDP)進行了為期3年的多方法評估[8]。該項目旨在為加拿大不同文化背景的低收入家庭青少年(9~15歲)提供藝術技能強化教育。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的參與度、技能發展、親社會性和任務完成度均有明顯提高。家長的報告稱,青少年的自信心和自尊、問題解決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包括與同伴的積極互動能力和沖突解決能力)均有提升。家長和青少年均在報告中表明,由于該項目提供實際的激勵措施(如項目免費、免費零食和免費交通),鼓勵家長參與,并為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性環境,因此青少年會更積極地參與項目。
該項目實施5年后,萊特等人對參與國家藝術和青少年示范項目的32名青少年進行跟蹤調查[9]。參與項目的青少年稱,項目帶來持續的積極影響,這得益于技能習得、良好的師生關系、團隊合作、積極的同伴關系、歸屬感以及項目的靈活性。他們表示會繼續上學,并打算在中學畢業后繼續接受高等教育。
盡管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在藝術類校外項目中能獲得積極成效,但與高收入家庭的同齡人相比,他們參加音樂項目的比例極低。凱瑟羅爾指出,在藝術強化類項目中,與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學生相比,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學生能在學業成績和非學業素養上獲得相同、甚至更大的效益,包括取得高分成績、獲得上大學的機會等[10]。此外,參與藝術項目的學生,無論社會經濟地位高還是低,獲得學士學位的可能性都是未參加藝術項目學生的三倍[10]。
針對低收入家庭兒童的藝術類校外項目需要更多研究。此外,對這些項目中特定類型的藝術媒體和以藝術為基礎的課程進行比較也非常重要[8]。研究發現,與一般的藝術類項目一樣,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很少有機會報名參與音樂項目,尤其當這些項目資金面臨或實際受到削減時,機會更少[11]。然而,有研究表明,參與音樂項目與學生學業成績和非學業素養的提高有關。
(三)音樂項目
多項研究表明,參與音樂項目與良好的學業成績有關。例如,研究發現,參與音樂項目與閱讀成績[12]、語言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13]、數學成績[2]和一般智力[14]呈正相關。研究還表明,這些積極影響的程度和持久性取決于參與音樂項目的時間和投入程度,諸如持續數年學習一種樂器[11]。因此,參與為期數年的音樂項目,特別是專注一種樂器演奏的音樂項目,青少年可能會獲得更持久的益處。
僅有少數研究針對校外音樂項目展開專項調查(相較于校內音樂項目或個人音樂培訓而言)。例如,克勞斯等人[15]開展了一項隨機對照研究,研究對象是參與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市長期社區音樂項目的兒童群體。該項目為低收入家庭的弱勢兒童提供免費音樂指導。結果顯示,接受2年音樂指導的兒童在聽覺加工方面出現顯著的生物學變化,這對以語言為基礎的閱讀能力和日常交流能力有積極影響。
安德瑞森調查了兩個主要服務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校外音樂項目(一個側重于樂器教學,另一個側重于合唱教學)[16]。結果顯示,大多數青少年稱,他們的學業成績因參與項目而得到提高,非學業素養也有所提升,如專注力、團隊合作、社交技能、時間管理、毅力、領導力、同伴關系等。教師和家長的報告也顯示,青少年在學業成績和非學業素養方面都有進步[16]。
上述研究指出,音樂項目通常以間接方式對個體的智力和學業成績產生積極影響,并通過情緒、幸福感、自尊、專注力及壓力水平等非學業因素起作用[16]。例如,里卡德等人研究了小學學齡兒童的校內音樂課程[17]。研究發現,盡管并非校外項目,但參加這些課程可以防止兒童自尊的下降。研究者認為,兒童參加音樂活動,進行音樂游戲,可以促進其親社會行為,增強自尊。與同伴一起參與音樂活動可以提高團隊合作能力、增強社交技能。因此,在研究音樂項目帶來的影響時,評估這些與學業成績密切相關的非學業素養是非常必要的。
(四)關于本研究
本研究旨在對城市低收入家庭兒童和青少年群體的校外音樂項目——“音樂港灣”項目進行評估。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法,包括焦點小組訪談和問卷法,調查參與該項目的學生在學業和非學業素養方面的獲益情況。前人研究成果和焦點小組訪談結果已確定的非學業素養,包括音樂技能、責任感/紀律性[7][16]、自我效能感(如自尊感)、賦能[8][17]、社交能力[6][8]和家庭關系。本研究參考上述指標設計年度問卷,希望每年通過該問卷獲取信息,問卷也將作為音樂港灣項目綜合評估程序的一部分,檢驗音樂項目如何對參與的兒童和家庭產生預期影響。評估此類項目,有利于了解項目是否會對弱勢青少年群體產生積極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是如何發生的,并據此設計出更有效的項目,讓青少年有更多機會參與其中并得到發展。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程序
“音樂港灣”是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的一個校外音樂項目,主要服務來自貧困社區的約90名兒童。“音樂港灣”的使命是:“由居住在紐黑文市中心的音樂家提供特殊的免費音樂教育、音樂指導和音樂表演,從而讓兒童和青少年獲得力量,增強彼此的聯系,讓所有孩子都有機會享受音樂”(www.musichavenct.org)。
該項目包括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確定焦點小組。我們將參加該項目的青少年及其父母或照料者確定為焦點小組。第二階段,設計問卷。依據前人研究成果和前期焦點小組訪談結果設計問卷,隨后將設計好的問卷發放給所有參加此項目的兒童父母/照料者。
1.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確定3個獨立的焦點小組,其中2個由父母/照料者組成,1個由參加該項目的青少年組成。受訪的父母/照料者參與訪談,并對項目提出反饋意見。同意參加訪談的父母/照料者可以享受免費飲食和免費兒童照看服務。他們分成兩組,一組在“音樂港灣”辦公室接受訪談,另一組在一所學校(兒童正常上課)接受訪談。5個月后,研究人員邀請參與“音樂港灣”項目的青少年組成第三個焦點小組,為其提供免費飲食,利用課間時段在辦公室接受訪談。參加訪談之前,首先要征得父母/照料者和青少年的同意。
3個焦點小組的訪談時長均為1小時。獲得知情同意后,被采訪者先填寫一份簡短的個人信息調查問卷。每組安排2名研究人員,一名負責主持訪談,另一名負責記錄和錄音。訪談采用半結構式。
10名父母/照料者(8女2男)參與本次訪談。其中包括黑人或非裔美國人(n = 5)、拉丁裔(n = 2)和非西班牙裔白人(n = 2,缺失= 1),均為參加該音樂項目的13名兒童(年齡跨度6~15歲)的父母/照料者。這些兒童參加該項目的平均時間為2.78年(范圍= 0.5~8年)。
青少年焦點小組包括8名參與者(5女2男,1其他),年齡范圍在13~16歲(M = 14.75),參與該項目的平均時間為7.44年(范圍= 2~9年),其中包括拉丁裔(n = 2)、非西班牙裔白人(n = 2)、黑人和拉丁裔(n = 2)、拉丁裔和白人(n = 1)以及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n = 1)。
2.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利用前一階段焦點小組訪談和以往研究確定的主題檢驗該音樂項目現有的年度調查問卷中的問題。修改問卷中的問題,與訪談主題保持一致,并根據現有測驗設計新的問題用于評估確定的主題(即變量)。調查的目標是確定主題,同時保持主題簡潔明確。
學年末,本次調查的工作人員通過電子郵件邀請父母/照料者參與在線問卷調查。53名父母/照料者完成了問卷調查。受訪者報告,他們的子女年齡為7~16歲(M =10.83),參與“音樂港灣”項目的平均時間為3.20年(范圍= 0.5~10年)。在完成調查的父母/照料者中,家庭年收入低于5萬美元的占64.2%。盡管未在對父母/照料者的調查中收集相關數據,但“音樂港灣”項目約90%的學生是少數民族或種族。
(二)測量
1.訪談問題
焦點小組訪談采用半結構式,主持人根據這些問題展開訪談。為父母/照料者設置的第一個問題是“孩子(孩子們)從‘音樂港灣’項目中學到了什么?”為學生設置的第一個問題是“您參加‘音樂港灣’項目有何收獲?”后續問題圍繞這些問題進行細節詢問,如“您的孩子(或您)在演奏樂器中有何收獲?”以及“參與‘音樂港灣’項目對家庭和學校生活有何影響”。父母/照料者和學生還需要回答最初參加項目的原因是什么,以及為什么會繼續參加。最后,受訪者需回答參加該項目有哪些困難、是否需要幫助以及對項目提出改進建議。
2.年度問卷調查
父母/照料者完成一份針對本研究的調查問卷。問卷包括參與者基本情況調查,內容涉及子女年齡、參加音樂項目的年限和家庭年收入。調查問卷共包含17個題目,主要關注焦點小組訪談和以往研究中確定的5個主題。受訪的父母/照料者使用5點李克特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作答,選項范圍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用于評估音樂技能變化和家庭關系變化的題目各1個,分值范圍1~5。其他4個主題分為4個分量表。責任心/紀律性分量表共5個題目,分值范圍5~25,得分越高,表明學生責任心越強且紀律性越好。自我效能感和社交能力分量表共4個題目,分值范圍5~20,得分越高,表明學生自我效能感越好,社交能力越強。測量賦能的分量表共1個題目,分值范圍1~5,得分越高表明學生賦能越強。
三、研究結果
(一)焦點小組訪談結果
研究人員將焦點小組訪談錄音轉為文字后閱讀并進行主題分析[18]。根據(經過歸納的)受訪者的語言以及關于低收入家庭兒童校外項目(尤其是關于音樂項目的研究)的現有知識和研究結果,對訪談錄音進行編碼。三位研究人員先分別閱讀每份文本,記錄文本中出現的主題。然后一起討論各自的筆記,共同確定核心主題。最后,研究人員將這些主題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以及確定這些主題所進行的變量測量進行比較,最終確定6個核心主題,并用于修改“音樂港灣”項目年度調查問卷。6個主題如下:
(1)音樂技能提升。幾乎所有父母都表示,即使孩子剛開始參加“音樂港灣”項目,他們的音樂技能也有顯著提升。一名照料者表示,“孩子不僅可以學習自己選擇的樂器,也可以學習其它各種樂器”。青少年也在報告中稱自己的音樂技能得到提升:“這是一種學習體驗——學習如何講不同的語言。”
(2)學業成績。一些父母表示,孩子的專注力、注意力和時間管理能力有所改善。正如一位照料者所言:“我女兒的學習成績提高了很多,成績優異。現在她更愿意開口了,會提問,能參與課堂活動等等。”
(3)責任感/紀律性。受訪父母表示,孩子的責任感和承諾感都增強了,不僅在音樂方面,還包括其他方面。學生們則表示,參與“音樂港灣”項目讓他們更加自律、更有耐心、更投入。一名學生說:“很小的時候,我們演奏時就得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拉琴的手要張弛有度。我們必須學會耐心練習……學會演奏,不能半途而廢。”
(4)自我效能感和賦能。父母指出,通過參加“音樂港灣”項目,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心有所增強。一名照料者表示:“‘音樂港灣’項目讓孩子更有力量。很多孩子可能會在學校遭遇欺凌或困擾,但在‘音樂港灣’的學習會為他們賦能,讓他們認可自己的行為,相信自我。”
(5)社交能力。父母表示,“音樂港灣”項目增強了孩子的自信心,孩子在音樂課、獨奏會以及學校中與他人有效互動的能力也增強了。一名照料者表示:“我發現我兒子更外向了;他可以進行獨奏,在眾人面前表演或講話時并不害羞。我認為‘音樂港灣’項目還鍛煉了他的社交能力。”青少年也表示,參加“音樂港灣”提升了他們的社交技能,擴大了社交關系網:“我已在此扎根,‘音樂港灣’擴大了我的社交圈。”
(6)家庭時間/家庭關系。父母覺得,全家一起參加“音樂港灣”的音樂會有利于增進家庭關系,這樣的機會很難得。他們非常贊賞這一點。此外,他們還談道,參加“音樂港灣”項目的哥哥姐姐在音樂興趣、責任感和信守承諾方面為弟弟妹妹樹立了榜樣。例如,一名照料者說:“‘音樂港灣’項目為家人營造了十分寶貴的相處時光。我丈夫工作很努力,非常辛苦。在參加音樂會時,我們可以聚在一起,享受彼此的陪伴。一家人相聚一堂的感覺真的很美好。‘音樂港灣’項目不僅提供了學習樂器的機會,還能營造家人相處的美好時光。”
(二)年度問卷調查
研究人員根據問卷分量表的結果變量對父母/照料者填寫的問卷結果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音樂技能項平均得分為4.72(SD = 0.57),滿分為5分;賦能項平均得分為4.23(SD = 0.80),滿分為5分;責任感/紀律性項平均得分為20.74(SD = 2.56),滿分為25分;自我效能感項和社交能力項平均得分分別為16.79(SD = 2.02)和17.26(SD = 1.97),滿分為20分。
研究人員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人口統計學變量對調查結果是否有影響。研究人員對家庭收入進行分析,以確定年收入低于5萬美元的家庭和年收入高于5萬美元的家庭是否存在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家庭收入較低的父母/照料者對子女責任感/紀律性的評分高于家庭收入較高的父母/照料者(t[51] = 2.08,p < .05)。此外,賦能評分的差異邊緣顯著,家庭收入較低的父母/照料者對子女的賦能評分高于家庭收入較高的父母/照料者(t[51] = 1.95,p = .06)。以上兩種類型家庭的孩子在音樂技能(t[51] = 0.31,ns)、自我效能感(t[51] = 1.29,ns)和社交能力(t[51] = 0.87,ns)方面沒有顯著差異(見表1)。

表1 獨立樣本t檢驗:家庭收入的影響

續表1
研究者還對兒童每周參加“音樂港灣”項目活動的時間進行統計。根據父母/照料者提供的信息,將每周參加時間超過3小時的兒童與每周參加時間小于等于3小時的兒童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與每周參加時間小于等于3小時的兒童相比,每周參加時間超過3小時的兒童,其責任感/紀律性更強(t[51] = -2.34,p< .05)。兒童每周參加活動時間對其他結果變量沒有顯著影響,數據如下:音樂技能(t[p51] = -0.69,ns),自我效能感(t[51] = -1.42,ns),社交能力(t[51] = 0.73,ns),賦能(t[51] = 1.71,ns)。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獨立樣本t檢驗:每周參加校外活動的時間對兒童的影響

續表2
最后,研究人員對參與者的年齡和性別進行分析,確定結果變量是否存在性別差異,或者是否與年齡具有顯著相關性。結果顯示,結果變量的性別差異不顯著,年齡與結果變量之間不存在顯著相關。
研究人員采用相關分析法分析各個分量表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相關。結果顯示,責任感/紀律性、自我效能感和社交能力呈顯著正相關(責任感與自我效能感:r = 0.71,p < .01;責任感與社交能力:r = 0.35,p < .05;自我效能感與社交能力:r = 0.57,p < .01)。研究還發現,音樂技能提高與賦能之間存在顯著相關(r = 0.44,p < .01)。
四、討論
本次研究使用混合設計法,旨在調查校外音樂活動對城市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群體的影響。第一階段,邀請10名父母/照料者和8名青少年參加焦點小組訪談。根據訪談結果得出青少年及其家庭參加“音樂港灣”項目獲得收益的幾個核心主題(結果):青少年在音樂技能、學業成績、責任感/紀律性、自我效能感、賦能、社交能力和家庭關系方面得到提高。
本研究調查結果與前人研究結果一致。例如,在責任感/紀律性方面,薩盧斯基等人發現,參加校外發展項目的青少年責任感增強[7];安德瑞森發現,參加校外音樂項目的青少年表現出專注力、時間管理能力和毅力的提升[16];以往研究還發現,參加藝術項目[8]和音樂項目[17]能夠增強青少年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最后,一些研究列舉了參加校外活動帶來的社交能力方面的收益,如親社會能力、團隊合作、積極的同伴關系和沖突解決能力等[6][8][16]。以往研究沒有特別強調家庭成員共處時間這一結果,可能是由于未對這方面進行測量,或者這一變量是“音樂港灣”項目特有的,因為該項目要求家庭成員共同參與,一起參加某些活動。后續研究可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調查。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總體來看,父母/照料者對大部分分量表評分較高。因此,對這些分數的解讀要謹慎,因為高分可能代表某些強烈希望項目取得理想效果的父母對結果的夸大,也可能準確反映出父母在孩子身上看到的變化。這一問題將在下文詳細討論。
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參加音樂項目的家庭中父母收入水平對兒童責任感/紀律性和賦能有影響: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對子女的評價高于高收入家庭的父母。這一結論與已有研究結果一致。凱瑟羅爾發現[10],參加音樂和藝術項目的收益對低收入家庭青少年更顯著,他還強調增加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參與這類項目的機會的重要性,因為這些青少年參與此類活動的途徑較少。
問卷調查結果還顯示,參加“音樂港灣”項目時間較多(每周超過3小時)的兒童,其責任感得分顯著高于參加時間較少(每周少于3小時)的兒童。這表明,參加音樂活動可能產生劑量效應。有研究得出類似結論:學生參加音樂教學項目一年以上,可從中獲得更明顯的收益[11][15]。因此,鼓勵青少年長期、頻繁參加的項目(如“音樂港灣”)能讓青少年獲得更多收益。
(一)研究局限
本次研究有幾個局限需要考慮。首先,本研究采用橫斷設計,未設置控制組或對照組,因此,無法判定問卷調查得分是否因為青少年參加音樂項目所致,也無法評估研究期間這些分數是否發生變化。盡管存在這一重大局限,但本研究獲得的結果仍非常重要,因為它提供了關于父母和青少年對該音樂項目作用的定性數據,以及傳統意義上“有風險”的青少年在這些方面的初步了解。
其次,本研究受樣本性質的限制。樣本包括自愿參加訪談的父母和青少年,以及同意完成問卷的父母。那些沒有參加調查的父母和青少年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另一個限制是調查問卷內容僅基于父母的報告。如果由參與音樂項目的教師或青少年本人來完成問卷,答案可能會有所不同。此外,如前所述,父母對青少年參與活動的結果總體評分都很高——這可能是由于樣本偏差或父母的回答受社會贊許影響。后續研究必須控制這些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二)啟示
總的來說,對父母和青少年進行定性研究表明,參加校外音樂項目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非學業素養,且這些能力與學業成績相關。本研究和之前的研究還表明,相較于參加其它項目,兒童長期、頻繁參加音樂教學項目能夠獲得更積極的結果。
這些研究結果強調,需要設置更多的校外音樂和藝術類項目,特別是考慮到校內音樂和藝術類課程資源缺乏,甚至有時被削減的事實[11][19]。本研究證實以往研究的結果,研究表明,參加這類校外項目有利于青少年學業成績和非學業素養的提高,非學業素養與青少年的整體幸福感、人際交往能力和最終的學業成績有關。此外,盡管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參加校外音樂項目的收益超過中等或高收入家庭的學生,但他們參加這些項目的機會較少[11]。為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創造更多參與音樂項目的機會并鼓勵他們參加,對于確保這些項目惠及能從中受益的青少年至關重要。因此,資助并鼓勵低收入家庭青少年每周數次、長期參加校外音樂教學項目可能是一個重要的途徑,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提高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和非學業素養,為他們創造一個與條件優越的青少年公平競爭的環境。
本研究還強調當前學界對音樂項目,尤其是校外音樂項目的研究不足。此外,還需要對“音樂港灣”項目進行更多的跟蹤研究,了解青少年參與該項目的研究結果是否會發生變化。研究過程也應設計控制組或對照組,確定青少年從音樂項目中獲得的具體收益,并與其他校外活動的影響進行區分。另外,對這類校外項目進行評估意義重大,有助于了解弱勢青少年參加這些項目能否獲得積極影響以及獲得了哪些積極影響,這樣才能設計出更有效的校外項目,并增加青少年參與活動的機會。
致謝
感謝“音樂港灣”的工作人員和董事會對本研究設計和實施給予的幫助。此外,感謝社區研究與行動協會(SCRA)于2015年1月18日提供的社區小額贈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