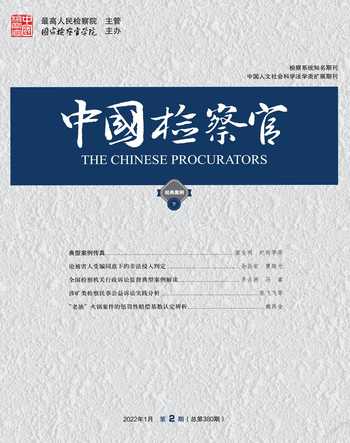論被害人受騙同意下的非法侵入判定
余昌安 曹曉光
摘 要:對于行為人騙取被害人入戶同意后再實施搶劫行為的,行為人是否構成“非法侵入”以及進而能否將其認定為入戶搶劫,一直存在爭議。應將該類案件理解為被害人的瑕疵同意問題,即只要得到有效同意而入戶就不屬于非法入戶。對于判斷被害人基于受騙同意的有效性這一問題,客觀真意說的“法益關系錯誤判斷→同意自愿性判斷”思考進路值得提倡。非法入戶目的等內在屬性不應影響“非法侵入”的認定,且被害人對行為人內心屬性的誤認不構成法益關系錯誤;同時,居住權人作出有效的入戶同意,須認識到對方的客觀身份屬性,否則將構成法益關系錯誤。
關鍵詞:瑕疵同意 非法侵入 客觀真意說 法益關系錯誤 入戶搶劫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 被告人何某某等人以索要賠償為由攔下被害人蘭某某,蘭某某拒絕給予賠償后被踢了一腳,遂表示:“有什么事到家里去好好說。”到達蘭某某家后,何某某等人對其實施了搶劫行為,獲得2000元。在該案中,審理法院考慮到“被告人何某某與被害人的女兒確曾相熟,也曾常到其家中”,因此沒有認定何某某屬于“非法入戶”,否認了入戶搶劫這一加重情節的成立。[1]
[案例二] 2020年2月,被告人業某某攜帶刀具到某小區,冒充疫情防控人員,以登記疫情為由騙得小區住戶趙某某同意后進入室內,隨后持刀威脅趙某某要求給付財物,得逞后迅速逃離現場。法院認定業某某構成入戶搶劫。[2]
在案例一中,審理法院考慮到蘭某某固然受到了一定的欺騙,其誤以為何某某等人只是來索要非法債務,并沒有意識到行為人隱藏于心的搶劫意圖。但蘭某某對于“讓何某某進來”以及何某某的熟人身份并沒有認識錯誤,甚至還主動邀請,說明其作出了允許何某某入戶的許可。因此,不應將該案評價為“非法入戶”,進而否定了入戶搶劫的成立。而在案例二中,裁判法官以行為人入戶前的搶劫犯意為根據認可了“非法入戶”的成立,但在裁判說理上較為粗疏化,完全忽視了其間存在的被害人同意問題,難免給人以“說理不充分”之感。
應當說,上述兩個案例具有相似性,都涉及到被害人因受騙而明示或者默示同意入戶的事實,行為人以平和方式入戶,其惡意潛藏于心、并未表露于外。只不過案例一將這類案件理解為被害人的瑕疵同意問題,即如果得到居住權人的有效同意或者推定同意而進入,將阻卻非法入戶的成立,進而也就不成立相應的侵入住宅型犯罪(如非法侵入住宅罪、入戶盜竊、入戶搶劫等)。[3]這也是刑法理論界的通行看法。與之不同的是,案例二將這類案件理解為非法入戶目的之認定問題,這樣一來,居住權人基于欺騙作出的錯誤同意要么被無視、要么被無效化。就此而言,面對同一類案件,理論和實務存在兩種思考路徑,哪一種路徑更優,值得深入思考。
要而言之,在該類案件中,值得研究的問題在于,進入者隱瞞搶劫等犯罪目的,居住者陷入認識錯誤以后“同意”其入戶,以平和手段入戶的行為人是否不構成非法入戶?從溝通理論與實務的“溝壑”而言,討論這一問題具有重要意義。此外,考慮到一旦行為人被評價為“非法侵入”的話,便有可能施以入戶搶劫的加重法定刑,將對被告人產生重大的利益剝奪,所以審理法官應當對此進行充分釋法說理,做到“以理服人”。有鑒于此,在入戶搶劫案中,被害人受騙后同意行為人入戶是否構成“非法侵入”問題兼具理論與實踐的價值,有必要予以細致研判。
二、思考路徑的選擇
前面已經提到,構成入戶搶劫要求滿足非法入戶這一要件,倘若行為人合法入戶后、在戶內臨時起意當場實施搶劫行為,只能算是“在戶內搶劫”而不屬于入戶搶劫,這也得到了相關司法解釋的明確認可。至于如何判斷“非法入戶”,則存在不同的理解路徑,具體論述如下:
(一)司法實務的傾向性態度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頒布的《關于審理搶劫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入戶搶劫”是指“以侵害戶內人員的人身、財產為目的,入戶后實施搶劫”。也即,應將非法入戶理解為入戶目的的非法性,進而將“非法侵入”這一構成要件要素主觀化為人身犯罪、財產犯罪的事先目的,之前的兩個搶劫罪司法解釋也同樣認可了這一點。正是基于相關司法解釋的傾向性意見,在行為人以平和手段進入他人住處時,實務部門常常以“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入戶”肯定非法入戶的成立[4],或者僅僅是因為行為人的欺騙行為而認可了“非法入戶”。顯然這一裁判邏輯操作起來簡潔明快,具有一定的實踐便利性,但是同時也存在三個弊端。其一,該處理邏輯較為形式化,沒有顧及到欺騙之中存在的被害人同意,并沒有做到充分尊重居住者“決定誰可以進入該住宅”的自我決定權。而國民的自我決定權是一項憲法性基本權利,基于合憲性解釋的要求,解釋刑法分則罪名時應朝著最大限度保障自決權實現的方向邁進。其二,該處理邏輯過度倚重于主觀化判斷,根據主觀上的目的決定加重法定刑的成立與否,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司法恣意判斷的可能性,并不可靠。事實上,司法實務在認定犯罪時固然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但更應強調客觀判斷先于主觀判斷的方法論規則。其三,該處理邏輯存在處罰漏洞,不利于發揮刑法的法益保護機能。例如在公訴機關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入戶前具有非法入戶目的的情況下,則不能論以入戶搶劫。就此而言,從利弊思維的角度出發,上述這種思考路徑并不可取,司法實務應尋求更優的處理方案。
(二)刑法理論的方案選擇
只要認可被害人同意的法理,就應認為,非法入戶和未得居住權人有效同意入戶是一體兩面的關系。也就是說,只要得到有效同意而入戶就不屬于非法入戶。進而認為,侵入住宅型犯罪中的“非法侵入”認定關鍵在于被害人對其入戶的瑕疵同意是否有效。于是,進入者是否構成非法入戶這一問題,被轉化為居住者基于受騙而作出的瑕疵同意是否有效的問題。而圍繞被害人受騙而同意的有效性問題,我國學界在借鑒比較法的基礎上主要形成了兩種處理方案。第一種是以錯誤為中心加以考察,其根據錯誤的內容判斷同意的有效性,具體可以分為法益關系錯誤說、重大錯誤說、動機錯誤說等諸種學說。第二種是以欺詐為重點加以考察,其認為行為人欺詐導致的被害人同意是不符合其真意的重大瑕疵意思表示,同意無效。[5]筆者認為,在判斷被害人錯誤同意是否有效時,應以錯誤內容為中心加以細致探討,并非只要被害人陷入認識錯誤就將導致同意無效。重大錯誤說和動機錯誤說的判斷標準可操作性不強,而法益關系錯誤說強調構成要件的定型性及其罪刑法定機能,立足于客觀基準進行判斷,合理限定了處罰范圍。[6]因此,以法益關系錯誤說為判斷瑕疵同意有效性的標準,總體上是可取的。
法益關系錯誤說也稱法益錯誤說,其主張欺騙所致的錯誤同意,只有當同意人對自己所處分的法益的種類、范圍或者危險性有認識錯誤的情況下,其同意才構成無效;如果該錯誤僅僅是與交換動機、期待回報有關,屬于動機錯誤,同意仍然有效。[7]例如,甲男假裝富豪,以“嫁入豪門”為噱頭引誘乙女發生性關系。此時乙女對自己與行為人發生性交行為的事實并無錯誤認識,只是誤以為發生性關系能夠實現“嫁給富豪”的目的(系單純的動機錯誤)。顯然,乙女并不存在法益錯誤,其性同意有效,甲男并不構成強奸罪。
自法益錯誤說產生以來,得到了德日不少學者的贊成,傳入我國后也日漸成為有力說。法益錯誤說總體上正確,不過還存有缺陷。因此,有學者在既有的法益錯誤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客觀真意說,客觀真意說比原來的法益錯誤說多了一步,即對同意是否具有自愿性的判斷。在動機錯誤的場合,需要從一般人視角考察被害人是否在具有選擇可能性的情況下作出自主決定。[8]應當說,客觀真意說有力地擺脫了法益錯誤說在面對緊急狀況或者利他動機之欺騙所遭遇的尷尬境地,較法益錯誤說而言是處理瑕疵同意問題的更優解,值得實務加以借鑒。因此,本文也贊同客觀真意說這一觀點。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基于有效溝通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這一目標,刑事司法實務理應重視主流理論成果,對于客觀真意說不應無視,完全可以在裁判文書釋法說理中進行參考借鑒。
三、客觀真意說框架下的瑕疵同意效力分析
承前所述,在客觀真意說的立場下,認定瑕疵同意的效力,需要同時考慮法益錯誤和同意自愿性。對于同意自愿性的判斷,往往爭議不大。例如,前述案例二本質上是一個同意自愿性的判斷問題,考慮到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是戶主的行政法義務,進而認為,居住權人趙某某的入戶同意是在不自愿的狀態下作出的,在同意的自愿性層面能夠否定同意的效力。[9]但是,對被害人因受騙而作出的同意是否屬于法益錯誤的情形,常常引發爭論。由此,法益錯誤的成立與否是本文聚焦的重點。需要指出的是,法益錯誤的判斷不是一個抽象的判斷,而是需要結合分則各罪保護法益的性質予以個別化考察。有力見解認為,非法侵入住宅罪的保護法益是居住權,即權利人自由決定是否允許他人進入住宅的權利。[10]筆者也贊成這一見解,接下來將以居住權說為預設前提,討論侵入住宅型案件中法益錯誤的認定問題。
(一)非法入戶目的不應影響“非法侵入”的認定
值得指出的是,前述案例一暗合了法益錯誤說和客觀真意說的理論邏輯,并沒有一概否定瑕疵同意的效力。進一步來說,何某某等人雖隱藏其搶劫意圖,但作為居住權人的蘭某某不存在法益錯誤,其對處分居住權和住宅安寧的內容具有默認,其對法益處分的性質、內容、范圍程度不存在認識錯誤;而且,從同意的自愿性角度看,居住權人僅僅是受到輕微強制,仍應認為此時蘭某某對法益的放棄具有選擇可能性,其可以選擇同意法益處分,也可以選擇拒絕法益處分。雖然居住權人存在信息“盲區”,但基于相對的被害人自治概念,每個人在作出法益處分決定之時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不需要法益主體絕對充分、全面地認識到為決策提供基礎的所有信息。[11]應當認為,即使居住權人沒有認識到行為人偽裝心中的搶劫惡意,只要其認識到作出同意的必要基礎事實,仍然能夠認為該同意系出于居住權人的真實意思,該瑕疵同意為有效。綜上來看,何某某等人入戶是得到居住權人的有效同意,而難言是“非法侵入”,審理法院否認“非法入戶”的裁判理由值得贊許。
筆者認為,行為人暗藏于心的犯罪目的、意圖等往往難以客觀判斷,如果要求作出同意的法益主體必須對此有所認識的話,可能會帶來一系列弊端:其一,為被害人同意附加苛刻的成立條件,可能會不當限制被害人的自治,存在完美自治概念的嫌疑;其二,從訴訟的便利性、公正性角度出發,由于內心目的不易證明,其形成于入戶前還是入戶后在實務中可能難以分辨,這不僅無形中加重了公訴方的證明負擔,而且還可能導致裁判者對入戶搶劫的認定偏向恣意化;[12]其三,如果要求戶主的有效入戶同意延及對入戶目的非法性的認識,必然面臨著哪些內心意圖要認識、哪些內心意圖不需要認識的選擇問題,可能產生不必要的爭議。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居住許可權的行使不應包括對入戶者內心意圖的認識。也即,從權威案例的立場來看,其傾向于居住權人行使許可權只需認識到“對象人物的外在屬性”,而不需要認識到“包括意圖在內的內心屬性”。[13]總之,法益錯誤的范圍不包括入戶者的內心目的、意圖。
如果再作進一步的延伸,既然居住權人作出入戶同意不需要認識到對象人物的非法入戶目的,只需要從客觀上認定“非法侵入”的成立與否,那么完全可以認為,非法入戶目的不是入戶搶劫的構成要件要素。沒有必要從主觀目的上對入戶搶劫進行限定,而可以通過總則條款對入戶搶劫這一加重條款的適用進行限制性認定。[14]當然,這一見解可能會被認為“與刑事司法解釋相矛盾”,不過這也不難回應。因為司法解釋所強調的“以侵害戶內人員的人身、財產為目的”只是類型化的主觀目的規定,僅僅是將最常見的入戶目的規定在文本中,以實施其他違法犯罪為目的入戶也有成立入戶搶劫的可能性。如此理解,也有利于更加周延地保護被害人的人身、財產法益。
(二)入戶同意需要認識到對方的客觀身份屬性
居住權人作出入戶同意是否需要同時認識到“讓對象人物進來”(認識到他人在物理空間上進入自己的戶內),以及“對象人物”的身份屬性呢?對此,車浩教授認為,只要戶主對他人在物理空間上進入自己的住宅沒有錯誤認識,即可排除“非法侵入”的成立。為便于理解,車浩教授進一步舉例加以說明:張三向戶主謊稱是“修理工”而騙取其同意進入戶內。在該種情形下,張三獲取的許可入戶同意有效,其并不構成“非法入戶”,也就談不上構成入戶搶劫。[15]然而,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住宅權人作出入戶許可的同意條件應包括對象人物的客觀外在身份屬性,而不是僅僅認識到對象人物的空間位移就夠了。主要理由有以下三個方面。
1.主流觀點認為,在關乎人身法益的場合,關于行為人同一性的錯誤應屬于法益錯誤,被害人有效同意的前提是對侵害相對方沒有認識錯誤。詳細來說,居住權人的許可同意通常會指向具體的對象,不應僅僅是對抽象人的認識,而理應包括對入戶者客觀身份屬性的認識。[16]居住權屬于基本人身權,在法益價值位階中處于較高地位。住宅安寧的自由是自我決定權的重要表現,而個人自主決定權是近現代法秩序中的最高保護價值。[17]也就是說,居住權人對人身法益的同意帶有高度個人化的特質,因此其對侵害相對方的認識要求也應更加細致化,而不能僅僅是認識到“讓他進來”。由此可見,居住者雖然是自愿許可他人進入,但如果是基于受騙而誤解了入戶者的客觀身份屬性(如熟人、快遞外賣人員、煤氣檢修人員等),這樣的錯誤屬于法益錯誤中的“行為人同一性的錯誤”,將導致入戶同意無效。正是基于此,對于前述案例二,可以認為,疫情防控人員屬于客觀外在身份屬性,戶主基于受騙而誤解了業某某的客觀身份屬性。此處戶主的錯誤屬于法益錯誤,將導致入戶同意無效化,行為人屬于“非法侵入”。
2.侵入住宅型犯罪是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犯罪類型,因此應當對“侵入”添加社會文化背景的經驗性理解。筆者認為,之所以居住權人會作出入戶的同意,背后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基礎信賴關系,居住者正是基于信賴對方的客觀身份屬性(如外賣員、快遞員等),才作出允許入戶的同意。這類似于附條件同意的法理,住宅權人的入戶同意也附帶有一定的要求。根據上述邏輯,入戶的有效同意需要住宅權人對被許可人客觀身份屬性的信賴實現來支撐。如果被許可人的客觀身份屬性存在重大虛假成分,足以打破人與人之間的基礎信賴關系,那么居住權人最初形式上的入戶同意仍然無效。此時,行為人的入戶本質上是違背居住者的自由意志,屬于“非法侵入”,倘若滿足入戶搶劫的其他構成要件,便可成立入戶搶劫。
此外,還需要加以說明的是,盡管當下中國正在慢慢步入陌生人社會,但這僅僅是意味著人與人之間趨向于不能建立穩定的社會關系,并不影響人與人之間的基礎信任關系。舉例而言,現在的互聯網虛擬平臺經濟本質上是數字化的信任經濟,在平臺信息的共享中建立起信任關系。[18]換言之,當前仍應認為,居住權人對入戶者外在身份所附隨的信賴也屬于刑法的保護范圍,將影響到分則罪名中法益錯誤的認定。
3.客觀真意說以客觀的法益衡量為標準,旨在尊重法益主體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客觀表達,通過判斷標準的客觀化來減少司法認定的恣意性。基于此,認定法益錯誤的范圍應強調一定的客觀性和可操作性,居住權人沒有認識到入戶者真實的外在身份屬性就屬于法益錯誤。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所謂的“客觀外在身份屬性”應當結合具體個案進行相應判斷。例如行為人以嫖娼之名騙取“站街女”同意入戶后實施了搶劫行為,由于“站街女”在作出入戶同意之際,對行為人的“嫖客”身份并沒有產生錯誤認識,故入戶同意為有效。這里的“客觀外在身份屬性”——“嫖客”,在該性工作者與行為人達成性交易合意的時候即可生成,不需要待到性交易行為的實際進行。所以,“站街女”的此種對嫖客變劫匪的同意入戶認識錯誤不屬于法益錯誤。筆者認為此時不會構成入戶搶劫,而是“在戶內搶劫”。
四、結語
案例作為法治的細胞和“刑事司法與法教義學互動的橋梁”,應當受到刑法理論的重視和審視。刑法是一門實踐的技藝,應當將可取的理論學說在司法實務中加以運用。就上述事例的刑法分析而言,客觀真意說的立場值得認同,但解釋者仍然需要對該學說作進一步的體系化和精細化,以更好地為司法實踐提供明確的可操作規則,實現個案的妥當解決。基于此,司法官在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過程中,既不能停留于“本院認為”的寥寥數語,也不能停留于法條、司法解釋的簡單復述,而應當在判決書中進行一定程度的論證,更加注重說理的詳實度。唯有如此,才能充分保障司法的公開性和公正性。
[1]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庭編:《刑事審判參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0頁。
[2] 該案系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一批依法懲處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之三。參見周光權:《精準打擊涉疫情犯罪,貫徹罪刑法定原則——評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依法懲處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報》2020年3月21日。
[3] 參見周光權:《刑法各論》(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頁。
[4] 參見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6)京0102刑初527號。
[5] 參見陳家林:《外國刑法理論的思潮與流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群眾出版社2017年版,第337-338頁。
[6] 參見付立慶:《有關被害人受騙同意的幾個問題》,《刑事法評論》2018年第1期。
[7] 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最高法院判例:刑法總論》,何慶仁、蔡桂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頁。
[8] 參見付立慶:《被害人因受騙而同意的法律效果》,《法學研究》2016年第2期。
[9] 同前注[8]。
[10] 參見[日]山口厚:《從新判例看刑法》(第三版),付立慶、劉雋、陳少青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148頁。
[11] 參見王鋼:《動機錯誤下的承諾有效性問題研究》,《中外法學》2020年第1期。
[12] 參見黎宏:《入戶搶劫中“入戶目的非法性”的要求應當取消》,《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19年第6期。
[13] 參見[日]松原芳博:《刑法總論重要問題》,王昭武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頁。
[14] 同前注[12]。
[15] 參見車浩:《車浩的刑法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頁。
[16] 參見王復春:《論非法侵入住宅罪客觀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斷》,《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17] 參見黎宏:《刑法總論問題思考》(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51頁。
[18] 參見劉根榮:《共享經濟:傳統經濟模式的顛覆者》,《經濟學家》2017年第5期。
1285500783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