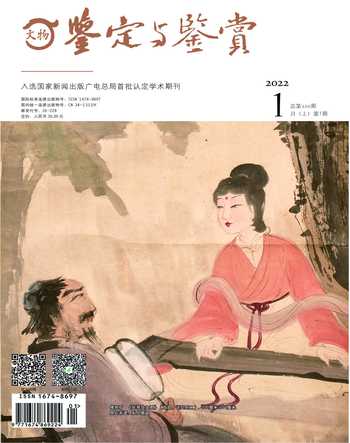文博事業與文物保護、文化傳承之間的關系
李靜

摘 要:文博事業屬于一個國家、民族、社會、群族等多元組織維度下的文化事業范疇,其中文博單位是文化建設的主體。文博事業價值構成與行為導向中包含文物保護、文化繼承的成分,但三者又不能簡單地混為一談。同時,鑒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深邃歷史性、品類廣博性、體系復雜性等原因,理清文博事業與文物保護、文化傳承之間的關系,在“互聯網+”文化語境中顯得尤為重要,將有助于新時期文化建設者、傳播者、創新者之間的互動協同,更好地承擔自身的文化職能。文章將結合實例,論述三者和諧關系下產生的優秀文化產業案例,以供借鑒。
關鍵詞:文博事業;文物保護;文化傳承;“互聯網+”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1.033
1 文博事業在“互聯網+”環境中面臨的復雜競爭
人類文明出現以后,競爭就成為不同國家、民族、地理聚落之間的永恒旋律。無論哪一種競爭形式,人都是發起者與參與者,因此從人或人類的角度出發,競爭的本質才呈現得更加立體與全面。人的基本需求源自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其中物質方面的競爭可以抽象為經濟競爭,精神方面的競爭可以抽象為文化競爭,由于人是物質與精神的結合體,所以經濟與文化之間在理論及現實維度下都是不可分割的。有所不同的是,經濟競爭表面復雜,在全球化格局中,競爭的內容、方式、目的等不斷趨于一致(如能源競爭、金融競爭等),而文化在競爭過程中表現出復雜化—源自不同民族、宗教、地域等屬性的文化既存在矛盾沖突,又在相互接觸中滲透融合,進而衍生出全新的文化形態—這一現象在“互聯網+”文化語境中尤為突出。互聯網技術構建了一種幾乎無法設防的文化競爭環境,便捷的網絡渠道、開放的網絡生態,為排浪式的文化運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外部文化可以輕松地覆蓋互聯網受眾。而文博事業主要面向本地區、本民族文化,遵循歷史時空的線性推進規律,強調文化架構的系統性構建,因此無論在文化傳播還是文化創新領域,都很難抵御碎片式、淺層性的外部文化沖擊。以我國文博單位為對象,在“互聯網+”環境中面臨的競爭壓力主要源自三個方面。
1.1 低水平與同質化建設模式
改革開放40年間,我國文博單位建設取得了斐然成績,僅以博物館數量而言,截至2020年年底已達5788家,加上我國悠久的人文歷史傳承、種類豐富的文物遺產,我國是當之無愧的文博資源大國。但同時,我國文博單位實力非常薄弱:一方面,在宏觀建設上單純注重數量、忽視質量,很多博物館、圖書館等空有名頭,在自身發展與服務社會方面力不從心。另一方面,在微觀建設上形式單一、乏善可陳,如博物館多以文物展示為主,但文物質量、等級較低,且無法深度發掘民族特色文化,所組織開展的文化活動大同小異,難以讓受眾產生良好文化體驗①。整體上,這種低水平、同質化的建設模式,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文物保存、文化展示,距離文物保護、文化傳承尚有差距。
1.2 難以撬動經營性文化產業
文博事業雖然是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但文博單位多為公益性質,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間接性的,需要通過一系列的產品設計、生產、營銷等手段,才能將自身文化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但現實中,文化館、博物館、文獻館、圖書館等文博單位參與市場活動的動機較弱,很少具備文化創意、視覺傳達設計、品牌塑造等能力,很多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資源沉睡在陳列架上,無法形成文化產業優勢,自然就無法撬動經營性文化產業。事實上,不止文化產業如此,工業、農業、制造業等領域同樣存在與文博事業相脫節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中國產品謀求與“國際標準”的一致,經營視域下的概念提出、形象打造、標識設計等迎合“國際流行”,實質上是將文化話語權拱手讓人,無形中造成文博資源價值的邊緣化。
1.3 復合型人才培養能力不足
從博物館規模與數量上看,我國稱得上是文博大國但并非文博強國,這一觀點的產生,除了我國人均博物館擁有比例較低之外,更關鍵的是博物館人才培養能力缺陷。聚焦競爭領域,人才是絕對的核心資本,但長期以來我國博物館人才的培養存在定位不清、特色不明的現象。以高校文物與博物館專業為例,人才培養所涉及的知識體系主要由文物學、考古學、環境學等構成,目的是更好地保護、研究、管理博物館文物實體(實質化文物與紙面化史料)②,而在“互聯網+”環境下如何轉化文物價值,實現文物保護與利用的統一、文化傳承與創新的統一,此類復合型人才相當欠缺。
2 文博事業與文物保護、文化傳承之間的關系梳理
文博事業涉及多種社會組織機構,如紀念館、博物館、圖書館、文物考古部門等,相關組織機構的職能主要包括文物收藏、研究、保護與文物發掘、展示、宣傳等,無論從文化遺產繼承角度還是從文化傳播創新角度來說,都屬于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立足文化產業審視,文博事業、文物保護、文化傳承三者之間并沒有明顯的界限,即文博之“文”,既可以理解為文物,亦可以解讀為文化,而文博之“博”可以確定為“博物館”這一代表性主體。從這一角度出發,三者之間功能交叉、價值滲透、要素融合,所創造的價值都能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然而,從“主要業務”維度出發,三者之間又存在一定差異。
2.1 文博事業旨在打造文化平臺
作為一個社會公益機構,博物館雖然陳列大量寶貴的文物、藝術品,但它并不是一個封閉的建筑。根據我國《博物館條例》的要求,博物館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滿足公民精神文化需求,同時明確表示“國家鼓勵博物館向公眾免費開放”。事實上,在地域空間維度下,博物館實際上是一座城市、一定地區、一段歷史的文化象征符號,承載著所在地人民群眾的共同記憶。因此,博物館除了具有文物保存、收藏、研究等作用外,對公眾開放是體現自身價值的應為之舉。數據顯示,在“十三五”期間,國內有5214家博物館是免費對公眾開放的,這就意味著文博事業發展的基本途徑,就是結合自身文化特質面向公眾打造文化平臺。當然,所謂文化平臺不僅僅是展廳而已,為了優化受眾的參觀體驗,博物館應在建筑空間內進行必要的科技升級,如利用聲光電技術演繹,讓受眾從聽覺、視覺、觸覺等多個方面感受文物帶來的震撼。例如,開封博物館為全面展現宋代市井文化,結合大量文物雕塑、畫作等還原出來的北宋街景(圖1),在群組雕塑構成的人物走廊中,配合光線變化、吆喝聲音等,讓人瞬間產生夢回東京汴梁的體驗。
2.2 文物保護旨在發掘文化沉淀
從文博事業背景出發,文物保護的內涵是相當豐富的,不能止步于“保存文物、安全防護”的程度,重心應放在文物所蘊含的文化沉淀發掘上。
第一,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與利用。此類文物屬于遺址性質文物,無法通過空間轉移的方式放置在博物館建筑內,但其歷史價值、紀念價值、文化價值等相當豐富,不能任其暴露在毫無保護的情境中。同時,相對于可轉移文物,此類文物往往質量、規模較大,如古代城墻遺址、墓地、崖刻等,如果簡單地采用封閉性手段進行保護(如建立圍欄),容易與城市規劃建設產生沖突,且文物自身的歷史氣息與日新月異的現代文化不相匹配。鑒于此,深度發掘此類文物的文化沉淀價值,通過文旅融合的形式,將其融入現代化城市場景中,不僅實現了文物保護目的,還能夠形成社會效益、生態效益。例如,我國西安、洛陽、開封等古都,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古代城墻遺址,可通過建立城墻文化公園、廣場的方式,將其中的文化底蘊發掘出來,滲透到現代人的生活、現代化城市群中。在此基礎上,建立與不可移動文物相關的展廳、添加歷史人物雕塑、修復周邊生態自然,有助于提升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
第二,館藏文物研究、分類與管理。館藏文物通常指具有較高文化、藝術、歷史價值的文物,可移動性是基本特點,也是館藏的前提條件。此類文物種類多元,包括書畫、瓷器、石器、錢幣、絲織物等,其中不乏國寶級的展品,是文物保護工作的重點。博物館需要聯合政府部門、考古單位等進行聯合發掘,在文物出土之后,博物館要廣泛收集文獻資料、聯合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展開文物研究,界定其年份、特征、等級,按照文物屬性(金屬、瓷器、絲織物等)做好分類,為下一步面向公眾展示做好準備。此外,館藏文物的管理工作應久久為功,不得絲毫懈怠,每個博物館管理人員都要具有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態度。
第三,社會文物普查、收購與建檔。文博事業的發展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支持,事實上,我國作為文物大國,有相當一部分文物流落在民間,成為私人藏品。在眾多文物中,既有價值連城的古物,也有凝聚歷史年代特色的藏品,根據我國《文物保護法》的規定,絕大部分可移動文物歸屬國家所有,為了避免重要文物非法交易、收藏人發生法律風險,博物館有義務對社會文物展開普查,并對其中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文物進行收購,這本身也是一種文博事業建設行為③。同時,從發掘文化沉淀角度出發,回收文物不能一藏、一展了之,還要對社會文物做好建檔工作,表明文物屬性、來源、分布等,這一工作可以為深度發掘地域文化內涵提供強大支持。
2.3 文化傳承旨在展示文化魅力
文化傳承在時間維度下,不僅意味著今人從古人處“接過來”,還意味著今人要向來人“傳下去”,讓更多的中華兒女了解民族文化、歷史文化,這是文博事業的光榮使命,也是博物館的具體工作之一。換句話說,文化傳承不僅是將一份民族記憶原汁原味地留下來,還應該積極尋求當代人喜聞樂見的展現方式,更高效、更廣泛地傳播出去,以培養文化傳承的新生力量④。以非遺為例,國家及地方都在探索非遺文化產業化發展模式,旨在讓古老的文化“活”過來,向世人展現它別具一格的魅力。近年來,在“互聯網+”優勢的作用下,國內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文化傳承類影視作品,如《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國家寶藏》(電視綜藝)、《典籍里的中國》(電視綜藝)等,讓世人了解到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同時也進一步促進了文博事業發展,提高了人們文物保護意識。
整體上,文博事業、文物保護、文化傳承之間形成了相互協同的關系。其中,文博事業為文物保護提供實現途徑、為文化傳承提供資源支持,而文物保護是文博事業、文化傳承的前提,文化傳承進一步彰顯了文博事業、文化保護的價值。
3 一個典型案例:河南衛視“奇妙游系列”
在“講好中國故事”的背景下,文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們是中國故事的忠實記錄者⑤。以文物為媒介展開文化、事件、人物等方面的深度發掘,引入新媒體表達的方式,足以為現代人奉上一道精神大餐,文博事業、文物保護、文化傳承深度整合的價值也能夠得以彰顯。
2021年河南衛視推出的“奇妙游系列”火出圈際,以中華民族傳統節日為脈絡,目前已經推出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五個單元。與傳統節日類電視節目不同的是,“奇妙游系列”通過一組特殊人物將五個單元串聯起來,以彰顯“游”這一主題。而這一組特殊人物,正是由河南省博物院的樂舞俑演化而來的“唐宮小姐姐”。2021年河南電視臺春節晚會《唐宮夜宴》首次推出了唐宮小姐姐的形象,實現了對樂舞俑文物的現實復刻,從體態到服飾、從發型到妝容,宛如文物復活,給全國的文化受眾帶來了極大震撼。
此外,被外交部、《中國日報》海外版等推薦的端午奇妙游水下舞蹈《祈》,創作靈感源自東晉顧愷之的名作《洛神賦圖》,而這一幅畫作可謂國寶級館藏文物。在七夕奇妙游單元中,舞蹈《龍門金剛》再次驚艷觀眾,六個金剛力士的形象源自龍門石窟(不可移動文物)的佛教形象,通過虛擬技術、新媒體技術的塑造,已經成為與唐宮小姐姐齊名的文化符號,而在這一舞蹈節目的背后,得到了龍門石窟研究院的大力支持,為節目組提供了相近的文物研究文獻、資料。
河南衛視“奇妙游系列”的成功,表明文博事業與文物保護、文化傳承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三者相互協同,能夠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巨大賦能。一方面,文博事業發展為文物保護提供了有利條件,實現文物豐富、管理有序、利用有效。另一方面,文博事業的興盛發展,可以很好地激活人們向傳統文化汲取靈感的意識,自覺地在文化生產中履行文化傳承責任。
綜上所述,理清文博事業、文物保護、文化傳承之間的關系,將有助于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在全世界范圍內形成更大的影響力,一系列文化產品就此誕生,為經營性文化產業鏈的建構奠定良好基礎。
注釋
①崔卉.博物館:在文化傳承、創新、發展中本固枝榮[J].大眾文藝,2017(4):58-59.
②王慧茹.文博事業與文物保護、文化傳承之間的關系[J].赤子,2018(23):60.
③張美東.簡析加強縣級博物館文物保護利用—以林口縣博物館遺存文物為例[J].邊疆經濟與文化,2017(7):117-118.
④馬嘉憶.文博事業與文物保護、文化傳承的關系研究—以吉林市城市發展為例[J].黑龍江史志,2012(22):49-50.
⑤孫月.新時期博物館在傳統文化傳承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J].文物鑒定與鑒賞,2020(18):110-112
sdjzdx202203231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