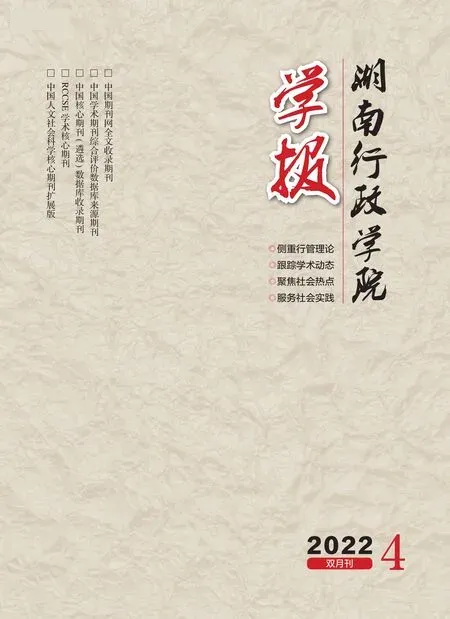當代鄉村書寫倫理困境下韓少功的鄉村詩學的建構
廖小嬋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鄉村”是鄉土中國現代進程中最廣大的現實,也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各種現代話語和文學書寫中的巨型“他者”[1]。韓少功曾說,“這個時代變化太快,無法減速和剎車的經濟狂潮正鏟除一切舊物[2]”,而在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文學的“根”應深深扎根于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韓少功對鄉村文化的體悟,始于上山下鄉的插隊歲月。不管是《馬橋詞典》中對當地插隊生涯體驗的描述,還是《山南水北》中對山野自然和底層民間深刻的體察,還是在《長嶺記》中充當“義務守夜人”與知青歲月的深情回望,韓少功都在重新厘清文學與鄉村的關系,將鄉村傳統和現代文明、漢語和方言碰撞在一起,將“問題中國”轉向了“理解中國”[1]。
盡管鄉村書寫都喜歡從作者和他者世界的接觸講起,但似乎再也沒有發生像魯迅《祝福》中“我”遭遇祥林嫂那樣的“事件”。今天,農村的面貌和問題已經發生了變化,但“祥林嫂”事件持續散發著意義。而這一偶遇被韓少功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主題和當代的日常現實來處理。鄉土小說的展開始于作者對破碎瓦片般日記的清理、拼接、修補,就像一個義務守夜人守護遍地月光一般[3]。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建設美麗中國為目標,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指導原則,對于今日在世界范圍、歷史長河中重新定位鄉土中國、治理鄉村生態環境、重塑鄉村詩學具有重要的理論依據和實踐價值。
一、當代鄉村書寫的倫理困境
在以城市為主導的語境下,鄉下人在城里人眼里是“愚”的:鄉下人在馬路上聽見背后汽車連續地按喇叭,慌了手腳,東避也不是,西躲也不是,司機向著那土老頭,啐了一口:“笨蛋!”[4]10隨著近代鄉村生產力的發展,我們無法無視科技對傳統人文生態(人情倫理)的消解與解構,以及對新的人文生態(物化倫理)的建構。鄉村生態思想研究已成為“顯學”,有對鄉村生態危機和文化根源的反思,也有對鄉村生態環境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關系的探尋。21世紀以來,鄉村生存和發展的現實,向人們提出從鄉村出發去理解中國的重大課題。
(一)鄉村發展下的認知錯位
人類對生物圈的影響正在產生著對于環境的壓力并威脅著地球支持的生命的能力[5],正是資本控制下對鄉村資源的瘋狂開發與揮霍,導致了自然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認知錯位,使得鄉村書寫失去了以往的活力和力量。
首先,鄉村書寫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是發展書寫的困境,即無法把握當下,無法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塑造出站得住腳跟的新型農民形象。鄉村書寫自誕生以來就與發展書寫結緣,有時描繪的是鄉村過去與現在的變化,有時呈現的是鄉村主人公依靠自身、依靠自然所產生的價值和滿足感,有時又是主流價值觀的引導,使得鄉村書寫不再處于邊緣地位。但當今鄉村書寫中引領一時的“朱老忠”“梁生寶”“江姐”“楊子榮”新農民英雄人物普遍消失,很多作品都以鄉村的破壞和消逝為結局,鄉村發展中環境破壞、資源消耗等弊端都顯露出來:如莫言《四十一炮》中農村改革的沖突和裂變,格非《望春風》中江南鄉村的演變,阿來筆下《機村史詩》中藏族村莊的發展流變。鄉村發展的盡頭似乎就是被現代文明所泯沒。
其次,新的鄉村現實問題越來越多,鄉村變化也不斷被記錄和解釋,但它無法被我們的認知所消化,所以一種無力感、衰落感就會蔓延開來。閱讀當下的鄉土小說會發現,鄉村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并未被有效地記載,或是所記載的都是讀者所已知的。這樣已知的作品并不像《活著》《平凡的世界》那樣令人心潮澎湃,而這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鄉村書寫的整體現狀。格非針對這一質疑發聲,“有的讀者批評我對當代鄉村生活的問題沒有提供多少借鑒的意義……我再次強調,描寫當代的鄉村社會的空間不是我的任務,也不是我要做的,我沒法在小說里和讀者講它到底是怎么回事[6]”。這些質疑都說明作家沒有做好面對鄉土的變化的準備,進而導致作品直面歷史和日常現實問題力度的削弱。當代鄉土社會正處于快速發展的時代,但它為何發展,何以發展都已經遠遠超過人們的經驗范疇,那些涉及到鄉村發展的本質根本無法在歷史長河中找到原因。
列夫·托爾斯泰曾言,“(作家的責任)是經常地、永遠地處于不安和激動之中,因為他能夠解決與說明的一切,應該是給人們帶來幸福,使人們脫離苦難,予人們以安慰的東西”[7]。鄉村書寫者應走出自身局限,擴大視野和題材范圍,重新建構和定位中國鄉村,處理好文學與鄉村的關系。
(二)城鄉解構下的人性物化
近年鄉土中國城鄉二元化的格局正被城鎮化進程所打破。正如馬克思所言,“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日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卑劣行為的奴隸”[8]。在鄉村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最大的錯誤在于對大自然采取了對立乃至敵視的態度,破壞了人與鄉村的生態關系、人與人的生態關系等等。其中,最為鮮明的表征是環境異化下的物質生命化、人的生命物質化。
第一,近現代以來,在西方先進城市文明的肆意渲染下,在中國反封建的大旗下,中國古代傳統鄉村文化不斷被解讀為“無知、落后、閉塞”的文化形態;農民被描述為自卑、落后文化的代表,并成為國民性改造的主要對象。費孝通提出, 鄉村社會的生活形式表現為以倫理為標準和依據的“差序格局”[4]29。大量農村人口的遷徙和流動而出現的村莊空心化現象,不僅導致大批鄉村文化精英紛紛遠離家鄉,也造成以鄉村文化為標志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衰落。空洞文化世界里的人們如何處理肉體和靈魂的分裂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人生課題。當今的中國鄉村社會正在由以年長者為主導的前喻文化迅速向以年輕人為主導的后喻文化過渡,年長者在鄉村文化秩序中已被迅速邊緣化[9]。而人性中的真、善、美又驅使人們不得不反思自身身體與靈魂的分裂,其結果是促使人們陷入更加痛苦的精神境遇。
第二,當鄉村不再是過去的樣子,鄉村發展也不再采用過去的方式時,作者對鄉村發展經驗的理解以及賦予這些經驗重要性的方式遭遇了失效,這導致了發展寫作的“倫理俘獲”效應[10]。一直以來鄉土小說除了要寫出鄉村的發展變化,更要強調人的主體性和力量感,鄉村發展依靠的是自然資源和我們自身的力量,這似乎是亙古不變的真理。十七年文學中,趙樹理、柳青、羅廣斌、楊益言、浩然等人的小說都充滿了對勞動的贊美,對新型農民的贊美。但在1990年以后,單純依靠勞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社會整合的任務從道德轉移到了市場[10]。如趙德發的“農民三部曲”《君子夢》《繾綣與決絕》《青煙或白霧》反映的是山東村莊的農民所面臨的道德困境,展現了作家對新型鄉村的不理解和不認可。所以村莊不再是被文學化的鄉土空間,而是政策整合下政治話語的代表。于是,鄉土作家一邊適應鄉村發展的話語,一邊又對發展不滿和批判,那么一種割裂感就會蔓延開來。
總之,中國鄉村小說的敘事存在兩個困境:一是在認知層面上,鄉土小說作家并沒有消化和理解新的鄉土經驗,對鄉村地域性的理解存在嚴重的誤區;二是在人的物化上,鄉村重構書寫似乎只能進行道德、懷舊以及倫理層面的補救,而非直面歷史和當下現實。這種雙重困境有著復雜的社會文化背景,也深刻影響著中國鄉村書寫的成就和發展[11]。
二、鄉村書寫者韓少功如何建構鄉村詩學
鄉村城鎮化、現代化浪潮下,人們對于鄉土小說的消極態度日益加深,很大程度是源于作者無法把握和認可當代鄉村的時代變化,是對鄉村發展本質把握得不自信。那該如何書寫好鄉村,新型鄉村文化又該從哪里入手?
第一,尋找后鄉村時代寫作的路徑,知識體系的更新是必要的。新中國成立以后,鄉土書寫作家的創作理念在很多時候依賴于國家政策、主流意識形態的指引。在資源匱乏的時代,生產和發展是硬道理;而到了今天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使得人民群眾對“軟需求”的渴望日益加深,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更是要求我們更加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當代鄉村中國的面貌越來越多元化,旅游村、示范村、新型社區等層出不窮,于鄉村而言是一種幸運,說明國家有意識地去反哺鄉村;而對鄉村書寫者而言是困境,代表著“鄉村”意義的解構、方向指引的缺失。但韓少功敢于正視當下的后鄉村現實,其作品中有大量巫楚文化的方言俚語和風俗民情。如《長嶺記》中寫到當地口頭禪是“鬼”“鬼咧!”或者是“好大一只鬼”;有關“世上有沒有鬼”的爭論,他們認為“火焰高”的人就看不到鬼,年輕的、讀書的、城里來的人就是“火焰高”的人;在當地也流傳著一個傳說,五神廟中的五位神主與敵軍大戰,打退了日本人、美國人,保佑著世世代代村民的安全;在方言中稱碘酒為“碘酊”,紅藥水為“紅汞”,肥皂為“堿”,打死你、弄死你為“武死你”。同樣,《爸爸爸》中也提及了一些落后卻有趣的習俗,如罵人的時候在胯里摸一下,這樣能增強語言的毒辣性;迷路的時候,要趕緊撒尿罵娘,據說這樣岔路鬼就不會近身等等。于是韓少功用“武”“坨坨”“逞驁”“擂”等古老的具有湖湘特色的方言,“三根香結拜”“螞蟥聽水響”等風俗文化為鄉村籠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更為重要的是,作家用現代的眼光去看待傳統巫楚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弊端,惟其如此,才能重新認識鄉村的現代化發展。如關于“打裹包”的描述,家家戶戶帶一張草紙或者一片荷葉來吃酒席,沒吃完的就連湯帶料打包回去。這一特別的農村習俗讓人發笑又覺得無奈,“這哪是吃酒席,差不多是分豬潲吧……不無心酸:可憐天下慈母心![3]”70年代隊里有收化肥(人糞)的習俗,化肥要按質按等級計算,所以常出現“前幾天吹牛說他家條件好,長期是吃茶油、豬肉和面條的,后幾天等隊里收化肥的時候,就又換一套說辭”令人哭笑不得的場景。這些古老的、具有時代特性的農村習俗在現代鄉村書寫中顯得滑稽可笑、無所適從。因此,在更為復雜的新型鄉村框架中,需要更為寬泛的視角、敏銳察覺變化的能力,和直面新的現實景觀的勇氣。
第二,當代鄉村書寫并不缺乏關注現實的勇氣,但缺少將這種關注提煉為本質的敏銳度和厚重感。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以“以人民為中心”為發展思想,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影響下,作家韓少功除了有精英知識分子的理性思考,更有站在底層農民立場上的民間關懷、接納和理解,以及面臨鄉村中國各種不適的審視和思考。作為汨羅長嶺文化的“闖入者”,他用過濾的現代眼光發現了這片土地的落后和閉鎖,同時也發現了這塊土地上地方文化的生命力與活力。如在作品中民眾對待政治運動的態度是不滿的,甚至本應自由的婚戀都逃不開以利益為驅動的“例行公事”:團支書李簡書和戴鐵香的戀愛關系,因為戴家的政治成分問題而困難重重;新來的公社書記“鐵姑娘”本來是組織重點考察和培養的對象,但因為她愛抹雪花膏、燙劉海,展現出與傳統“鐵姑娘”截然不同的一面,導致前程阻力重重。作家正是通過年輕人的婚戀,將政治話語反駁消解,從日常、現實、人性多維度審視嚴肅的政治運動。雖然人們現實生活艱難,但閃耀的同樣是干部、民眾的人性光輝:桃林公社的書記“曹明天”捉到賊,反而擔心起賊的生活起居,“我是你的書記,搞得你沒有飯吃,是我的錯[3]”;自己的煤要留給劉爹爹、四婆婆,還要多貼一點錢。面對人性的裂縫,韓少功放棄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優越感,更多是從民間的視角平等地看待底層人民的艱難生存和落后思想。
第三,回歸作家本位,同樣也是必要的。當代鄉村書寫者大多屬于鄉愁派,但在書寫過程中經常存在越位現象,即一邊以理性主義自居,一邊懷念逝去的鄉村;一邊認同鄉村的變化發展,一邊又不滿發展過程中鄉村的破壞。在情感上同情和親切底層農民,希望平等對待不同群體;但又因為啟蒙者的文化優越感作祟,無法用平等的姿態去保留和記載當地農民原始的生命活力。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的新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引下,鄉土書寫者韓少功嘗試回歸自己作家的角色和本分,不僅有對歷史和日常現實的關注,同時也有知識分子理性的決絕、洞穿現實的能力,平靜關注鄉村命運的作家書寫責任。韓少功的精神原鄉是楚文化源遠流長的湖南汨羅,游離于正統文化之外的方言土語、民俗風情在書寫中營造了極具湖湘風味的美學效果。其中既有拋秧把田里的泥漿砸出一個個笑聲和罵聲的場景,也有育杉秧、捉肉蟲和甲蟲、捉鱔魚、放鴨、賽龍舟等農村勞作娛樂場景的描寫。另外,農民樸素的生死觀——“木匠、砌匠、剃匠、篾匠死不得,不然大家不方便,好人也應該有點壽”,也被韓少功敏銳地察覺到,并把此提煉到生存哲學的高度——農民把一粒種子撒進土里,結出果實;把自己丟在地里,長出墳墓。而當作家面對當地落后的“牛頓是女的”“地球不是圓的”“婚鬧”“打裹包”的思想和習俗時,放低精英知識分子傲慢的姿態是關鍵,平等地記載著這些令人發笑但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畫面。若當代鄉村書寫不再流于表層鄉愁情緒的宣泄,其實于鄉土而言也是一次成功的回歸,也能從鄉村日常中發現充滿人情和理性的中國。
三、新的鄉村書寫的文化出路
傳統意義上的鄉村逐漸走向“虛空化”是無法否認的事實,趙本夫《即將消失的村莊》直接以“即將消失”明示[12]傳統鄉村以及鄉村民俗文化的時代結局。新世紀鄉村書寫的“新”,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而且鄉土中國的轉型、中國城鄉關系的發展變化豐富了“新”的內涵。新時期如何理解鄉村,已經成為理解中國、現實及世界最重要的視角之一。韓少功的《長嶺記》聚焦于普通農民瑣碎的日常生活,以新的歷史眼光掃描和表現鄉村農民的生存現實,重構地方文化和人文傳統的認同。我們該如何為鄉村找尋到曾經的意義和未來的出路?
首先,新世紀鄉村書寫的目的不是簡單的歷史復刻,而是基于新時代語境下探討人與鄉村、歷史與現實的關系,真誠表現中國新農民的生活史、精神史和心靈史,以此重建對地方文化和傳統文化的認同。韓少功的作品中既有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爸爸爸》的雞公寨充滿著國民劣根性的蒼老遺傳,丙崽是這個蒙昧社會的畸形產物;又有向民族歷史文化深處汲取力量的趨向,展現出被忽視的地方文化獨有的活力:汨羅長嶺大隊的人們,他們的生活方式、民風俚俗、觀念情感從來都是一成不變的——打鼓打得是“鳳點頭”“獅子滾繡球”的花樣,吃飯用的是剁辣椒或者干辣椒咽飯,叫小輩或同輩的昵稱一般是一個字再綴一個“子”,把紅薯叫作“肥”。這種儀式被社會和文化系統賦予一種特殊的規定性,也就是說許多儀式的功能是事先被規定的社會意義所預設[13]19。因為長嶺人民所面對的是原始地方文化所規定的、參與者所認可的“神圣”,無論這種認可屬于個人自愿還是帶有集體強制性意味,迷信儀式的意義在形式之中和行為之前已經鑄就和確定。對沒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來說,“文化記憶”主要以非文本的形式得以流傳[14]。絕大多數的民族儀式屬于某一個民族或族群歷史傳承的產物,即使是同一個民族或族群的人們也已經無法真正還其“原生形態”[13]5。在當今現代化語境下,我們要增強自身的文化自信和文學自信,轉身向鄉村地域和歷史敘事下汲取經驗,努力找尋鄉村人文傳統的新鮮感,站在新的歷史的結點講好鄉村中國的故事。而講述鄉村中國故事的主體,不只有精英階層的知識分子,還有當地的鄉村文化精英。長沙市岳麓區蓮花鎮龍洞村創辦的龍洞詩社,最初只是為了把愛詩歌的一群老人聚在一起,充實晚年生活,但慢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加入了詩社。在龍洞,國事入詩,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開設專欄傳遞正能量;村規民約也編成了詩,用吟詩作詞這種傳統又大眾的方式,弘揚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農民詩社唱響了鄉村文化之歌!
其次,“人民性”就是韓少功創作的活力。人們組成一個統一的社會,其根據在于他們以共同的或一致的思想方式看待神圣的世界以及與世俗世界的關系,在于他們把共同的觀念化作共同的實踐活動[13]74。很多鄉土作家離生活很遠了,但韓少功仍像候鳥一樣飛回汨羅過起真正的鄉村生活,主動去接近農民、鄉村生活和鄉村文化,努力去填補新時代鄉村生活的虛空。正如作家所言,“真正偉大的自我,無不富含人民的經驗、情感、智慧、愿望以及血肉相聯感同身受的‘大我’關切”[15]。因此,他在鄉村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尋找湖湘巫楚文化魅力的同時,還能保持作家的本分,理性探索巫楚文化的荒謬怪誕,展現現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例如,當時的鄉村家長們根本無法理解“教育革命”的意義,對撿茶籽、扒松須、挖菜土極為反對,這導致學生輟學情況日益嚴重;哪怕是留在學校上課的學生,對新來的老師和課堂學習也全不在乎,睡午覺的時候也老是講話和打鬧。值得肯定的是,韓少功對底層人民的書寫并沒有從道德層面給予更多價值判斷,而是尊重生活的質感,注重從生活的邏輯和民間的邏輯理解底層人的生存[16]。另外,作品重新復寫了一些封閉落后環境中人的愚昧和鄉村的迷信文明,散發出一種荒誕、神秘和魔幻的色彩:搶救一只誤食農藥的雞,用剪刀剖開食袋洗一洗,再縫合起來,吹一口氣,公雞就活了;在農村不能打蛇,打死一條,明天會有十幾條來報仇。作家對此是持理性警覺的態度,正如《爸爸爸》的結局,一個婦女走過來對另一個婦女說“這個裝得潲水么”,于是把丙崽面前那半個壇子旋轉的光流拿走了。韓少功對鄉野巫楚文化的思考和批判,不僅增加了小說的歷史感,也由此上升對人類生存樣態的探討[17]。
最后,農村類非虛構鄉村寫作依托的是“田野調查”類的工作方法,盡可能客觀地記載鄉村記憶,強調作者的在場。尊重差異、尊重他者,是文學和藝術的本性。因此,要給予鄉村聲音足夠的話語空間和想象空間,呼喚一種新的鄉村詩學——真正地探入事物深處和詩性思維,看到文化背后的生態、生活和靈魂。于是,當描寫鄉民面對城市文明涌入村落的心理時,作家用充滿詩意的場景描寫“天上星海,地上燈河,交相輝映[3]”,沖淡了鄉民內心的局促不安。何為“詩學”,“詩”可以看作人類所有人文、社會活動的總和,而“學”指的是學科化。有人會疑惑將鄉村寫作學科化是否會造成其凝固化?其實不然,文學性是敞開與流動的,這種文學性、文化關懷的眼光有利于將人放在特定歷史現實語境下的存在化和具體化,而這一切最終指向的是如何解答當代人的存在的困境。于是當代鄉村寫作所面臨的,不僅是理性探索鄉村地域人文傳統的新鮮感,而且要求鄉土書寫者創造出新的鄉村詩學和文化關懷。
因此,在新世紀中國鄉村正發生劇烈的現代性變化之時,正如錢理群先生建議的“重建文學與鄉土的血肉聯系”和作家李洱所倡導的“重建小說與現實的聯系”,我們一方面需要作家進入鄉村以感知的方式重新了解鄉村生活;另一方面需要作家的智性參與,依托新農村生活的認知,重新找尋鄉村書寫的新可能。在今天以“中國經驗”講述“中國故事”已經成為文學創作的一個基本要求,是我們面對世界文學與西方經驗的一次自我身份的重新確定,是中國文學的一次自我覺醒與真正獨立。
四、結語
中國鄉村與鄉土小說存在一種“異質同構”的關系。當今鄉村正面臨著“鄉土中國”向“城鎮中國”的社會轉型,以“人情”為紐帶的互助式鄉村關系[18]的裂變,因此必然引發鄉村書寫的文學新變。而韓少功對“鄉村詩學”意義的探尋,猶如一位虔誠的守夜人。他依托湖南汨羅的知青下鄉經驗所構建的鄉村詩學,既是面對都市文明的個人選擇[19],也是在城鎮化進程中建構鄉村生態烏托邦的勇敢嘗試。他指向鄉村書寫這一命題,必然要承受絢麗楚文化沒落的精神危機,甚至會存有王國維先生那樣的“文化殉道主義”之感想。而作為鄉土書寫者,韓少功始終關注城鄉的發展變化,既以農民的身份無聲地抵抗鄉村中國所面臨的各種不適,又以作家的身份返回到湘楚文化的大地上,深度挖掘鄉村楚文化背后的生態、生活和靈魂,發掘鄉村與現代的雙重陷阱,挖掘湖南楚文化的文脈結晶,將湖南人的歷史沉思和精神歸宿寄于山水又高于山水,旨在為鄉村詩學提供一種新的書寫方式。
在中國鄉村轉型的重要階段,新的中國故事正在不斷發生。因而,在習近平新時代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鄉村書寫要善于從社會轉型和變革中汲取力量,社會的快速發展應當為鄉土小說的發展注入更多的資源和能量,但如今鄉土小說反而走入自我鎖定的壁壘,這是重建一種新的鄉村書寫需要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