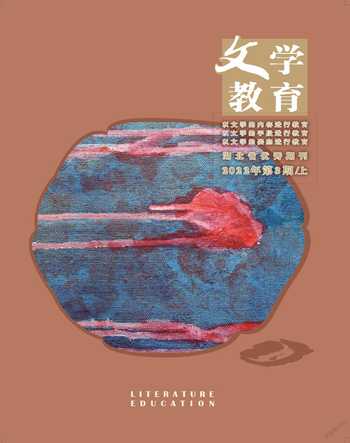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女性的雙重囚籠
陳磊
內容摘要:《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國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內羅絲的成名作。全書通過芒果街上少女埃斯佩朗莎的童年記憶,用貌似“詩話”的語言控訴了拉美裔女性遭受的白人文化和男權社會的雙重壓迫。本文從族裔文化和女權主義兩方面嘗試解讀雙重壓迫的歷史原因、社會原因以及拉美裔女性的反抗。
關鍵詞:《芒果街上的小屋》 拉美裔女性 雙重壓迫 族裔文化 女性主義
《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國作家桑德拉·希斯內羅絲(Sandra Cisneros)發表于1984年的一本詩小說。“芒果街”是一個拉美裔聚居的貧民街區,這里貧窮、混亂、遭受種族歧視并且以男權為中心,芒果街上的女人們遭受著白人社會和男權中心的雙重歧視。
一.少數族裔被邊緣化的“囚籠”
米歇爾·福柯在討論“權力與話語”的關系時指出“話語即權力”:所有話語、知識都是權力的某種表述,而不是純符號的、純文本的意指過程。[1]掌握了權力就意味著掌握了話語權,因為語言和知識可以用來為鞏固權力提供服務。反之,知識又能產生權力,因為你的認知決定了你的行動范圍。美國白人文化一直都是美國的主流文化,擁有絕對的話語權;而少數族裔由于政治、經濟地位的低下很少有發聲的機會。直到20世紀60年代,后現代主義的興起開始打破“邏各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傳統與權威逐漸被消解,多元文化被提倡,少數族裔“開始嘗試解構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霸權,擺脫白人強加給他們的弱勢群體、邊緣人的身份,重新審視社會上的道德規范和審美標準,反對一切白人主流文化下不合理的陳規舊律。”[1]在此后現代語境下,族裔女性比如非洲裔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所羅門之歌》、貝爾·胡克斯《詩集:我從不哭泣》、華裔女性作家譚恩美《喜福會》、湯亭亭《女勇士》等打破長久以來被壟斷的話語權,開始為自己的族群發聲。1984年墨西哥裔女性作家桑德拉·希斯內羅絲發表小說《芒果街上的小屋》,全書以“小屋(房子)”為主題,展現了美國拉美裔在多元文化語境下追尋文化身份過程中的苦澀與不屈。
德國哲人海德格爾曾引用“人,詩意地棲居。”魯迅先生曾嘆“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杜甫在窮困潦倒之際不忘“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房子這個空間意象不僅是身心的避難所,也是身份認同(identity)的象征,更是權力(話語權)的象征。但是在《芒果街上的小屋》里,房子(包括芒果街)卻像是西西弗身上背負的“巨石”,是約束和禁錮少數族裔的“囚籠”,是他們被排斥被孤立的枷鎖。小說一開始,小女孩埃斯佩朗莎就說“芒果街上的房子是我們家的,再也不用付房租,再也不用與樓下的人家共用后院,再也不必害怕發出噪音而小心翼翼,再也沒有房東拿著掃把猛敲天花板了。盡管如此,芒果街上的小屋依然不是我們心里想要的房子”[2],因為“房子很小,是紅色的,前面鋪著窄窄的臺階,窗戶窄小得讓你覺得它們好像是屏住了呼吸。有幾處墻皮脫落,大門鼓脹得要使勁推才能進去”[3]。在這里,被“物化”的小屋是像埃斯佩朗莎這樣的少數族裔貧窮、卑微的標簽,房子的破爛不堪暗示了拉美裔生活的艱辛與多舛。文中埃斯佩朗莎想要留在象征白人社會的學校食堂吃飯,卻遭遇了大嬤嬤的懷疑,“那棟嗎?她說,指著一排丑陋的三戶式公寓樓,那里是衣衫襤褸的人都羞于走進去的地方。是的,我點頭,盡管我知道那里不是我的家。我哭了起來。”[4]此時,房子與埃斯佩朗莎的命運緊緊地裹挾在一起,他們的處境一樣尷尬屈辱、毫無尊嚴。與芒果街不同,富有的白人們住在高高的山上,他們享受著陽光雨露,全然不知低洼處芒果街上人們的艱辛與疾苦。“那些住在山上、睡得靠星星如此近的人,他們忘記了我們這些住在地面上的人。他們根本不朝下看,除非為了體會住在山上的心滿意足。”[5]房子反映的身份上的差異,深深撞擊了小埃斯佩朗莎的心靈。由于芒果街上的小屋帶給埃斯佩朗莎夢魘般的屈辱和不堪,她一直夢想著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她找伊倫妮塔算命的時候,
“有房子嗎?我問,我是因為它才來的。
啊,是的,心中有一所房子。我在心中看到一所房子。
那是房子嗎?”[6]
……
“心里的一所房子,我是對的。”
……
“一所新房子,一所心造的房子。我會為你點上一只燭。”[7]
埃斯佩朗莎對房子的執念反映了她想要逃離芒果街和對自由平等生活的強烈愿望,也是作者希斯內羅絲希望少數族裔掙脫被轄制被歧視的“囚籠”獲得“平權”的強有力地吶喊。
書中有一個細節:埃斯佩朗莎有一個只有“一周朋友關系”的朋友——貓皇后凱茜。之所以只有一周朋友關系是因為擁有白人血統的凱茜一家下星期二要搬離芒果街。“他們要從芒果街向北搬遷,離開這里一點路,在每次像我們這樣的人家不斷搬進來的時候。”[8]其實在美國,由于移民的涌入以及多元文化的盛行,不少白人持有“移民威脅論”,他們認為移民及其激發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在消解連接共同國家的紐帶,降低共同的國家使命意識,使美國面臨被巴爾干化的危險。塞繆爾·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中擔心:由于拉美裔移民的涌入、次國家認同的強化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盛行而導致盎格魯-新教文化在美國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動搖。[2]為應對來自其他文化的挑戰,亨廷頓積極倡導強化對盎格魯-新教文化的認同。在他看來,拉美裔(特別是墨西哥裔)移民的涌入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盛行對美國國家特性構成挑戰,這些挑戰可能導致美國變成一個兩種文化、兩種語言的社會。
面對強勢的白人文化,面對日益高漲的“移民威脅論”,面對這窒息的“囚籠”,是逆來順受?還是奮起反抗?作者希斯內羅絲在文中給出了答案。在《四顆細瘦的樹》里,象征拉美裔的四棵樹“它們的力量是個秘密。它們在地下展開兇猛的根系。它們向上生長也向下生長,用它們須發樣的腳趾攥緊泥土,用它們猛烈的牙齒噬咬天空,怒氣從不懈怠。這就是它們堅持的方式。”[9]細瘦的樹下是龐大的根系,看似平靜的表面下蘊含著巨大的力量。“么么有條灰眼睛的狗,一條有兩個名字的牧羊犬,一個英文名一個西班牙名。”[10]離開故土來到美國求生的拉美裔用對拉美文化的堅持和堅守頑強地對抗著各種歧視與排斥。
拉美裔和其他少數族裔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根,他們會掙脫“囚籠”在美國這片土地上創造自己的奇跡,就像博爾赫斯在《雨》里寫到:這蒙住了窗玻璃的細雨 必將在被遺棄的郊外 在某個不復存在的庭院里洗亮架上的黑葡萄。
二.女性被約束的“囚籠”
后現代主義打破的不僅僅是“西方中心論”,也打破了“男權中心(androcentrism)論”,喚起了女性意識的覺醒。《芒果街上的小屋》不僅是一本族裔小說,更是一本女性主義小說。在全書44個章節里,作者一共塑造了29個女性,她們年齡各異,性格迥然,卻都被禁錮在芒果街這個以男人為中心的地方,卑微又堅韌地生活著。弗吉尼亞·伍爾夫早在1928年《一間自己的房間》里寫道:女人要想寫小說,必須有錢,再加上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可是芒果街上的女人們從來都沒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她們被禁錮在房子里,像折翼的天使倚在窗邊凝望外面自由的天空。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II》的第一章《童年》開篇寫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經濟的命運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會內部具有的形象,是整個文明設計出這種介于男性和被去勢者之間的、被稱為女性的中介產物。唯有另一個人作為中介,才能使一個人確立為他者。[3]在漫長的歷史文化進程中,人類社會形成了以男權為中心的文明。男權文化占據著統治地位,男性作為第一性一直處于社會的中心;作為“第二性”的女性處于受支配的附庸地位,被男性控制操縱,沒有存在感,沒有話語權。比如在英語里,“歷史”這個單詞是“history”,是“他的故事”而不是“herstory”(她的故事):男人是歷史的參與者和編撰者,而女人向來都是歷史的是缺席者。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描述了“凝視”模式:管理者通過“凝視”的可見性,管理轄制下的居民。邊沁的“全景監獄”就是利用“凝視”模式,一個中心暸望塔和數個環形單人監獄,不管管理者在場還是離場,都能對囚犯起著震懾作用。而幾千年來,女性在“男權”的“凝視”下逐漸失去自由,她們的空間已不是她自己的身體可以認識和自由支配的領域,而是一個囚禁她的封閉的監獄。
20世紀60年代后現代主義的興起開始打破舊的文明秩序,以男性為中心的意識形態開始被人質疑,原有的男女二元對立關系開始消解,人們開始重新看待兩性關系,越來越多的女性打破沉默開始為女性特別是被邊緣化的女性吶喊。比如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的《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瓊·里斯的《藻海無邊》分別從文學評論和文學作品的角度解構了奧斯汀的經典《簡·愛》。她們沒有把目光放在按照男權社會要求下完美的簡·愛身上,而是把目光鎖定在那個受男權、宗法壓迫的“瘋女人”伯莎身上。而在《芒果街上的小屋》里,希斯內羅斯借埃斯佩朗莎之口,用看似輕松童真的筆調,講述了一個個被禁錮在小屋里的拉美裔女性屈辱的故事。
在父權制的的社會,女性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都受到男性的壓制,她們被剝奪了所有和男人一樣的權利包括財產權、受教育權、婚姻自由權等,更有甚者失去人生自由。幾乎芒果街上所有的女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束縛和限制,而房子就是約束和禁錮她們的牢籠:被丈夫強迫結婚的曾祖母難以解開心結而一生在窗邊凝望;推銷雅芳的瑪琳在嬸嬸下班回家前不能出門,因為她要照顧表弟家的小妹妹們;曾經漂亮而健美的瓜達盧佩嬸嬸因為病重又丑又瞎,只能躺在床上等待生命的終結;聰明的鷺鷥兒被丈夫遺棄只能搬到芒果街和母親住在一起。
芒果街上的女性面對社會和家庭的雙重壓迫,除了屈辱地忍受,還有令人欣喜地自我救贖和無聲反抗。她們通過詩歌、通過知識反抗著社會和命運的不公,為爭取自由獨立,為擁有自己的空間不懈地努力。失去母親的阿莉西婭雖然被父親強迫待在家里為兄弟姐妹準備早餐,但她并沒有放棄自己的夢想,堅持每天乘兩趟火車和一趟巴士去上學,因為只有上學,才是她獲得知識和重獲自由的唯一途徑。瓜達盧佩嬸嬸雖然重病臥床,但是她仍然鼓勵埃斯佩朗莎寫詩,因為她知道,只有知識才可以讓埃斯佩朗莎擺脫在芒果街的悲慘命運。她在臨終前對埃斯佩朗莎說“記住你要寫下去,埃斯佩朗莎。你一定要寫下去,那會讓你自由。”[11]正是有了這些人的激勵和典范作用,埃斯佩朗莎有了追求自由獨立的動力。她逐漸意識到“寫作使精神自由”,她開始拿起筆書寫,為了自己,為了芒果街的女人們,為了自己的族群,更為了整個少數族裔爭取到更多的話語權。
“你離開時要記得為了其他人回來。一個圈子。懂嗎?你永遠是埃斯佩朗莎。你永遠是芒果街的人。你不能忘記你知道的事情。你不能忘記你是誰。”[12]
“你要記得回來。為了那些不像你那么容易離開的人。你會記得嗎?”[13]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心智的成熟,埃斯佩朗莎逐漸完成了對身份的認同和自我覺醒。她決心掙脫芒果街的束縛,遠離父權的壓制,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不過離開的目的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歸來。“有一天我要擁有自己的房子,可我不會忘記我是誰,我是從哪里來。路過的流浪漢會問,我可以進來嗎?我會把他們請上閣樓,請他們住下來,因為我知道沒有房子的滋味。”[14]
作為一部女性小說,作者希斯內羅絲在《芒果街上的小屋》里用細膩地筆觸描述了拉美裔女孩成長的心路歷程。小說哀而不傷,在關注底層族裔女性遭受白人文化和男權社會的雙重壓迫的同時,不時表現出女性迸發出的綿密而堅強有力的反抗力量。小說結尾處埃斯佩朗莎描述了心中的房子:
不是小公寓。也不是陰面的大公寓。也不是哪一個男人的房子。也不是爸爸的。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那里有我的前廊我的枕頭,我漂亮的紫色矮牽牛。我的書和我的故事。我的兩只等在床邊的鞋。不用和誰去作對。沒有別人扔下的垃圾要拾起。
只是一所寂靜如雪的房子,一個自己歸去的空間,潔凈如同詩筆未落的紙。[15]
這是作者為族裔女性勾畫的擺脫了種族歧視和男權壓迫的房子,是完完全全屬于自己的房子,是可以自由呼吸的房子。
參考文獻
[1]米歇爾·福柯.劉北成,楊遠嬰譯.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2]塞繆爾·亨廷頓.程克雄譯.《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3]西蒙娜·德·波伏瓦.鄭克魯譯.《第二性II》[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4]拉曼·賽爾登編.劉象愚,陳永國等譯.《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注 釋
[1]梁艷,《后現代語境下美國非裔和華裔女性文學中的族裔意識研究》[J].《牡丹江大學學報》2017年第12期,p.48
[2]桑德拉·希斯內羅絲,潘帕譯,《芒果街上的小屋》[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1版,p.3
[3]同上,p.4
[4]同上,p.59
[5]同上,p.117-118
[6]同上,p.85
[7]同上,p.86
[8]同上,p.16
[9]桑德拉·希斯內羅絲,潘帕譯,《芒果街上的小屋》[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1版,p.105
[10]同上,p.27
[11]劉媛、董良峰.《從女性視角解讀<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父權制》[J].《科教文匯》,2018年7月(上),p.151
[12]桑德拉·希斯內羅絲,潘帕譯,《芒果街上的小屋》[M].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1版,p.141-142
[13]同上,p.142
[14]同上,p.118
[15]桑德拉·希斯內羅絲,潘帕譯,《芒果街上的小屋》[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1版,p145
(作者單位:西南醫科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