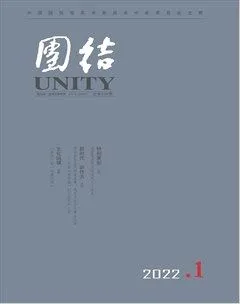從涉外漁業談判看我國國際化談判人才的培養
一、涉外漁業在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方面的重要性
“漁界所至,海權所在也”,漁權是海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和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漁權的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漁權是發展海洋漁業經濟的重要保障。歷史上海洋經濟利益沖突主要表現為對捕撈權益的爭奪,如17世紀英國與荷蘭之間關于英國沿岸鯡魚漁業的捕撈權,就牽涉對于鯡魚漁業的經濟利益之爭。當前,漁業在部分國家,特別是非洲、太平洋等發展中國家的海洋經濟中仍占有非常可觀的比例。其次,漁權是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重要戰場。各國對海洋權益的爭奪,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因海洋漁業利益的沖突而對漁場、捕魚權的爭奪。漁業爭端是推動海洋法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對于構造國際海洋法的一系列基本概念起到關鍵作用。漁業爭端在國家海洋劃界談判及國際司法糾紛中,仍占有一定的權重。
漁權的重要性并不因為其在國民經濟中占比的降低而減少。2021年英國與法國之間因對澤西島捕撈權的爭奪而引發的持續對抗,再一次證明了漁業在海權爭端中的重要性。英法漁業爭端緣起于脫歐協議在漁業安排方面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導致在具體制度制定和實施中,激化了當地原有的漁業生產矛盾,釀成了重大沖突。然而,究其根本,仍然是歐洲大國之間對于海洋權益爭奪的具體體現。相較于真槍實劍在海上對峙,漁業以其低敏感性、相對溫和的對抗方式,以“存在”彰顯“主權”,可以稱之為和平時期海上利益爭奪的“重要戰場”。
二、我國涉外漁業談判面臨的嚴峻形勢
隨著我國國家海洋戰略的提出,建設海洋強國驅動下漁業內涵不斷豐富,漁業活動不斷拓展,涉外漁業在新時代政治、外交及其他更為廣泛的國家利益方面具有了重要意義。然而,相較于美西方漁業強國,我國在一系列國際規則制定和問題應對上仍較為被動,在周邊、多邊、全球和雙邊談判中面臨著嚴峻形勢。
(一)周邊漁業談判阻滯增多
我國是海洋地理相對不利國家,周邊島嶼環視,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與鄰國重疊較多。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加入《海洋法公約》后,與周邊國家長期存在海洋劃界紛爭。秉持鄧小平同志“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我國與日本、韓國和越南通過達成漁業合作協議,共同開發海域生物資源,有效緩和了周邊潛在沖突。然而,隨著蘇巖礁、釣魚島、沖之鳥礁問題不斷發酵,新時代漁業談判愈加復雜。中越漁業合作協議2019年失效后,漁業合作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中日漁業談判則陷入僵局,日本利用中國漁船盜采珊瑚礁事件大做文章,雙方分歧不斷增大。
另一方面,我國在南海面臨著極大壓力。漁業是我國擁有南海主權的重要證據。自漢代以來中國人民世代遠赴南海從事漁業生產活動,并逐漸在南海諸島居留甚而定居。中國對南海U形線內的島礁享有領土主權、水域享有歷史性權利,這是依據國際法“先占”和“歷史性水域”規定取得的既得權利。然而,部分西方國家利用我周邊國家,插手東亞事務,間接分化離間我與東盟“戰略伙伴”關系。南海事務當前已經成為我構建區域合作網絡,推動東南亞共同繁榮的重要阻滯,而其中漁業談判如何推動,如何在發展中秉持“求同存異”“擱置爭議”的理念,考驗著我國涉外漁業談判的能力。
(二)區域漁業談判被動應對
加入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是我國參與全球水生生物資源分配的重要方式。目前我國是八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的成員,通過長期的制度建設和能力建設,履約成績逐步提高,并能通過采取公海自主休漁等方式,主動貢獻于全球漁業的可持續發展。然而,區域漁業組織的規則基礎對新興遠洋漁業國家非常不利,基于歷史捕撈量的配額分配對我國遠洋漁業發展形成掣肘,而在可持續發展理念下,發達國家不斷要求加強資源養護義務,進一步壓縮了我國發展空間。如何從履約走向規則制定,在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的履約活動及新規則制定中占據主動,使利益分配向發展中國家傾斜,成為我國參與區域漁業管理組織談判的重要考量。然而,對于以科學數據和模型建構為基礎,基于科學研究決策的漁業規則,我國在談判中僅能做到基本應對,難以提出質疑,及高質量回應或提供基于我國利益的解決方案。很多時候以技術專家為主,在技術細節上有所關注,卻不能在規則層面進行系統性批駁與應對。
(三)全球漁業談判挑戰不斷
在全球層面,通過聯合國大會、糧農組織及其下的漁業委員會,以《負責任漁業守則》為代表的國際文書提出了復雜精密的治理要求。發達國家通過提出建設公海保護區、南極保護區、設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等,限制國家活動。這些成熟的治理制度及新發展制度都制約了我國進一步擴展海上活動范圍,而西方國家還利用漁業補貼、打擊IUU非法捕撈、勞工問題等,試圖抹黑我國形象,制造障礙將我排除在全球治理之外。面對諸多挑戰,我國在國際漁業談判舞臺上需要做到的不僅僅是回應質詢,更應利用挑戰,轉危為機,在危局中創造新局面。這就要求我國充分參與到國際規則的游戲之中,不僅僅是被動回應,更應從復雜細密的國際規則中尋找機遇;不僅僅是否定對方,更應通過構造更加合理的規則創造有利于我國的局面;不僅僅是口舌之爭,更應用事實說話,利用充分的科學論證、論據進行反駁。然而,與歐盟、美國相比,我國法律人才培養起步較晚,加上語言障礙,當前法律從業人員對于復雜的國際規則體系把控能力不足,難以利用規則為我國服務。
除了上述三個方面,漁業談判在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中扮演著重要作用。我國全球最大的漁業生產國、加工國和貿易國,漁業合作的成功是我國拓展與發展中國家友誼的重要手段。我國水產養殖技術發達,通過派遣專家,技術轉移,“授人以漁”,為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做出重要貢獻。另一方面,我國通過簽訂雙邊漁業協議,兩千余條船舶遍布四大洋幾十個國家,成為我國外交向外延伸的重要觸角。近期,湯加發生嚴重地震,我國駐當地漁船在援救方面便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目前這種合作仍面臨著范圍較窄、程度較低的問題。遠洋漁業局限于簡單入漁,養殖則僅在局部推廣,其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仍廣受質疑。這些都與我國當前“軟實力”嚴重滯后相關。較之技術能力的不斷增強,我國仍缺乏以“漁”為引,持續擴大合作的能力。在談判方面往往僅局限于技術問題探討,難以“溝通感情”,發掘更深層的共同利益,以漁業帶動更廣泛層面的經濟、文化、社會層面合作。gzslib202204021507三、從涉外漁業看國際談判人才培養的方向
漁業的高度國際化和全球關切度使涉外漁業談判成為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試金石”和“排頭兵”。一葉以知秋,由涉外漁業談判困局可窺見我國當前國際談判的短板,由此判斷我國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國際化人才。
一是需要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和斗爭意識的人才。以涉外漁業為典型代表的國際談判往往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需要談判人員政治立場堅定,對外敏感性高,對談判具體事務內容具有很強的政治判斷力。同時,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局面,要有捍衛我國利益的堅強斗志,方能從以西方為核心的規則體系中找到發展機遇。
二是需要具有知曉技術與法律的復合型人才。無論是環境領域、氣候變化領域還是漁業規則,都具有以科學研究為基礎,以信息和數據為支撐的特點。這是當前國際規則的一大趨勢。因此,國際談判往往需要能夠知曉科學原理和技術規程,可以進行簡單數據分析并理解數據涵義,方能在規則制度上能夠進行宏觀把控。
三是需要能夠理解并操控復雜規則體系的人才。以西方法律制度為模型的國際規則結構精巧,內容復雜,體系龐大,且往往變化較快,而國際談判往往準備時間短,談判強度高,在短期內如何快速掌握內容并進行評價,需要的是經過專業訓練和長期經驗積累,能夠理解并掌握復雜規則體系的法律人才。
四是需要熟知當地社會風土人情的人才。談判,談的是面上,考究的是里子。在談判中,能夠抓住問題核心,尋找利益契合點,達成共識,往往靠的不是嘴皮子,而是真正的知己知彼。因此,談判最重要的還是桌下準備,只有長期積累的對對方的了解,才能成為談判桌上增加自身籌碼的財富。
四、對加強我國國際化談判人才培養的建議
事實上,能夠滿足上述四個方面條件的人才,可謂寥寥無幾。人才的厚度決定了人才的高度,相較于西方悠久的談判歷史和人才培養機制,加上語言優勢,我國似乎在國際談判人才培養上劣勢明顯。那是不是我國短期內就難以培養國際化談判人才?從涉外漁業人才的培養看,想要在短期內“彎道超車”,培養能夠服務于中國第二個百年偉大復興目標的國際化人才,可以從下述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以談判需求為導向,培養服務于全球海洋治理的新型法律人才。新時代人才培養的一個特點是以需求為導向,以適應世界的快速變化。我國當前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培育國際化的談判人才。而根據上述分析,我國當前最需要的是通曉國際規則,能夠融會貫通協調技術與法律的復合型人才。對此,在人才培養上我國應不拘泥于學科限制,在基礎法律訓練之上,加強對相應領域專業知識的學習和實踐訓練,學科設置上增加談判相關支撐學科內容,培養熟悉英語與法律,具有專業知識和實踐能力的人才。
二是加強國際組織人才輸出與國外人才吸納的雙通道建設。我國要參與全球治理,第一步就是要了解世界。通過廣泛外派人才與吸納外部人才,方能加速對外部世界的深入了解,同時向外傳播我價值理念。這種雙向交流應既是學科層面的,也是實踐層面的。在學科層面,吸收外國談判學科建設經驗,并在國際層面實踐我國傳統談判智慧;在實踐層面,通過參與國際組織相關工作,培養符合當前談判需求的人才。
三是構建領域內跨學科專業團隊,搭建穩定的智庫平臺。我國在遠洋漁業履約上短期內快速發展的經驗顯示,通過在專業領域內構建穩定的智庫平臺,可以彌補短期內人才供給短板。雖然同時滿足上述四方面條件的人才很少,但通過依托高校或科研機構,構建穩定的智庫平臺,可以有機利用不同人員在各自專業方向上的特長,在國際談判中打出組合拳。就此而言,兩方面條件必不可少。首先,團隊需與涉外實務部門緊密聯系,以決策需求為導向進行活動,團隊骨干成員通過參與實務決策,深入了解形勢和挑戰,有針對性地開展研究;其次,團隊內需形成穩定而緊密的聯系,在良好的激勵機制引導下,不同學科人員之間通過任務配合和交互學習,培育以某一學科為主的跨領域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