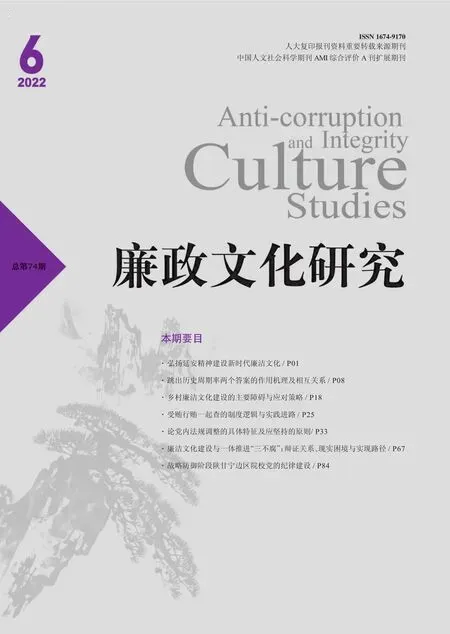戰(zhàn)略防御階段陜甘寧邊區(qū)院校黨的紀律建設
畢 霞
(河海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抗日戰(zhàn)爭進入戰(zhàn)略防御階段①1937 年7 月“七七事變”到1938 年10 月廣州、武漢相繼淪陷。,隨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以國共兩黨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國共兩黨進行了較為密切的軍事合作和政治合作。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zhàn)的政治主張,使其政治影響迅速擴大,全國各地及海外華僑中,大批知識青年紛紛奔赴延安尋求救國救民之路,中國共產黨也積極宣傳并設法促成其到來。黨中央在1937 年7 月底籌辦陜北公學,開始獨立領導創(chuàng)辦新型高等教育事業(yè),到1938 年10 月,在陜甘寧邊區(qū)這塊“沒有一點教育的遺產可繼承”的“文化荒地”[1]上,中央直屬院校發(fā)展到六所②“院校”一詞來自《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3 卷:抗日戰(zhàn)爭時期(1937.7-1945.8)》中第一編“中央組織機構”第四章使用的標題:“中共中央創(chuàng)辦的院校”。本文所指院校,主要為這類中央直屬院校,突出強調其體制特征。包括中央黨校、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陜北公學(簡稱陜公)、吳安堡青年訓練班職工大隊(工人學校的前身)、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馬克思列寧學院(簡稱馬列學院)。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3 卷:抗日戰(zhàn)爭時期(1937.7-1945.8)》,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75-81。,在短時間內把約兩萬名以小資產階級為主要成分的知識青年培養(yǎng)成為抗戰(zhàn)骨干和無產階級戰(zhàn)士,在這一過程中黨的紀律建設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學界對此關注的程度不高,成果暫付闕如①正如學者張靜如的觀點,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高校黨建,但是卻鮮有黨建專家關注高校黨建,關注高校黨建史的學者更少。已知高校黨的紀律建設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現實層面,且多聚焦于黨的十八大以來,學術論文居多,未見系統(tǒng)論著出現。從中國革命史視角研究延安時期高校黨的紀律建設的成果基本散見于延安時期黨的建設,或是少量的黨的紀律建設史、高校黨建史等成果中,如《中國共產黨建設史》《延安時期黨的建設研究》《黨的紀律建設簡史》《中共高校黨建史1921-1949》等等。。鑒于此,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參考現有檔案文獻,考察戰(zhàn)略防御階段陜甘寧邊區(qū)院校黨的紀律建設的基本情況,旨在以歷史經驗深化對當前高校黨的紀律建設的認識。
一、重啟高校黨的紀律建設新的歷史命題
(一)高校黨的紀律建設迎來新的發(fā)展機遇
高校是馬列主義政黨紀律觀傳播的源頭。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論戰(zhàn)中,接受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即“集中制,紀律和空前的自我犧牲精神”[2]。1920 年9 月,蔡和森在和毛澤東的通信中探討建黨組織原則時指出:“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基于馬列主義主要是在知識分子中間傳播的事實,蔡和森對在非無產階級群體中建黨進行了主動自覺的思考,他認為惟有鐵的紀律“才能養(yǎng)成少數極覺悟極有組織的分子”[3],擔當戰(zhàn)爭和改造社會的重任。這是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在非無產階級群體中紀律建黨的初步思索,遺憾的是這一思索沒有持續(xù)下去。
雖然從二大開始,黨基于共產國際的意見將工作重點轉向工人階級,但是高校還是可以被認定是黨的紀律建設的濫觴之地,理由是:第一,從黨的一大到五大,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里“大多數是智識分子”[4]420,他們奠定了黨的紀律建設的基本框架;第二,高校培養(yǎng)了無數工人運動的骨干,他們的紀律觀念直接影響到工人運動的水平;第三,1925 年春成立的中共廣東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監(jiān)察委員會,以及1927年中共五大選舉產生的第一屆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近半數是知識分子②1925 年春成立的中共廣東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監(jiān)察委員會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地方紀律檢查機關,書記為林偉民,委員有楊匏安、楊殷、梁桂華,有兩人是知識分子出身。1927 年中共五大選舉產生的第一屆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有王荷波、張佐臣、許白昊、楊匏安、劉竣山、周振聲、蔡以忱,候補委員有楊培森、蕭石月、阮嘯仙,王荷波任主席,楊匏安任副主席,有四人是知識分子出身。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卷:黨的創(chuàng)建和大革命時期(1921.7-1927.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36、586。,他們對紀律的認識直接影響到地方和中央紀律檢查工作。大革命后期開始,受共產國際“三階段論”方針的影響,“左”傾關門主義政策,以及黨的工作重心向農村轉移的實際,使高校黨的建設“邊緣化”[5]101。
遵義會議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新階段。1935 年12 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黨制定了適應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政治路線,提出“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做堅決斗爭”[6]。進入戰(zhàn)略防御階段,黨在政治路線成熟后開始著手解決思想路線問題,陜甘寧邊區(qū)創(chuàng)建的新型高等教育事業(yè),在領導體制和教育理念上都是全新的開始。這些院校承擔著培養(yǎng)抗戰(zhàn)建國先鋒的重任,作為知識精英和人才的匯聚地,是黨構筑意識形態(tài)和進行廣泛社會動員的橋梁,高校黨的紀律建設迎來新的發(fā)展機遇。
(二)教育為長期抗戰(zhàn)服務方針的內在要求
戰(zhàn)略防御階段是抗日戰(zhàn)爭中最為慘烈的階段,日本經濟軍事等戰(zhàn)爭要件明顯優(yōu)于中國,但中國具有國土面積和人口優(yōu)勢,國共兩黨對此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黨在洛川會議上確立了持久戰(zhàn)的戰(zhàn)略方針、全面抗戰(zhàn)路線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由于之前受三次“左”傾錯誤的影響,“有經驗的干部大批犧牲”[7]200,1937 年中組部掌握的全國黨員人數只有3 萬多,組織力量“還是很微弱的”[8]394。對此,1937 年5 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蘇區(qū)代表會議),制定了正確的干部路線。10 月,毛澤東提出黨要“從蘇區(qū)與紅軍的黨走向建立全中國的黨”[9]的宏偉戰(zhàn)略目標,實現這一目標最好最有效的辦法是辦學校培養(yǎng)抗日干部。
教育方針隨著政治方針而轉變。1937 年7 月,毛澤東明確提出“國防教育”[8]348的方針,明確了教育在抗戰(zhàn)中的重要地位。周恩來在《對日作戰(zhàn)芻議》中,也強調了國防教育對于廣泛、有效地實施社會動員的重要性,他呼吁要有步驟地實施國防教育,這“對于青年學子和失業(yè)的知識分子的救濟,是異常急迫的任務”[7]492。8 月召開的洛川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具體闡述“抗日的教育政策”,必須以抗日救國為目標設立“新的教育制度和新課程”“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7]477。由于抗戰(zhàn)干部的培養(yǎng)成為國防教育的重中之重①“中統(tǒng)局檢送陜甘寧邊區(qū)教育文化設施狀況的調查專報”,也強調了邊區(qū)教育“適應干部需要這一特點”。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2 編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22。,具備嚴格的紀律素養(yǎng)是合格黨員干部的必備條件,作為起源于戰(zhàn)爭的紀律,自然成為教育為長期抗戰(zhàn)服務方針的內在要求。
(三)黨的紀律建設面臨的困境
戰(zhàn)略防御階段的困苦是多方面的,“戰(zhàn)爭的緊張環(huán)境,敵人與友黨的危害”[10]709,我方多數民眾無組織、軍力不強,克服上述困苦的基本條件就是黨的團結和統(tǒng)一。對這一基本條件的挑戰(zhàn)首先來自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張國燾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分裂黨和紅軍,直至在日寇猖狂進攻面前“公開背叛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共產主義事業(yè)”[10]763。其次來自王明的“宗派機會主義”。王明在長江局期間擅自以中央名義對外發(fā)布宣言,完全無視1937 年《中央政治局工作規(guī)則和紀律草案》的有關規(guī)定,拒絕執(zhí)行中央路線、方針、決議,公開否認中央權威。張國燾、王明嚴重破壞黨的政治紀律的行為,給黨的團結和統(tǒng)一造成了極大危害。
赴延安求學的知識青年,抗日熱情高但成分復雜②以抗大第4 期為例,投考抗大的知識青年除來自全國(除青海和西藏)外,還有來自南洋、暹羅、越南等地的華僑(64人),以及朝鮮等民族;職業(yè)有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新聞記者、教授、軍人(第4 大隊第10 隊有1 名國民黨軍隊的團長)、學生、商人、產業(yè)工人、手工業(yè)者、農民;家庭成分絕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也有其他成分,如國民黨將領的子弟,如黃興之子黃鼐、馮玉祥之侄馮文華、傅作義之弟傅作良等,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兒女;年齡自十三、四歲到四、五十歲;文化程度自文盲到海外留學生。參見抗大總校政治部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史》,載于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黨史資料》,1955 年第2 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133。動機不同③據王仲方回憶,有懷著好奇心來看看共產黨究竟為何的,有不滿國民黨統(tǒng)治棄暗投明的,有沒有出路來找出路的,有不滿包辦婚姻逃離家庭的。動機和出發(fā)點各異,甚至是奇怪的。但人群中的主流是青年學生,是懷著熱情真心奔向共產黨抗日的。參見任文《我要去延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15。,不少人還帶有舊社會的陳腐習氣,“至于共產黨究竟是什么?頭腦里并不十分清楚”[11]。加上國民黨對青年的爭奪④1937 年陜西省教育廳為處理陜北公學在三原招生事致電教育部請示處理意見,教育部回電“應由該廳詳密調查,并商承行營及省政府妥為處理”。此外,胡宗南于1938 年7 月在西安組建戰(zhàn)時工作干部訓練團,自成立起就在通往延安的三原、洛川等縣建立招待所,截留與招收前往延安的流亡青年,擔任戰(zhàn)時限制中共發(fā)展的政治任務。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2 編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58;楊者圣《在胡宗南身邊的十二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1。,甚至有少數學生當了逃兵。大量快速發(fā)展黨員也帶來了思想基礎不牢等問題,抗大第四期開學時,4655 名知識青年中只有黨員530 人,畢業(yè)時“已有3304 名共產黨員”[12]59,由占知識青年總數的11%上升到70%;1937 至1938年間,陜公培養(yǎng)的6000 多名知識青年中,“發(fā)展新黨員就有3000 多人”[13],比例也達到50%⑤據李維漢回憶,當時發(fā)展組織的任務十分迫切,關于黨員發(fā)展比例,由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最后提出60%到80%。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324-325。。1938 年3 月21 日,劉少奇在《華北戰(zhàn)區(qū)工作的經驗》中尖銳指出,到地方工作的某些抗大的畢業(yè)生“尚有貪污腐化驕傲的現象發(fā)生”[10]197。
此外,由于剛剛經歷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殘酷斗爭,黨內馬列主義修養(yǎng)還不“普遍于深入”,制度不完善,紀律執(zhí)行中“宗派傾向”、懲辦主義與“思想斗爭中的過火政策”[10]648現象依然存在。
二、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開展紀律教育
(一)紀律教育成為思想建黨原則的實踐
在與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戰(zhàn)中接受馬列主義政黨紀律觀,是黨的紀律教育的起點,也是黨從思想上開始自身建設的起點。在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黨的紀律教育處于萌芽狀態(tài),高校黨的紀律教育有諸多首創(chuàng)。上海大學作為黨主持的學校①茅盾稱上海大學是“黨辦的第二個學校”。參見茅盾《文學與政治的交錯——回憶錄(六)》,中新文學史料,1980(1):165-182。以多種方式開展紀律教育:一是以上大名義承辦中共上海地委兼區(qū)執(zhí)委②1921 年7 月至1927 年6 月,上海區(qū)中共組織的演變經歷了四個階段:1921 年12 月至1922 年7 月,為中國上海地委階段;1922 年7 月至1924 年4 月,為中共上海地委兼區(qū)執(zhí)委階段;1924 年4 月至1925 年8 月,為中共上海地執(zhí)委階段;1925 年8 月至1927 年6 月,為中共上海區(qū)執(zhí)委階段。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 卷:黨的創(chuàng)建和大革命時期(1921.7-1927.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263-265。活動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如十月革命紀念日③1923 年11 月1 日,中共上海區(qū)委(應為中共上海地委兼區(qū)執(zhí)委)召開第二十次會議,討論十月革命紀念活動:一是在報刊發(fā)表紀念文章;二是由上大社會學系組織召開紀念會議,黨團員參加;三是印傳單,到工廠門口散發(fā)。1923 年11月7 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紀念號專刊,發(fā)表了陳獨秀《蘇俄六周》、施陶父《十月革命之歷史的根源》、瞿秋白《十月革命與經濟改造》。參見丁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134。、列寧追悼大會④《上海民報》1924 年3 月10 日報道,“上海各公團于昨日下午二時起,假小西門少年宣講團舉行列寧追悼大會,……次由瞿秋白報告列寧史略,……是日有追悼會特刊及學生總會宣言等印刷品,在會場散發(fā)……”。和馬克思誕辰紀念大會⑤1924 年5 月5 日,在上海大學舉辦的紀念馬克思誕辰106 周年紀念大會上瞿秋白發(fā)表演說,并與任弼時高唱《國際歌》。參見丁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153。等活動;二以教學活動宣傳馬克思主義,1923 年4 月,鄧中夏主持上海大學行政工作,他創(chuàng)辦社會學系⑥瞿秋白(上海大學教務長)、施存統(tǒng)、彭述之先后擔任系主任,是共產黨員最多的一個系。參見王家貴、蔡錫瑤《上海大學1922-1927》,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3。,邀請李大釗到校演講、聘請瞿秋白⑦1923 年,瞿秋白完成《社會哲學概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上,瞿秋白的貢獻在于,他在上海大學所作的系列講稿,從不同角度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參見丁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140-141。等以及其他進步人士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培養(yǎng)了大批工人運動的骨干;三是依托嚴格的組織⑧1923 年7 月,鄧中夏擔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兼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長,著手改組上海的黨小組,第一組是上海大學組(鄧中夏也在這一組),有11 名黨員,占全市黨員數的四分之一。1923 年8 月到11 月先后擔任第一組組長的有許德良、施存統(tǒng)、王一知和陳比難。1924 年上海大學組有黨員23 名。1925 年初,上海大學黨小組改建黨支部,成為按照中共四大精神率先在全市學校系統(tǒng)中建立黨支部的高校,黨員發(fā)展到25 人。1926 年3 月,成為直屬中共上海區(qū)執(zhí)委的獨立支部,支部書記先后由高爾柏(1926.3-8)、張曉柳(1926.9-冬)、張耘(1926 年冬)、黨伯弧(1927.2-4)擔任,由區(qū)執(zhí)委書記羅亦農直接領導。1926 年12 月,黨員人數已有130 人。隨著北伐戰(zhàn)爭的推進,很多黨員因投入武裝斗爭離開學校,1927 年3 月,上海大學獨立支部有黨員34 人。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1 卷:黨的創(chuàng)建和大革命時期(1921.7-1927.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262-284;王家貴、蔡錫瑤《上海大學1922-1927》,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137-140。生活開展紀律教育⑨1923 年10 月11 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區(qū)執(zhí)委第十七次會議,指定黨小組會議演講員為蔡和森、瞿秋白、施存統(tǒng)、惲代英、向警予和鄧中夏,每人每月演講一次。參見丁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133。。據楊尚昆回憶,他在上海大學期間接受了“要保守秘密,要絕對服從黨組織”“訓練”[14]。上海大學寓黨的紀律教育于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之中,是對思想建黨原則的初步探索。大革命時期“文有上大,武有黃埔”的美談,生動說明了高校黨的紀律建設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然而由于受共產國際,以及傳統(tǒng)習慣勢力的影響,黨內存在“根源于書生主義”的“官僚式紀律觀”,黨內教育“大半是注入的,而不是啟發(fā)的”[4]84,86,這些問題推動了黨的紀律教育,以及黨的思想建設的深入。
1929 年,黨對思想建黨和紀律教育問題的探索①1929 年8 月24 日,《中共中央關于鄂西黨目前的政治任務及其決議案》(以下簡稱《決議案》)首次在黨的文件中提出“紀律教育”概念,要求鄂西紅軍“生活有機化,紀律教育化”。《決議案》雖然涉及到提高士兵政治認識的問題,但目的還只是“充實紅軍生活”。《決議案》所強調的“紀律教育”,主要通過紀律頒布時向士兵解釋,經過士兵委員會通過,“紀律的執(zhí)行可能時(戰(zhàn)時在外)可以經過士兵群眾自己決議”,這一條實際上帶有隨意性,違背了紀律適用一致性(平等性)屬性,仍帶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廢除肉刑”,以自我批評或罰崗等替代,廢除肉刑是正確的,但規(guī)則的制定沒有跟上。最后,《決議案》原則性地強調紅軍中紀律的制裁必須堅持,“必須帶有教育性的,嚴格的執(zhí)行”,但沒有提供具體的落實政策。總之,這份文件對紀律屬性的認識還不夠深刻,對于政治素養(yǎng)與紀律教育的關系沒有闡述清楚,但對于紀律教育具有推進意義。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405-415。產生了質的飛躍。12 月召開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對紅四軍黨內存在的極端民主化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及表現展開批判,深入推進了黨對紀律教育的認識,確立了思想建黨的原則。毛澤東指出,如若“不提高黨內政治水平,不肅清黨內各種偏向”,就不能發(fā)展紅軍,不能擔負重大的斗爭。毛澤東針對“廢止肉刑問題”[15]741,754-756,緊緊圍繞紀律教育詳細闡述了其根源、危害,以及操作的法律程序。毛澤東的論述繼承和發(fā)展了馬恩和列寧關于黨的理論素養(yǎng)與組織發(fā)展水平密切相關的思想,深刻闡述了紀律教育與思想建黨原則的關系。雖然《決議》中思想建黨的影響在當時僅限于紅四軍,但被瓦窯堡會議“直接繼承”[5]155并得以在全黨貫徹落實。
進入戰(zhàn)略防御階段,黨對以往解決問題的經驗加以提煉和深化②1929 年12 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分析了紅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產生的根源,一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最大部分由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構成”,二是由于“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于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進入戰(zhàn)略防御階段,黨中央汲取了上述經驗教訓,一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青年學生,克服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二是進行軍事化管理加強組織紀律;院校負責人由黨和軍隊中擔任重要職務的同志兼任,加強領導。,并在陜甘寧邊區(qū)院校進行運用。首先,以教育為中心,通過提高政治理論素養(yǎng)使紀律成為其內在的堅定信仰。1938 年6 月1 日,羅瑞卿在總結抗大辦學兩年的經驗時指出:政治教育在抗大整個教育內容中占據重要地位,因為抗大要培養(yǎng)出“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了頭腦,而又要能夠最好的掌握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軍事干部”[16]13。其次,對紀律教育內容和形式的經驗進行理性的提煉。1938 年10 月14 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論新階段》中,強調將馬列主義政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四個服從”作為“全黨尤其是新黨員”開展紀律教育的內容;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黨規(guī)”的概念,并且要求以黨規(guī)的形式開展紀律教育,“制定一種黨規(guī),把它當作黨的法紀之一部分”[10]645-646。毛澤東的論述表明黨對紀律教育認識實現了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由理性認識到實踐的飛躍,在實踐中確立起了思想建黨的原則。
(二)黨政軍領導親自授課開展紀律教育
陜甘寧邊區(qū)各院校按照“理論與實際并重”“政治與軍事并重”原則③“中統(tǒng)局檢送陜甘寧邊區(qū)教育文化設施狀況的調查專報”評價邊區(qū)教育的特點之一是,“注重政治訓練與軍事訓練,高度發(fā)揚教育之戰(zhàn)斗性”,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2 編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22。,以及“少而精”的方針,開設“基本政治常識”“抗戰(zhàn)形勢與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抗日軍事問題”這三類課程④各院校根據培養(yǎng)目標不同課程設置存在一些差異。抗大以培養(yǎng)抗戰(zhàn)軍事干部為目標,每一期的教學重點都會根據學員情況有所調整,從第二期開始,課程基本是“基本政治常識”“抗戰(zhàn)形勢與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抗日軍事問題”(續(xù))這三類,七分軍事三分政治,針對青年學生還進行艱苦奮斗、不怕犧牲、英勇作戰(zhàn)的傳統(tǒng)教育和革命人生觀教育。陜公的培養(yǎng)目標是在三、四個月內,把青年學生培養(yǎng)成具有一定政治覺悟和初步軍事知識,有獨立進行群眾工作、政治工作能力的抗戰(zhàn)建國干部;根據這一目標開設“社會科學概論”“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游擊戰(zhàn)爭”“民眾運動”,高級研究班增加“世界革命運動史”“三民主義研究”“世界政治”“戰(zhàn)區(qū)政治工作”等,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中央黨校以培養(yǎng)黨務干部為目標,開設“哲學”“政治經濟學”“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問題”“馬列主義基礎”“游擊戰(zhàn)爭”等課程,建有相應的研究室。吳安堡青年訓練班職工大隊以培訓工人干部為目標,開設“基本政治常識”“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理論與實踐”“抗日軍事問題”“職工運動的統(tǒng)一問題”“文化課和輔助課(包括時事報告、學習方法、工作方法)”等六門課程(后期并入抗大,由抗大安排軍政訓練)。魯藝以訓練適合抗戰(zhàn)需要的藝術干部為目標,除基本政治常識課和軍事課外還開設文藝理論課、專業(yè)知識課、專業(yè)技巧課。馬列學院以培養(yǎng)具有馬列主義基礎的理論干部為目標,開設“政治經濟學”“哲學”“馬列主義基本問題”“黨的建設”“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西洋革命史”等課程外,還學習時事政治和中央政策。(根據《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成仿吾年譜》《張聞天年譜》《回憶與研究》《延安時期中央黨校》、《張浩傳》等資料整理。)。黨中央要求知識青年首先要學到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①1938 年3 月3 日,毛澤東對陜公第六、七、八、九、十隊畢業(yè)學員作臨別贈言,“你們在陜北公學學到了政治方向和工作作風”。1938 年3 月5 日,毛澤東為抗大同學會題詞“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機動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用以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中國。”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83-1949)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53。,為此,除抗大外其他院校政治類課程占七成,引導學生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以及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方法,很多學生自此“懂得了一些馬列主義”[17]301,抗戰(zhàn)熱情被引導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解放新中國的高度。
為克服教員稀缺的困難,各院校充分利用延安的政治資源,“約請”在延安的“黨、政、軍領袖與負責人兼課”[18]131,六屆六中全會期間,還有計劃地邀請了各地赴會的領導同志作報告。“這些更好的教員”[16]14引導學生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馬克思主義。其中最著名的是1937 年5 月至8 月,毛澤東在抗大講授《辯證唯物論》課程,每周兩次,每次4 小時,歷時3 個月,向學員系統(tǒng)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以及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其講稿的主要部分后來成為《實踐論》《矛盾論》的主要部分,奠定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成果——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根據這一哲學基礎,毛澤東要求黨員結合中國具體環(huán)境、具體斗爭制定工作方針,同時對于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進行了系統(tǒng)論述,標志著毛澤東黨建思想的日臻成熟。1938 年4 月和夏天,張聞天分別在陜北公學和抗大作了題為《論青年的修養(yǎng)》的演講,7月26 日,張聞天又在抗大第三期畢業(yè)典禮上作了題為《論待人接物問題》的演講。作為黨的歷史上“干部教育等工作中成績卓著”[19]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張聞天將儒家等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從提高黨性修養(yǎng)入手,將無產階級政黨的紀律意識植入青年心中,使之成為一種內在的要求和自覺的意識。以提高道德水平增強紀律意識,也是黨在紀律教育中的創(chuàng)新②國防部史政局戰(zhàn)史編撰委員會檔案記錄:在抗大“紀律重在自覺的遵守,由教育與說服的方法,使大家了解紀律的重要,八路軍對士兵早就廢止了打罵,養(yǎng)成士兵的自尊心,提高了士兵的人格,而他們才把紀律看得如同自己的命脈,異常的尊重。”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2 編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77。。中央領導同志的授課和講話③根據《毛澤東年譜(中)》《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簡史)》《張聞天年譜》等資料統(tǒng)計,1938 年7 月到1938 年11月初,毛澤東在抗大授課、演講、講話、談話共計約27 次,在陜公授課、演講、講話共計7 次。除文中已述外,1938 年其他中央領導在抗大的講話還有:3 月21 日,劉少奇作《華北戰(zhàn)區(qū)工作的經驗》講演;4 月,陳云演講“怎樣做一個革命者”;5 月2 日,林彪作題為“抗大教育方針”的演講;8 月29 日,朱德作題為“一年余以來的華北抗戰(zhàn)”的報告;9 月,周恩來演講“第三期抗戰(zhàn)的形勢與前途”、陳云演講“論干部政策”、劉少奇作題為“共產主義事業(yè)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事業(yè)”(后經過整理成為《論共產黨員修養(yǎng)》的一部分)演講。1938 年2 月20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張聞天、毛澤東、康生、凱豐等中央負責同志每人每月到陜公作一次報告。1938 年的4 月、8 月和9 月,張聞天、(續(xù))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中央黨校分別作了“傳達三月中央政治局會議”“當學生,當先生,當戰(zhàn)爭領導者”“第三期抗戰(zhàn)的形勢與前途”的報告。1938 年4 月,毛澤東在魯藝作題為“怎樣做藝術家”的講演。同年5 月,毛澤東在馬列學院作題為“論持久戰(zhàn)”的演講,等等。1938 年9 月至11 月,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期間,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彭真、秦邦憲、肖克、程子華、潘漢年等外地赴會同志分別到各院校作了根據地建設、部隊建設以及革命斗爭的報告。,引導學生掌握馬列主義理論聯系中國實際的理念和工作方法,既推動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形成,也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武裝了高校,推動這些院校迅速發(fā)展并做出重大貢獻①在黨關于國防教育方針的推動下,陜甘寧邊區(qū)教育有了飛速發(fā)展,這一點連國民黨也不得不承認。“中統(tǒng)局檢送陜甘寧邊區(qū)教育文化設施狀況的調查專報”對陜甘寧邊區(qū)國防教育方針評價為“收效頗有可觀”,“值得仿效”。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2 編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22-523。。經過數月的學習和艱苦斗爭的鍛煉,把“大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培養(yǎng)成為有組織性、紀律性、團結性,堅強的抗戰(zhàn)干部”[18]134,是在黨的紀律教育史上創(chuàng)造的一大奇跡。
為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六屆六中全會對部分院校的學制和課程設置做了調整②規(guī)定中央黨校開設“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運動史與中國問題、中共黨史與黨的建設”等課程,學制3-6 個月;馬列研究院,學制無定期,主要培養(yǎng)理論干部與教員;抗日軍政大學分政治工作系、軍事系和較高干部培養(yǎng),學制3-6 個月。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 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665-712.,要求知識青年在斗爭中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認真地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人民所接受”[10]701。
(三)以思想斗爭方式進行紀律教育
毛澤東繼承了馬恩和列寧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思想斗爭達到黨內團結的建黨思想,他在1929 年提出要針對各種錯誤思想開展“一致的堅決的斗爭”[15]726。進入戰(zhàn)略防御階段,毛澤東對于思想斗爭的認識升華到哲學高度,提出“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20]。1937 年,毛澤東針對抗大第二期部分教職學員的自由主義傾向作了一次講話,后來以《反對自由主義》為題發(fā)表在抗大內部校刊《思想戰(zhàn)線》(1937 年9 月7 日)上。文中毛澤東有針對性地列舉了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指出其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及其危害,懇切地指出要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斗爭”[8]361。
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武器進行思想斗爭,改造人的思想,是陜甘寧邊區(qū)院校紀律教育的又一特色③國防部史政局戰(zhàn)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存有“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訓練方式與生活意識鍛煉情況簡介(1938 年7 月22日)”,將“生活檢討與自我批判”作為生活意識鍛煉部分,有如下記錄:方式是每一周一次到兩次,檢討或批判;內容是工作做到與否,缺點克服與否;評價“這種優(yōu)良的制度”“可以教育同志,推動工作。”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2 編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78。。在全黨開展的清算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抗大于1937 年10 月召開首次黨代表大會,進一步批判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消極影響,在認真學習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基礎上,“以大量鐵的事實揭露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12]36,與到會的張國燾展開面對面的斗爭,自覺肅清了其錯誤影響,在清算張國燾錯誤的同時也團結了同志。抗大的民主生活會十分有特色,田嘉谷在他的《抗戰(zhàn)教育在陜北》一書中,詳細記錄了圍繞“王克事件”開展的“思想斗爭”全過程[21]79。王克同學經常在一些思想比較落后的同學面前發(fā)表自由主義傾向的言論,經過反復多次的批評、辯論,幫助王克糾正了錯誤思想。馬列學院某班曾有一位“支部書記,在學習六屆六中全會精神期間,以個人名義發(fā)表了‘告黨員書’”,支部經過“針鋒相對的思想斗爭”[22]44,批評了其宗派情緒和違反黨的原則的錯誤,教育了支部全體黨員,也促進了支部思想進步和政治上的團結。
三、以政治紀律制度化建設為核心完善紀律規(guī)范
(一)政治紀律制度化的探索與逐步完善
1927 年2 月,瞿秋白在《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中首次使用“政治紀律”概念,主張對黨內右傾機會主義“應嚴格的執(zhí)行政治紀律”[4]89。同年4、5 月間,中共五大制定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也主張“宜重視政治紀律”[4]208。“政治紀律”的提出是針對大革命失敗原因及責任的追究,從1920 年開始到1932 年,以派駐代表的方式對中國革命進行指導和監(jiān)督的共產國際批評中共,在革命發(fā)生嚴重危機時刻,“居然堅決拒絕共產國際最高指導機關的命令和決議”[4]438,中共則完全接受國際的批評。1927 年11 月,中央政治局臨時擴大會議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對八一事變前委等起義失敗的組織及個人給予了政治紀律“處罰”,這種以政治紀律為手段推行錯誤路線的做法,顯然是“不完全妥當的”[23]。
進入戰(zhàn)略防御階段,黨開始了政治紀律制度化建設的探索。1937 年①原件無年代,《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 冊》和《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7-1949.9 第8 卷 文獻選編 上)》中均標注為1937 年。,依據黨章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規(guī)則和紀律草案》,《草案》共十條內容,詳細規(guī)定了政治局的產生、主要職責、工作制度、職權等,根據實踐中逐一顯露的問題,規(guī)定了政治局委員應遵守的五條紀律。對于破壞紀律的政治局委員,政治局依情節(jié)“給予適當的處分,或提交中央委員會解決”[7]769。12 月25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規(guī)則和紀律草案》出臺,《草案》詳細規(guī)定了中央書記處職責、工作內容、程序、要求,與地方黨部的工作關系,以及各項工作紀律;《草案》對陜甘寧邊區(qū)中央直屬院校的招生也提出明確規(guī)定:“中央直屬各校招生,亦必須得到書記處之同意。”[7]771這一規(guī)定將中央直屬各校招生工作納入政治紀律規(guī)范建設中。兩份草案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的團結和統(tǒng)一搭建了基本制度架構。
在1938 年9 月至11 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完整地提出了“四個服從”,其核心是全黨服從中央,黨中央對“四個服從”這一政治紀律原則形成了高度一致的認識。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制定黨內法規(guī)思想,劉少奇主持起草了《中央委員會工作規(guī)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委暫時組織機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guī)則與紀律的決定》,并作了《黨規(guī)黨法的報告》。三個《決定》對黨的政治紀律、宣傳紀律、組織紀律、保密紀律作了較為詳細的規(guī)定,作為對六大黨章的補充,為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提供了行為規(guī)范。三個《決定》進一步強調了“四個服從”,強調“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領導,是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10]773。民主集中制與黨的制度和紀律“交叉互現、同體并用”[24],成為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無條件執(zhí)行的紀律,為“保證按民主集中制來建設我們的黨”[10]750提供了有力武器,六屆六中全會以政治紀律制度化建設為切入點開啟了依規(guī)治黨新局面。
(二)出臺擴大黨員隊伍的規(guī)范化文件
明確恢復黨籍和重新入黨的要件及組織程序。1937 年7 月7 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頒布。《決定》對“非自首分子”的四種客觀“自首”情形②一是國民黨清剿區(qū)內,整個鄉(xiāng)村的群眾均須填寫自首書或類似文件,黨員也同群眾一樣,填寫這類文件,以保存黨在群眾中秘密組織的行為,不是自首;二是在獄中表示堅定坐滿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辦自首手續(xù),或填一般反共志愿書,才能出獄,無論是否經過組織允許,經過組織考察后,可以恢復組織關系。三是凡支部同志,被過去領導機關負責人叛變后供出他的姓名和住址,因而被捕被強迫照例填寫自首書,但并未供出組織內部秘密,又未進行任何反共工作破壞黨的組織,經過工作中考察之后可以恢復其組織關系。四是凡在群眾斗爭中被捕或因黨的嫌疑人被捕未供出他自己與組織的關系(即未承認自己是黨員),因有人擔保,而法庭一定要照例填寫自首書或一般反共志愿書,才能出獄者,也可不作自首論,經過考察后,可以恢復其組織關系。以上四種情形均屬非自首。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4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354-355。進行了界定,規(guī)定符合這四種情形的人員,經過工作考察后可以恢復其組織。《決定》對于主觀上“自首”的兩種處分情形,增加了相應的限制性規(guī)定③一是“沒有破壞或損害黨的組織者”處以“開除黨籍”的處分,這類人員經過一定的組織程序可以重新介紹入黨。二是對于破壞黨的組織者,處以“永遠開除黨籍”的處分,這類人員僅“可以左傾群眾看待”。參見:同上。。《決定》提醒各級黨組織在處理“所謂自首分子”問題上要注意防止“左的關門主義”,以及“腐化黨破壞黨的紀律的右傾機會主義”[7]355兩種錯誤傾向。針對在恢復黨籍和重新入黨過程中出現的右傾傾向,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嚴格恢復黨籍和重新入黨的審批。同年12 月25 日發(fā)布的《中央書記處關于恢復黨籍及重新入黨問題的第一次通知》規(guī)定:已經恢復黨籍和重新入黨黨員的黨籍,或正在辦理恢復黨籍者,“均需經中央黨務委員會依據黨的原則、黨的章程重新審查和決定”[25]500。將原來的特委省委以上黨部審批,調整為中央黨務委員會。但是由于戰(zhàn)爭環(huán)境的復雜變化,地方黨部不便或不易將此類材料送交中央,1938 年5 月23 日,《中央關于恢復黨籍及重新入黨問題的第二次通知》將審批部門調整為“各省委”“各師黨務委員會”,要求審批部門將審批結果“設法報告中央組織部和黨務委員會”,“中央所在地仍照原來通知辦理”[25]507。上述切合實際又操作性極強的規(guī)范性文件,極大地規(guī)范了黨組織的發(fā)展。
明確黨員發(fā)展的紀律要求、增加對新黨員的教育內容。1938 年3 月,《中共中央關于大量發(fā)展黨員的決議》頒布,將黨的組織大發(fā)展提上議事日程。為防止黨員大發(fā)展帶來忽視黨員質量的問題,《決議》規(guī)定新黨員的發(fā)展必須經過“支部一定黨員的介紹與一定黨部的審查”,并且重新規(guī)定了新黨員的候補期:“工人雇農不要候補期,貧農、小手工工人一個月,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小職員、中農、下級軍官三個月,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得伸縮之。”此外,《決議》在對新黨員進行馬列主義教育的內容上增加了黨的建設,以幫助新黨員了解馬列主義政黨“與其他黨派理論思想的基本區(qū)別”[10]187。1938 年5 月,延安馬列學院開學,作為中組部部長的陳云親自擔任該校黨的建設課程的一部分教學工作,10 月,陳云在抗大和陜公赴新疆工作的二十三名選調干部培訓班上,專門開設“黨的支部”問題講座。《決議》關于新黨員候補期的規(guī)定和學習教育內容的增加,是對六大黨章十分必要和充分的補充①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規(guī)定,候補黨員的考察期限至少為兩個月。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沒有規(guī)定新黨員的候補期。黨的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規(guī)定:“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但地方委員會得酌量情形伸縮之。”黨的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延續(xù)了這一表述。1927 年6 月1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在第一章專列第三條說明后增補了黨員的候補期:“勞動者(工人,農民,手工工人,店員,士兵等)無候補期;非勞動者(知識分子;自由職業(yè)者等)之候補期三個月;但市委員會或縣委員會得酌量情形伸縮之。”變化在于明確了勞動者和非勞動者,以及地方委員會的具體類型,取消了勞動者的候補期。黨的六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黨章修正案再次取消了關于候補期的規(guī)定。,對于擴大黨員隊伍起到了有力的規(guī)范和指導作用。
1938 年3 月15 日,中共中央下發(fā)《關于征收黨費的通知》,針對個別組織和黨員“不注意征收黨費或不交黨費”的問題,規(guī)定了黨員應繳黨費的比例,學生黨員以及其他社會成分黨員應繳黨費數額,規(guī)定連續(xù)至三次以上不繳黨費者,“應負組織處分,直至開除黨籍”[10]189。
(三)細化貪污罪的處罰規(guī)定
“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7]476,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zhàn)進入防御階段提出的政治主張。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成立以來,政府機關及群眾團體“均以‘廉潔’、‘盡職’的原則為選任和鑒別干部的標準”,“營私舞弊的現象是很少發(fā)生的”[10]499。
為進一步加強抗日模范區(qū)建設。1938 年8 月,陜甘寧邊區(qū)政府頒布了《陜甘寧邊區(qū)懲治貪污條例》。《條例》一共九條,詳細列舉了構成貪污罪的十種情形,較為完善地規(guī)定了對第二條“買賣公用物品從中舞弊者”懲處標準:貪污500 元以上者,“處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貪污300 元以上500 元以下者,“處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貪污100 元以上300 元以下者,“處一年以上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貪污100 元以下者,“處一年之有期徒刑或苦役”。除按照第三條之規(guī)定處罰外,并追繳貪污所得財物,無法追繳時沒收犯罪人財產抵繳。“前第3 條之未遂罪罰之。”[10]538-539《條例》彰顯出黨懲治貪污腐敗的堅強決心,嚴格的律法使黨員干部漸知敬畏,經過兩年的努力“建立了廉潔的抗日的全民的政府”[26]。
四、在克服懲罰主義與極端民主化傾向中加強紀律執(zhí)行和管理
(一)在嚴格執(zhí)紀中提升對紀律屬性的認識
《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之第十三條,對“鐵的紀律”的界定是“近似軍事紀律”[27]。受共產國際的影響,以及在經過幾千年封建社會“缺乏政治上的感覺力與組織力”[28]的文化環(huán)境下,很多人對“近似軍事紀律”的理解偏重于“懲罰”,導致紀律執(zhí)行中命令主義、懲辦主義、極端民主化傾向并存。1931 年8 月27 日,《中共中央關于干部問題的決議》指出了黨內紀律執(zhí)行中存在的兩個極端:一端是“家長式的濫用紀律”,另一端是“廢弛和輕視紀律”[29]。進入戰(zhàn)略防御階段,隨著中國革命任務的歷史性改變,黨對紀律屬性形成了新的認識,除前述的制度嚴格性規(guī)范性建設外,在權威性、一致性(平等性)和自覺性方面都有新的實踐,最典型的就是對張國燾問題的處理。對于張國燾長征期間的嚴重錯誤,黨中央“曾一貫地采取了教育和說服的方針”[10]261,盡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但面對他堅持不改直至選擇叛黨的行為,中央為維護黨的紀律的權威性,于1938 年4 月18 日“特決定開除其黨籍”[10]282,并在全黨開展了肅清其影響的教育①毛澤東于1938 年5 月4 日,在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隊成立大會上作《關于國共合作問題和開除張國燾黨籍問題》的講話;5 月7 日在陜公對第二期即將畢業(yè)的學員講“張國燾叛黨及開除黨籍的問題”,對廣大師生進行路線教育。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83-1949)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66-67。運動。
國防部史政局戰(zhàn)史編撰委員會檔案中有這樣的記載,抗大和八路軍一樣實行“官兵一致”,“是上下一致的精神在鞏固團結”[30]577。“官兵一致”的精神同樣體現在紀律的執(zhí)行中。1937 年10 月5 日晚,抗大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在延河岸邊逼婚未遂,槍殺了陜北公學女生劉茜。黨中央對此十分重視,邊區(qū)保安司令部會同陜北公學、抗大調查此案,案情很快水落石出。黃克功雖然戰(zhàn)功累累,但他的行為嚴重破壞了“紅軍鐵的紀律”,“違犯革命政府的法令”[31]。10 月11 日,在陜北公學對黃克功進行了公審,邊區(qū)最高法院宣布判處黃克功死刑并立即執(zhí)行。毛澤東要求在公審大會上宣讀他給雷經天的信件,要求全黨全軍要以黃克功案為鑒。在這起案件的調查審理中,黨中央充分發(fā)揮了它的教育意義,一是同意各院校圍繞這一案件組織討論,二是陜公師生參加公審大會,三是公審大會結束后,張聞天和毛澤東先后作了關于革命戀愛問題的演講。案件處理后,抗大以案促改,取消了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不準結婚的規(guī)定,提升了學校的管理能力。
(二)軍事化管理中發(fā)揮民主②關于軍隊民主的問題,毛澤東在1938 年5 月21 日出席抗大對第三期總結的干部會上指出,軍隊在軍事指揮上應強調單一的指揮,強調服從,而官兵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同艱苦,這就是民主。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83-1949)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71。自治能力
為培養(yǎng)文武兼?zhèn)涞目箲?zhàn)骨干,陜甘寧邊區(qū)各院校實行軍事化管理。即使像陜公這樣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的學校也采用軍事編制,按照隊、分隊、班設置層級,隊相當于連,既是教育單位又是自治單位,每隊約有120 人,隊長負責學習、副隊長負責生活和軍事,“隊指導員是隊支部書記,負責黨的支部和思想政治工作”[17]310。抗大作為軍事性質的學校,在第三期提出了“強化軍事訓練和軍事生活”的口號,成立了特別注重軍事訓練的“軍事隊”[18]131。1938 年1 月28 日,抗大舉辦了“一二八”運動大會,進行政治、軍事、文化學習競賽,極大地推動了各項學習的進步。除抗大將軍事課程作為主要課程外,其他院校也都開設軍事課,對學生進行“制式教練和作戰(zhàn)訓練”[17]300,按照軍事化標準每天出操,輪流站崗,野營拉練,要求做到令行禁止、秩序規(guī)范。
知識青年的增加,推動各院校領導作風發(fā)生了改變。陜甘寧邊區(qū)各院校負責人由黨和軍隊中擔任重要職務的同志兼任③抗大隸屬于中央軍委,1937 年7 月至1938 年10 月間,林彪兼任校長,羅瑞卿任第二、三期教育長。中央黨校隸屬于中央組織部,李維漢(1937.5-1938.4)和康生(1938.4-1938.11)先后任校長。陜北公學直屬中宣部和中組部,成仿吾任黨組書記兼校長,李維漢在1938 年3 月任副校長、黨組書記;1938 年4 月底任分校黨組書記兼校長。馬克思列寧學院院長由張聞天兼任。張浩兼任吳安堡青年訓練班職工大隊大隊長。魯迅藝術學院直屬中宣部,沙可夫任副院長(院長是毛澤東兼)。,組織機構很精簡,軍事化管理非常嚴格。1938 年7 月,毛澤東得知抗大第四期學生有自由主義和極端民主化傾向,而個別領導的處理方式過于簡單時,他專程來抗大作了“抗大民主問題”的報告,向知識青年闡述了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紀律的關系,要求抗大“取消斗爭會”代之以意見箱等方式。抗大師生通過學習討論毛澤東的報告,辨明了發(fā)揚民主與極端民主化的區(qū)別,不負責任的評頭品足消失了,代之以討論時的暢所欲言,政治空氣異常活躍,組織紀律性得到了加強,更推動了學校領導作風“有較前更大的進步”[18]135。
“救亡室”和學生會發(fā)揮了民主自治的作用。1937 年12 月11 日,抗大第三期第九隊率先成立“救亡室”①1937 年12 月26 日,抗大頒布的《政治工作暫行條例》對“救亡室”的性質、任務、原則、組織、工作內容、工作人員的工作及領導方式作出明確規(guī)定。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71。,得到了毛澤東的贊揚和親筆題詞,隨后各院校也紛紛建立。“救亡室”是在校政治機關領導下吸收全體學員進行抗日救亡和補助教育的“群眾性團體”[12]71,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抗日軍政大學動態(tài)》對救亡室的作用②中統(tǒng)局檢送陜甘寧邊區(qū)教育文化設施狀況的調查專報稱,救亡室的作用在于以“文化娛樂方式,調劑學生學習生活,團結學生意志、感情,發(fā)揚學生自治能力,補助學校管理之不足”。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2 編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26。大加贊賞,認為經過“救亡室”活動的陶冶,大多數學員都改變了初進學校時的自由散漫等不良習慣,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都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同學之間的團結友愛加強,克服困難的勇氣增強,展現出了“團結、緊張、活潑、嚴肅”的校風③參見(日本)Taicho Mikami,《抗日軍政大學の動態(tài)》,1965:108-112,發(fā)布于抗日戰(zhàn)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2022-08-26,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救亡室”的組織形式是“民主選舉”產生委員(報政治部審批),各隊“救亡室”設有經濟節(jié)省委員,負責監(jiān)督全隊伙食給養(yǎng)。
對于陜公,中央強調要按照其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性質“要更多的用民主的群眾的工作方法”。陜公的學生會是學生的自治組織,據李維漢回憶錄記載,陜公全校有總會,各隊有分會,它的職責是“領導全體同學恪守學校的制度、規(guī)則和紀律”[17]315,組織各種課外活動,組織開展各種互助活動,動員和帶領學生參加各種改善學校辦學環(huán)境的活動。學生會干部有機會參加學校的會議,促進學生和行政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是學校管理的有益補充。
(三)制度治校作風嚴肅活潑
中共中央在創(chuàng)辦院校之始就明確規(guī)定,學員入校需經人或機關介紹,還需填寫很詳細的調查表,不僅有政治文化考試④這一政策也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1937 年12 月,張聞天、毛澤東、康生、陳云就招收南方學生來陜北學習問題致電羅炳輝、董必武、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指出:“南方學生來此甚少,望改變方法,不必舉行考試,亦不必要介紹信。”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云年譜上》修訂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249。。學員入校后需嚴格遵守政治紀律、軍事紀律和生活紀律,對于違反規(guī)定者,一律按規(guī)定懲處。學員畢業(yè)時要通過結業(yè)考核,中央黨校有組織鑒定或政治鑒定、以及學業(yè)鑒定兩種制度,前者“衡量學員的黨性修養(yǎng)”,后者“衡量學員的學習好壞”[17]299。
抗大在制度治校方面走在陜甘寧邊區(qū)院校的前列。1937 年12 月26 日,抗大頒布《政治工作暫行條例》。《條例》共8 個部分91 項具體內容,對政治部、總支委、組織科、宣傳科、俱樂部、大隊政治協(xié)理員、連隊指導員以及連隊救亡室等政治部門和學生組織的職責、工作任務、以及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宣傳紀律以及工作紀律作了詳細規(guī)定。1938 年6 月,《抗大組織條令》頒布實施,對抗大的性質、任務、教育方針、教育方法、課程設置、管理制度、組織機構作了明確規(guī)定,完善了抗大的規(guī)章制度,使各項工作和每一位成員的言行都有章可循。抗大從第三期開始實行了嚴格的財務預決算制度。
各院校都有嚴格的作息制度。抗大作息制度是,“晨五時半起床,六時早操,七至九時自習(整理筆記、準備提綱、閱參考書),九至十二時學科。十二時半午餐。午后一至二時午睡。二到五時學習功課或出操,五到七時課外活動,七時晚餐,八到十時自習”[30]527。延安馬列學院“讀書、上課、討論、就餐、睡覺均有嚴格的時間規(guī)定,以哨為號”[22]217。
學習生活異常艱苦①自己建校舍,“原計劃一百五十個窯洞現在成功一百七十個”,“粉了二分之一的窯壁,打了三分之一的炕”,“開了約二千米的‘抗大公路’的干線和許多的支線”。“八個人睡一個炕,三頓小米飯、八個人一碗菜”“每日粟飯,冬夏灰布軍服各一套,學生物質生活異常艱苦,……此為抗大不可克服之苦難”。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406-407;羅瑞卿、成仿吾《成群結隊》,北京:華文出版社,1939:6;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 輯第2 編教育(2),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7:527。,“的確是臥薪嘗膽的那一步”[21]102,但學生的精神生活是活潑愉悅的,一是源于官兵政治上平等②1937 年11 月27 日,毛澤東在給其表兄文運昌的信中,勸他不要來延安,因為無法解決他的經濟困難問題:“我們這里僅有衣穿飯吃,上至總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無薪水。”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83-1949)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39。、生活上同艱苦,師生打成一片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寬松氛圍”[33];二是豐富的文化娛樂活動,“從沒有見過一種軍與民有那樣著重文化娛樂,其中以演劇唱歌最為盛行”[30]578。晨起和睡前,“只要不是上課或自習的時間,歌聲是不會斷絕的”[30]567。一方面把校訓唱進歌聲里,教育③《我要去延安》這本口述史里,幾乎每篇回憶都有關于歌聲的回憶,從開篇記錄著來延安路上在三原看到紅軍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時,“心里充滿了親切與尊敬”。在延安街頭送別抗大畢業(yè)生奔赴前線軍民齊唱《再會吧,在前線上》,“氣壯山河的情景,……受到了比課堂更加強烈的教育”。在陜北公學學期期間,“一有空,鄭律成就為大伙兒表演他自己編寫的節(jié)目,使我們緊張整天的生活,頓時輕松活躍起來。……他拉起自己創(chuàng)作的《延安頌》,大伙兒就跟著他的節(jié)奏一起輕輕地唱……這首歌曲一直激勵著我,激勵著中國人民為著民族解放而奮斗。”參見任文《我要去延安》,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8、16-17、25-26。和鼓舞士氣;另一方面培養(yǎng)健康的娛樂生活,給緊張艱苦的生活帶來無限的樂趣,培養(yǎng)高尚的情操。魯藝成立后,更是組織了近百次的公演晚會。
“粗糙的飯食,嚴格的紀律和繁重的學習”[21]43就像熔爐的錘煉,把“自由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變成紀律嚴明的無產階級戰(zhàn)士”[34],轉變成抗戰(zhàn)建國的橋梁和先鋒。
戰(zhàn)略防御階段,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黨局部執(zhí)政的條件下,陜甘寧邊區(qū)院校黨的紀律建設重啟了在非無產階級群體中紀律建黨的思索和實踐,并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以紀律教育實踐了思想建黨原則,開啟了依規(guī)治黨新局面,在嚴格紀律執(zhí)行和管理中揉合了民主、平等的理念和方式,創(chuàng)造了針對知識青年以思想改造、制度約束、自覺遵守為特征的紀律建設奇跡。這些寶貴經驗推動黨對紀律屬性全方位認識的深入,在推進馬克思主義黨建思想中國化的進程中,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組成部分,對于新時代高校黨的紀律建設具有借鑒和啟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