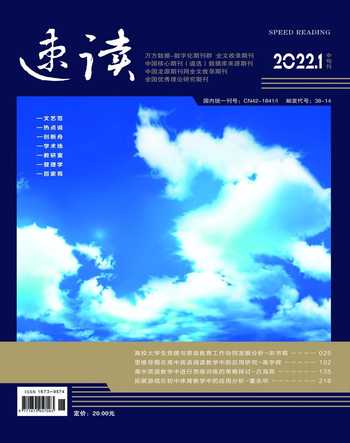論李煜詞中“風雨”意象的情感內涵
◆摘? 要:“風雨”是李煜詞中頻繁出現的意象之一,不僅符合意象的諸多特點,亦具有自身獨特的文化價值與藝術魅力。在李煜詞中,作者憑借對“風雨”意象的抒寫細致獨特地表現出男女相思之苦、時光易逝之悲、兄弟離散之愁以及國破家亡之痛等深刻復雜的情感內蘊,可以說“風雨”意象貫穿著李煜整個生命歷程。
◆關鍵詞:李煜詞;“風雨”意象;情感內涵
意象是客觀物象經過創作主體獨特的情感活動而創造出來的一種藝術形象,是賦有某種特殊含義和文學意味的具體形象。在中國封建社會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知識分子由于社會遭遇的近似和精神生活的一致,形諸歌詠,常常通過類似的意象寄托大體差不多的情思。作為自然界中普通尋常的“風雨”意象,不僅符合意象的諸多特點,亦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價值與藝術魅力。筆者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璟李煜詞校注》為參考,對李煜詞中涉及“風雨”意象的詞作進行統計得15首,約占其詞總數的一半。其中與風有關的詞匯有“東風”“秋風”“春風”“林風”“斷續風”等,與雨有關的詞匯有“細雨”“雨聲”“寒雨”等,因此可以說“風雨”意象貫穿著李煜的整個生命歷程,飽含著李煜豐富獨特的情感內蘊。在李煜詞中,作者主要以“風雨”意象表現男女相思之苦、時光易逝之悲、兄弟離散之愁以及國破家亡之痛。
一、以“風雨”意象表現男女相思之苦
自晚唐五代花間詞派以來,描寫女性生活,反映男女情愛一直是詞中最主要的內容,這類詞作風格柔美婉約,脂粉色彩濃烈,故歐陽炯的《花間集序》稱:“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作為一位“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的南唐帝王,李煜在繼承傳統艷情詞藝術手法的基礎上,運用更為細膩的筆觸對男女愛情生活進行直率真切的描寫,生動展現出男女主人公在戀愛過程中的相思離別之苦。這時作者詞中的“風雨”意象成為了阻隔男女愛情外部環境的象征,也是為表達青年男女不能長期廝守而苦悶與無奈情感的藝術符號。如:
“云一緺,玉一梭,澹澹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長相思·云一緺》)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搗練子令·深院靜》)
“亭前春逐紅英盡,舞態徘徊。細雨霏微,不放雙眉時暫開。綠窗冷靜芳音斷,香印成灰。可奈情懷,欲睡朦朧入夢來。”(《采桑子·亭前春逐紅英盡》)
在這類詞中李煜多以女性的口吻表達對意中人的思念,如《搗練子令》,全詞以搗衣為題材,在深夜的庭院里思婦聽見秋風聲夾雜著搗衣聲,孤獨惆悵,寂寞難眠,整首詞構成一種凄冷的境界,情感難以言說。“風”意象的運用主要是為襯托女子內心的苦悶孤寂,于景中見情。又如《長相思·云一緺》,這首詞寫女子秋雨長夜中的相思情意。詞的上片以刻畫女子外在容貌形態為主,“輕顰雙黛螺”之句已顯示出女子雙眉輕皺的哀怨之態。下片則注重對場景氛圍的塑造,在深秋的夜晚,屋外傳來的風聲本就容易催發女子相思的愁緒,況又有苦雨相應和。在這種凄涼冷寂的環境下,女子遙望簾外“風吹葉落”“雨打芭蕉”的景象更覺痛苦難眠,作者連用“風雨”意象反復渲染出女子相思之苦。《采桑子·亭前春逐紅英盡》則是一首描寫思婦傷春懷人的作品。春天將盡,落英隨風,霏微迷濛的細雨正如閨閣女子心中千絲萬縷的愁緒一般連綿不斷。“細雨”不僅打濕了繁枝落花,女子對美好愛情的憧憬也被這點點滴滴的雨聲打碎。在以“風雨”意象表現男女相思之苦的作品中,《謝新恩·秦樓不見吹簫女》一詞更為特殊:
秦樓不見吹簫女,空余上苑風光。粉英金蕊自低昂。東風惱我,才發一衿香。瓊窗夢醒留殘日,當年得恨何長!碧闌干外映垂楊。暫時相見,如夢懶思量。
這首詞是李煜悼念已故昭惠后即大周后的作品,周后生前容貌美麗,通音律、擅歌舞,李煜與其情感深厚、恩愛有加,因此這首悼亡詞情感纏綿悱惻,字里行間充滿著悲哀與無奈。秦女難見,上苑空留,五顏六色的鮮花雖然繽紛絢麗但卻無共賞之人,東風本是尋常,作者卻責怪其不停地撩撥自己痛苦的內心,“東風”意象正是作者苦悶情緒的化身,與其說是“東風惱我”,不如說是“我惱東風”,言得無理,也言得無奈。
總之,在李煜涉及男女情愛的詞作中,“風雨”成為了作者渲染凄涼孤獨的場景氛圍,奠定全詞感傷情緒基調的常用意象,“風雨”意象和其他自然景物意象的組合應用使得李煜詞中男女人物的相思離別之情更為豐富深刻。
二、以“風雨”意象表現時光易逝之悲
與浩瀚無盡的宇宙相比,人類盡顯渺小卑微。時光荏苒、寒暑流易,時序的不斷變化促使著文人士大夫對個體生命意識的感發。先秦時期,《詩經·唐風》中的《蟋蟀》、《山有樞》等感物傷時的篇目已可見古人生命意識的萌發。以《唐風·蟋蟀》為例,全詩以蟋蟀起興,正因蟋蟀由野入堂的遷居狀況生發作者對時光飛逝的感嘆,勸勉世人勤勉努力,切勿耽于淫樂,荒廢本業。漢代時期,一些樂府民歌則將感嘆個體生命的短暫作為抒寫的主要內容。如《薤露》,這是一首西漢無名氏創作的雜言挽歌,作者以薤葉上的露珠起興,以露水的干枯象征生命的流逝,又將干而能復生的露水與奄忽卻不可再得的人生形成鮮明對比,傷悲之情令人嘆息不已。到了東漢末年,生命的時間性問題第一次在文學史上占據了主導的位置,《古詩十九首》對人生無常、生命短暫的感慨,第一次把個體生命的有限性作為首要的主題加以表現。諸如《生年不滿百》《回車駕言邁》等作,皆是因為韶華流逝而引起對人生目的朦朧思考,表現了東漢時期文人士子面對生死問題的苦悶與彷徨。歷經文學自覺的魏晉時期后,文學作品緣情的主張更越來越多的文人士大夫所接受。作為一位情思細膩、多愁善感的文學家,李煜對自然現象的變化體察細致入微,其作品中所抒發的光陰易逝之悲,物是人非、好景難留之嘆都可變現在作者對“風雨”意象的抒寫中,如:56C1D5C0-D52A-44B6-9D4F-343E916292E5
冉冉秋光留不住,滿階紅葉暮。又是過重陽,臺榭登臨處,茱萸香墜。紫菊氣,飄庭戶,晚煙籠細雨。雍雍新雁咽寒聲,愁恨年年長相似。(《謝新恩·冉冉秋光留不住》)
遙夜亭皋閑信步,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澹月云來去。桃李依依春暗度,誰在秋千,笑里輕輕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蝶戀花·遙夜亭皋閑信步》
庭空客散人歸后,畫堂半掩珠簾。林風淅淅夜厭厭。小樓新月,回首自纖纖。春光鎮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窮!金窗力困起還慵。一聲羌笛,驚起醉怡容。(《謝新恩·庭空客散人歸后》)
《謝新恩·冉冉秋光留不住》是李煜重陽時節登臨縱目之作。秋光漸過,紅葉滿階,又是一年重陽時節。在煙雨籠罩的傍晚,作者登臨望遠,隨處雖見茱萸香墜,紫菊繞庭,但卻心情黯淡,豪無欣賞雅志,遠處傳來新雁的哀鳴頓時勾起作者滿腹的愁情,作者年年相似的愁恨正化在這晚秋煙雨中。全詞多處以景見意,上下兩片渾然一體,深切表達出作者對時序流逝的感嘆與哀愁。又如《蝶戀花·遙夜亭皋閑信步》,詞的上片寫主人公信步閑情、傷春感懷的情形,下片寫主人公感慨春去、無以自慰的悲愁情懷。時至暮春,清明將過,作者因長夜難眠獨自在水邊漫步,只見雨停風住,月色朦朧,春光明媚如依依桃李但卻暗暗溜走,他人歡笑而我獨傷神,不禁平添萬千愁緒,作者的傷春之情亦如時停時止的風雨一般深曲綿渺。《謝新恩·庭空客散人歸后》亦是一首感傷色彩濃烈,傷時嘆時之情難以言表的作品。人散庭空,珠簾半掩,在漫漫長夜里作者聽見淅淅的林風,遙望樓上纖纖的新月,倍感寂寞難耐。春光雖好人卻逐漸憔悴,新愁舊恨郁積于心頭,作者想要酣睡晚起卻一聲羌笛驚醒。詞中“林風”以及其他諸多自然景物意象的運用使得全詞更具光陰易逝、物是人非之悲。《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中的“風雨”意象則象征著外部惡劣環境對美好事物的摧殘,從側面反映出作者在面對時序流逝時的凄涼無助: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
林花凋零落盡,引發作者匆匆之嘆,況又遭受寒雨冷風的不斷侵襲,更覺無奈之悲。全詞將人生失意的無限悵恨寄寓在對暮春殘景的描繪中。由于作者對詞中客觀景物強烈主觀情感的注入,原本由個別的景物情事所發出的“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的感嘆便更能引起讀者普遍性的情感共鳴
三、以“風雨”意象表現兄弟離散之愁
與父親李璟不同的是,李煜雖為帝王之尊,但卻與兄弟相處和睦,感情真摯。他的八弟出鎮宣州時,他曾率領臣子設宴于綺霞閣,賦詩并作《送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序》餞別。七弟從善出使汴京被扣,他上表乞求宋太祖許之歸國遭拒,因此作《卻登高文》見意,在李煜表達兄弟離散之愁的詞作中,“風雨”亦是其常用意象。如《采桑子·轆轤金井梧桐晚》:
轆轤金井梧桐晚,幾樹驚秋。晝雨新愁,百尺蝦須在玉鉤。瓊窗春斷雙蛾皺,回首邊頭。欲寄鱗游,九曲寒波不泝流。
這首詞看似寫男女相思,實際是李煜因思念入宋不歸的弟弟從善而作。深秋時節,梧桐樹下落葉滿地。樹木入秋而變,人見秋色而愁。閨中人獨守著瓊窗,眼望窗外細雨想到心愿難成,只有雙眉緊皺,愁在心頭。回首邊地,征人久無音訊。想要寄書信,可是寒波滔滔,溯流難上,只能在孤獨寂寞中苦苦守望。全詞以意融景、風格蘊藉,“梧桐”“寒波”等意象的選用構成了一幅蕭瑟清冷的秋景圖,而詞中的“晝雨”不僅是單純的自然景象,也象征著作者因思念兄弟而百轉千回的愁緒。又如《阮郎歸·呈鄭王十二弟》:
東風吹水日銜山,春來長是閑。落花狼藉酒闌珊,笙歌醉夢間。春睡覺,晚妝殘,憑誰整翠鬟?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闌。
這首詞也是李煜為其弟李從善而作。詞的上片主要寫主人公空虛無聊、無所寄托的醉生夢死的生活;下片則寫主人公憑欄自傷的落寞惆悵。整首詞由大處著眼,至小處落筆。東風吹動春水,遠山連接落日,春天來臨作者卻倍感無聊。落花一片狼藉,酒興也逐漸衰減,吹笙唱歌整日就像醉中夢里一般。因為相思之苦,詞人只有在黃昏時候獨自倚靠著欄桿嘆息。
四、以“風雨”意象表現國破家亡之痛
李煜生性懦弱,雖然在文學上頗有才華,但在政治上只屬平庸之輩,難有雄主勵精圖治的決心。開寶八年冬末,宋朝軍隊攻陷金陵,李煜率眾臣肉袒出降,南唐政權滅亡。第二年正月李煜被押解至汴京,開始了囚徒般的悲慘生活。身份的巨大轉變與深切的痛苦悲哀使李煜的詞作上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其詞作中的“風雨”意象由于作者對亡國之悲的反復宣泄更覺沉痛之悲。“風雨”承載著作者的撫今追昔的悔恨和悲傷,如: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
“昨夜風兼雨,簾幃颯颯秋聲。燭殘漏斷頻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烏夜啼·昨夜風兼雨》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任珠簾閑不卷,終日誰來。金鎖已沉埋,壯氣蒿萊。晚涼天凈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往事只堪哀》)
《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相傳為李煜的絕命之作。五更夢回、春意零落,薄薄的羅衾擋不住寒意的侵襲,簾外潺潺的雨聲更讓詞人滿腹憂愁,所以詞人只有追憶夢中情事,才能貪戀片刻歡娛,可是夢醒之后水流花落,春去人逝,只留下無盡的感概與悲哀。全詞情真意切、哀婉動人,抒發了作者由天子降為臣奴后難以排遣的失落感,以及對南唐故國故都的深切眷念。深刻地表現出作者的亡國之痛和囚徒之悲,而觸發這一切情感的媒介正是詞中的“雨”意象。在《浪淘沙·往事只堪哀》中,全詞開篇將已將情感基調凝結到一個“哀”字上。“秋風庭院蘚侵階”之句則將“對景難排”的亡國之恨表現得具體形象。時值深秋蕭索之季,黃葉凋零,作者身處高墻圍困的庭院,觸目可見暗綠的苔蘚爬滿臺階。景色已然寂寞,秋風拂過,更覺黯然傷神。《烏夜啼·昨夜風兼雨》全詞開篇則用“風雨”起興,“風兼雨”與“颯颯秋聲”相對應,在這種凄涼寒苦的景色中,作者的心境便可想而知。加以“昨夜”二字點染,不從日而偏從夜寫起,正見作者因滿懷愁思而夜不能寐,亦有往事不堪回首之嘆。雖是客觀的寫景,但作者的形象,尤其是他的彷徨、郁悶的心情卻隱然可見。
在李煜后期的作品中,作者還擅長借用“風雨”意象以樂景寫哀情,通過詞人前后生活方式、身份地位的巨大反差形成鮮明的對比,將亡國之痛表現得深切感人。如《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這是李煜亡國入宋被囚后創作的一首記夢詞。春風和煦,花好月圓,作者回憶當時在上苑快活游玩的盛大氣派,內心充滿了喜悅。“花月正春風”五字正點明了游賞的時間以及觀賞對象,渲染出熱鬧繁華的氣氛,還象征著作者生活中最美好,最無憂無慮、春風得意的時刻。“花月”與“春風”之間,以一“正”字勾連,景之艷麗、情之濃烈,一齊呈現。這一句將夢游之樂推向最高潮。夢境越是繁華熱鬧,夢醒后的悲哀便越是濃重。就意象“風”的使用而言,“春風”所代表的還是一種歡愉舒適的情調。又如《虞美人·風回小院庭蕪綠》:
風回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憑闌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笙歌未散尊罍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暗畫堂深,滿鬢青霜殘雪思難任。
全詞在對生機盎然、勃勃向上的春景中寄寓了作者的深沉怨痛,在對往昔的依戀懷念中也蘊含了作者不堪承受的痛悔之情。春風吹回,庭院的雜草變綠,柳條上的新葉細長如人睡眼初展,但是詞人卻獨自依靠著欄桿半天沒有話說。也許東風解凍透露春天的氣息,但對詞人說來春天已經永遠過去了,因此在賜第里雖有故妓,還可以奏樂,酒杯還在,還可以飲酒,但詞人卻已兩鬢如霜,故國憂思更是難以承受。
參考文獻
[1]黃田田.論唐詩中的風雨意象[D].山東:山東師范大學,2011.
[2]詹安泰.李璟李煜詞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3]吳婕.《詩經》中的時間意識及對后世的影響[J].浙江: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2.
作者簡介
鐘耀東(1997.06—),男,漢族,四川南充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方向。56C1D5C0-D52A-44B6-9D4F-343E916292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