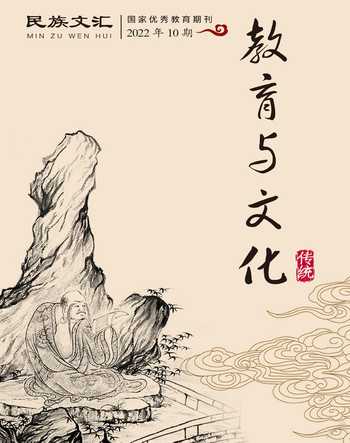《包法利夫人》和《寒夜》女主人公形象對比分析
耿辰忻
關鍵詞:《包法利夫人》;《寒夜》;人物形象;女性意識
一.人物背景的比較
《寒夜》這本小說是巴金先生寫于1944年至1946年底,它的故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重慶,當時的“五四運動”的余波仍在,但此時距離“五四運動”快30年了。在這約30年期間, 隨著西方新的文化思潮大量涌入, 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種與男性社會抗衡、追求男女平等的新的意識形態, 被稱作女性意識。在這之后,隨著五四運動的勝利,女性解放運動在中國的推廣,現代的女性也開始站起來了。她們勇敢的對抗封建制度,捍衛自己的尊嚴。《寒夜》則是圍繞當時的女性意識和形象而創作的一本小說。
《包法利夫人》是福樓拜寫于1848年,一個資產階級取得全面勝利后的社會的樣子。當時法國資產階級引以為豪的時代已經結束, 接著人們到來的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時代。《包法利夫人》反映出女主人公對浪漫主義的追求和平庸生活之間的矛盾。在當時,男人占據著主導地位,從神話——女人夏娃是從男人亞當身上一根肋骨誕生起,男人就被認為是世界的中心,女人應該并且必須服從于男人。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欲將一股“平等” 之風吹向歐洲大陸,試圖打破一成不變的等級觀念。
二.比較人物對愛情和婚姻的態度
《寒夜》中的曾樹生是受過先進良好教育的新時代女性,她年輕時追求自由和浪漫,主張男女平等戀愛自由和擺脫傳統封建禮義的束縛。曾樹生作為新時代的女性,并沒有向封建傳統低頭,她和汪文宣在個性解放的大環境中相遇且相愛。受過新教育的二人年輕時也有共同的理想追求。
但《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瑪,對于婚姻并不真誠。從小沉浸在美好浪漫愛情故事里的她,只希望通過婚姻愉悅自己,而并非對其負責。她渴望貴族的奢華生活,渴望嫁給一個白馬王子。但她對于婚姻里每一個男人都不太滿意,在有丈夫的情況下與他人私會追求刺激,是一種及其不負責任的觀念和做法。一種“病態的熱情”在艾瑪身體中滋長。
三.女性意識覺醒的對比
《寒夜》中的故事發生在抗戰勝利前夕的重慶,曾樹生和汪文宣便是在思想解放的風潮中墜入愛河的。曾樹生她不僅年輕漂亮、健康活潑, 同時也追求個性解放、個人價值。受當時“教育救國”的影響, 她選擇了教育事業, 希望和丈夫共同創辦鄉村化、家庭化的學堂。因為曾樹生她受過新型的教育,她堅持著先進的價值觀念,有先進的理想。她講求男女平等,并始終保持與丈夫在一個平等的位置之上。她的態度和作風也不卑不亢,甚至于在經濟實力和生存能力方面已經超過她的丈夫,她盡可能用嶄新的姿態為女性占據現代社會的一席之地做出了開創性的嘗試與示范。
但她也在生活中經歷苦楚,患病的丈夫,與自己思想意見不和的婆婆,但是這并沒有使曾樹生改變自己。她依舊不依附于丈夫和家庭,努力甩開“花瓶”這個標簽,堅持獨立自主的意識。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曾樹生是一個生活在舊社會惡劣且過于傳統的社會環境和矛盾重重的家庭環境中的女性。但是她身上依然有著“五四”文化精神, 既有反抗意識, 又在抉擇面前痛苦無奈、孤立無援卻努力掙扎的中國知識女性形象。
同樣,在《包法利夫人》的西方世界里,隨著手工業的發展,女性有機會進入工廠開始工作,她們擺脫了女性傳統的相夫教子的任務,她們認識到女性也可以讀書看報,女性也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其中一部分思想先進的女性甚至開始擺脫對男人的依附,她們心中已經逐漸有了獨立意識。
愛瑪認為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樣自由地活著,不能去很多國家旅行,不能隨心而活。她的想法也體現了她女性意識的覺醒,表達了她對男女不平等的不滿與控訴。愛瑪對愛情的追求和對生兒子的渴望,都體現了她敢于拋棄世俗的眼光,摒棄男權社會對女性形象的定義。她這些行為和大膽的追求都體現了女性意識的覺醒,體現了她對男權社會的厭惡,對女性思想和身體解放的訴求。
但是與曾樹生相比,愛瑪是不成熟的。她接受的不是當時先進的教育,而只是從美好的文學作品中推理出的理想中的愛情,是從照顧她的修女口中了解到社會的繁華。這與曾樹生所接受到的新式教育完全不同。艾瑪的社交圈子中,大部分是為生活奔波的人,她自詡和這些人不是一個層面,整日無所事事。于是在百無聊賴中,她只能倚著窗臺渴望著愛情的到來。這種對愛情的近乎瘋狂地執著存在著很大的弊端。她對丈夫由親近變得疏遠,片面地追求家中華麗的裝飾,想要通過搬家和舞會進入更高層次的社會。她在閱讀中虛構浪漫的故事,把自己生活的改變強加到男人身上,這只是女性獨立意識的萌芽,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女性的崛起。
四.總結
本篇論文我們研究了三個大問題,分別是人物背景的比較,人物對于婚姻和愛情的態度以及女性意識的覺醒。我們大致了解了福樓拜與巴金的創作年代和寫作手法。艾瑪和曾樹生的人物形象對比,二人在女性意識上的不同認知。
綜上所述,雖然身處不同文化背景,兩位女主人公的結局一個是出走一個是死亡,二者的悲劇性結尾是一樣的。
艾瑪的悲劇源于她尋求理想中的幸福而不得的墮落, 但這絕不僅是她個人造成的, 是整個資產階級葬送了她。因此這場悲劇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悲劇。
曾樹生盡管從那個壓抑的“家”走了出來, 但事實上她并沒有得到她所想象的幸福與自由。由于始終處于對丈夫的虧欠中, 她最終還是從蘭州返回那個早已家破人亡、人去樓空的家中, 卻發現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
女性意識覺醒的她們,努力在舊式社會劃開口子,嘗試吸吮外部世界的空氣,掙脫傳統家庭中夫妻關系和倫理道德的束縛,做出順從內心的人生抉擇和追求幸福的決定。然而, 由于傳統社會秩序和意識形態觀念的束縛, 她們并沒有找得到一條真正獨立、自由的道路, 她們也沒有得到她們所追求、渴望的幸福與自由, 她們也很難從對男權的依附中擺脫出來, 她們最終會被當時那個男權社會所吞噬。我們通過巴金的《寒夜》和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我們應該對女性解放的時代命題有更深刻的思考。在那個時代, 女性的個性解放不能僅局限于女性自身行為, 還需要依靠整個社會的進步, 女性解放的真正實現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Fabienne Dupray : madame Bovary et les juges. Enjeux d’un procès littéraire Genèse et enjeux d’une institution Fabienne Dupray Dans Histoire de la justice 2007/1 (N° 17)
[2]陳彥龍.完整的人性——《包法利夫人》與《寒夜》的比較分析[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6(S2):52-53.
[3]賈煒.寒夜中的微光——論巴金作品《寒夜》中的曾樹生[J].牡丹,2020(08):111-112.
[4]江臘生,龔玲芬.世情困厄與人性糾結——論巴金《寒夜》中的三重戰爭文化圈[J].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8(04):179-188.
[5]李昌云.淺論《寒夜》與《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人公[J].技術與市場,2013,20(11):157-158.
[6]石錦旭.論《包法利夫人》中艾瑪的婚姻觀及其悲劇性[J].青年文學家,2021(11):106-107.
[7]田檸.《寒夜》和《包法利夫人》女性主人公形象對比分析[J].青年文學家,2021(09):24-25.
[8]熊婷.巴金《寒夜》中小人物的創傷解讀[J].文學教育(上),2021(03):27-29.
[9]晏暉.論《包法利夫人》中的女性主義思想[J].名家名作,2020(11):122-123.
[10]張伊楠.比較視域下女性的成長困境——《寒夜》與《包法利夫人》主人公形象解讀[J].深圳社會科學,2019(05):127-13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