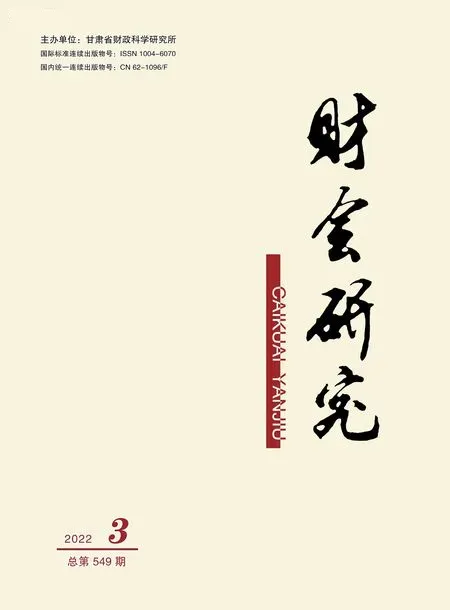高管違規處罰、企業社會責任與債務融資成本
——基于“關鍵少數”治理的視角
■/ 田冠軍 劉雨雙
一、引言
上市公司高管在資本市場具有獨特的職業地位,其所言所行代表企業形象,由于聲譽機制的傳播效應,高管嚴重的“負面輿情”往往會給公司聲譽帶來較大沖擊,既會給企業帶來當前損失,也不利于品牌形象的維持和長遠發展。2020 年10 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促進規范運作的主體責任。作為“關鍵少數”的高管人員,理應在優化上市公司治理模式和治理機制,推動公司“做優做強”和高質量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少數”提法,最初來源于政治領域,強調領導干部在治國理政中的關鍵作用,在重點領域和重要工作中發揮領導干部的表率和“風向標”作用,在問題導向和追紀問責中約束領導干部,強化反腐敗、反不作為、反亂作為,進一步凈化政治生態。隨后該概念引申到了資本市場領域,最近一年多來,“關鍵少數”已頻繁出現在上市公司監管部門的會議或領導表態中,治理對象、權力界限和責任界定明確指向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和“董監高”。
改革與管理如同“鳥之兩翼”,既要對標管理、提質增效、增強活力,也要聚焦關鍵業務和重要環節,強監管、嚴問責。當前上市公司高管違規集中體現于財務造假、內部交易、濫用職權、徇私枉法等方面,相應的處罰措施包括警告、罰款、沒收所得、市場禁入、賠償損失甚至是刑事處罰。無論程度高低,證監會或交易所的處罰都會引起社會關注,從而引發對企業聲譽、形象以及未來發展的擔憂,進而影響企業的資源優勢和關鍵能力(如融資)。黨的十九大、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世界一流企業不僅市場競爭力強、價值大,而且需要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也就是說,不僅在企業規模、活力、管理水平、經營成果和市場價值,還應在企業文化、形象與履行社會責任、創造社會價值上達到一流水準。近年來,上市公司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在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和治理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但仍面臨一些問題和不足,主要表現在部分公司對社會責任重視不夠、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質量不高、社會責任治理機制不完善等。
現有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動因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積極與市場和社會溝通,展示其價值取向和良好形象,另一方面是為了追求利益而產生“掩飾”動機,通過“偽裝”緩解企業負面行為帶來的沖擊。因此,社會責任的積極履行在高管違規處罰對企業融資影響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作用的發生機制是亟待探討的問題。為此,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從公司治理角度來揭秘“關鍵少數”負面事件及程度與企業債務融資能力之間的關系,同時從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角度來研究其對兩者關系的調節作用和影響路徑。
二、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主要針對企業違規處罰,直接研究高管違規處罰的文獻很少。兩者雖視角和概念范疇有差異,但均是企業負面行為及其后果的體現。本文以企業違規處罰為基礎來進行文獻梳理。
(一)企業違規處罰與債務融資成本
關于企業違規處罰,現有文獻傾向于剖析其發生的緣由,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基于外部治理角度,例如從分析師跟蹤、媒體監督、行業投資信心等方面分析企業違規的取向;二是基于內部治理層面,例如從股權集中度、高管薪酬、CEO 影響力和獨立董事特征等方面分析企業違規的動因。對于違規處罰后企業所面臨的后果研究較少。企業的違規風險直接導致產生所謂的信貸配給現象,因為債權人會更看重企業的形象和聲譽。Karpoff and Lott(1993)認為,負面事件的發生,不僅表面上由于行政處罰會帶來直接影響,更在于對企業聲譽的沖擊及額外增加各種成本。由于信息不對稱,公司違規會加大企業獲取融資信息的成本(Karpoff et al,2007);當企業受到處罰聲譽受損時,債權人會認為其信用風險增加,繼而通過提高利率、加大貸款擔保、縮短還款期限等增加融資難度和成本(Goss and Roberts,2010)。我國學者進行了類似研究,謝紅軍等(2017)發現企業的負面聲譽會加大企業的融資難度;竇煒等(2018)運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發現受到違規處罰的企業,下期的債務融資成本更高,同時法治水平越低的地區,違規行為對債務融資成本的負面影響更為嚴重。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債務融資成本
現有實證研究證實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與良性后果,不僅體現在能使企業獲得良好的經濟回報和利益(Barnett and Salomon,2006),還對員工幸福感的提升有明顯的正向影響(朱月喬等,2020);許罡(2020)研究發現企業高質量的社會責任能更有效地抑制商譽泡沫的產生,從而降低風險,維護市場穩定。總體來看,將社會責任與債務融資成本聯系起來綜合分析的文獻還較少。從融資便利性分析,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會向市場傳遞積極的信號,化解其面臨的信任困局,從而更容易獲得融資;從融資成本分析,社會責任的履行不僅有利于降低綜合融資成本,還會降低債務融資成本。Verrecchia(2001)研究證實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可以減少利益相關者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從而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周宏等(2018)研究發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可以減少企業債券信用利差,促進融資成本降低;Attig et al(2013)研究證實企業完善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機制能夠更加正向地影響評級機構對企業的信用評級,從而降低企業債務融資成本。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違規處罰
企業社會責任與違規處罰兩者均會對企業的聲譽形象產生重要影響。基于聲譽和合法性理論,違規行為會給企業帶來嚴重的負面沖擊(Pfarrer,2008),而社會責任可使企業樹立起對社會負責的品牌形象。由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能有效調節企業與利益相關人之間的關系,因此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納入可持續發展戰略管理體系。徐詩意與陳永麗(2021)從利益相關者理論視角出發,發現社會責任履行能有效抑制違規處罰的發生,這種抑制主要是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風險等潛在路徑實現。與此相對應的是——違規企業更傾向于主動披露社會責任履行報告,以維持和修復自身的合法性(車笑竹和蘇勇,2018)。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成果有較多可資借鑒之處,但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本文拓展了其研究方向與范圍,具體貢獻在于:1.將高管違規處罰和企業融資放入一個框架進行研究,為探索政府宏觀治理行為的經濟后果提供了經驗證據;2.現有的實證分析主要探討企業違規處罰,而對于企業的“關鍵少數”——高管負面行為對企業的影響,相關文獻極為缺乏,本文為此提供了補充經驗證據;3.在高管違規處罰影響企業融資時,企業社會責任有無可能產生“救贖”功能?本文重點探討三者之間的關系,分析社會責任的履行可否緩解高管違規處罰對企業融資能力的影響,以為上市公司和其他市場主體強化微觀治理提供新的經驗證據。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高管違規處罰與債務融資成本
資本市場具有不完美性和不確定性,融資能力易受信息不對稱程度的約束。具體而言,為應對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企業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銀行更傾向于采用信貸配給而非調整資本成本來促使供需平衡(Stiglitz and Weiss,1981)。在信用時代,除銀行外,其他融資方也都很看重企業信譽。已有文獻表明,信號傳遞與聲譽約束是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的重要舉措。由于聲譽具有信息傳遞功能,良好的聲譽能夠提高企業的融資能力,帶來額外收益(Mathews,1984)。然而,企業聲譽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較長時間的用心經營;一旦失信,交易伙伴就很難再愿意與其發生經濟往來。高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企業的“形象代言人”,根據證監會及滬深兩所近年的公開處罰信息,多數由于信息披露不及時、財務造假、違規擔保等原因受到處罰。高管違規處罰會傳遞監管部門或機構凈化市場生態等信號,暴露企業高管的誠信傾向和聲譽風險,進而影響企業的融資信用。作為對高管無視法律法規的一種制裁,處罰會降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及其高管的信任,利益相關者之一的債權人會質疑企業的運作、經營業績表現等,因而會要求更高的成本以對沖其承擔的風險。綜上,提出假設1:
H1:企業高管由于違規受到處罰后,會加大企業本身的債務融資難度,具體表現為債務融資成本的增加。
(二)高管違規處罰、社會責任與債務融資成本
現有研究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并非純粹的“利他主義”,也可能是出于“工具型動機”獲得一定利益。從戰略上看,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是一種戰略行為,可以有效地幫助企業獲得競爭優勢(Por?ter and Kramer,2011);從績效上看,企業社會責任和盈利并不矛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張兆國等,2013);從風險上看,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有益于其獲得利益相關者的認可和支持(Hoffman,2007),在負面事件發生時,可以轉移公眾對負面事件的注意力,減輕其帶來的損失(Koehn and Ueng,2010)。Guangming Song et al(2018)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與債務融資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社會責任不僅是支出,更是可以給企業帶來正面效應的“投資”。從企業聲譽理論來看,盡管企業聲譽“看不見”、“摸不著”,但其蘊藏的威力巨大;若不能快速識別聲譽風險,便會出現“滾雪球”效應,最終釀成重大危機。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較快修復聲譽損失,緩解高管負面事件給企業帶來的形象沖擊,因而可以緩解債務融資約束和融資成本壓力。基于此,提出假設2:
H2:社會責任的履行在高管違規處罰與債務融資成本之間發揮著顯著正向調節作用。
四、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選取
本文以2010-2017 年我國A 股上市公司相關數據為初始樣本。為了研究的需要,按照如下步驟進行了樣本篩選:剔除金融保險類、ST 類企業;剔除研究期所選變量有缺失的數據;為減少數據極端值的影響,對主要連續變量進行了1%和99%水平的縮尾處理。本文所需數據主要來自國泰安數據庫、Wind數據庫和筆者的手工整理。經上述處理,最終得到5364個樣本。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債務融資成本,借鑒姚立杰等(2018)和倪娟等(2019)的研究,具體采用利息支出除以期末總負債作為債務融資成本的衡量方式。
2.解釋變量。
(1)高管違規處罰。對于高管違規處罰的測量,本文借鑒戴亦一等(2017)的研究,利用違規處罰是否發生作為測量指標。本文依據中國證監會以及深滬兩所發布的公告,手工整理了高管違規處罰數據,若企業存在高管違規處罰,則定義為1,反之為0。
(2)高管違規處罰程度。同樣借鑒戴亦一等學者的研究,衡量高管違規處罰程度,輕微處罰(批評、警告、譴責等)賦值為1;中度處罰(罰款、立案調查等)賦值為2,超重處罰(市場禁入等)賦值為3。因企業高管非一人,因而將同年度同家企業高管違規處罰變量值進行累加并加自然數1,最后取其對數衡量高管違規處罰程度。
(3)社會責任。采用和訊網發布的企業社會責任評級報告,用企業社會責任總得分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程度。
3.控制變量。借鑒已有研究,本文設置企業規模、托賓指數、自由現金流量、企業成長性和產權性質作為控制變量。
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三)研究模型
為檢驗假設1和假設2,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上述模型中,模型(1)、模型(2)用于驗證假設1。模型(1)中Vioi,t為解釋變量,代表i公司第t年高管違規處罰,α1是其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程度。Con?trols為控制變量的集合,包括企業規模、托賓指數、自由現金流量、企業成長性和產權性質。而模型(2)則以Vio_penaltyi,t為解釋變量,再次進行假設1的檢驗,以增強結論的穩健性。
模型(3)、模型(4)用于驗證假設2。其中Vi?oi,t×CSRi,t用以驗證企業社會責任的調節作用,α2代表其對被解釋變量的調節程度,其他部分含義與模型(1)相同。同樣模型(4)以Vio_penaltyi,t×CSRi,t為替代變量,再次檢驗假設2 的合理性。
五、實證分析
(一)基本分析與檢驗
1.描述性統計。由表2 可知:企業債務融資成本(Cost)的均值為0.0229,樣本標準差為0.0152,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0.0669 和0,表明企業債務融資成本平均不高,不同企業之間的債務融資成本在整體上差異不大。社會責任得分(CSR)均值為26.75,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76.49和-4.390,標準差為18.74,表明社會責任整體水平不高,不同企業之間社會責任表現存在明顯差異。控制變量與現有文獻報告結果一致。

表2 描述性統計
2.基本回歸分析。
(1)高管違規處罰與債務融資成本。為了明確高管違規處罰對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分別按高管違規處罰和高管違規處罰程度進行檢驗。由表3模型(1)的回歸結果可知,高管違規處罰(Vio)與債務融資成本(Cos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高管違規處罰會加大企業債務融資成本。本文還使用替代變量高管違規處罰程度與債務融資成本進行了回歸,由表3模型(2)的回歸結果來看,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進一步支持了假設1。盡管經濟運行及監管更加規范,但仍有不少企業及高管為追求自身價值或利益鋌而走險,管理機構發布的高管違規處罰公告無疑是在向社會傳達一個負面的“聲譽信號”,債權人必然對此有所警惕并通過設置門檻、加大融資成本等措施降低風險。
(2)社會責任的調節效應。為檢驗假設2 成立,本文采用高管違規處罰(Vio)與社會責任得分(CSR)的交乘項來衡量社會責任對高管違規處罰的調節效應。由表3 的模型(3)回歸結果可知,交乘項(Vio×CSR)在5%的水平上顯著且為負,而高管違規處罰(Vio)顯著且為正,表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減輕高管違規處罰導致企業融資成本增加程度。另外為測試結果的穩健性,采用替代變量違規處罰程度(Vio_penalty)與社會責任得分(CSR)進行交乘再次檢驗調節效應,結果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與上述結果一致,進一步證實了社會責任履行的緩解效應。

表3 基本回歸結果
3.穩健性檢驗。為了檢驗上述結論的穩健性,我們還采用了以下方法:一是為消除可能存在的選擇性偏差造成的回歸結果不穩健,通過隨機刪除樣本的方式改變樣本容量,結果與前文結論仍然保持一致。二是對調節效應進行了穩健性檢驗,考慮社會責任履行的時滯性,將其滯后一期處理并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結論仍然穩健。
(二)高管違規處罰對公司債務融資成本的作用機制檢驗
1.機制檢驗模型構建。高管違規處罰對市場傳遞了企業信譽不佳的信號,會引起市場的負面反應,從而打擊外部投資者的信心,加大企業的融資難度與融資成本。在理論分析部分提到,作為緩解信息不對稱的重要舉措,不良信號與聲譽的傳遞會加重企業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隔閡與信任問題。為了檢驗上述信號傳導機制是否存在,本文借鑒鐘覃琳等(2018)的做法,以分析師關注數(ANA?LYST)來衡量企業的信息環境,從而反應企業所面臨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并且利用如下中介效應模型進行檢驗:


2.機制檢驗結果。表4 報告了中介效應檢驗的實證結果。模型(5)中Vio 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高管違規處罰會提升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模型(6)中Vio 與ANALYST 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明高管負面事件的發生會加劇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弱化企業信息環境的質量。模型(7)加入變量ANALYST 后,其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了中介效應的存在。而模型(8)-(10),利用Vio_penalty 變量再次檢驗了高管違規處罰所帶來的負面信號,加大了企業與外部投資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程度,使得債權人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對企業而言就表現為債務融資成本的上升。

表4 信號傳導機制檢驗
(三)考慮公司治理機制差異的進一步分析
1.產權性質差異的影響。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良好形象的塑造既是企業經營發展的需要,更是提高企業實力、優化改革環境的重要內容。由于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其在債務融資中處于優勢地位,在融資便利度、融資規模和融資成本方面占有優勢。社會對國有企業有較高的期望值,而監管機構對高管的違規處罰將影響對企業的信譽評價,進而影響國有企業的融資。本文根據產權性質進行了分組檢驗,從表5 結果可以看出,在國有企業組,模型(1)中高管違規處罰(Vio)對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而在非國有企業組,高管違規處罰對于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不明顯。模型(2)中高管違規處罰程度(Vio_penalty)的檢驗結果與此一致。由此可知,國有企業高管違規處罰更容易使企業遭受負面信息沖擊,期望反差更大,負面效應更加明顯。
從債務融資來說,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可以提升企業聲譽,得到利益相關方認可,從而提高融資能力,降低債務融資成本。我國各類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力度、深度和廣度差異較大,由于特殊的產權特性,國有企業在社會責任實踐中,無論在“質”上還是“量”上表現更為突出。國有企業受到更強的社會責任履行監管與考核,因而更有壓力和動力持續強化社會責任履行,滿足更高的社會責任要求,也會獲得更大的“信任度”。合作者“信任度”的提升,可以促進合作愿望,降低交易成本及相關費用。從表5中模型(3)的回歸結果來看,國有企業組中,社會責任的調節效應(Vio×CSR)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非國有企業組中影響不顯著;而模型(4)高管違規處罰程度(Vio_penalty×CSR)的回歸結果與此一致。由此可見,不同產權性質下社會責任履行的調節效應呈明顯差異,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能顯著降低高管違規處罰影響債務融資成本增加的程度。

表5 產權性質分組檢驗
2.資產規模差異的影響。銀行或其他債權人對于企業舉債的風險考量最根本還是取決于企業的資本實力。實力強的企業可以抵押、擔保等形式為企業“增信”,降低債權人放債風險。因而,我們將樣本根據資產規模大小進行了分組。從表6 的回歸結果來看,當企業資產規模較大時,高管違規處罰對于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并不顯著;而資產規模較小的企業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以高管違規處罰程度(Vio_penalty)進行回歸時,其結果與上述一致。這更加證實了資本實力強的企業可以緩解負面消息帶來的不利影響。

表6 資產規模分組檢驗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10-2017 年我國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以監管或交易機構發布的高管違規處罰公告為數據進行實證檢驗,著重討論了高管違規處罰對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及社會責任履行所起到的調節效應,更傾向于研究負面事件造成的影響和結果以及如何應對。實證檢驗發現:
1.高管違規處罰明確地向市場傳遞違規“零容忍”和凈化市場生態的信號,這些信號會被債權人有效捕捉和吸收,因而,高管違規處罰會增加企業的融資難度,顯著影響企業債務融資成本。
2.社會責任履行有明顯的“溝通效應”,可以有效地展現良好形象,吸引利益相關者,促進商業的可持續性,實證結果也證實了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確實能起到正面作用,可以緩解高管違規處罰對于企業融資成本增加的影響程度。
3.在進一步研究中,我們發現國有企業更易受到高管違規處罰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同時社會責任的調節作用也更為有效;相比輕資產企業,重資產企業因其資本實力雄厚,信用優勢更為明顯。
本文有如下啟示:
1.監管層面。應加強重點事項的過程監管,明晰上市公司高管等“關鍵少數”的主體責任,加大對高管違規案件的追責力度,促進規范、透明、開放的資本市場建設,構建債權人、投資者等利益保護新機制;同時,強化多方協同監管機制,建設和優化基礎性制度,推進社會責任信息的強制性披露,進一步發揮資本市場價值發現與優化資源配置功能。
2.上市公司層面。應強化內部控制建設,定期梳理制度缺失或流程缺陷,確保內控體系完整和執行有效;提升依法合規經營管理水平,以“關鍵少數”治理為重點,對高管違法違規行為事前做好防范、事中及時糾違、事后落實問責;加強社會責任風險管理,完善高管聲譽風險防控機制,及時、有效地防范和化解負面事件給企業帶來的消極影響;國有上市公司更應以落實2021 年3 月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意見》為契機,突出對“關鍵少數”和關鍵環節的內部監督。
3.債權人層面。應加強信用風險管理,完善企業信用評價體系,防范并有效應對部分上市公司高負債、高違規、低績效現象,提振市場信心;建立健全債權人利益保護機制和相機參與治理機制,有效防范上市公司債務違約風險,更好地發揮市場信號作用,營造更加理性的投資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