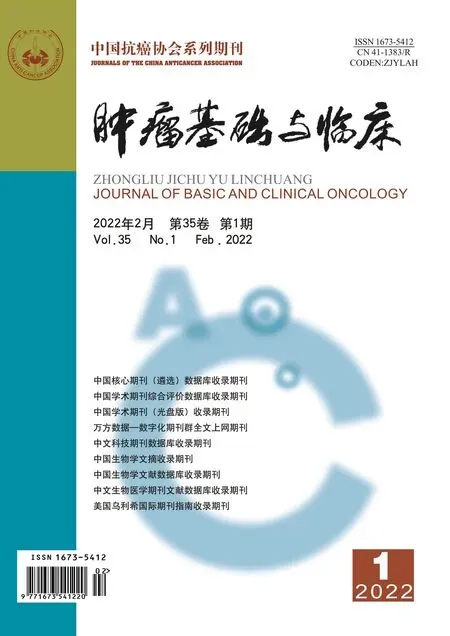術前系統免疫炎癥指數對非肌層浸潤性膀胱癌預后的評估價值
李 攀,王博文一,洪星磊,馮一鳴,苗騰飛,喬保平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河南 鄭州 450052)
膀胱癌作為泌尿系統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質量,全球每年死于膀胱癌的患者約達17萬人[1],是全球惡性腫瘤的第13大死亡原因[2],且發病率呈現逐年增長趨勢。膀胱癌可分為非肌層浸潤性膀胱癌(non-muscular invasive bladder cancer,NMIBC)和肌層浸潤性膀胱癌(muscular invasive bladder cancer,MIBC),其中新發的膀胱癌患者中,NMIBC是其最常見的類型,約占75%[3],經尿道膀胱腫瘤電切術(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r,TURBT)是目前治療NMIBC的標準治療方式,術后輔以膀胱灌注化療或免疫治療,但其復發率仍高達約30%~80%[4],嚴重影響患者的預后和生存,因此尋找可靠有效的預后評估指標對患者臨床治療有重大意義。有研究[5]表明,營養缺乏和全身炎癥反應可能在腫瘤的發生、增殖、進展和轉移中發揮重要作用。
系統炎癥免疫指數(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是一種基于血小板、中性粒細胞和淋巴細胞的新型免疫炎癥指標。Yang等[6]在Meta分析中報道稱SII是惡性腫瘤患者疾病無進展生存時間(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和總生存時間(overall survival,OS)的重要預測因子。有研究表明其與胃癌[7]、胰腺癌[8]、前列腺癌[9]、食管癌[10]等多種實體腫瘤的預后密切相關。但目前關于SII評估NMIBC患者預后的研究報道較少。本研究旨在探討術前SII對接受TURBT的NMIBC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回顧性分析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泌尿外科2014年3月至2017年1月收治的257例行TURBT的NMIBC患者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1)首次行TURBT且病理確診為NMIBC的初發患者;2)相關臨床隨訪資料完整。排除標準:1)術前行手術治療或放化療患者;2)合并嚴重心腦血管系統、血液系統、免疫系統疾病及嚴重肝腎功能不全等;3)合并其他惡性腫瘤或有其他惡性腫瘤病史;4)圍手術期發生嚴重并發癥。
1.2 方法通過我院的電子病歷系統收集患者相關指標。流行病學指標:年齡、性別、吸煙史、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術后病理學指標:腫瘤數量、腫瘤大小、病理學T分期及病理分級。術前1周實驗室指標: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血小板,并計算SII值(SII=血小板×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術后治療及隨訪:患者術后常規行膀胱灌注化療,藥物選擇吡柔比星(術后24 h灌注第1次,之后每周1次,共8次,隨后每個月1次,共10次),術后2 a每3個月隨訪1次,3~4 a每6個月隨訪1次,4 a后每年隨訪1次,截止時間至2021年9月。隨訪采用電話、門診及住院等方式,內容包括泌尿系彩超、計算機斷層掃描或膀胱鏡,計算無復發生存時間。定義無復發生存時間為患者初次手術至首次復發的時間,隨訪時間2~90個月,中位隨訪時間63個月。隨訪結束時存活、死亡及失訪患者的末次數據納入統計分析。
1.3 統計學處理采用SPSS 26.0進行統計學分析。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法確定SII的最佳截斷值,并根據最佳截斷值將其分為高SII組和低SII組。計數資料用百分數表示,比較用χ2檢驗。用Kaplan-Meier法進行生存分析,并用log rank檢驗比較組間差異。利用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確定術前SII的最佳截斷值采用ROC曲線確定SII的最佳截斷值。SII的曲線下面積為0.629,約登指數為0.224,敏感性為73.0%,特異性為49.4%,根據約登指數求得其最佳截斷值為340.57,并將患者分為低SII組(SII<340.57)和高SII組(SII≥340.57),其中低SII組患者107例(41.6%)、高SII組患者150例(58.4%)。
2.2 術前SII與NMIBC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關系SII與病理T分期、腫瘤數量以及冠心病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546,P=0.019;χ2=4.345,P=0.037;χ2=3.867,P=0.039)。見表1。
2.3 術前SII與NMIBC患者術后無復發生存的關系低SII組無復發生存率為(76.5±2.5)%,明顯高于高SII組的(60.5±2.9)%,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圖1。
2.4 影響NMIBC患者預后的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結果COX單因素分析結果表明SII、年齡、吸煙史、病理T分期、病理分級、腫瘤數量及腫瘤大小與患者術后復發有關(P=0.001,P=0.018,P=0.033,P<0.001,P<0.001,P<0.001,P=0.001),多因素分析結果表明SII、吸煙史、病理分級及腫瘤數量是影響NMIBC患者術后復發的獨立危險因素(P=0.001,P=0.048,P=0.004,P<0.001)。見表2、3。
3 討論
膀胱癌作為泌尿系統常見的惡性腫瘤,尤其是NMIBC,盡管患者進行了手術完全切除和輔助膀胱治療,其復發率、進展率仍較高。一些預后模型和生物標志物已被作為其預后的指標,但尚未有足夠的證據支持納入臨床實踐。因此針對患者通過合理的預后影響因素篩選出準確可靠的預測指標,指導臨床醫師行針對性決策和個體化治療,從而改善患者的預后尤為重要。本文旨在研究SII對NMIBC患者復發的影響,探討其預測價值,為NMIBC患者預后提供幫助。

表1 2組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比較 n(%)

圖1 SII與NMIBC患者RFS的生存曲線

表2 NMIBC患者術后復發相關因素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表3 NMIBC患者術后復發相關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結果
SII客觀反應全身炎癥及免疫狀態。多項研究[11-13]表明,SII在MIBC、高危及中危NMIBC患者中具有預后價值。炎癥與惡性腫瘤密不可分,炎癥為惡性腫瘤的形成和發展創造滋養環境,由炎癥因子如趨化因子或細胞因子介導的炎癥反應幫助腫瘤細胞的生長、血管生成、增殖及轉移,而激活后的腫瘤細胞又驅動內在的炎癥通路[14-15]。中性粒細胞是炎癥的標志物之一,其與循環腫瘤細胞相互結合,可促進循環腫瘤細胞與組織中內皮細胞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通過誘導腫瘤細胞增殖、刺激血管生成、抑制腫瘤微環境中的適應性免疫應答功能來促進腫瘤的進展和轉移[16]。腫瘤細胞可誘導血小板的激活和聚集,被激活的血小板產生促凝微環境,使腫瘤細胞被血小板和纖維蛋白網絡覆蓋,最終逃避宿主免疫系統攻擊并遠處轉移[17-18]。淋巴細胞介導的細胞體液免疫,通過分泌腫瘤壞死因子-α和干擾素-γ等炎癥因子殺傷腫瘤細胞,淋巴細胞減少,其細胞毒性作用下降,免疫監視減弱,導致腫瘤進展[19]。總體上,SII客觀反應了炎癥和宿主免疫系統狀態的結合,高水平SII能夠導致腫瘤進展,從而造成患者不良預后。Katayama等[13]證實了SII在NMIBC中具有顯著的預后價值,高水平 SII是預測疾病無進展生存時間和無復發生存時間的獨立因素,Zhang等[20]發現SII與行根治性膀胱腫瘤切除術患者的總生存時間相關,術前SII越高患者的總生存時間越低。本研究也提示,SII與NMIBC患者無復發生存時間顯著相關,SII是患者復發的獨立危險因素,且高水平SII的患者預后較差。
本研究通過比較不同SII水平的NMIBC患者在相關臨床病理特征上的差異,繪制無復發生存曲線,并利用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評估SII的預測價值。結果表明,低SII組和高SII組在病理T分期、腫瘤數量以及冠心病等方面有明顯差異。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SII、年齡、吸煙、病理分級、病理T分期、腫瘤大小及數量與患者的復發有關,排除無關因素后的多因素分析結果表明,SII、吸煙、病理分級及腫瘤數量是影響患者術后復發的獨立預測因素,即術前低水平SII、無吸煙史、較低的腫瘤病理分級及單發腫瘤的NMIBC患者復發率更低,這與Akan等[11]在高危NMIBC患者中發現SII是患者經卡介苗治療后復發和進展的獨立因素一致,但病理T分期、腫瘤大小等不是影響患者復發的獨立預測因素,與既往研究[12]不一致,可能與本研究樣本量較少有關。
綜上所述,我們通過回顧性分析257例接受TURBT的NMIBC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可以發現術前SII是NMIBC患者術后復發的獨立危險因素,并在預測患者復發方面具有一定的預后價值,作為一個廉價及簡便的檢驗指標,SII將對指導臨床醫師評估患者復發風險及個體化治療提供幫助。當然,由于本研究存在選擇性偏倚可能、樣本數量較少且是一項單中心回顧性研究等不足,可能影響結果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未來仍需進行大型多中心前瞻性隊列研究來證實SII的預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