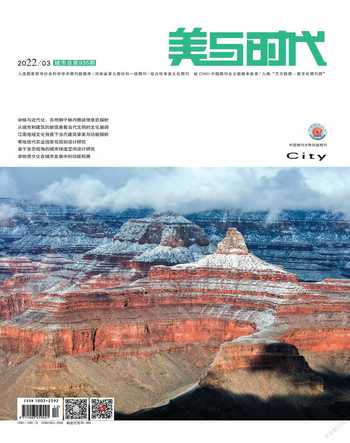本土文化再生的原住地居民主體作用研究
胡夢婷 馮艷 陳治軍
摘 要:原住地居民主體作用在本土文化保護與發展中有著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原住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關系還是主體態度等,都影響著本土文化再生。通過分析本土文化核心精神流逝,以及主體與文化本身分離脫節等現狀,提出了本土文化再生應以當地居民為主導,保障文化保護意識上本土居民的認同覺醒,同時需要本土居民的參與和實際行動,發揮居民本體作用,參照本土文化再生過程中原住地居民作用,以求推動當代本土文化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本土文化;原住地居民;文化再生
基金項目: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廳新文科、新醫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新文科下對接城鄉突出環境問題的環境設計專業跨界融合改造升級探索與實踐”(2020wyxm078)研究成果。
歷史文化遺產包括在過去建立的歷史街區、歷史環境、歷史建筑等,可以反映某個地域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且具備傳統和地方特征,而本土化是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重點,是其在保護、發展過程中繼續維護地域性特色的關鍵。費孝通曾在《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中提出,“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體記憶而維護著的社會共同經驗”[1]。其實,社會共同經驗是一種生活中的文化,是依附特定的空間環境、人群以及歷史經驗的“活態文化”,是本土居民將在本地區的生存習慣和思維模式進行積淀打磨而成的,結合各種外來文化加以重新闡釋的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本土性。然而,由于保護措施的不完善、保護理念的偏離,歷史文化遺產在保護傳承過程中出現了地域特色缺失、不同文化遺產間的同質化、文化傳承主體斷層等現象。因此,本文從本土文化再生角度,強調原住地居民在促進本土文化再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相關的研究有利于維護歷史文化遺產特色,有利于增強我國文化的多樣性和地域性,對實現建設美麗、特色城鎮具有重要意義。
一、本土文化再生中原住地居民主體作用發揮現狀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布迪厄提出了文化再生產概念,他認為文化再生產是社會文化的一種動態演變進程,文化經過不斷的再生產來維持其本身發展的均衡,使得社會得以延續。被再生產的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體系,而是在既定時空之內各種文化力量彼此作用的結果,文化以再生產的形式不斷演進,推動了社會、文化的進步[2]。而文化保護的核心就是本土文化的傳承、再生,其是一個地區所傳承的優質文化基因與文化核心元素,以及二者在時代背景下進行的延續發展,即便是在日益變化的全球化大浪潮中,也成為本土文化的遺傳基因和當地居民文化身份的核心標識。故而,本土文化地域特色缺失是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中出現的主要問題。
首先,本土文化核心精神流逝導致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的同質化,地域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本土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在“地球村”以及現代化浪潮中逐步模糊與喪失,進一步迷失在喧囂繽紛的多樣文化潮流之中,找不到自身文化特性,又或者是擔心受到外來文化影響而不敢接受,越來越陷入固守僵化的沼澤中無法脫身。同時,面向發展的歷史文化旅游類遺產,為了滿足市場需求、追逐熱點,往往存在著某種預設前提。在這種前提之下,對本土文化的保護傳承以及內涵闡釋等易成為被動的狀態,其目的在于吸引游客。而以市場需求為預設形成的旅游產業鏈,往往伴隨一些與當地文化核心精神不相符合的、流于形式的噱頭民俗。一些外來的不熟悉當地文化核心內涵與精神的專家和設計者,為了吸引游客,往往會設計出一些徒有其表的“假鄉土”景觀。游客們最開始看到這些噱頭民俗的時候會感到好奇、新鮮,然后在得到了體驗感的滿足之后,便也失去了對本土文化核心精神的探究、對歷史遺產的尊敬。當以滿足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噱頭民俗成為本土居民的日常,文化遺產傳承的主體也就是本土居民,對歷史文化遺產中的本土文化精神的闡釋往往有誤讀部分,久而久之本土文化中的核心精神也就無人問津、逐漸流失了,而本土文化的傳承行為也往往被弱化了。
其次,主體與文化本身分離脫節,導致出現歷史文化傳承與保護的結構性問題。當本土文化開始被商品化,被貼上用于制造利益的某種文化標簽之后,本土文化就和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脫離開來了。這種文化遺產也就沒有了群眾基礎,更沒有了可持續發展的后勁,缺少了發展的源頭——居民日常生活和行為實踐。這樣的“本土文化”就變成了真正的本土文化的一個附庸商品,成為“游離于本土居民的一件展品或觀賞品”[3]。相應的,缺少了當地居民的實踐參與,本土文化的再生也就變成了表面上的形式延伸,而不是貼近當地文化內核的真正的文化再生。
最后,本土文化核心精神流逝,以及主體與文化本身分離脫節,這兩種情況往往是保護者或設計者對當地本土文化了解不透徹不熟悉導致的。絕大部分本土文化是和居民日常生活緊密聯系的,它們是人們日常生活空間的一部分,比如一些節日民俗、舞蹈形式、居民建筑等。這些本土文化形式在歷史的長河中亙古不變,作為遺產它們是沉默無言的,但是一旦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它們就變得鮮活有生命力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遺產并不是不變的,在歷史河流中前進的文化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充盈著居民的活動痕跡。
二、本土文化再生中原住居民的主體作用
文化遺產和居民是相互獨立而又不可分離的關系,文化遺產本身一旦脫離大眾,就失去其承載的主體;反過來說,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對文化遺產的依附有需求,需要借助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因此,二者的結合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生命有機整體。
一般而言,本土文化再生應以當地居民為主導,強調對當地居民居住區域的文化氛圍的保護,重視居住地居民對區域文化改造的認同,保護本土文化核心精神,這樣的再生的歷史文化遺產才具有特征和意義。2012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將其全球戰略由“4C”改為“5C”,在可信度(credibility)、保護(conservation)、能力建設(capacity-building)、溝通(communication)的基礎上增加了社區(community)的理念[4],強調了當地社區在遺產的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只有當地居民認同本土文化遺產的意義與價值,并愿意付諸實踐將其活化,本土文化才能在時代下連續演進再生,這也就是文化再生了。“風”帶來的雨水養料是有用的,但隨著時間的變化,文化卻只會生根發芽于“土”里,從某種意義上講,居民就是本土文化的“土壤”,是最了解本土文化的,并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踐行著本土文化。故而,居住地居民應當是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主體,而不是讓外來的設計者成為歷史文化保護與開發的核心實踐者。否則當地居民會對自己生活的空間環境營造懈怠,形成被動接受現狀的狀態,進而削弱本土方案的可實施性,使本土文化失去傳承的“土壤”。
同時,以本土居民為主導而實現文化再生策略,主要體現在文化保護過程中居民對于本土文化意識的覺醒,也就是文化保護意識上本土居民的認同覺醒。本土居民長期生活在當地文化精神所滋潤的空間場所環境中,其實他們的日常行動與生活也被當地文化精神所浸透,祖祖輩輩的行動與思想中也早已被當地文化精神耳濡目染。因此在居民的內心深處,當地文化的精神內核是一直潛藏于內心深處的,只需稍加引導便能如雄獅蘇醒一般。基于此,相關政府部門與社會媒體應該積極發揮宣傳帶動作用,通過各種媒介或是政策性引導加快促使居民對本土文化認同感的覺醒。對那些早有覺醒意識的代表性居民進行宣傳,使其起到前浪帶動后浪的領頭作用。如20世紀90年代的杭州市 “舊城改造”運動,原本改造方案中清河坊街建筑群都將被拆除,拆除前,杭州某市民給市政府寫了封緊急呼吁信,在此期間媒體也發布了相關保護資訊文論與專題報道,并從各種層面、角度激發當地市民重視古都傳承發展的文化遺產保護現狀。這引發了社會對清河坊街保護問題的關注,并喚醒了杭州市民對清河坊街的文化認同感和保護意識[5]。最終,這次市民的集體呼吁促使市政府停止了拆遷并提出了保護的決定,使清河坊街一帶成為杭州的重要歷史文化景觀和旅游勝地。故而,本土居民在文化意識上認同的覺醒對于保護傳承本土文化有著重要作用,意識的覺醒也能保證保護后期政策實施的可持續性。
事實上,文化再生與保護的前提,不僅需要當地居民文化意識的覺醒,對居住地文化內涵的珍惜,還需要本土居民的參與和實際行動,發揮居民本體作用。當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地區的人們都擁有對當地文化的保護認同感,社區之間就會形成默契感和氛圍感,并在意識的能動性驅動下參與當地文化保護以及文化再生的過程。居民們會在日常實踐中去發掘和欣賞當地文化的特殊性和閃光點,并把它作為文化印記潛移默化地變成了日常生活習慣,以此完成本土文化在當代的文化再生。當地政府部門也應該為居民提供參與實踐的平臺和機會,這樣不僅能傳播文化遺產保護理念,也能逐步完善市民保護參與機制。同樣,在杭州西湖文化景觀申遺過程中,多位遺產保護先行市民以他們的文化認同和文化保護行動推動了申遺過程。除了這些自己在生活中堅持參與實踐文化保護的市民行動之外,杭州市也會定期舉辦一些活動,目的在于接收當地市民對保護傳承西湖文化景觀管理上的一些問題和建議。縱觀最近幾年,杭州市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融合度已經算得上是國內走在前列的,而西湖文化景觀的保護與發展也在市民的積極參與中越來越有當地特色。
三、結論與啟示
本土文化再生不是對一個個“文化碎片”或者“文化孤島”的“圈護”,而是對文化全局的關注,不但要保護文化遺產自身及其有形外觀,還要注意它們所依賴和應用的結構性環境[6]。然而,文化遺產在離開了人類之后,其服務于居民日常生活的那部分社會文化價值也隨之喪失了,與此同時也失去了時代的烙印,永遠停留在了時代的角落。目前,本土文化再生過程中原住地居民主體作用受到廣泛關注,面臨諸多問題,也具有挑戰和機遇。
第一,讓原住地居民生活融入本土文化,成為保護與發展的一部分。本土文化再生的主要途徑,是本土文化遺產的“原真性”源于社區居民作為文化主體持續參與文化遺產的再創造與維護過程。讓本土社區的居民親自參與保護和傳承的過程,將保護意識融入本土社區和本土文化,這就要求設計者回歸“日常生活”視角看待文化遺產,而不是刻意地區分“保護”與“發展”。2021年2月份,一場嚴重的大火將被譽為中國部落文化最后的“活體”翁丁古寨的百余棟房屋燒毀得僅剩三四棟。這樣慘痛的代價凸顯翁丁古寨保護與開發忽視了原住地居民與文化遺產之間的關系,強行使村民離開了寨子,出現了村子的守護者和村子分開的“人村分離”現象。因此,尊重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尊重原住民和文化遺產的共生關系,是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必須踐行的重點,要使原住民作為文化主體持續參與當地文化的再創造與維護過程。
第二,充分發揮原住地居民主人翁作用,使其珍惜、愛護本土文化。本土的歷史文化保護與發展需要幾代人的努力,需要一個主體去延續和發展,這個主體既不能是“空降的”專家,也不能是直接主導的政府,而必須是本土文化原住地居民。只有對當地文化十分熟悉的原住民參與認同當地文化并對其進行日常化的實踐,文化遺產活態化保護傳承才有了意義。在社區居民作為文化主體持續參與文化遺產的再創造與維護過程中,居民的日常生活實踐就變成了本土文化在當代的踐行,由此形成了本土文化實踐—文化意識—再實踐—文化意識再提煉的螺旋上升的發展,并在這個過程中進一步加深本土居民的文化認同感,為下一個文化保護參與實踐提供意識主導。
第三,挖掘原住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精神元素,并融入本土文化。文化歷史遺產的活態保護要求更多地從日常生活場所、居民的生活方式的視角去理解文化歷史遺產的價值。真實的日常生活關系才是文化遺產依存的原真性所在,而本土居民的參與認可也正是居民在本土文化保護過程中能體現出真實日常生活關系的重要方式。文化歷史遺產最初是以實現人類生存和發展為核心價值的,而空間形態也不過就是文化遺產的物質外觀伴隨它而產生的自然結果。即便是其物質外觀在當今時代發生了劇烈改變,只要其文化層面和精神層面依舊能被當地居民所繼續傳承發展下來,那被賦予了當代意義的遺產的精神方面依舊能反映文化遺產物質方面的內容,這就是遺產保護的彈性所在,也就是文化遺產的文化再生。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3.
[2]宗曉蓮.布迪厄文化再生產理論對文化變遷研究的意義:以旅游開發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變遷研究為例[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22-25.
[3]金光億.實踐中的文化遺產:看文化不見人[J].西北民族研究,2018(4):70-79.
[4]田婷.老城保護中的遺產管理規劃研究[D].南京:南京工業大學,2013.
[5]阮云星.文化遺產的再生產:杭州西湖文化景觀世界遺產保護的市民參與[J].文化遺產,2016(2):36-45.
[6]劉魁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的整體性原則[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2004(4):1-8,19.
作者簡介:
胡夢婷,安徽建筑大學藝術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環境設計。
馮艷,碩士,安徽建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城市化及城市景觀規劃研究。
陳治軍,博士,安徽建筑大學藝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藝術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