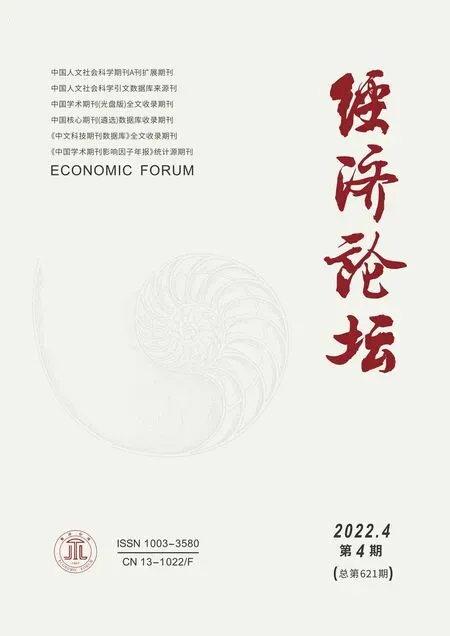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對不同類型親社會行為的溢出效應
郭婷婷,吳正祥
(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遼寧 阜新 123000)
引言
產品更新換代速度的加快、購物的便捷性以及消費者對個性化消費的強烈訴求促使消費者在購物之余囤積了大量的閑置物品。這些閑置物品棄之可惜、用之不順,它們像廢品一樣被隨意扔在角落或保留在箱柜里,導致大量閑置資源無法重新進入流通環節,難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產生了巨大的資源浪費問題,與國家大力倡導的綠色發展理念背道而馳。鼓勵消費者回收閑置物品是減少生活垃圾對資源和環境產生負面影響而采取的必要行動。消費者回收行為作為一種社會責任行為,是指消費者將終止使用的廢舊物品進行分類、儲存和移除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行為[1]。“互聯網+回收”環境下,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是指消費者將未使用或停用的、尚有利用價值的閑置物品通過網絡回收平臺進行處置的行為[2]。目前學者已經對消費者回收行為的定義、影響因素、測量方法以及干預策略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研究[2-8]。然而,現有相關研究中,學者主要聚焦于探究影響消費者回收行為決策或意向的前置變量,對消費者回收行為產生的后置結果關注較少。
近年來,不斷有研究發現某領域的特定行為對該領域其他行為具有增強或抑制作用,即行為間存在溢出效應[9-10]。若第一種行為增強了個體實施第二種行為或在不同的時間、環境中實施相同行為的可能性,則該種行為產生了正向溢出效應;反之,若第一種行為的實施降低了第二種行為發生的概率,則該種行為產生了負向溢出效應[11]。盡管部分學者探究了消費者回收行為產生的溢出效應,但是這些研究結論存在矛盾,導致消費者回收行為溢出效應的研究沒有形成容易理解和規范化的理論成果。例如,Kidwell等[12]的研究發現,消費者的垃圾回收行為會產生正向溢出效應;而Truelove 等[13]以及Stavins[14]的研究發現,消費者的垃圾(如塑料瓶)回收行為會產生負向溢出效應。徐林和凌卯亮[15]的研究則指出,居民的垃圾分類回收行為對其節電行為產生何種溢出效應受到垃圾分類政策的影響。
在現實生活中,為了激發消費者參與閑置物品回收的積極性,企業和社會組織不斷嘗試利用各種策略,通過誘之以利、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方式刺激消費者參與閑置物品回收。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消費者參與閑置物品回收的可能性。然而,鼓勵消費者參與閑置物品回收真的有利無弊嗎?消費者參與閑置物品回收是否會對其未來生活中實施其他親社會行為產生影響?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對與之同屬于環保行為的生態行為以及與之相似性較弱的非環保類親社會行為產生的后續影響是否存在差異?現有研究尚未給出明確答案。基于此,本研究借用親社會行為溢出效應的相關研究成果,利用實驗研究方法,探究閑置物品回收行為產生的溢出效應,以期為回收領域溢出效應理論提供新的觀點,為企業和社會組織預測消費者對閑置物品回收行為中未包含方面的認知,制定提升閑置物品回收行為產生積極溢出效應的相關策略提供理論指導。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行為一致性理論認為,人們具有保持一致性愿望(在他人看來也是一致的)的動機[16]。依據該理論,個體在某一特定領域內采取有利于環境的行為不僅可能改變其對該行為的態度,而且還可能激發個體的整體心理傾向,進而影響到個人在其他領域未來可能實施的行為。親社會行為溢出效應研究中發現的登門檻效應(Foot-in-the-door effect)就是行為一致性的一個具體表現,即誘發個體產生一個微小的行為之后,個體在后續的活動中可能踐行更多的親社會行為。Evans 等[17]研究表明,僅僅讓被試者在實驗前想象一種親環境行為就能夠提升其回收意愿。在研究消費者垃圾回收行為過程中,Kidwell等[12]發現,消費者的垃圾回收行為會影響與垃圾回收無關的行為,例如環保產品購買意愿。Cornelissen 等[18]研究表明,通過暗示常見的環保行為能夠促進個體的可持續消費行為。此外,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個體最初的行為形成了其作為特定類型人的自我認知,這種自我認知能夠引導個體按照該種類型人的行為方式行事[19]。提示人們過去的環保行為,如節約用水、節約能源、參與環保消費等,可以加強他們的環境自我認同,這種強烈的環境自我認同增加了其未來踐行環保行為的可能性[20]。綜上,本研究推測:消費者在踐行閑置物品回收行為以后,一方面因行為間的相似性,初始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促使消費者形成了親社會認同,在后續的活動中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另一方面,為了避免認知失調和認知失調引發的緊張感,閑置物品回收行為通過促使消費者形成親社會行為態度,進而提升其在后續行為中踐行更多親社會行為的可能性。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1A: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會對其綠色消費意愿、二手產品購買意愿、親社會意愿、節約行為、垃圾分類回收意愿產生正向溢出效應。
行為一致性理論和社會認同理論為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對相似或相關行為產生正向溢出效應提供了潛在解釋。但“道德許可效應”的研究指出,當個體感知自身的道德形象高于理想道德形象時,其可能降低道德行為發生的頻率[21-22]。換言之,個體之前的親社會或道德行為會讓其感知“有權”以反社會或不道德的方式行事[23]。
Sachdeva 等[24]認為,道德或不道德行為的產生是個體對道德自我價值和利他行為固有成本內在平衡的結果,啟動被試者的正面道德特質會降低被試者的捐款數目和合作行為。部分基于道德許可效應的研究發現了回收產生負向溢出效應的證據。Truelove 等[13]的研究發現,消費者的塑料瓶回收行為降低了其綠色基金支持度。Christian 等[25]的研究發現,除了過去的道德行為經歷,僅讓被試者想象可能會發生的道德行為也能夠促使其產生道德許可感知。閑置物品回收作為一種社會責任行為,參與閑置物品回收傳遞出消費者在資源循環利用方面做出了貢獻的信號,該信號線索提升了消費者的自我道德形象感知,這種積極的自我形象感知可能促使其在未來產生更多違背社會道德或社會規范的行為。基于此,提出競爭性假設:
H1B: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會對其綠色消費意愿、二手產品購買意愿、親社會意愿、節約行為、垃圾分類回收意愿產生負向溢出效應。
Davis 等[26]的研究指出,生態行為包含節約能源、避免浪費、綠色消費、回收、綠色出行以及其他與環保相關的親社會行為六類。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屬于生態行為,與其他類型生態行為間的相似性或關聯性更強。雖然二手產品購買、志愿活動、慈善捐贈、獻血等與非環保相關的行為也屬于親社會行為,這些行為與回收行為在消費者心理認知中也具有相似性或關聯性[12,27],但是相較于環保類親社會行為,這些行為同閑置物品回收行為之間的可接近性和可診斷性較弱。依據Lynch等[28]的觀點,信息的可接近性和可診斷性決定了其是否會影響消費者的認知評價,本研究推測:與其他非環保類親社會行為相比,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對環保類親社會行為產生的影響更強烈。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設:
H2:與非環保類親社會行為相比,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對環保類親社會行為產生的溢出效應更強。
二、實驗設計與假設檢驗
基于行為一致性理論,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能夠對相似或相關行為產生正向溢出效應。基于道德許可效應,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導致其感知實施不道德或違背社會規范的行為被許可,進而對相似或相關行為產生了負向溢出效應。針對上述不同溢出效應產生機制及其研究成果得出的矛盾結論,本實驗旨在探討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是否可以發揮信號線索作用,促進或抑制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愿、二手產品購買意愿、親社會意愿、節約行為以及垃圾分類回收意愿;識別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對環保類和非環保類親社會行為是否產生了差異化的溢出效應。即驗證競爭性假設H1A 與H1B 以及H2。
(一)預實驗
預實驗的目的是選擇合適的實驗品。據統計,二手電商平臺中最受用戶關注的閑置物品是手機、服裝鞋帽、圖書以及數碼產品(不含手機),關注度分別為49%、46%、40%、39%[29]。根據消費者心理與行為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手機、數碼產品屬于搜索型產品,服裝鞋帽和圖書屬于體驗型產品,且消費者對不同類型產品的感知存在差異[30],這可能導致不同類型產品回收行為產生的溢出效應存在差異。
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科學性,本研究在實驗前對參與過閑置物品回收的部分消費者進行了訪談。在訪談基礎上,結合閑置物品回收商業實踐的實際情況,選取智能手機、iPad、筆記本電腦、圖書、手提包、服裝鞋帽6種產品作為實驗備選產品。預實驗共邀請27 名被試者對備選產品進行評價。分別利用“您對該種閑置物品的熟悉程度高”測試被試者對備選產品的熟悉程度;利用“您認為該種閑置物品適合被回收、您認為該種閑置物品被回收合乎邏輯、您認為該種閑置物品回收的可能性高((=0.863)”3個題項測試備選產品適合作為閑置物品被回收的程度。4個測試題項均采用李克特七級量表進行測量。
實驗備選產品評價統計結果見表1。由表1 可知,被試者對6種備選產品熟悉程度的均值顯著大于中間值4。在6 種備選產品中,被試者感知iPad和圖書作為閑置物品被回收的程度適中,且對兩種產品作為閑置物品被回收程度的感知不存在顯著差異,t(52)=-0.142,p>0.5;同時,被試者對兩種閑置物品的熟悉程度不存在顯著差異,t(52) =-0.929,p>0.5。據此,正式實驗中選取iPad和圖書作為實驗品。

表1 實驗備選產品評價統計結果
(二)正式實驗
正式實驗采用單因素(iPad 回收組VS 圖書回收組VS 控制組)組間實驗設計,因變量是綠色消費意愿、二手產品購買意愿、親社會意愿、節約行為、垃圾分類回收意愿。為了避免被試者對真實網絡回收平臺熟悉程度或偏好差異導致實驗結果失真,實驗過程中網絡回收平臺名字虛擬為“ELEG”,并以普通消費者為樣本,通過問卷星調研平臺付費在線發放問卷。考慮到研究分組,實驗共形成iPad回收組、圖書回收組以及控制組3個網頁鏈接。為了保證實驗結果的準確性,減少社會贊許性偏差,在被試者打開網頁時向被試者承諾調研分析針對總體樣本而非個體消費者,調研結果僅用于學術研究且嚴格保密。為了提高被試者作答的積極性,作答完成后被試者可以參與現金抽獎,抽取1到10元的微信紅包現金獎勵。
1.實驗過程。第一部分是閑置物品回收情景刺激材料。根據Jordan等[31]的研究,對過去道德或不道德行為的回憶會影響被試者未來的行為意愿。該部分iPad 回收組請被試者努力想象以下情景:11 月20 日是國際兒童日,為了喚起人們對兒童教育的關注,11 月20 日當天閑置物品回收平臺“ELEG”發起并實施了“兒童數碼助學計劃”,知道該消息后,11 月20 日那天您通過該平臺將您閑置的iPad 進行了回收。圖書回收組請被試者努力想象以下情景:4 月2 日是國際兒童圖書日,為了喚起人們對兒童教育的關注,4 月2 日當天閑置物品回收平臺“ELEG”發起并實施了“鄉村閱讀計劃”,知道該消息后,4月2日那天您通過該平臺將您閑置的圖書進行了回收。控制組請被試者閱讀一段旅游目的地信息,之后,請被試者對場景的真實性進行打分,完成該部分后進入下一個環節。
為了避免被試者猜到實驗目的,第二部分測試題項開始前,告知被試者為了節約調研成本,課題組將幾個不相關的問題組合到一起進行調研,請被試者認真閱讀各個題項,根據自身的實際感受對各個題項做出評價。之后進入對綠色消費意愿、二手產品購買意愿、親社會意愿、節約行為以及垃圾分類回收意愿5個因變量測試題項評價頁面。完成該部分后進入下一個頁面填寫個人基本特征信息,包括性別、年齡、職業和受教育程度4個題項。
2.變量測量。為了保證各個變量的測試題項能夠準確反映所要測量的指標,本研究對各變量的測量均借鑒已有成熟量表。參照Wagner 等[32]的測量量表,利用兩個題項測試被試者的情景真實性感知。參照Chen 和Chang[33]以及王漢瑛等[34]對綠色消費的定義和測量,將綠色消費定義為消費者出于環保考慮而購買特定的產品,利用3個題項測試被試者的綠色消費意愿。二手產品購買意愿的量表由Dodds 等[35]的量表改編而來,從4 個方面進行測量。參照朱一杰等[36]以及Jordan 等[31]的研究,請被試者填寫未來一個月內其愿意參與三項親社會活動(參加志愿活動、向慈善機構捐款、獻血)和三項娛樂活動(參加聚會、度假、看電影)的程度,三項娛樂活動參與意愿主要用做干擾項,不做深入分析。參照Lanzini 和Thogersen[27]以及Spence 等[37]的研究,利用5 個題項測試被試者的節約行為。參照Chu 和Chiu[38]的研究,利用2 個題項測試被試者的垃圾分類回收意愿。所有測試題項均利用李克特七級量表進行測量。各變量的測量量表見表2。

表2 測量量表
3.數據收集。考慮到研究效率和質量,在正式實驗前本研究使用Gpower 3.1.9.7 軟件進行事前分析以確定最佳的被試量[39]。將效應量f值設置為Cohen[40]建議的大效應水平0.40、將統計檢驗力1-β值設置為0.95、將顯著性水平a值設置為0.05進行計算,得出被試量為100。據此,本研究在正式實驗中預計招募有效被試者120人左右。此外,考慮到研究分組,正式實驗預設每組回收問卷50 份,共回收問卷150份。問卷搜集完成以后網頁鏈接停止作答。為避免重復作答,剔除IP 地址重復的問卷6份,剔除答題時間低于40秒的疑似機械問卷9份,剔除操作檢驗和主體問題部分回答不認真的問卷7份,正式實驗共得到有效問卷128份。被試者的基本特征見表3。被試者的年齡特征符合閑置物品回收人群較為年輕的現實狀況[41]。

表3 被試者的基本特征
(三)數據分析與結果
1.信效度分析與操控檢驗。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a值對各個變量測量量表進行信度分析,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法對測量量表進行效度檢驗。為了保證實驗場景能夠反映現實情景,采用描述性統計方法對實驗情景材料進行檢驗。
首先,對各個變量進行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場景真實性感知、綠色消費意愿、二手產品購買意愿、節約行為、垃圾分類回收意愿測量量表的 Cronbach's a 值分別為 0.806、0.845、0.798、0.891、0.773。親社會意愿整體測量量表的Cronbach’s a 值為0.704,其中3 個干擾題項(娛樂活動)的Cronbach's a 值為0.844,3 個親社會活動題項的Cronbach's a值為0.830。各個變量測量量表的Cronbach's a值均大于0.700,說明整個量表的信度良好。
其次,對由綠色消費意愿、二手產品購買意愿、節約行為、垃圾分類回收意愿、親社會意愿組成的測量量表進行效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整個測量量表的KMO值為0.705,巴特利特球形檢驗結果sig.=0.000,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共提取出6 個特征根大于1 的公因子,累計方差解釋率為73.584%。親社會意愿六個題項共提取出兩個因子,3 個歸于親社會活動,3個歸于娛樂活動。驗證性因子分析擬合指數見表4,可以看出各個指標均達到了理想值,說明模型擬合度良好。各個變量測試題項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700,各個變量測試題項的組合信度(CR 值)大于0.700,平均方差抽取量(AVE) 值大于0.500,說明量表的效度良好。

表4 驗證性因子分析模型擬合指數
最后,對場景真實性進行檢驗。結果顯示,被試者的場景真實性感知顯著大于中間值4(M=5.066,SD=0.711),且控制組(M控制組=5.070,SD=0.712)、iPad回收組(MiPad=5.143,SD=0.743)以及圖書回收組(M圖書=4.988,SD=0.686)被試者的場景真實性感知均值均大于中間值4,說明實驗場景同現實場景具有較高的契合度。
2.假設H1 檢驗及結果分析。以實驗情景(iPad 回收組VS 圖書回收組VS 控制組)為自變量,分別以綠色消費意愿、二手產品購買意愿、親社會意愿、節約行為、垃圾分類回收意愿為因變量進行方差分析。結果顯示:
當因變量為綠色消費意愿時,自變量的主效應顯著,F(2,125)=7.694,p=0.001。進一步的事后檢驗(Fisher’s LSD)發現,相較于控制組(M控制組=3.992),iPad 回收組 (MiPad=4.444,p=0.007) 和圖書回收組 (M圖書=4.612,p=0.000) 被試者的綠色消費意愿更強,且iPad 回收組和圖書回收組被試者的綠色消費意愿不存在顯著差異,p>0.1。
當因變量為二手產品購買意愿時,自變量的主效應邊緣顯著,F(2,125)=2.885,p=0.060。進一步的事后檢驗(Fisher's LSD)發現:相較于圖書回收組 (M圖書=3.390),iPad 回收組 (MiPad=3.810,p=0.018)被試者的二手產品購買意愿更強;控制組(M控制組=3.587)與圖書回收組被試者的二手產品購買意愿不存在顯著差異,p>0.1;控制組與iPad 回收組被試者的二手產品購買意愿不存在顯著差異,p>0.1。
當因變量為親社會意愿時,自變量的主效應不顯著,F(2,125)=0.581,p>0.1。圖書回收組(M圖書=4.674)、iPad回收組(MiPad=4.595)以及控制組(M控制組=4.519)兩兩之間的親社會意愿不存在顯著差異。
當因變量為節約行為時,自變量的主效應顯著,F(2,125)=12.093,p=0.000。進一步的事后檢驗(Fisher's LSD) 發現:相較于控制組(M控制組=4.405,p=0.000) 和iPad 回收組 (MiPad=4.752,p=0.014),圖書回收組(M圖書=5.116)被試者表現出更強的節約行為;同時,相較于控制組,iPad回收組被試者表現出更強的節約行為,p=0.018。
當因變量為垃圾分類回收意愿時,自變量的主效應顯著,F(2,125)=6.659,p=0.002。進一步的事后檢驗(Fisher's LSD)發現:相較于控制組 (M 控 制 組 =4.430), iPad 回 收 組 (MiPad=4.929,p=0.001) 和圖書回收組 (M圖書=4.814,p=0.008)被試者表現出更強的垃圾分類回收意愿;且iPad 回收組和圖書回收組被試者的垃圾分類回收意愿不存在顯著差異,p>0.1。
由上述檢驗結果可知,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對其綠色消費意愿、節約行為以及垃圾分類回收意愿均產生了正向溢出效應。此外,兩種類型閑置物品的回收行為沒有對二手產品購買意愿和親社會意愿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假設H1A得到部分支持,而其競爭性假設H1B 沒有得到數據支持。
3.假設H2 檢驗及結果分析。如前文所述,綠色消費、節約行為、垃圾分類回收這些生態行為屬于環保類親社會行為,二手產品購買、捐贈、獻血、參加志愿活動屬于非環保類親社會行為。為了進一步驗證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是否對不同類型親社會行為產生了差異化的溢出效應,分別以綠色消費意愿、節約行為、垃圾分類回收意愿3 個變量的均值以及二手產品購買意愿、親社會意愿2個變量的均值為因變量。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對其進行檢驗,結果顯示,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對兩種類型親社會行為的溢出效應差異顯著。相較于非環保類親社會行為(M=4.023),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對環保類親社會行為的溢出效應更強(M=4.628),t(127)=8.167,p=0.000。假設H2得到驗證。
以上分析結果說明,行為之間的相關性是溢出效應存在的基礎,且行為間的關聯性越強,溢出效應越明顯。這主要是因為,行為之間的相關性越強,其相似性越高,行為人在進行信息推斷時也就越容易,外部線索對個體的認知評價產生的影響進而也更大。
三、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現有關于消費者親社會行為溢出效應的研究結論尚未達成共識,甚至有學者指出,因道德許可效應的存在導致消費者的親社會行為可能產生負向溢出效應。本文的研究結果同行為一致性理論相關研究的觀點相似。也就是說,雖然存在一些特殊情況,一般情況下消費者的親社會行為可以從一種行為向另一種行為積極溢出[27]。具體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沒有因啟動個體積極的自我形象感知產生負向溢出效應,而是產生了正向溢出效應。具體而言,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對綠色消費、節約行為以及垃圾分類回收這些同環保相關的生態行為產生了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對二手產品購買、向慈善機構捐款、志愿活動、獻血這些非環保類親社會行為產生的溢出效應不明顯。這說明:一方面,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啟動了消費者的利他目標,該行為一旦激活可以啟動更廣泛的利他目標,進而引導其實施其他親社會行為;另一方面,溢出效應更可能發生在與溢出源具有符號相似性的行為之間。綠色消費、節約行為以及垃圾分類回收同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同屬于與環保相關的生態行為,這些行為之間具有更強的相似性或可接近性,更容易被閑置物品回收行為激活,是閑置物品回收行為的產物。
第二,消費者對回收搜索型產品和體驗型產品的不同感知或動機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引發閑置物品回收行為產生了差異化的溢出效應。具體而言,消費者的圖書回收行為對節約行為的溢出效應顯著高于iPad回收行為,iPad回收行為對二手產品購買意愿的溢出效應顯著高于圖書回收行為。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消費者日常生活中閑置的體驗型產品主要有圖書、服裝鞋帽、手提包、化妝品等,消費者回收這些產品更多的是出于節約資源、避免浪費的目的,回收這些閑置物品的行為同節約行為的行為動機具有更強的一致性[42];消費者日常生活中閑置的搜索型產品主要有智能手機、iPad、數碼相機等,消費者對這些閑置物品的回收行為降低了其購買二手產品的感知風險,進而對其二手產品購買意愿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43]。
(二)管理啟示
消費者的行為過程是一種與儲存在記憶中的觀念、目標取向、特征等相關聯的復雜系統過程,行為動機的激活會促使其做出與自我概念相一致的行為,并且時刻警惕與自我概念不一致的行為。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能夠促進其垃圾分類回收參與意愿、節約行為以及綠色產品購買意愿,對親社會行為意愿的促進作用不明顯;搜索型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增強消費者購買二手產品的意愿。商業實踐中企業和社會組織應該認識到:一方面,初始行為能夠引導消費者形成特定的自我認知,為了避免認知威脅,消費者在后續的行為過程中會按照這種認知行事。當最初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沉淀并內化為個體的行為基準時,其所產生的溢出效應能夠促使消費者為改善環境做出更多努力,最終形成保護環境的目標信念。另一方面,消費者參與閑置物品回收并不代表其愿意購買二手產品。二手產品是閑置物品回收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和社會組織在出臺鼓勵性政策刺激消費者參與閑置物品回收的同時,應該考慮如何刺激消費者購買二手產品,增強閑置物品市場的流通效率,進一步提升消費者參與閑置物品回收和購買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價值。
(三)研究展望
本文揭示了消費者閑置物品回收行為產生的溢出效應,能夠為“互聯網+回收”商業模式下企業實踐提供理論指導,為回收領域學者的研究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鑒。閑置物品回收行為溢出效應的研究尚處于初步探索階段,未來仍然有很多有價值的問題值得深入挖掘:第一,閑置物品回收平臺的發展尚處于成長期,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消費者的閑置物品回收行為可能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后續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究促進或抑制消費者閑置物品回收行為產生溢出效應的因素;第二,本文證實了閑置物品回收行為能夠提升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愿、節約行為以及垃圾分類回收意愿,未來可以驗證這些行為對閑置物品回收行為能否產生溢出效應,增加行為溢出效應相關的研究成果,為行為溢出效應理論矛盾結論的揭開進一步提供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