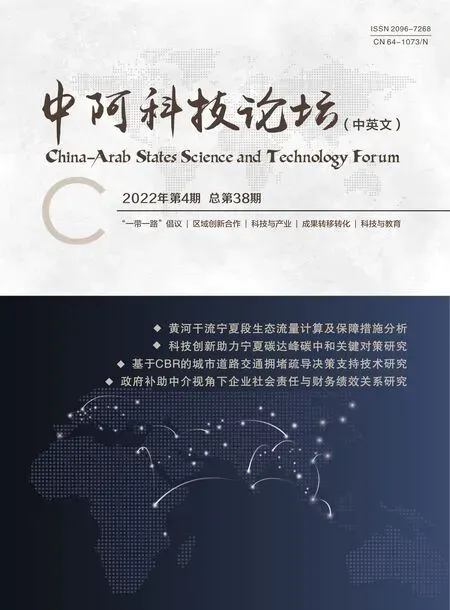基于內隱關系評估程序的高校學生合作態度測量
王世壯 賈澤民 孫紅日
(南昌大學,江西 南昌 330031)
1 研究背景
合作態度是個體對合作的一種評價性心理傾向,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學生的學習動力、獲取成功的策略取向以及自我評價能力[1]。近年來,隨著內隱測量理論和技術的發展,研究者們開始采用內隱測量技術探討我國高校學生對合作的態度。然而,這些研究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通過評估記憶中概念間聯結強度的相對大小間接測量態度,無法直接評估這種聯結的本質或方向性(即關系),更無法評估具有方向性聯結的復雜結構[2]。因此,本研究將引入內隱關系評估程序(Implicit Relational Assessment Procedure,IRAP)從合作態度的四個方面——喜歡合作、厭惡合作、喜歡非合作和厭惡非合作——探討高校學生合作態度差異,并重點探討其在專業背景和社會價值取向上的差異,以探尋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前因變量,為科學制定和優化高校學生合作培養方案提供依據。
從本質上講,內隱態度是過去經驗和已有態度積淀下來的一種無意識痕跡[3]。有關合作的研究發現,經歷可以提升與合作相關變量的水平。對于高校學生,專業學習與訓練是其主要的日常經歷。由于專業自身特點的不同,當前我國高校文、理、工不同專業的日常教學方式、學習方式均存在較大的差異。這種由專業背景所引發的個體經歷的不同是否會產生內隱合作態度的差異,還需要實證研究進一步證實。
社會價值取向是互依情境中資源分配時,決策者對“自己和他人特定結果模式的穩定偏好”[4]。大量的研究表明,社會價值取向是一種相對穩定的人格傾向,是影響個體合作行為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分析研究發現,社會價值取向影響個體對他人的合作期望,相對于競爭取向者和個人取向者,親社會(合作)取向者表現出更多的合作行為[5]和對他人更高的合作期望[6]。可見,社會價值取向不同的群體合作行為水平也存在著明顯差異。那么,不同社會價值取向的高校學生,其合作態度是否存在差異,差異如何,將是本研究的另一研究內容。
綜上所述,本研究基于IRAP范式將高校學生內隱合作態度細化為四個方面,并在內隱社會認知框架下探討這四個方面在專業背景和社會價值取向變量上的差異。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樣的方式在南昌市高校中選取在校本科生354人,剔除中途退出實驗和填寫不全、有規律回答問卷者,最終得到有效數據共315份,問卷有效率88.98%。被試者年齡在18~25歲之間(M=21.02,SD=2.580),男生150人,女生165人;文科111人,理科101人,工科103人;合作價值取向為230人,非合作價值取向為85人。
2.2 測量工具
2.2.1 IRAP測驗任務
通過等級評定法實驗選出包含合作信息和非合作信息的各6張圖片共12張圖片作為目標刺激,以“合作”和“非合作”為標簽刺激,以“相似”和“相反”為關系評定反應詞匯的IRAP測驗結果表明,兩類圖片所包含的信息與假設是一致的。
在本研究中,采用Barnes-Holmes等人提出的經典的IRAP范式[11],具有較好的信效度,以上述實驗評定的12張具有“合作”或“非合作”意向的圖片為目標刺激,以“喜歡”和“厭惡”為標簽刺激,以“一致”和“非一致”為關系評定反應詞匯編寫計算機化測驗對高校學生合作態度進行測量。相容任務為在目標刺激與標簽刺激關系相容時,做出“一致”按鍵反應,反之,則對“不一致”做出按鍵反應;不相容任務為在當目標刺激與標簽刺激關系相容時,做出“不一致”按鍵反應,反之,則做出“一致”按鍵反應。
2.2.2 三重對策矩陣
采用嚴進等(2000)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和重測信度的“三重對策矩陣”[7]來測量個體的社會價值取向,該方法通過個體在12個三選項題目上的選擇結果,可以將他們歸為合作價值取向(傾向選擇自己和他人共同收益最大化選項)、競爭價值取向(傾向選擇自己和他人收益差異最大化選項)、個人價值取向(傾向選擇自己收益最大化選項)及混合價值取向(沒有表現出固定的一種價值取向)4種類型。參考De Dreu等(1997)的標準[8],將在12次對策中有7次以上(包括7次)一致反應的研究對象才規劃為其中的一類。在本研究中,依據研究目的將個體劃分為合作價值取向和非合作價值取向(包括競爭價值取向、個人價值取向和混合價值取向3種類型)兩種類型。測驗時,每個題目的三個選項順序隨機排列。并且,識別出合作價值取向者230人,非合作價值取向者85人。
2.3 施測過程
整個實驗過程由E-Prime編寫的程序控制。完整實驗程序包括呈現實驗說明、各測驗指導語及刺激并記錄被試的反應。為了平衡呈現的順序效應,價值取向測量和合作態度測驗的呈現順序在被試間隨機,在合作態度測驗前調查研究對象的年齡、性別、專業等基本信息。整個施測過程大約為25 min,均在安靜的寢室或自習室中以單一被試形式進行。
2.4 因變量
采用Greenwald等(2003)計算內隱聯想測驗效應時提出的D算法[9],分別計算喜歡合作、厭惡合作、喜歡非合作和厭惡非合作在成對相容任務和非相容任務上的反應時平均數的差值與聯合方差的比值,各個成分的所有比值加和則為其IRAP效應值D值。D值越大,說明相對于不相容任務,個體在相容任務上的反應越快,IRAP效應越大,相對應的信念或態度強度越大。
3 統計結果
3.1 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狀況
在本研究中,高校學生的合作態度由四個方面構成:喜歡合作、厭惡合作、喜歡非合作和厭惡非合作。高校學生在合作態度四個成分上D值的均值如圖1所示,喜歡合作為0.78,厭惡合作為0.29,喜歡非合作為0.43,厭惡非合作為0.37。

圖1 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狀況
為了比較這四個方面是否存在差異,以四個IRAP效應D值為組內變量進行單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經Mauchly's球形假設檢驗,因變量的方差協方差矩陣相等,χ2=1.17,p=0.948。各成分D值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如表1所示,以“均數±標準差”形式表示,喜歡合作為0.78±0.64,厭惡合作為0.29±0.72,喜歡非合作為0.43±0.69,厭惡非合作為0.37±0.69,且它們之間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F(3,942)=37.03,P<0.001,ηp2=0.106,說明四個成分中至少有兩個成分之間的D值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進一步的事后比較分析發現,喜歡合作的D值明顯大于其他三個成分的D值,95%置信區間分別為厭惡合作0.35~0.63、喜歡非合作0.22~0.49、厭惡非合作0.28~0.54;厭惡合作的D值明顯小于喜歡非合作的D值,95%置信區間為-0.27~-0.001,但與厭惡非合作的D值差異不明顯,95%置信區間為-0.22~0.06;喜歡非合作與厭惡非合作之間的D值差異不明顯,95%置信區間為-0.08~0.19。

表1 各成分D值的均數、標準差與平均數單樣本t檢驗結果
IRAP效應D值大于0,說明個體對相容任務的反應快于不相容任務,反之則反。在本研究中,“喜歡—合作—一致”“厭惡—合作—不一致”“喜歡—非合作—不一致”和“厭惡—非合作—一致”是相容任務,“喜歡—合作—不一致”“厭惡—合作—一致”“喜歡—非合作—一致”和“厭惡—非合作—不一致”是不相容任務。各成分D值平均數單樣本t檢驗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四個成分的D值均大于0[喜歡合作t(314)=21.86,p<0.001;厭惡合作t(314)=7.24,p<0.001;喜歡非合作t(314)=11.10,p<0.001;厭惡非合作t(314)=9.58,p<0.001],這一結果說明,高校學生在合作態度四個成分上的反應與實驗中目標刺激與標簽刺激的關系假定是一致的。
3.2 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專業背景差異
由于不同學科專業的知識結構和認識論假設不同,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可能采用各自學科所特有的方式進行,致使不同學科專業背景的高校學生可能具有不同的學習經歷。文、理、工不同專業背景的D值平均值在合作態度的四個成分上分布如圖2所示,為了進一步考察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專業背景差異,以合作態度的四個成分為因變量、專業背景為組間變量分別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得到厭惡不合作的專業背景差異明顯,F(2,312)=5.94,P=0.003,η2=0.037,其他三個方面的專業背景差異不明顯。方差同質性檢驗未達到顯著性水平(p=0.139),采用Bonferroni法事后多重比較結果表明,文科學生厭惡非合作的D值高于理科學生0.32(95%置信區間:0.09~0.55),而與工科學生的D值差異不明顯(95%置信區間:-0.11~0.34),理科學生和工科學生的D值差異不明顯(95%置信區間:-0.44~0.02)。單樣本t檢驗分析結果表明,文、理和工專業學生厭惡非合作的內隱關系評估程序效應D值均明顯大于0[文科t(110)=8.44,p<0.001;理科t(100)=2.62,p=0.01;工科t(102)=6.13,p<0.001],這說明不同專業高校學生對“厭惡—非合作”的一致評價反應均快于不一致反應,即“厭惡—非合作—一致”關系與高校學生內在心理具有一致性。

圖2 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專業背景差異
3.3 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社會價值取向差異
根據圖3所示,由實驗結果得到合作價值取向和非合作價值取向在合作態度的四個成分上平均數分布,為進一步研究不同價值取向(合作/非合作)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差異,采用多變量方差分析檢驗不同社會價值取向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差異,四個成分的研究數據均為方差齊性。合作價值取向高校學生在喜歡合作、厭惡合作和厭惡非合作三個方面的D值均明顯大于非合作取向者[喜歡合作F(1,313)=6.82,p=0.009,ηp2=0.021;厭惡合作F(1,313)=4.87,p=0.028,ηp2=0.015;厭惡非合作F(1,313)=5.63,p=0.018,ηp2=0.018],差值分別為0.21,0.20、0.21,95%置信區間分別為0.05~0.37、0.02~0.38、0.04—0.38;合作取向者和非合作取向者的喜歡非合作D值差未達到統計學意義。

圖3 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社會價值取向差異
單一樣本t檢驗發現,合作價值取向者四個成分的D值均大于0[喜歡合作t(229)=20.97,p<0.001;厭惡合作t(229)=7.50,p<0.001;喜歡非合作t(229)=9.70,p<0.001;厭惡非合作t(229)=9.40,p<0.001]。非合作價值取向者喜歡合作、喜歡非合作和厭惡非合作三個成分上的D值均大于0[喜歡合作t(84)=8.45,p<0.001;喜歡非合作t(84)=5.37,p<0.001;厭惡非合作t(84)=3.06,p=0.003],而厭惡合作的D值與0差異不顯著,表明非合作價值取向者對“厭惡—合作”的“不一致”反應與“一致”反應沒有差別,即對“厭惡—合作—不一致”關系的評價沒有明確的方向性。
4 結論與啟發
本研究采用IRAP范式測量高校學生合作態度,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學科專業背景和社會價值取向不同的個體的合作態度差異,以尋找能夠調節和改變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可操作變量及可行途徑。結果表明,高校學生合作態度四個成分的IRAP效應均非常明顯,說明本研究中對四種關系的假定與高校學生內在心理傾向是一致的。但是各個成分之間的強度存在著差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喜歡合作的IRAP效應值明顯大于其他三個成分,厭惡合作的IRAP效應還明顯低于喜歡非合作;二是不同成分的IRAP效應在專業背景和社會價值取向兩個變量上的差異是不同的,理科生厭惡非合作的IRAP效應明顯低于文科生,非合作價值取向者在喜歡合作、厭惡合作和厭惡非合作三個成分上的IRAP效應明顯低于合作價值取向者,且在厭惡合作成分上IRAP效應消失。可見,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各個成分之間的強度差異,還表現在學科專業背景和社會價值取向作用的差異。
改變和調整態度使之符合社會期望是我們探討高校學生合作態度的目的之一。積極的合作態度有利于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和社會融入。依據關系精細化和一致性(Relational Elaboration and Coherence,REC)模型[10]原理,IRAP測量合作態度的四種試次——“喜歡—合作”“厭惡—合作”“喜歡—非合作”和“厭惡—非合作”,實質上是四種不同的合作信念——“喜歡合作”“不厭惡合作”“不喜歡非合作”和“厭惡非合作”,它們的方向性和強度共同決定著合作態度的方向和強度。因此,欲培養高校學生積極的合作態度可以將其細化為上述四種信念,針對這四種信念的特點來設計差異化的培養方案,增加教育培養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具體而言,喜歡合作、不厭惡合作和厭惡非合作三種信念的增強可以通過合作價值取向(或親社會價值取向)培養這一途徑進行。但是,對于不厭惡合作信念可能需要先改變非合作取向者的評價方向性;對于厭惡非合作信念還需要考慮學科專業背景的差異。然而,對于不喜歡非合作信念,難以通過上述途徑增強其強度,還需要未來研究繼續尋找可改變和調整這一信念的操作變量,為設計符合其心理規律的差異化培養方案提供科學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