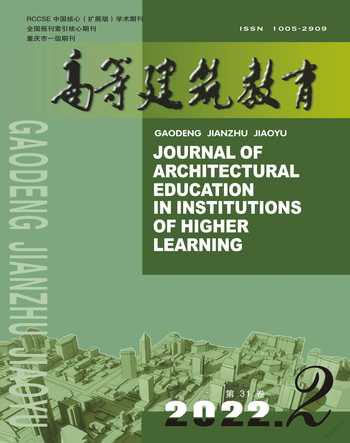面向智能建造的多專業實訓教學體系重構路徑
張美亮 張軍俠 何忠茂
摘要:培養智能建造工程人才,需要優化實訓教學體系。建筑行業正在經歷整體轉型,一是從人力稀缺導出建筑工業化、二是從管道產品轉向零部件產品、三是從一次交訖轉為全周期運維;與此對應,土建工程師的適崗能力也有新訴求,尤其是應用型人才的工程能力、建筑工業化的協作能力和產品服務化的數據能力。應用系統動力學理論,解析實訓教學與技能習得兩大變量之間的因果鏈、增強回路、調節回路和反饋機制,研究結果表明:地方高校土建類專業可以從設計教學語境、人機交互平臺和產教融合課程三個方面優化實訓要素的連接關系,重構多專業全周期實訓教學體系,契合智能建造人才需求。
關鍵詞:智能建造;職場變遷;實訓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2909(2022)02-0152-08
為實現建筑業轉型升級、持續健康發展、邁入智能建造世界強國行列目標,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十三個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推動智能建造與建筑工業化協同發展的指導意見》(建市〔2020〕60號),要求各地建立智能建造人才培養和發展長效機制。智能建造是信息技術與工程建造融合的創新結果,對應專業人才要求具有T形知識結構、工程建造能力和工程社會意識[1]。按照多學科融合交叉,培養復合型新工科人才的思路,高水平大學相繼開設智能建造專業,探索人工智能與土木工程全壽命周期深入融合[2]。根據工程認證理念的要求,優化實踐性教學環節方案設計[3],高職院校積極推動智能建造專業集群建設[4],利用“互聯網+”的優勢,構建“共享平臺+專業模塊+方向拓展”課程體系[5],地方本科院校逐步實現從CAD設計制圖到BIM技術集成的基礎教學平臺遷移[6],初步形成基于智能建造的創新創業實踐教學新思路[7]。
智能建造應用型人才培養應突破加法思維的路徑依賴。在智能建造人才培養的起步階段,
基于物理世界的確定性、因果關性和機械思維的進化邏輯,
增設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電子信息及其自動化、工程管理等知識課程和技能訓練,從而改造傳統土木工程專業。在“互聯網+ ”背景下傳統產業轉型過程中,智能商業成為模范生,其運營主要依賴網絡協同和數據智能[8],而建筑行業和教育領域受數據離線和遷移成本約束,總體數字化程度偏低[9]。進入“互聯網×數據×計算”的在線時代,互聯網已成為基礎設施,云計算將成為公共服務,大數據就成為生產要素[10],土建工程師的工作場景和適崗能力在演化迭代,應用型人才的專業知識傳授和實踐技能訓練也需系統化重構。
一、建造智能化的工作場景變遷
智能建造的興起將極大地改變建筑工人和工程師的工作場景,可見結果是從機械代人、機器助人轉向人機協作[11],在動力機械相繼取代手工操作的自動化進程中,智能機器正在快速獲得結構化知識,助推建筑產品向空間服務融合迭代,實現建筑工業與數字經濟演化升級。
(一)從人力稀缺導出建筑工業化
以往建造浪費現象與建筑要素供給特征相關聯。建筑要素供需決定生產組織方式,1930年以來,在住房需求激增和建筑工人短缺的影響下,歐美國家以建筑標準化設計、構配件工廠化生產和現場裝配式施工為基本特征的建筑工業化得到持續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建筑產業規模化增長與工業化滯后并存的背景,帶來了鋼材、水泥、玻璃等建材和農民工供給充分的典型表征,現場現澆結構體系和線性分工生產方式,雖然滿足了快速城市化的大規模建設需求,但也產生了資源能源浪費、產品質量不高、運維服務滯后等轉型升級問題[12],還伴生出工作環境差、勞動強度高、收入水平低等職業場景認知。隨著人口紅利消失,人力要素供給已成為傳統建筑產業維持和可持續發展的約束條件,尤其是普遍接受中高等教育的獨生子女成為社會勞動主力,建筑業勞動力稀缺局面進一步加劇,建筑工業化成為必然選擇。
人機協作進化是建筑工業化的主導變量。近年來許多建筑企業陷入微利、無利甚至虧本經營狀態,高校土建類專業報考人數和招生分數持續走低,雖然主管部門不斷出臺建筑工業化相關政策,國家層面也明確了智能建造發展目標,但與機械、電子、化工和諸多服務行業的人工智能革命相比,建筑業仍停留在機械化階段,自動化程度普遍較低,既與產業組織模式有關[13],也受轉型升級成本約束。建筑工業化依賴技術創新和人才支持[14],在大數據驅動的人機協作進化過程中,人工智能機器不僅會取代低技術工人和熟練技工,被認為是“腦力工作”的設計和管理崗位也將不復存在。
(二)從管道產品轉向零部件產品
現行建筑質量問題與最終產出特征相關聯。建筑雖然由樁柱、梁板、門窗等各部件組成,也可區分為磚木、混凝土、現澆和鋼構等結構體系,但現行生產模式,是與牛奶面包類似的管道產品,而非如汽車手機一樣的零部件產品。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幾乎摧毀中國的奶制品產業,事后調查發現,從原料供應、生產加工到包裝運輸等各個環節,都存在污染或惡意添加的可能,同行業品牌企業不得不采用垂直整合方式,重建全要素全過程質控體系。反觀汽車質量監控,很容易就可以追蹤到是哪個零部件不合格或組裝操作不達標,因為各主體都知道自己能被追溯,所以即使小企業也能保證配件質量,結果就是市場分工不斷深化,生產效率持續提升。類比分析,現場澆筑就像一桶桶奶倒進奶罐車里,一旦產品出現建筑質量問題,很難快速鎖定問題源頭,責任調查不得不覆蓋設計、材料、施工、管理等全過程,不僅維修整改成本大幅提升,也成為建筑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推行裝配式建筑是為實現零部件產品轉型。為推進建筑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大力發展裝配式建筑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6〕71號),明確要求發展裝配式建筑,全面推動建造方式深徹變革和建筑產業轉型升級。但在管理實踐中,許多地方卻簡化“裝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這一硬性規定。現澆向裝配轉型,是從管道產品向零部件產品轉型,前提條件是實現建筑構件模數化、標準化、通用化和系列化,這對現有建筑企業和相關利益主體產生極大的沖擊,更有可能引發行業重組。除了垂直整合和橫向聯合,裝配式建筑還將催生各類預制構件生產、現場裝配和信息服務企業,進而實現基于網絡協同的建筑數字化,因此面向智能建造的土建工程師需具備網絡協同能力。
(三)從一次交訖轉為全周期運維
既有建筑運維難題與商品交易特征相關聯。建筑不是標準品,而是一種具體的個性化服務。以房地產為例,盡管是裝配式建筑,名義上是一種產品,且有不動產權證加持,但每套房不僅有面積、戶型、樓層、設施、裝修等空間屬性差異,還對應著地段區位、周邊配套、未來規劃等環境條件,所以是一房一價成交,更有學區房、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等類別[15]。人們買一套房,首先是要能滿足私人性的居住需求,其次還要能得到就醫、入學、換乘、娛樂等公共性的生態服務,當然還不乏有投資性的收入預期。公共建筑、市政工程也類似,一座圖書館既要提供購書、閱讀等學習服務,更有彰顯城市品味和城市品質的潛在功能。既有建筑改造更新,雖然可以按原始圖紙更換部件,維持原初設計形態,但在功能升級的基礎上,必須建立空間實體與在線數據的信息對應。
建筑數據采集是智能建造的基礎性工作。人工智能的顯著特征是機器能夠直接做決策,然后配置物料、引導機器運轉。雖然裝配式建筑是建筑工業化的必由之路,但數據將成為核心生產力,數字化就成為傳統建造向智能建造轉型的關鍵環節。要讓數據與建造對接,實現建材配置自動化、建造流程在線化、建成實體智能化,需要數據在線、實時更新,也就是在實際建造場景中全本、實時記錄,而非抽樣、主動采集。針對既有建筑提供精準運營服務,首先要建立物理實體、空間數據和多元需求的有效連接,通過在線數據持續記錄建筑信息,通過數據智能不斷深化對用戶的理解。在線數據是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務的決策基礎和實現平臺,面向智能建造的土建工程師需強化數據決策思維。
二、土建工程師的適崗能力訴求
當信息科技大面積席卷生產領域時,許多人通過習得知識,接受培訓,獲得與機器組成新系統的能力,就可以在需要更高技術的生產領域、服務部門或辦公園區找到工作[16],對于智能建造應用型人才而言,適崗能力首先表現為工程思維、協作能力和數據意識。
(一)適應建筑工業化的系統性思維與工程能力
專業化分工與系統性合作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建筑工業化發展依賴縱向分工和橫向協作。智能建造雖然類似樂高積木,但裝配式構件本身就是材料、技術和工藝的復合物,系統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構件組合既要符合物理定律,也需遵從演化規律,實現建造需要統籌人、機、料、法、環要素,每位工程師不應只關注自身負責的部分,還要從系統層面思考并提供協作。現行施工領域有分工無合作
的“五大員”或“八大員”,以及設計單位的工種設計、總工統籌、產值分配模式將難以維繼。
現行教育模式忽視系統性思維與工程能力。具有工匠精神的工程師,不應局限于學習、應用和傳承科學知識和工匠手藝,還應在工程實踐中,思考如何把手藝變成工藝,進而實現標準化操作。
掌握手藝需要個體工匠日積月累,個體消亡手藝有可能失傳,而工藝是系統性思維與工程能力的集合,形成工藝就可以導向機械化、自動化,而且可以實現數據累積,通過快速迭代完成智能化轉型。智能建造工程師需要掌握工藝所包含的工程知識和實操能力,但在現行教育體系下,土建類專業普遍重視知識傳授,忽視技能實訓,很難形成對工藝的準確理解,“眼高手低”“學無所用”成為建筑企業對畢業生的評價共識。
(二)適應裝配式建造的批判性思維與協作能力
建筑業向智能建造轉型,離不開科學家和工程師這兩類核心人力要素。一方面,在中國傳統分工語境下,建造活動由工匠承擔,因此最早的工程師,多數是從工匠轉化而來,工匠精神與批判性思維一脈相承,許多土建工程師的職業追求就是成為“大國工匠”。另一方面,智能建造是由一系列新技術和新產品組合而成的復雜系統,而任何復雜系統都具有不確定性,這就需要科學家發現未知之事,工程師創造未有之物,前者提出并論證可能性,后者把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17],在此分工體系下,工程思維與協作能力相互轉化。
現行教育模式輕視批判性思維與協作能力。智能建造工程師面對的是1+1大于2的挑戰,關注的是一個部分的變化,會不會對整個系統產生影響。大量針對裝配式建筑和建筑工業化的研究探索,表明以往土建類專業教育存在明顯缺陷,工程師教育未能有效對接建筑業轉型升級訴求[18],雖然有校企合作教學創新實踐,但教師自身對預制裝配式建筑的設計理論、建造技術、信息化工具和教育模式的理解還有待深化,還需要從建造教學的角度重新審視土建類專業教育的新特征和新要求[19],尤其需要關注在競爭導向的高考體系下成長的獨生子女,如何在工程技能訓練中提升合作意愿和協作能力。
(三)適應產品服務化的創造性思維與數據能力
智能建造將打通建筑產品與運維服務的交付邊界。以房地產為例,在現行建造體系下,房產交付與物業服務提供有明確時間節點,多數情況下分屬不同的市場供給主體,現實交易中產生的大量糾紛,都可歸結為產品與服務的機械分割。部分品牌企業已經放棄一次性銷售開發模式,組建物業服務團隊,落實“產品即服務”供應鏈模式。除垂直整合外,類似服務外包的橫向協作模式,也能實現建造與運營一體化,而基于數據驅動的區塊鏈和物聯網技術,將引導建筑產品、服務、體驗一體化創新演化[20]。
現行教育模式漠視創造性思維與數據能力。數據意識是人工智能時代的普適訴求,包括數據生成能力、數據運用能力和信息系統開發能力,對應著組件化產品生產與體驗性服務供給的人機交互進程[21]。住建部《關于推廣建筑信息模型技術應用的指導意見》(建質函〔2015〕159號),明確要求到2020年底90%規模以上項目都要應用BIM,在注冊執業資格人員的繼續教育必修課中增加有關BIM的內容。如果說傳統建造是通過人與人交流,完成從圖紙到實體的漸近生成,那么智能建造主要是通過人與機器互動,實現從物理空間到數據空間的實時映射[22],基于數據決策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務,智能建造工程師面對的就是混合型工作,不僅需要土建工程技能,還要具備數據編程和在線分析能力。
三、土建類專業的實訓教學體系重構
面向智能建造的工作場景變遷,響應工程數字化、多專業協同和全周期服務能力訴求,應用系統動力學理論和方法[23],解析專業實訓與技能習得兩大變量的因果鏈,優化思維與能力對應的增強回路、調節回路和反饋機制,重構實訓教學要素的連接關系。
(一)全面優化數字化設計教學語境
大數據是智能建造的生產力,培養學生的系統性思維和工程能力,是土建類專業實訓教學體系重構的近期目標。構建并維護標準統一的建筑信息模型,是實現建筑工程數字化的前提,浙江省建筑信息模型(BIM)服務中心組織編制了《專業技術人員建筑信息模型(BIM)能力評估標準》(T/SC0244638L19ES3),獲得國家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社會企業的廣泛認可。因此,土建類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重構的第一步,就是突破從Auto CAD向Revit教學軟件轉換的約束條件,全面優化面向工程數字化的設計教學語境。
重組系統性思維與工程能力培養的增強回路。以建筑設計教學為例,在傳統的類型化設計和Auto CAD軟件模式下,建筑設計基礎(1-2)、計算機輔助設計(1-2)、建筑設計(1-6)等課程既有承接關系,也可獨立運作,教師多結合各自熟悉的工程項目選擇設計場地和功能定位,學生主要通過手繪、計算機輔助設計和實體模型呈現設計思路,雖然教學的靈活性大,但空間表達缺少數據完備性支持,教學內容重復與關鍵技能缺失的問題長期存在,規劃條件、建筑設計、結構優化之間固有的增強回路很難形成。基于建筑全周期和學習全周期的相互關聯特征,各專業同步轉向Revit軟件系列,分解規劃策劃、建筑設計、結構選型、材料設備、工程造價、裝配建造等系統要素,分析類型設計和階段設計的增強機制,激活設計教學與工程建造環環相扣的增強回路,提升實訓教學的真實有效性。
(二)統籌建設多專業人機交互平臺
人機協作是智能建造的生產方式,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協作能力,成為土建類專業實訓教學的中期目標。智能建造意味著土建工程師要與人工智能機器、組件化復雜系統一起工作,機器能夠理解建造要素的變量關系,但不擅于處理復雜信息的運用場景,尤其是多專業訴求的矛盾沖突,凡是重復性的體力勞動都有機器承擔,凡是能實現結構化表達的專業知識也將轉化為機器行為。因此,土建類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重構的第二步,就是解析在線數據驅動的機器智能遷移條件,統籌建設面向多專業協同的人機交互平臺。
重設批判性思維和協作能力的調節回路。學生在校接受的是分專業教學,工作中面對的多是集合性問題,“會的用不上,要用的沒學過”,類似抱怨在應屆畢業生與中小建筑企業主間普遍存在。以建筑學和土木工程為例,雖然實訓教學普遍采用計算機輔助設計制圖,但各專業通常采用不同的第三方軟件,實訓項目雖有基礎、專業和綜合之分,但囿于學分學時和考核評價,通常只會設定具體的單一目標,很難反映實際建設項目的集成邏輯和協作條件,也不呈現真實建造過程的工序延誤沖突和動態調節場景,類似實訓教學雖能訓練學生的專業自洽技能,但無助于培養協作意識、平衡理念和批判性思維。基于土建類多專業全周期實訓統籌目標,考慮不同專業實訓教學所需要軟硬環境條件,建議選擇中等規模民用建筑作為通用模型,提取規劃、建筑、結構、材料、設備等形態數據,納入BIM人機交互平臺,打通協作行為與目標平衡的調節回路,有助于突破實訓教學的專業局限性。
(三)合作開發全周期產教融合課程
體驗服務是智能建造的持續產出,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數據能力,可作為土建類專業實訓教學的長期目標。智能建造意味著創新設計與用戶思維有效關聯,體驗服務與建筑實體全面對接,對未來的土建工程師來說,創新敏感性與工程建造技能同等重要,甚至要求更高,但目前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主要還是關注知識的傳播和吸收,學生通過工地參觀、課程實驗、課題研究、畢業實習等途徑獲得的真實體驗相對有限,難以了解用戶最終的使用需求。因此,土建類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重構的第三步,就要按照大數據支持服務創新的智能建造發展趨勢,校企合作開發面向全周期服務的產教融合課程。
重組創造性思維和數據能力的反饋閉環。產教融合是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實施路徑,傳統師徒制是教學雙方合意、產教全面融合的典型模式,徒弟的勞動投入和產出,對應著師傅在傳幫帶過程中的顯性收入,但在工業化催生的分工體系中,教學是學校的事務,生產是企業的職能,產教融合需要相應的制度創新[24],企業本質上是經濟人,要追求利潤最大化,但因為現代社會高度關聯,承擔學生實習任務就成了企業的社會責任,當社會責任與經濟成本偏離時,校企合作的不確定性就會突顯,尤其在學生實習存在一定安全隱患的現實語境下,實訓教學的場景體驗效果和實時反饋功能也會大打折扣。基于以人為本的動態視角,專業教育與行業就業的交匯點,在于培養具有創新敏感性和用戶思維的工程技術人才,專業教師與企業工程師分工合作,開發并承擔面向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務的產教融合課程,增強知識吸收、校內實訓和現場實踐的體驗場景,形成實訓教學效果評價的反饋閉環。
四、結語
研究智能建造發展與土建工程教育的關系,不能忽視產業的發展現狀和教育的滯后效應。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土建類專業曾經是熱門專業,但近年來學生報考意愿和高校招生分數持續走低。教育的經濟意義和投資屬性已廣為大眾接受,大多數學生希望在知識經濟時代獲得體面的白領工作,但傳統公司經濟形態下的辦公室崗位卻在持續減少,地方本科院校的辦學初衷是培養應用型人才,但招生宣傳還是側重學生發表論文、申請專利、競賽獲獎、考證考研、出境留學等量化等級指標。與此同時,除大型建設集體和品牌房地產公司外,多數中小型建筑企業很難吸引應屆本科生,智能建造的底層創新能力嚴重受限。
未來已來,機器智能在解放人的同時,也會取代一部分人的工作,如何應對智能機器的競爭挑戰,高水平知名大學和普通地方院校的可選策略先天不同,但在實訓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的系統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是土建類專業教學改革的共同目標。人才培養和教學改革具有滯后效應,從智能建造的產出來看,建筑企業并非土建類專業人才的終極用戶,但當前的實訓教學體系重構,離不開建筑企業這一最現實的用人單位支持,校企合作能提供真實的創新創業場景。除此以外,地方高校還應深入研究支持個性化成才的實訓模式和評價方法,進一步打破專業選擇限制,為學生提供更多的選擇自由。參考文獻:
[1]
丁烈云. 智能建造創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養的思考[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5):1-4+29.
[2]鮑躍全,李惠. 人工智能時代的土木工程[J]. 土木工程學報,2019,52(5):8-11.
[3]劉世平,駱漢賓,孫峻,等. 關于智能建造本科專業實踐教學方案設計的思考[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1):20-24.
[4]徐廣舒. “互聯網+”時代智能建造專業集群的教學資源建設[J]. 江蘇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綜合版),2019,19(3):83-86.
[5]張衛華,李照廣,隋智力,等. 新工科背景下智能建造專業集群建設探析———以北京城市學院為例[J]. 高教學刊,2020(21):96-98.
[6]李富平,皇甫平,郭鐵能. 提高土建類專業學生制圖創新實踐能力的探討[J]. 高等建筑教育,2019(3):116-121.
[7]吳軍. 智能時代[M]. 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6.
[8]曾鳴. 智能商業[M]. 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8.
[9]袁烽,趙耀. 智能新工科的教育轉向[A]. 數字技術·建筑全生命周期——2018年全國建筑院系建筑數字技術教學與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8.
[10]王堅. 在線[M]. 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8.
[11]吳光東,唐春雷. BIM技術融入高校工程管理教學的思考[J]. 高等建筑教育,2015,24(4):156-159.
[12]王俊,趙基達,胡宗羽. 我國建筑工業化發展現狀與思考[J]. 土木工程學報,2016,49(5):1-8.
[13]劉禹. 我國建筑工業化發展的障礙與路徑問題研究[J]. 建筑經濟,2012(4):20-24.
[14]陳振基. 我國建筑工業化60年政策變遷對比[J]. 建筑技術,2016,47(4):298-300.
[15]薛兆豐. 薛兆豐的經濟學講義[M]. 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8.
[16]約瑟夫·E. 奧恩. 教育的未來——人工智能時代的教育變革[M]. 李海燕,王秦輝,譯.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20.
[17]娜塔莎·麥卡錫. 人人都該懂的工程學[M]. 張煥香,寧博,徐一丹,譯.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
[18]吳國雄,茍寒梅,董莉莉,等. 對接裝配式建筑產業鏈的專業集群人才培養體系創新與實踐[J]. 職業技術教育,2018,39(32):25-28.
[19]羅佳寧,張宏,叢勐. 建筑工業化背景下的新型建筑學教育探討——以東南大學建筑學院建造教學實踐為例[J]. 建筑學報,2018(1):102-106.
[20]劉占省,劉詩楠,趙玉紅,等. 智能建造技術發展現狀與未來趨勢[J]. 建筑技術,2019,50(7):772-779.
[21]涂子沛. 數文明[M]. 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8.
[22]魏力愷,張備,許蓁. 建筑智能設計:從思維到建造[J]. 建筑學報,2017(5):006-012.
[23]丹尼斯·舍伍德. 系統思考[M]. 邱昭良,劉昕,譯.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
[24]李玉珠. 產教融合制度及影響因素分析[J]. 職教論壇,2017(13):24-28.
Reconstruction path of multi-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for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ZHANG Meiliang1, ZHANG Junxia2, HE Zhongmao1
(1.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300, Zhejiang, P. R. China;
2.Ningbo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Ningbo 315211, Zhejiang, P. R. China)
Abstract:
The talents training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requires optimizing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undergoing an overall transformation, three salient features can be observed, one is to derive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from the scarcity of manpower, the second is to shift from pipeline products to parts and components, and the third is to shift from one-time delivery to full-cycl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rrespondingly, civil engineering engineers also have new demands for their job-fitting capabilities, such as the engineering capabilities of applied talents, the collaboration capabilities of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data capabilities of product services. Applying system dynamics theory, analyze the causal chain, enhancement loop, adjustment loop and feedback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major variables of training teaching and skill acquisi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learn from the design teaching context, man-machine interactive platform and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courses in three aspects, optimize the connection relationship of training elements, reconstruct the multi-professional full-cycle training teaching system, and meet the needs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talents.
Key words: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workplace changes; practical teaching
(責任編輯 王淼卉)
修回日期:2020-10-03
基金項目:
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教學改革研究項目“面向全周期設計的多專業實訓體系研究”(jg2019609);浙江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雙師型教師培養、評價與激勵機制研究”(2020SCG082)
作者簡介:
張美亮(1974—),男,副教授,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空間規劃與設計教學方法,(E-mail)6451257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