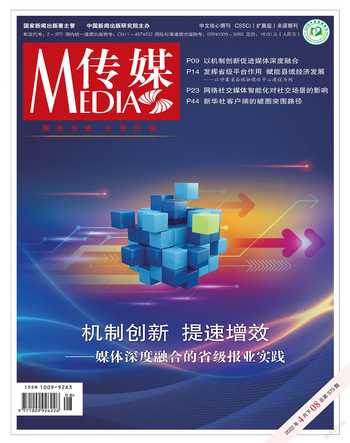媒體資源協同與書刊同源同業
李軍
我與《傳媒》有緣,緣自1993年。
當時,我在國家新聞出版署報紙管理司工作。本司有一本雜志叫《中國報紙月報》,我是這本雜志的編輯之一。本刊“封面人物漫像題記系列”即主要由本人策劃實施,此創意曾在報壇風靡一時:用文言文的寫法和手繪鋼筆淡彩人物漫畫作為封面設計,逐期展示報界精英的精神氣質和辦報理念。范敬宜、徐光春、丁法章等位列其中,還有著名老報人李莊,刊中也做了介紹。后來,報刊管理體制改革,這本雜志就交由署直單位辦,改名為《報刊管理》,2001年又改名為《傳媒》至今,我是這本雜志的見證者、參與者。我不僅與《傳媒》創辦有緣,亦與其主辦的中國傳媒年會有緣。過去,曾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新聞報刊司司長的身份出席;后來,又以中宣部傳媒監管局局長的身份出席;現在退休了,以中國期刊協會副會長的身份參加。數年先后以三個身份參會,見證著一本期刊的成長以及媒體融合發展的歷程。
在長沙的第十六屆中國傳媒年會上致辭時,我談到了一個觀點:我們現在談媒體融合,可見更多的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縱向融合,即“后手拉前手”;鮮見傳統紙媒之間的橫向融合,即“左手拉右手”。于是我呼吁,落實媒體融合戰略,建設新型主流媒體,要重視傳統出版的關聯媒體、關聯業務、關聯系統、關聯領域之間的資源協同,推動媒體“混血”創新。
從2014年8月中央印發《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算起,中國報刊融合發展已經七年多了。在這七年多的時間里,全國報刊業迎難而上、艱苦探索、轉型升級,取得了一系列好的經驗和成果,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和不足。比如,與新型媒體特別是頭部媒體深度合作,在兩微一端全面發力,卻恰恰忽視了最需要融合的部分——內容關聯產業的融合。舉一個例子,我曾經到一個省調研,這個省有兩本期刊發展得非常好,一本是市場類期刊、大眾媒體,另一本是學術期刊。在這個學術期刊的編輯部座談時,我提出一個建議,學術出版應借文化創意產業興起之勢,孵化和衍生新的產品線,夯實建設基礎、儲備發展后勁、促進動能轉換、擴大學術傳播、壯大主流輿論。這個期刊的負責人說,我們看到故宮文化發展得很好,我們也很想學,但是,我們是做學術、搞理論的,沒有渠道,沒有市場,沒有經驗,沒有團隊,沒有制作,沒有產品設計能力。我說:“你們沒有不要緊,你們沒有,你們隔壁有,你們旁邊那本走市場非常成功的期刊有。他們有經驗,有渠道,有制作,有產品設計能力,你們兩家可以來個強強聯合呀。”他說:“唉,我們不大認識呀,一直沒有打過交道”。你看,兩本大刊,一街之隔,“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于是,我在思考,我們都能和頭條、抖音、快手合作,為何不能刊刊合作、社社相聯,來個合縱連橫呢?再舉一個例子,在我國一萬多種期刊、五大辦刊體制中,有一類叫作“出版社辦刊”。出版社出刊也出書,但是,這么多年來,我們很難找到一社之中書刊兩塊業務打通、兩種資源協同、兩類渠道互補的樣本。本是“同根生”,仍為“兩張皮”。書刊同源,卻不同業!
2020年9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意見》指出,要按照資源集約、結構合理、差異發展、協同高效的原則,完善中央媒體、省級媒體、市級媒體和縣級融媒體中心四級融合發展布局。努力打造全媒體對外傳播格局,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文化。我們一定要按照中央要求,推動資源集約、協同高效發展,從書刊同源不同業,加快轉型為書刊同源又同業,推動媒體融合向產業融合發展。
作者系中宣部傳媒監管局原局長、中國期刊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