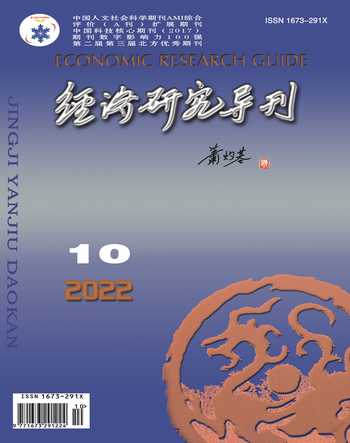“國進民退”之爭的周期性現象及其實質
何泓
摘 要:近年來,世界經濟呈現長期緩慢增長態勢,我國經濟發展中由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存在,有時呈現出相互競爭的態勢,這就使得兩者的發展成為經濟界關注的焦點,“國進民退”和“民進國退”成為經濟學界討論的主要話題,并表現出周期性爭論的現象。分析這一周期性現象的特征及其產生的原因,進而探討產生這一現象的實質,對認識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復雜形勢、解決當前經濟發展的問題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國進民退”;周期性;實質
中圖分類號:F276?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2)10-0007-03
一、現象問題
改革開放40年,我國在重大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果與進步,而這其中又尤以經濟領域的成功最為稱道,黨的十九大更是站在新的起點對十八大以來所取得的成就進行了全方位的總結。然而在進行總體肯定的同時,黨中央也指出了我們取得成績的來之不易,其中更是用“過去五年是我們極不平凡的五年”來加以概括,而這“極不平凡”當然也包括了我們在經濟改革中所面臨的諸多機遇與挑戰、成績與得失。
回顧改革開放40年所走過的歷程,我們在經濟領域的發展更是關山重重,困難疊遇。一方面,為了主動融入全球經濟發展的大流,與世界經濟對接,我們開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大門;另一方面,為了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選擇與制度方向,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樣一來,我們的經濟建設就自然地面臨著“公有制經濟為主體”與“多種所有制(民營、外資、特別是私營企業)經濟共存”的取舍與偏重問題。
世界經濟的發展雖然從總體上看是處在一種上升的態勢之中,但發展的不均衡、地區發展的差異、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自身局限,特別是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都使得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備受考驗,由此而產生的世界經濟發展的障礙問題總是間歇性地發生。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上所遇到的阻力更是層出不窮。而象征著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經濟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發展,在全面市場經濟建設的改革洪流中就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每當全球經濟低迷徘徊或是萎靡不振之時,人們就很容易開始對發展模式、經濟體制、經濟政策等諸多經濟問題進行反思甚至提出質疑,對于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代表的國有經濟和以中小企業為代表的民營經濟就自然地成為關注的焦點,“國進民退”和“民進國退”進而成為經濟學界討論的主要話題。
二、周期性爭論
關于“國進民退”之爭現象一開始發端于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1],圍繞著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誰最該優先發展這一基本問題,人們總是從體制機制、戰略決策、市場因素等多方面提出“國退民進”或者“國進民退”的經濟學觀點,并對此問題爭論不休。考量這一現象,筆者偶然發現,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2年我國全面開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以來,迄今為止,這一現象每間隔一定時間就會成為經濟學界討論的熱點話題,已然呈現出十分明顯的周期性特征,不僅在它興起的時間上具有周期性,而且在興起的原因、爭論的焦點上更是具有極高的相似性。
(一)“國進民退”之爭興起的周期性表現
1. 1998—2002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后的第一次爭論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決定了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建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地位,其他多種所有制只能是完善與補充。但是在1992年以后,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征程,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改革以釋放出更大活力的呼聲高漲,一些國有大中型企業在體制和機制上的弊端逐漸暴露出來。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民營企業等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的呼喚,開始被經濟學界、實業界所關注。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的國有企業出現虧損、倒閉和職工下崗現象,在當時,由于國有經濟所占比重相對還比較高,這就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一時之間,要求國有企業退出市場、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和非公企業的喊聲高漲,“國退民進”之聲四起。中央也是在這個時候提出了國企三年改革脫困計劃,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希望把國有經濟收縮到壟斷行業和更具優勢的競爭領域,這也從事實上表現出中央當時的“國退民進”的格局。但是很快,為了推進改革重組,2003年國資委成立并提出要求,央企必須進入行業前三名才能避免被淘汰。這樣一來,就迫使央企必須要不斷擴張、收購、兼并,這就表現出“國進民退”的新態勢。這一來一往之間,“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之爭開始摩擦生花,這可以說是我國在經濟轉型發展中的第一次爭論。
2. 2008—2012年“美元次貸危機與歐洲債務危機”之后的第二次爭論
第一次爭論的硝煙尚未完全熄滅,美元次貸危機與歐洲債務危機相繼爆發,其影響很快波及全球,全球經濟低迷徘徊,美國、日本等經濟放緩,歐元區經濟零增長,發展中國家增長緩慢,俄羅斯經濟負增長。為了應對這一輪危機所帶來的巨大風險,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勵國有大中型企業在新一輪競爭中站穩腳跟,要更多地參與市場競爭和引導國民經濟支柱發展,這就帶來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沒有必要大量保留國有企業”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不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爭論。
這一輪爭論觀點尖銳,參與者眾多,雙方正面交鋒激烈。對國有企業的發展持反對意見者主要代表人物如許小年、茅于軾、張維迎等,他們把“國進民退”現象與改革開放相聯系,認為這是改革開放的倒退。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在《國進民退與改革開放背道而馳》中認為,“‘國進民退與改革開放背道而馳”,“會制造社會不公平”,“權貴資本主義”正在抬頭[1]。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針對山西煤炭資源整合重組發表觀點說:“(山西煤改)現在看來是改革的倒退。”[2]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說:“我們的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國有部門比重太大,占有資源太多,這使得2009年發生了明顯的‘國進民退現象。我們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啟動‘國退民進改革。”[3]AEEC48EA-20D5-4AC5-8BF5-A859F541BCDC
有質疑也有肯定。對于“倒退論”觀點,上至國家統計局主要領導人,下至企業董事等,都給予了反駁與回擊。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目前中國的統計數據不支持總體上存在“國進民退”的現象[4]。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也表示,“國進民退”問題本身就不成立,“中國大型企業在前進,央企也由于投資者和股民的參加,進一步多元化,進一步走向市場。央企收購一些中小企業來進一步擴大它的實力,有資本的融合,也有企業組織的融合。這是一個雙向進步。”[5]針對民航業“國進民退”的說法,中國民航局局長李家祥也表示,航空業兼并重組問題是公司的市場化行為,民航局認為只要有利于民航業的發展,就應該積極支持。民航業并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各個航空公司的股權結構是多元化的[6]。
更有持不同意見學者認為,“國進民退”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是一種市場化的選擇,誰發展得快一些、好一些,誰發展得慢一些、困難一些,這都是市場行為,不存在誰進誰退的問題[7]。
不論其究竟是偽命題,還是現實存在,“國進民退”儼然已成國民焦點。這一階段是爭論最為激烈的階段,它表現為以下幾方面特征。
一是爭論激烈,參與者眾多。從中國知網等渠道搜集相關數據發現,2009—2013年期間是參與爭論的文獻最集中的時期,其總量接近300余篇,占全部搜索文獻的80%左右,2010年更是達到了一個峰值,單年發文超過100余篇。
二是爭論的內容、雙方交鋒的主要觀點上互不相讓,各抒己見,把這場爭論推向了一個高潮。
三是這一次爭論推進了我國經濟學界對國企與民企各自的優勢與不足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我國國企和民企對自身發展的定位,也推進了我國經濟的新一輪發展。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我國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后,逐漸拉開了與日本的距離,同時一步一步地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
3. 2018年至今“美國民粹主義掀起全球貿易戰至貿易保護主義全球蔓延”之后的第三次爭論
如果說前兩次爭論還停留在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所引發的階段,“國進民退”也好,“國退民進”也罷,都是一種經濟發展現象。而2018年3月過后,以美國特朗普政府悍然掀起的“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為核心,實行“美國優先”的單邊貿易保護措施,對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對未來經濟發展籠上了沉重的陰影。為了謀求美國經濟的發展,幫助美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得優勢,美國政府在全球施壓,其表現是一種典型的國家力量幫助企業發展的新態勢,被視作新的“國進民進”現象,即政府主打、企業跟進。在這樣的態勢下,各國遵守世界貿易規則的“模范企業”,在與這樣的對手進行競爭中就自然地處于劣勢,從根本上喪失了競爭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與政府撐腰的美國企業競爭就根本不可能。所以當前要求以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參與國際競爭的呼聲再次響起。一些學者強調,要想在世界范圍內贏得競爭,民營企業在與有政府支撐的強大對手競爭時很難立足,那就需要國有企業參與,自然地需要“國進民退”。
而反對者仍然堅持認為,大規模的“國進”讓民營企業看不見曙光,這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從長遠來看,極容易走回原有的老路上去。
就當前情形來看,在美國咄咄逼人的單邊貿易保護主義旗幟下,要求“國進民退”的觀點占著主導。
(二)“國進民退”之爭興起的原因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很容易發現,每一次爭論的興起,都與經濟發展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系。每當經濟發展萎靡徘徊之時,為了擺脫困境,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希望國家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利用國有企業的優勢來整合發展,希望國有企業能扭轉不利態勢,而這個時候,國有企業則表現得不辱使命;每當經濟形勢有了較好的發展勢頭之時,民營企業為了獲得更大的生存發展空間,就希望國有企業盡可能退讓出市場,以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
很顯然,“國進民退”之爭的出現,已然成了經濟發展反映的晴雨表,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需要正視。
三、“國進民退”之爭的實質
“國進民退”之爭,實際上是在中國經濟中要不要讓國有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體的問題;要不要讓國有企業有一個良好的發展態勢的問題。否定者更多的是從西方市場經濟原教旨主義理論出發,認為國有企業就是市場經濟的“另類”,它的存在旨在彌補市場失靈,而不是作為市場競爭的主體,而這樣的理論確實在發達國家、一些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得以驗證。但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應該是基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現實、傳統文化,而不是基于某種理論或他國實踐。檢驗的標準應是這樣的發展模式是否帶來了經濟的發展,是否能夠為這個國家所接受。
十多年來,爭論的重大分歧主要聚焦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國進民退”的真偽與規模的問題;二是“國進民退”與基本經濟制度和改革開放關系的問題。爭論的實質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還是反對和削弱這個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還是動搖和削弱公有制。黨的十八大全面重申要加快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全面重申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政策主張,這是對所謂“國進民退”炒作的明確回應。
鄧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計劃與市場”都是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不同的兩個手段而已。所以我們今天討論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這樣一個命題,不是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性問題,而根本性的問題是,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應該充分尊重市場經濟發展規律,都要按經濟規律來辦事,而不是借助于“第三方手段”來尋求發展。當然,面對當前國際經濟發展的新變化,特別是美國發動的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又特別是在對中國發展進行極限施壓的背景下,我們更要堅持我們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加強對國有企業改革,保護民族民營企業的利益,確保兩條腿都走好路,中國經濟才能在美國極限施壓的淫威下獲得突破。否則,我們不但無法戰勝強大的敵人,還很有可能在“自相殘殺”中不攻自破,這正是我們的對手所希望的。
參考文獻:
[1]? 許小年.“國進民退”與改革開放背道而馳[N].東方早報,2009-09-27.
[2]? 王紅茹,張偉.“國進民退”真偽[N].中國經濟周刊,2010-03-22.
[3]? 鄧偉.“國進民退”的學術論爭及其下一步[J].改革,2010,(4).
[4]? 楊新銘.對“國進民退”爭論的三大問題的再認識[J].經濟縱橫,2013,(10).
[5]? 衛興華,張福軍.當前“國進民退”之說不能成立——兼評“國進民退”之爭[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3).
[6]? 袁恩楨.“國進民退”與“民進國退”的爭議背后[J].探索與爭鳴,2010,(6).
[7]? 許保利.國進民退之爭:根本分歧在何方[J].國有資產管理,2012,(6).
[責任編輯 毛 羽]AEEC48EA-20D5-4AC5-8BF5-A859F541BCDC